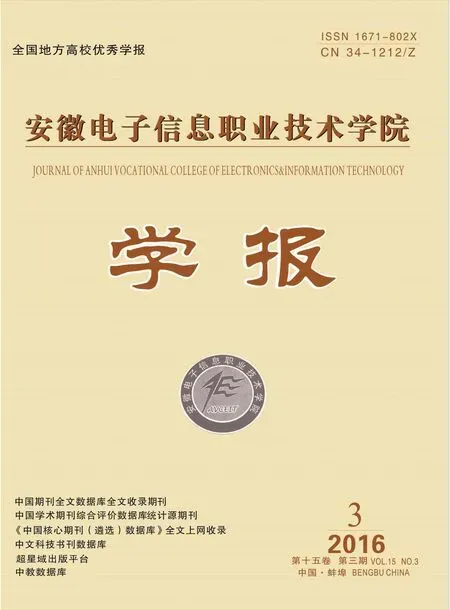论语篇翻译对等中的语义对等
张晓君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论语篇翻译对等中的语义对等
张晓君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翻译是一种转化过程,是一种语言活动。翻译对等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语言是翻译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在语言对等下又细分为语义对等(包括词汇和整个文档)、语法对等以及语用对等。本文主要讨论了语义对等和在原语与目的语中无法实现的概念对等翻译的情况,以及语境对语义选择的影响。
翻译对等;语义对等;语境
一、前言
翻译是实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实现交流的重要手段。翻译对等一直是翻译集中的问题,是翻译领域内讨论的热点。这不仅仅是由于其在翻译领域内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引起许多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了对等原则,其目标是“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依据奈达所说,传统上,人们一般在源语与目标语的词汇与语法的对应程度的基础上来判断翻译的准确性,这种对应被称为“对等”。Catford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等值论”。[2]由此可见,对等是翻译实践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在原语与译语之间实现语义对等,所有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相同的地方就在将翻译理论的对等性视为中心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对等性方面的许多研究强调的是源语与目标语在词、句子及语篇层次上的对等。翻译是源语语篇被目标语对等语篇代替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语篇是翻译者要认真对待的。不同语言中的语篇可能有不同程度(完全或者部分)、不同方面(内容,词汇,语法等等的对等),以及不同等级(词—词对应,短语—短语对应,句—句对应)的对等。一篇文档有其自身的语言特征、体裁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由于翻译要符合各项特征,所以翻译对等也体现在三个方面:1)语言对等;2)体裁对等;3)社会文化对等。在语言对等下又细分为几个分支:a)语义对等(包括词汇和整个文档);b)语法对等;c)语用对等。语义对等是现实翻译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翻译实现的一个基础。这是“从原语到译语的一种语义转换,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的恰当形式表达出来。”[3]
二、语义概念意义对等
在翻译对等的三个部分中,语言对等是最主要的,因为没有语言层面的对应,翻译过程不可能进行。语义就是话语的意义,词义是指字典中关于该词语的中心释义,是词语的一般意义。语言对等分为词层的对等、词层以上的对等。语义对等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直译”而非“意译”,就是要使原文与译文保持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英文中找不到中文“昨天、游泳、他”几个词的对应词汇(分别是“yesterday,swim,he”),怎么能准确快速地将句子“他昨天游泳了”翻译成英文?此外,如果我们对于英文语法没有必要的了解,例如我们不知道英文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我们就不能将那句话“He swamyesterday.”正确翻译出来。如果我们在中文中找不到英文“I,like,apples”几个词的对应词汇 (分别是“我,喜欢,苹果”),我们怎么能够将“I like apples.”翻译成中文。
对于语言对等(尤其是语义对等)的强调有较长的历史。首先,理论学家赞成“词-词对应”翻译,虽然由于该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以及翻译实践的不断发展,翻译者试着寻求其他的方法,如“句—句对应”翻译及语境翻译,但是不管怎样说,词语对等翻译是翻译的基础。同时,对于对等程度的观点不一,应该选择词、词的部分或者更长的单元。随后,翻译单元作为单词与句子之间连贯的部分出现了。也就是说,翻译单元可以被看作能实现语义对等功能的最小单位,它可能是词素、单词、短语、句子甚至是语篇。语义对等在翻译过程中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三、语义不对等
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但完全准确而又绝对对等是不可能的。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的思维是有存在决定的。由于每种语言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心理背景,所以处于不同语系的汉英之间的这个鸿沟是不言而喻的。英汉翻译中,语言概念意义完全对等的情况是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种语言用不同的言语表达同一个事物或影响,那样的英汉习语形式不同,但隐喻义却是相同或相似的。”[4]因此,在英汉表达中,就会出现语义不对等的情况,其分为外延意义不同和形式意义不对等。
从传统的词汇学来讲,词义包括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所谓概念意义,也叫外延意义 (denotative meaning)或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是词汇的最基本意义,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最基本特征的抽象概括,常视作是词语在字典中的定义或释义。所谓内涵意义是隐含或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词的内涵意义在日常谈话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因民族而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词义,英语词语和汉语词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对等性。请看下面的例子:
1)the milky way
2)the apple of my eye
3)The old man has just kicked the bucket
若把上述句子分别直译为“牛奶路”“我眼中的苹果”“那个老人刚才踢了水桶”,概念意义是对等了,但读者却糊涂了,不知所云,这时只能舍弃概念意义对等而意译为“银河”“宝贝”“翘辫子了”。还有些词概念意义上是对等的,但在内涵意义上却不对等。由于英汉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个词语所承载的内涵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汉语中的“狼”侧重于好色,而英语的“wolf”侧重于凶残;汉语里的“龙”是帝王吉祥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图腾,我们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英语里的“dragon”是喷火吐焰的妖魔;在西方“west wind”有“温暖的、革命的、进步的”等内涵,而在汉语中西风有“冷的、凉的、凄凉的、反动倒退的”等内涵。再比如;“Achilles heel”,如果我们直译为“阿喀硫斯的脚后跟”,那么中国的读者就会迷惑不解,阿喀硫斯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他的脚后跟是他的致命弱点,因此我们可以译为“致命弱点”。
形式是思维的外壳,任何一种语言的选择都不是任意的、无目的的,翻译中必须关注译出语的形式。只有完全明白源语的形式,才能忠实地传达到译入语中,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从属于不同语系,句法和用语习惯等诸多差异,真正完全对等是少见的。我们常把意义的翻译放在了首位,而形式的翻译放在了次要地位。
1)He was born in Furth on May 27,1923.
他是1923年5月27日在菲尔特出生的。
2)Londoners are great readers.
伦敦人很喜欢阅读。
3)He has a good handwriting.
他写得一手好字。
例子1)中状语排列位置进行了变换,而2)、3)中的名次分别采用了其动词形式进行翻译,源语与目的语的形式意义不构成对等。
四、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语境,是语言存在的环境,即言语环境。“语境是语义的唯一决定因素,没有语境,就不存在语义。”[6]可见,言语环境决定着词语的含义、句子的含义以及语篇的含义。语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时间、空间、谈话对象、话语前提,上下文等这些都是语境因素。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在语篇翻译中,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词的含义会随着情景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
1)He decided on roast chicken and vegetables,with apple pies to follow.
2)I am scared of the dark.I am a big chicken.
第一句中,根据“vegetables,apple pie”等表示食物的词汇可以看出“chicken”表示的是食物“鸡肉”,而第二句中,因为怕黑,所以可以判断此语境下,“chicken”应译为“胆小鬼”。
语境因素制约下的语义对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讲的“意译”。语境有很多种,如文化语境和文本语境等,甚至包括原作作者的个人情感、写作目的等等。因此必须把原著放在一定的文化、社会背景、文本、上下文等语境中加以深入理解,籍以理解原文的文化底蕴、情感意境等,然后才能译出传神的译文。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几个例子.
1)自行车坏了。
The bike has broken down.
2)不要背后讲别人坏话。
Don’t speak ill of others behind their backs.
3)苹果坏透了。
These apples are rotten to the core.
以上句子中的“坏”字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译成了break down(故障),ill(不友好的),Rotten(腐烂、变质),完全没有对应英语单词bad。另外,father这个简单不过的单词在译时根据语境也有着多种翻译。在正式场合可翻译为“父亲”,一般场合为“爸爸”,如果再表亲昵些可译为“老爸”“老爹”。
4)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菜,叫我怎么办呢?(曹雪芹《红楼梦》)
译一:Even the clea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How could I?(杨宪益夫妇)
译二:Even the clea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How could I?(霍克斯)
在这个例子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菜”是我国民间的一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作为依托,离开了特有的文化语境,就失去了其原有蕴涵的深层的意义。“米饭”在我国普遍作为主食,但是在欧美国家,主食是面包之类的食品,因此在译二中,霍克斯将文化语境融入了作品的翻译,考虑到了源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必定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将其译为“?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这样译入语读者就能得到与源语读者对原作相近的理解,是一个成功的译例。译一使用了语义对等方法,将原文直译为“?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中国读者对于这样的译句应该很容易理解,而译入语的读者就需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理解,而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就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我们把后两者归入一类,即将狭义的语义对等与语用对等通称为广义的语义对等。由此看出,在翻译过程所要遵循的原则中,语义对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5)He was so fond of talking that his comrades nicknamed him“magpie”.
他如此唠叨,同伴们给他起了一个“麻雀”的外号。“magpie”对应的汉语翻译是“喜鹊”,但在中文里“麻鹊”喻意却是唠叨、饶舌,于是取汉语中联想效果对应的比喻,不译为“喜鹊”而是“麻雀”。
6)“Don’t be scared,chickens!”came her voice with teasing gaiety.
“别害怕,你们这些胆小如鼠的东西!”只听得他用戏谑的口气说道。英语中鸡是懦弱、胆怯的代名词,汉语中的鸡却无法引起人们的这种联想,于是换成老鼠形象。从这些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语境对翻译实践的制约,文化语境直接制约着翻译目的语中的词汇选择。
五、结语
世界上没有两种相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各不相同。尽管语言对等是译者需要达到的首要目标,但是仍然有些时候,我们在目标语的中文或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汇。那么,翻译就不能局限于原文词汇的概念意义的约束,“要在理解原文和提供译文的过程中进行原文分析,才能在总体上实现原文和译文的语义对等。”[5]也就是说,译者想更好地做到语义对等,他们不仅要考虑翻译单元的本义,同时还要结合上下文;不仅要考虑其直接含义,还要看其内涵意义。事实上,任何翻译单元在语法与语义上都与其他语言成分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由此可见,语义对等不仅仅指的是概念意义的对等也包括外延意义以及不同文化所承载的意义。只有语言知识而缺少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的外延意义,是不能够译出令人信服的可读的译文的。
[1]Nida,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2]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UP,1965.
[3]刘学华,文珊.论翻译的“信”[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4]糜志芳.英汉翻译中的语义对等[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5]Venessa Leonardi.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Between Myth and Realty[J].Translation Journal,2000,(4).
[6]王栩彬,孙东红.语境、语义与翻译[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责任编辑:卓如)
H315.9
A
1671-802X(2016)03-0064-03
2016-03-15
张晓君(1980-),女,辽宁大连人,讲师,研究方向:多元文化。E-mail:4744869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