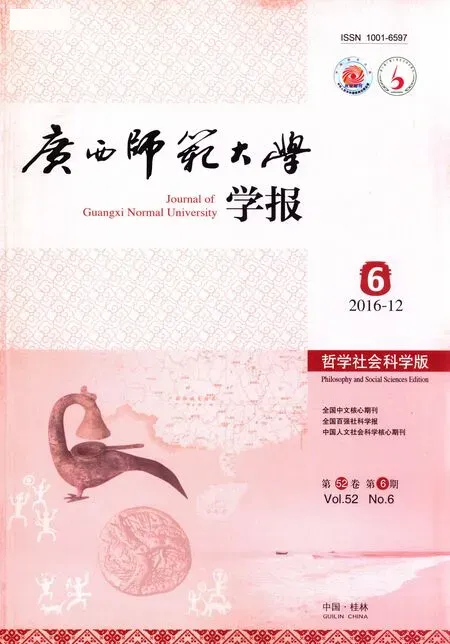“释事忘义”再评价
刘美燕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12)
“释事忘义”再评价
刘美燕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12)
《文选》注释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即对“释事忘义”这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持负面评价。厘清这个问题对诗文注释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谓的“释事忘义”其实是古人对于“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的批评。对于诗文注释来说,这两种注释方式各有优劣。文本类型、注释者的注释目标、读者预设、个性、兴趣、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了注释者的选择和使用。因此,用带有贬义色彩的“释事忘义”这个词一概而论地批评以“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这是不科学的。
《文选》;释事忘义;征引式;直解式
李善穷其毕生精力注释《文选》,开创了诗文注释的新体式——“征引式”。“征引式”注释是以征引古籍的方式“以古注古”,致力于揭示文学作品用语、用典的出处并引导欣赏。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语言学注解的传统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在注释史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李善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学界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却始终对其“释事忘义”问题争论不休。
首先出现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声音是以“释事忘义”为口实批评、攻击李善。《新唐书》卷二〇二《李邕传》载:“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1]5754《新唐书》这个记载可信度不高,但确实在唐朝就出现了对李善“释事忘义”的批评。吕延祚在《进集注文选表》中说:“往有李善,时谓宿儒……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2]对于李善“述作之由,何尝措翰”的特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为李善辩护。其一,否认善注“忘义”,并千方百计从善注中寻找例子说明。晚唐李匡乂在《资暇录·非五臣》中提出:“士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不解文意……大误也”,李氏之注“释音训义,注解甚多”[3]。王礼卿《〈选〉注释例》曰:“案:李氏释文义,词简意深,曲有理致。所释《文赋》等篇,并事义兼赅,文词工丽。所谓‘释事而忘义,不能文词,号为书簏’者,实厚诬之言也。”[4]648孙钦善《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亦指出:“李善注《文选》虽注重释事,但亦不忘释义,今存《文选注》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5]179其二,认为“释事”即“释义”,李善征引典籍在说明出处的同时其实也包含了他对意义的理解和解说。这种观点以王宁为代表。他在《李善的〈昭明文选〉与选学的新课题》中明确指出:“释典本身也就是释义,引典籍的目的也仍是释义。”[5]194
陈延嘉则在对李善注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量统计和分析证明,无论是批评李善注“释事忘义”还是赞美善注“事义兼释”,均是不准确的,李善注是释事为主,释义为辅。[6]99-135
综观这场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争论,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人们对于“释事忘义”中“释事”、“释义”两个概念的理解显然出现了某种混乱,以至于王宁提出“释典本身也就是释义”。第二,“释事忘义”这个词既然用了一个“忘”字,说明这个概念产生之初已经隐含了贬义性评价。以上争执三方尽管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释事忘义”这个注释学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持否定态度,认为其降低了典籍注释的质量。正是有了这样的观念作为前提,贬低者才会紧紧揪住这个小辫子不放,大肆攻击;而辩护者为了翻案,千方百计寻找李善并未“释事忘义”的证据;中立者则对善注中“释事”与“释义”的成分作量化的分析以期求得客观公正的结论。但问题在于:若“释事忘义”果真于典籍注释有弊无利,而且自唐代起就已经有那么多人明确地指出其弊端了,那么为什么李善之后,还有大批造诣极高的学者继续李善的路子,犯这个“错误”呢?很显然,“释事忘义”在注释史上的长期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古人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厘清这个问题对于诗文注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释事忘义”的理解
“释事忘义”乃“释事忘释义”之省称,涉及“释事”和“释义”两端。《文心雕龙·事类》对“事”有明确的界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源古以证今者也。”还说:“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7]472“释事”就是揭示事典和语典。这在理解上没有什么分歧。“义”,顾名思义就是意思、含义。朱自清在《古诗十九首释》中明确地说:“‘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8]4这也没有什么争议。混乱产生在人们对“释义”的理解上。“释典本身也就是释义,引旧籍的目的也仍是释义”的观点其实混淆了“释事”和“释义”的界限,并未揭示古人“释义”的真正含义。
《进集注文选表》的后面,有唐玄宗的“口敕”:“比见注本(按,李善注本),唯只引诗,不说意义。”[2]5唐玄宗要表达的意思很显豁,他认为李善的注只引古籍,而没有用直白、通俗易懂的话解释,不利于扫清文字障碍。五臣为什么批评善注“搅心”?正是因为他们觉得善注没有(按:准确地说应该是缺少)直白的解释,不便于理解。古人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李善的“释事忘义”的。因此“释事”和“释义”真正的分野并不在于有没有揭示意思,而在于以何种方式揭示意思,是征引古籍,还是直白的说解。亦即,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并不在于注释的内容,而在于注释的方法。当然,由于注释方法不同,也会带来注释内容、注释侧重点等一系列的不同,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释事忘义”古人还有一个提法叫作“引而不释”,这个提法中“引”和“释”这两个概念就很明晰地揭示了这种分野。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释事忘义”这个概念中,“释事”是指注家征引典籍的注释方式;而“释义”是指注家以直白、通俗的语言注释的方式,不论解释词义、句意、文意,还是揭示典故的用法、作者的情志、述作之由等,都包括在内。
王宁先生的理解当然没错,从广义角度看,任何注释方式,“释事”也好,“释义”也罢,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的含义。但是这样的讨论显然已经偏离了问题的核心,对于厘清纷争也就没有太大的针对性。而陈延嘉仅将“释义”的范围局限在句意和文意的阐释,将词义、典故含义的直解排除出去[6]99-135,原因也在于他没有认清“释事”和“释义”的分野,没有把握住古人争论的核心。
厘清了“释事”、“释义”这两个概念,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释事忘义”这个问题的实质,说白了就是对征引典籍以及直白说解这两种注释方式(以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这两种注释方式称为“征引式”与“直解式”)的选择和使用问题。古人之所以会带着贬义在二者之间冠以“忘”字,是出于他们对于“直解式”这种注释方式的重视,他们或许并不是那么反对“征引式”,但是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没有“直解式”,甚至数量太少都不行。相反,那些被批评为“释事忘义”的注释文本恰恰又不是那么重视“直解式”而更青睐于“征引式”的使用。这就需要弄清楚“征引式”和“直解式”的优势与劣势,明了影响注释者在这二者之间选择的因素。
二、“征引式”与“直解式”的优势与劣势
探讨优劣势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经、史、子、集这四种不同的文本类型对于注释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集部注释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扫清文字障碍、疏通文字功能之外,文学欣赏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这里对于二者优劣势的讨论是针对集部注释而言的。
基于大数据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新探索 …………………………………………………………… 卢 海 周 翔(1/23)
对于集部注释来说,“征引式”的优越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祖述的功能。文学作品的产生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对于前代的文学遗产都有借鉴和吸收。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以古为尚”、注重“家法”、重视模拟的国度,更是如此。而“征引式”采用“以古注古”的方式,致力于事典、语典的注释,探幽溯源,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揭示这种传承关系。李善在《两都赋》注的发凡起例即云:“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也。”[9]1其次,相对客观,能够为读者的自由赏析留下足够的空间。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字与字、词与词、意象与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语言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从而形成的一个包蕴丰厚的完整意思结构。它包含了无比丰富的思想情感、意蕴境界。面对这这样一个包蕴丰厚的意思结构,每一个读者所能够捕捉到的信息、体会到的感情、领悟到的意境、引起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学文本包含了理解的无限可能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在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阐释过程中毋庸置疑是存在的。
“征引式”注释方法的使用,有利于注释者以一个相对客观的态度,通过介引相关语境将文本中所可能包蕴的相关信息(包括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让读者在不致脱离文本的基础上自由地游弋,自由地理解,自由地体悟,这就为读者的自由赏析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提出了“秘响旁通”,与这种注释方式效果相类,他说:“我提出阅读时的‘秘响旁通’的活动经验,文意在字、句间的相互派生与回响,是说明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间所重视的文、句外的整体活动。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及交响。中国书中的‘笺注’所提供的正是笺注者所听到的许多声音的合奏与交响,是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该诗时整个心灵空间里曾经进进出出的声音、意象和诗式。”[10]71
“征引式”的劣势很明显,那就是五臣所批评的“搅心”。伽达默尔说:“诠释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11]202而“征引式”恰恰相反,它没有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而是将之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东西,特别不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阅读。“直解式”的利与弊也很明显。“直解式”注释则相对主观。注释者通过解说将个人的理解呈现出来,引导读者跟随着他理解的轨迹前行。这种权威式、武断化的注释方式以注释者个人的理解阻断了文本理解的无限可能性,消弭了文本内蕴的丰富性,将一个活泼的生命变成了僵死的存在。它最大的优势当然是通俗易懂,适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劣势则在于注释者常常以“己意”介入文本注释,阻断了文本内蕴的丰富性,从而缩小了读者自由欣赏的空间。
总之,对于集部注释来说,“征引式”具有祖述的功能,能够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姿态,为读者自由赏析留下足够的空间,但是不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而“直解式”通俗易懂,便于读者阅读,但若大量使用则容易使注释者之意介入文本,限制读者对作品想像的可能性。
三、影响注释者选择注释方式的因素
在中国集部注释史上,注释者对于“征引式”和“直解式”两种方式的选择和使用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以“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虽然历史上一直有“释事忘义”之说,但是并没有真的出现只有“征引式”而完全没有“直解式”的注本,被批评为“释事忘义”的注本其实都是以“征引式”为主而以“直解式”为辅。这种注释方式最典型的是李善的《文选注》[6]99-135,在李善之后则有任渊《山谷内集诗注》、《王荆公诗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等。
(1)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沈约曰:婉娈则千载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轻绝,未见好德如好色。
(2)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沈约曰:自我以前,徂谢者非一。虽或税驾参差,同为今日之一丘,夫岂异哉!故云万代同一时也。若夫被褐怀玉,讬好诗书;开轩四野,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没理一,追悟羡门之轻举,方自笑耳。
(3)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汉书地理志曰:河南开封县东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泽也。又陈留郡有浚仪县,故大梁也。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沈约曰:岂惜终憔悴,盖由不应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
李善《文选注》所保存的沈约注全部是“直解式”的疏通串讲,没有任何征引的内容。是沈约注本来如此还是李善只引疏通串讲的部分?由于其注原本已佚,无法探知究竟。但李善在注释阮籍诗的时候所引颜延年的注有“征引式”的部分,可见李善并不排斥对“征引式”旧注的使用。若沈约原注有“征引式”的部分李善应不至于弃置不用,因此沈约注阮诗应是纯粹的“直解式”注释。《文选》五臣注也是这一类型中较有代表性的。五臣不满李善注重“征引式”而不重视“直解式”,因此其注《文选》对具体的文字解释上很少引经据典,而是使用当时人们熟悉的语言直接描述、简明疏解。此外,元代张性《杜律演义》、明代朱谏《李诗选注辩疑》、明清之际唐汝询《唐诗解》、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等也都属于这一类型。
三是“征引式”与“直解式”并重。如前所说,“征引式”和“直解式”各有优劣,于是注释者尝试汇通二者,事义兼释,以图两全。《文选》六家本与六臣本的出现反映了人们汇通二者的努力,后代如曾益《李贺诗解》等就属于这一类型。事义兼释从逻辑上看可以有效地解决单用“征引式”或“直解式”所带来的弊端,事实并非如此。这类注本由于“直解式”大量使用,注家以己意干扰读者判断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是哪些因素在影响注释者对这两种注释方式的选择呢?
第一,文本类型。周裕锴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中说:“中国诗歌阐释策略的选择,与其对应的文本类型、或阐释者判断的文本类型密切相关,二者互相制约。”[12]38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息息相关,不同的文本类型要选择不同的注释方式。从诗歌的艺术类型来看,有赋类、比类、兴类三种类型的文本。赋、比、兴是前人对于《诗经》写作方式的一个概括,赋是铺陈直叙;比是以此物比彼物;也就是说诗人有意识地取物象来表意;兴是起兴,在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兴寄之兴,一种是兴会之兴。兴寄之兴类似于“比”,即诗人有意识地以此物比彼物,兴会之兴就是触物兴情,诗人的情志偶然为外物所触动,其所兴起的感情难以言说,苏轼说它“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13]56。我们这里所谓的赋类文本就是以“赋”的创作手法为主的文本;比类文本即以“比”及“兴”中的“兴寄”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本;兴类文本即以“兴会”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本。在这三种类型中,兴类文本乃诗人情感偶然为外物所动而作,这种感情本身就朦朦胧胧难以言说,再加上又以一种物我情融的状态呈现,它包含的内蕴是很丰富的,而且韵味深长。这样的文本常常是开放式的,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体会到不同的意义,因此也就不适合“直解式”,而比较适合以“征引式”为主。而赋类文本和兴类文本所描述的事情、表达的情感往往都比较清晰,无法给读者提供太多自由释义和欣赏的空间,这样的文本就不排斥“直解式”。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朱鹤龄在《辑注杜工部集序》中说:“诗有可解,有不可解者乎?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也。”[14]301-302浦起龙没有像朱鹤龄这么明晰地将兴类文本与赋类、比类文本分开,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义山诗可注不可解,少陵诗不可无注,并不可无解。”[15]5义山诗与少陵诗都具有典故密集的特点,少陵诗更是号称“集大成”、“无一字无来历”。因此,注释这两家诗明其祖述很重要,都要“注”。义山诗以兴类文本为主,诗歌意境朦胧难解,故不可解亦不能解。少陵诗有“诗史”之称,他的诗歌中赋类文本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不可无解”。而从诗歌语言风格来看,有些文本语言奥涩难懂,而有些文本则明畅通俗。在一般情况下,奥涩难懂的文本对于“直解式”的要求会多一些,而明畅通俗的文本就不需要注释者过多地去疏通语义。
第二,注释者的注释目的。古代注家注释典籍的目标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以恢复典籍原貌为注释目标;一种是“六经注我”,以典籍注释作为依托,通过注释表现注释者个人的思想、见解、情感、意念。当注释者以恢复典籍原貌为目的,他们就会力避“直解式”所带来的主观意识的渗入,而以较为客观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采用“征引式”,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文本的语言环境,提供给读者一个纯净的文本世界。当注释者持“六经注我”的态度的时候,作者原意、文本原意等都不重要了,文本成了注家“借杯浇臆”的工具,“我”成了注释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直解式”最适于顺畅无碍地表达个人的主观情绪。
第三,注释者的读者预设。注释者对读者的预设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注释方法的选择。如果他们预设的读者群体是贯通文史的学者,那么“征引式”注释无疑是最佳选择。而如果是针对一般的知识阶层甚至初学者的时候,“征引式”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五臣注在唐代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李善注而流行,主要是因为唐代科举考试重诗赋,参加科考的士子成为了《文选》最主要的读者,对于这些普通的知识阶层来说,五臣注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和学习。到了宋、清两代,重学问、尚博瞻、贯通文史的学者辈出,李善注的评价远远地超过了五臣注。在中国注释史上,不少注家在选择注释方式的时候都考虑到了读者的因素。如五臣在《进集注文选表》中说:“记其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复三十卷。其言约,其利博,后事元龟,为学之师。”[2]5徐曾《说唐诗》自序曰:“吾始欲深言之,则虑初学者,若无阶之可升。”[16]2潘眉为吴见思《杜诗论文》作序的时候谈到他注释的目的时提到的一点就是“便于初学”。这些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第四,注释者的个性、知识结构、个人兴趣等主观因素。学者型、理智型注释者偏好用“征引式”,而“直解式”则是“风人”型、感性型注释者的不二之选。这些因素都较为主观,兹不赘言。
以上论述了影响注释者选择的几个方面的要素,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注释者的选择是经过对各个要素的交叉综合考虑,最后做了取舍、妥协、退让的结果。比如同样是李商隐的诗歌,从艺术类型来说属于兴类文本,用“征引式”有助于最大程度地保存它的内蕴和韵味;若从语言风格来说它又属于较为晦涩难懂的本子,适于用“直解式”。注释者还需要考虑个人所长、注释目的、读者预设等方面的因素。
四、对“释事忘义”的再评价
所谓“释事忘义”其实是古人对于“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的批评。对于集部注释来说这两种注释方式各有优劣,文本类型、注释者的注释目标、读者预设、个性、兴趣、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了注释者的选择和使用。因此,用带有贬义色彩的“释事忘义”这个词一概而论地批评以“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这是不科学的。出现这种评价的原因在于,中国强大的经学注释传统使得大多数人对于注释的认识始终局限于扫清文字障碍、疏通文意上,没有认清集部注释不同于经、史、子部注释的地方。当他们带着这样的标准来看待“释事忘义”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作出了不太适当的评价。对于注释史上长期存在的这个现象,与其片面地使用带贬义的“释事忘义”进行批判,倒不如更加客观地使用较为中性的“引而不释”来重新审视和探讨。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萧统.文选[M].五臣,等注.首尔:正文社影印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活字本,1983.
[3] 李匡乂.资暇录[O].明正德嘉靖间顾氏文房小说本.
[4] 郑州大学古籍所.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赵福海,等.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6] 陈延嘉.关于《文选》李善注之“释事忘义”的评价问题[C]//赵昌智,顾农.李善文选学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09.
[7] 黄叔琳,李详,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 朱自清,马茂元.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 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王才勇,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2] 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38.
[13]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朱鹤龄.愚庵小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 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 徐曾.说唐诗[M].樊维纲,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阳 欣]
Reevaluation on the Tendency of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withou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LIU Me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 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120, China)
People have been holding a negative attitude to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withou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spel this misunderstanding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The so-called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withou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is a kind of criticism to ancient people as a method of glossing which uses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as a principal way an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directly” as an aid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In fact, the two ways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both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An annotator’s selection and usage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text type, annotator’s goal, targeted reader group, personality, interest and structure of knowledge. So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criticize the annotation method of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as a principal way an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directly” as an aid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by using the generalized expression of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withou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with derogatory sense.
Literary Selections;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withou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in poetry and prose annotation;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terary quotation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directly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13
2016-09-20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60038);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项目(13SKGC-QT05)
刘美燕(1981-), 女,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I206.2
A
1001-6597(2016)06-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