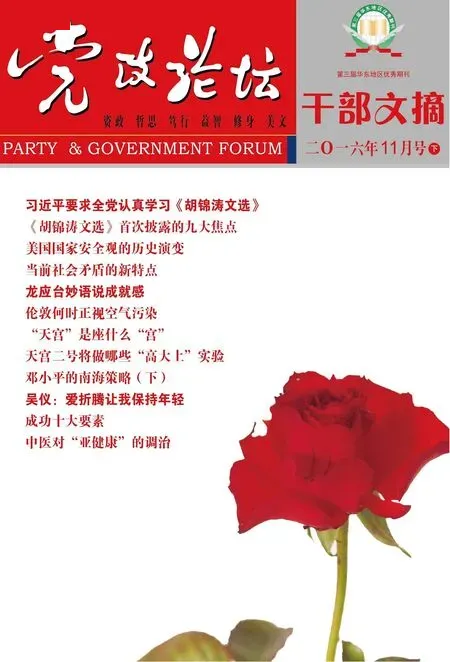“闲云野鹤”叶选宁
“闲云野鹤”叶选宁
7月10日,叶剑英元帅次子、原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8届全国政协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常委叶选宁先生,因病离世,享年79岁。
叶帅的馨儿
“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
当时,靠边站的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写信成了他和孩子沟通的路径。“馨儿”是叶选宁小名,1938年他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在湖南老家长大。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回京,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担负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
阿宁和老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和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那时的叶选宁喜欢音乐。有时,叶家父子会合奏一曲。叶剑英拉胡琴,叶选宁吹笛子,有观众的时候,就给大家表演一场,没观众的时候,父子俩自娱自乐。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文革开始后,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受了冲击,孩子们放了羊。叶家如同开了流水席,被抄家的、没地方去的,十几号人挤了进来,隔两天又换一拨人,大多是叶家孩子小时候的玩伴。文革之后,听说谁没平反,谁家的房子被占了拿不回来,叶选宁总会出主意、想办法。从老干部到文化人,很多人都和叶选宁有过来往,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许多事情,只要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他是红二代之间的粘合剂。”苏承德说。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他们回来了,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这天,是叶选宁的生日。苏承德看到了一张很大的音乐贺卡,上面写着: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肝胆江湖中人
叶选宁喜欢热闹,他的家里总有朋友在。苏承德说,叶选宁嗓子好,纯靠天然发声,唱姜育恒的那首《小丑》特别传神,不过他唱得最好的还是俄语歌曲,比如《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似乎有语言天赋,俄语、英语都不错,国内的方言学什么像什么。
他打小练书法,右手受伤十年之后,开始用左手练习。后来,他喜欢上草书,也喜欢隶书。写字见到好的、喜欢的,他都要抄写百遍以上,无论工作多繁重,每天都坚持。他的书法常落款为“雁洋叶三”。叶剑英是梅州雁洋人,叶选宁在叶家6个子女中排行第三。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叶选宁精研书法的严谨,像个潜心修行的和尚。“我们天各一方,有时夜半醒来,想到叶三此刻正在练字,登时眼前一个胖子灯下狂书的画面,十分好笑。”
朋友劝叶选宁开书法展,他拒绝了多次。2014年总算开了,把展览名字定为“习字展”,又出了一册《叶选宁习字集》。他说,60岁正是自己感觉有些心得的时候,73岁大病一场,鬼门关上一游,视力日差,腰腿也渐力不从心,字又写不出来了,又要从头来过。“出一本‘习字’,办个展,算是交份作业,拿出来请大家批评。”
在老朋友、曾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卫平眼里,叶选宁多年来没什么变化,尤其是,“爱哭”。走在路上,看到小女孩拉琴卖艺,叶选宁就坐下看着,回头问李卫平,带钱了没有,给她一百块。末了,俩人走了,叶选宁一步三回头,拿着手绢擦眼泪。
李卫平说,叶选宁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只喜欢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今年3月底,叶选宁给张延忠去电,想见她。自叶选宁退了之后,他们通常靠电话、邮件联络。有时,张延忠、王兴夫妇会去广州、珠海看他。张延忠赶到广州的中山医院。叶选宁已是肺癌晚期,十分痛苦,但仍问老朋友们的现状,尤其又问她:“你有没有缺口?”张延忠立刻就懂了。王兴因病住院,他们二人没有其他收入,全靠工资,叶选宁怕他们的工资不够花。
苏承德说,叶选宁“有名士气派,有侠肝义胆”。
李卫平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叶选宁去成都种牙,平时闲着没事,去了杜甫草堂。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卖字、刻章,叶选宁常去看,品评一番。后来,他和小伙子成了朋友。他请小伙子给他刻了一个闲章,一直保存着。上书四个字,是他自己选定的:闲云野鹤。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26期 徐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