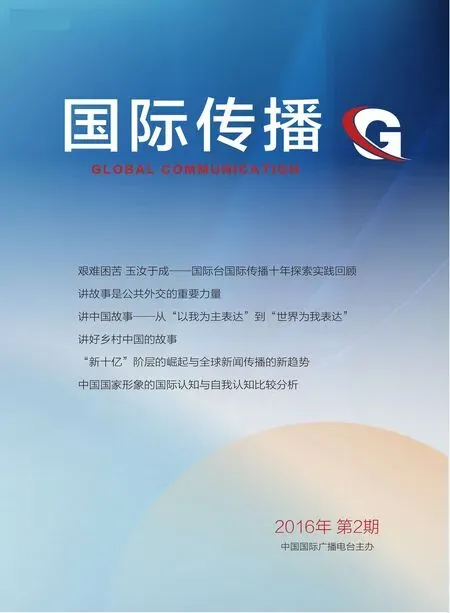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
(加拿大)赵月枝
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
(加拿大)赵月枝
乡村不仅是中国的主体元素和社会根基,也曾经诞生过对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故事,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韩丁的《翻身》就是典型案例。然而,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不但有很强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而且既存的乡村中国故事也带有较多的负面色彩。本文认为,从城乡关系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乡村中国故事具有六个值得讲述的面向:它是一个探索性的故事、一个理想性的故事、一个脱贫与致富的故事、一个追求幸福感的故事、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故事、一个生态修复的故事。要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需要从阶层分析出发寻找针对性,讲述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故事。
乡村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生态社会主义;第三者叙事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当前国际传播的核心话题。在接受《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的采访时,我曾经提到,中国如果要在国际传播话语争夺当中有所建树,必须“在国际场域一边挑战美国的网络霸权,一边走好‘群众路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即团结和争取亚非拉国家的积极力量,来促进全球传播民主化。”①赵月枝:“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全球传播格局与文化领导权之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24期。如果说在这个讨论中,“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在国际社会范畴的借喻,用来强调全球传播的民主化,那么,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之时,“农村”或曰“乡村”也恰恰是一个值得彰显的价值主题。换言之,如果要从更深的层面回应“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这一问题,我认为,这一力量之源就是乡村。最有价值的中国故事,正是乡村中国的故事。
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讲述中国故事之时,往往关注高远而宏大的叙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层。实际上,中国的基层蕴含着丰富的故事元素,它并非仅仅是中国崛起的细部和注脚,而是中国道路的精髓所在,是中国对世界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
为何要讲述乡村中国的故事
我们需要向全世界讲述乡村中国的故事,有三个重要理由。
第一个理由,乡村中国本来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构成主体。
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标志性事件。这部宣传片选取了13类59个人物来代表中国形象。让我好奇的是,其中有没有中国农民的代表呢?我只发现了一个,就是被称为“滇池卫士”的民间环保人士张正祥,但实际上他也不是因为农民身份而入选的。此外还有中国农业专家袁隆平,算是农业的代表。除了他们两位以及少数几位“感动中国”人物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形象代表是艺术家、企业家、运动员、学者、媒体人物和宇航员,换言之,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中上层,并且立足于城市。
如果从中国的整体人口构成来看,究竟谁才是中国的主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预计2020年才能达到45%。①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时间:2016-02-29。换言之,中国社会超过一半的人口,仍然是农村居民以及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是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如果要讲中国故事,能否忽略农民和农民工的故事,能否忽略这些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然而,中国的另一个“时代”人物,却与此相映成趣。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位居第一,而位居第二的就是“中国工人”,主要是中国的农民工。②Xin Zhiming:Chinese workers runners-up for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China Daily, 2009-12-18.在《时代周刊》的评选者看来,正是美联储和中国经济挽救了当时的金融危机。如果没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国经济又怎么可能逐步崛起,不仅为中国积累财富,更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当中国力图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与世界目光的焦点,又是否存在偏差?
第二个理由,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根基就在乡村。
中国社会从历史上说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曾是一个农业大国,现在也仍然如此。即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越来越少,但中国社会的根基并未彻底转移。从2004年到2016年这13年间,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主题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议题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从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核来说,乡村社会与农耕文明也是中国的基础性构件。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便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认为中国漫长的农业历史奠定了整个社会的根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说,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016年4月12日,许嘉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标题便是《中华文化的根在农耕文化》。在我的家乡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我带领团队作了很多调研,我们发现,像“迎案”①编者注:“迎案”是浙江省缙云县的一种民众自发组织、自发参与的传统民俗活动,集民间信仰、传统武术、杂技、舞蹈、造型、器乐等于一体。等源自乡村文化的习俗仍然在持续开展,农耕社会的遗产在相当多的人群中得到了维护。
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是一体发展的两个面向,农耕文明也因此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角落。只关注城市生活的“现代性”,却忽略其中丰富的“乡土性”,是否足以展现当代中国的丰富面貌?
第三个理由,讲述乡村中国的故事,最有可能获得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这方面早有成功先例。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提倡“借船出海”②刘健、陈昌凤:“国际传播新路径:借船出海与公民参与”,《对外传播》2015年第2期。,希望借助国际声音来讲述中国故事。我把它称为“第三者叙事”。这种叙事的好处是可以规避国际传播的对象对传播者具有的“宣传”色彩而产生的前置性反感。历史上,有两部作品曾经成为“第三者叙事”的成功之作。一部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另一部是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苏区进行了大量采访,写下了众多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社会状况丰富真实的通讯报道。1938年,这些系列通讯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伦敦出版,风靡一时,短短一个月之内再版三次,发行十万册,随后又在美国出版,同样引发轰动,单单报刊评论就有一百多篇。③刘国华、张青枝:“《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随后这本书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中国翻译出版,鼓舞了众多青年人奔赴苏区。对于当时的西方来说,这部作品对其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革命,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它讲的故事,不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的故事吗?
另一部作品同样是讲述中国乡村故事的杰作。美国人韩丁曾经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深受感动,由此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同情。1947年,他作为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农机专家来到中国,次年作为观察员亲历了晋东南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回到美国后,他因此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6年,他的记录终于在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必读著作。如果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讲述的还是中国革命精英与领袖在乡村领导革命的故事,那么韩丁记录的则是真正的中国农村的故事。在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教育和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进步青年。他们当时了解中国,就靠《翻身》这本书。我的美国和加拿大的老师与同事,大都知道并读过这本书。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西方的记者和学者讲述中国故事最成功的、最正面的、最有影响力的,恰恰是农村的故事、土地革命的故事。这说明了什么?又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如今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场以农民的解放为核心的、被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认为有“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的人们”①郭台辉:“崛起的意义: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社会——访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4-25,第003 版。的普遍意义的革命所具有的道义力量却从未磨灭;不仅如此,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反而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具有在各民族、各文化、各社会的基本共识上达成同情与合作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这三点,我认为,“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对于当代中国国际传播而言意义非凡。当然,强调“乡村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城市中国”的价值,更不意味着将两者割裂。恰恰相反,唯有在中国城乡关系的辩证理解之中,才能走向一个独具魅力和吸引力的中国叙事。
既存的乡村中国故事有哪些
如前所述,中国革命年代的乡村故事带给世界诸多感动与启发。新中国成立之后,乡村中国依然在提供源源不断的故事素材。
在毛泽东时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故事往往涉及乡村,如赤脚医生、乡村教师、电影放映员的故事,等等。例如,赤脚医生的医疗实践不仅仅为当时中国的健康体系带来了改天换日的变化,而且赢得了众多国际赞誉。1965年毛泽东在与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谈话中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②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03期。这成为“赤脚医生”和中国式乡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开端,此后二十年间,一批教育程度虽然不高但内嵌于农村基层的乡村医生为中国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1970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国内乡村医生中人手一册,而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1977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湖南革命健康委员会的《赤脚医生手册》至今仍然在亚马逊网站上出售,并一直获得好评。中国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代表人物王桂珍、黄钰祥和覃祥官等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等全球性会议上作报告。2005年,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NPR)还专门回顾了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乡村合作医疗革命,从而为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发展提供借鉴。①Vikki Valentine: Health for the Masses: China's “Barefoot Doctors”,http://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990242, 2005-11-04.
除此之外,新中国的农村还涌现了无数生动的故事。建国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变化,例如识字率的提升、女性的解放、“小水电”的发展,都为世界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实践,它们自然也为中国塑造正面形象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1979年,我的家乡浙江省缙云县盘溪梯级电站的照片,就在加德满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小水电会议上展出。1980年,在杭州参加第二次国际小水电会议的一个包括24个国家和国内专家的60多人团体到缙云考察盘溪梯级电站。②缙云县志编撰委员会,《缙云县志·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页。就这样,一个交通闭塞的山区小县也以自己因地制宜的现代化创新,开始对外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故事的主角也多半是中国农民。农民中的“万元户”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表征着改革开放最初的成功,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然而,1985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农业经济慢慢衰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农村的故事渐被遗忘,即使出现,也具有了更多负面色彩,反倒是国外媒体往往成为讲故事的主体。
首先,农村被描绘成衰败的领域,农业和农民被描绘成负担。他们的生活似乎失去了色彩、光亮和那些曾经美好的事物。2010年,我在温哥华的一家华人超市偶然读到一份华文报纸,它的头版头条讲述了一位农村青年通过互联网与外地友人相约自杀的事。③参见李笛:“青年朱小辉之死”,《青年时报》,2010-03-31。尤其让我揪心的是,这位青年就来自我的家乡浙江省缙云县河阳村。中国农村,真的已经衰落或凋敝,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包袱了吗?中国农民真的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了吗?这个悲伤的故事,促使我下定决心要重返我的故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中去。
2014年《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也以中国乡村为主题,充满了哀叹的语调。其中引述了来自中国研究者的数据,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1年间,中国的村庄从370万个锐减到26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300个村庄。该报用作家冯骥才的话作标题:“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①
其次,农村社会冲突的故事、尤其征地拆迁的故事,获得很多的关注。2011年的乌坎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这一事件由土地赔偿款纠纷肇始,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并引发了基层民主选举体制的试点改革,从而激发了外媒的浓厚兴趣。事件高峰时期,曾有数十家境外媒体记者赶到乌坎村进行采访。2012年3月5日“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团媒体开放时,先后有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广播公司等境外媒体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有关乌坎的问题。②黄丽娜等:“境外记者数问乌坎 汪洋一次圆满解答”,《羊城晚报》,2012-03-06。中国农村经历如此深刻的变迁与转型,矛盾不可避免,这过程中的激发性事件又容易引起新闻媒体的额外关注,将之塑造为社会新冲突的符号。如何丰富而全面地讲述中国农村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包括中国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需要反思的问题。
讲述什么样的乡村中国故事
当代乡村中国的变迁是复杂而多元的。三农问题真实存在,中国乡村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讲中国农村的故事,我们不能颠倒黑白、粉饰太平,也不必掩盖社会各界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存在的不同看法。进而言之,中国如此广阔,沿海和内地、北方和南方,乡村的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无法以一概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乡村故事。正如我在别处已经写到的那样,农村衰败,家乡沦陷,价值沦丧,礼崩乐乱——这一去年春节间达到高潮的城市小资“返乡体”的主题,也不应该是乡村中国故事的主调。③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在我看来,乡村中国故事是一系列故事的集合体,它们必须放置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讲述,必须放置在城乡关系一体化中进行讲述,也必须放置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7。这一过程中进行讲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村庄”一词“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⑤赵月枝:“生态社会主义: 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当全球资本主义依赖消耗农村的生产力要素获得发展,却又将农村视为落后包袱的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则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反哺农村,这种新的城乡关系是否展现了新的方向与新的道路?它是否“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核心部分,并因此是蕴含着丰富吸引力的故事?从此高度,我们可以提炼出六个乡村中国故事的面向。
第一,乡村中国故事,是一个探索性的故事。人类不断探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中国也在用自己的实践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道路何去何从,存在各种讨论、各种竞争、各种博弈。从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角度来讲,中国农村是重要的。例如,当下农村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土地确权。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性质,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不能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此同时,土地确权的试点也在进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问题,更有专家学者担心,这会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虚化村集体对土地的经营权利。中国是否要学西方部分国家,把私有权进行到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土地制度存在很多巧妙的设计,例如一块田地的产权分为田面权、田底权,有了田面权后还可以转租给别人,这种所有权是很复杂的,是几千年反复博弈下形成的很聪明的解决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产权概念?这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我们习惯于以西方、尤其以美国的产权制度为榜样。可是,我们需要知道,作为垦殖主义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农业建立在血腥掠夺的原住民的土地上。实际上,如果将土地私有权进行到底,今天我所在的加拿大大学,还是在原住民部落没有割让的土地上。
农村的金融改革也值得反思。资本下乡,把农村变成资本增值的新场域,有可能对土地革命的成果造成否定,这些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事情,都应当进行讨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应当协调发展,这是城乡一体化的真义。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如今城市反哺农村,带来新型城镇化,其中蕴含方向性的探索。中国农村的每一步改革,都具有丰富的价值,如果能够走出独特的中国道路,它将对世界发展作出贡献,这些故事也将成为引领世界的故事。
第二,乡村中国故事,是一个理想性的故事。中国农村何去何从,充满博弈,但需要有一个理想的彼岸。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乡村中国,是实现这个理想的重要实验田。农村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或经济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社区共同体,有鲜活的人在其中生活。农村建设,也不仅是发展农业、提高产值,更是要维系农村这个社区共同体的统一性和有机性,使其更加宜居。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理想性故事”,与当下媒体表达的、作为对城市危机情感反映的中产阶级乡愁对象的“去历史化”的“理想乡村”故事,有本质的差别。①相关讨论请参见孙佳山,“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三种乡愁纪实形态及其悖论”,《中国传媒报告》,即将出版。正如我在一个访谈里所说的:在我看来,乡愁是感性的——包含对乡土的依恋情感,是知性的——包含对有关乡村的一切知识的浓厚兴趣,也是理性的——它是几代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归宿的拷问;它是一个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本根的追寻;它是人们对日益深化的城乡鸿沟的跨越;它是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后,对自己所欲所求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的探索。①徐继宏:“一枝一叶总关情——记缙云籍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教授”,《文化交流》2016年第10期。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城乡互补的社会。等到鸦片战争开始,整个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1932年茅盾写的小说《春蚕》里就有生动的描述,而它已经隐含了农村凋敝的动因。随后农业衰落,农民被逼上梁山,开始跟着共产党搞革命。这正是斯诺和韩丁讲的一系列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故事的主线。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付出,但新中国建设也出现了前三十年围绕农村的许多好故事:耕者有其田理想的实现、人民公社、农田水利建设、赤脚医生、乡村教育、农村电影放映员,等等。
然而,历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农村先是被当作粮仓,后来粮食的重要意义下降,农民变成了廉价劳动力。更让人唏嘘的是,在一些故事里,“农民”成了无知和保守的代名词,“农民负担”被演绎成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可喜的是,自2003年重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中国对于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认识,已从单一维度拓宽到全方位的理解。如今,中国已经重新发掘农村作为社会和中华文明根基的重要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中国提出的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的发展策略,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故事,更接近于人类理想。“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57页。这已经是国家高度的认识,也应该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理想性故事的主题。
第三,乡村中国故事,是一个脱贫与致富的故事。如前所述,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是前沿阵地,也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直到如今,它依然是举世瞩目的成就。2015年10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洁说,据估计,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率达到了76%。③焦梦、范安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达76%”,中国网,2015-10-19。让人民吃饱了饭,不正是改革开放故事最大的吸引力源泉吗?脱贫与致富曾经是中国农村故事的主要内容,现在也并未逊色。而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中国政府努力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如水、电、公路等,充分展现了国家动员、国家能力的重要价值。
当然,“三农”对于减贫致富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农村本身。正如王晓明所言,是“乡村让城市更美好”。这里的“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乡村的几乎所有好东西——物产、资金、人力和人才,都被持续地收进了城。”①王晓明:“乡村让城市更美好”,《中华读书报》,2016-03-23。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村的土地和农民工的血汗之上,还有那些从农业产品中一点一滴积累的资本,以及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与科技人员。中国崛起故事的另一半正发生在农村,而这一半故事却往往被遮蔽或扭曲。
第四,乡村中国故事,是一个寻求幸福感的故事。它是一个村子成为美丽乡村、人成为现代人,拥有主体性与自豪感的故事。
这些故事正在缙云发生。例如,2015年,因寻找历史遗迹,我有机缘走进了舒洪镇仁岸村,从此知道了这个村庄美丽蝶变的故事。这是画家潘天寿在抗战期间曾经避难过的村子,原来的环境很差,如今却真的像一幅画卷。我随意进村,被眼前的一切所感动,情不自禁地把所拍的照片发在微信中,配的标题是“美丽乡村,呼之欲出”,后来,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关这个村的文章,发表在《浙江日报》上②赵月枝、龚伟亮:“仁岸村的‘三大战役’”,《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2016-07-26。。仁岸既不是穷村,也不是富得冒油的地方,而是“小富即安”。这里的主要特产杨梅,是1990年代搞“一村一品”发展农村经济的成果。由于本地农副产品的生产足以维持家庭经济,这里没有大规模外出打工导致“空心村”的现象,但是,由于社区建设的缺失,村子里一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后来,浙江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仁岸村评比排名倒数。这最终激发了村支部书记何伟峰的斗志。在县镇领导,尤其是当时舒洪镇驻村干部邱晓敏的帮助下,何伟峰带领仁岸村开始了全方位的建设,如今清溪环绕、绿树成荫、锦鲤成群、垃圾无踪,老祠堂、新建筑、石板路、长廊构成了让人舒心悦目的环境。仁岸村已经成为先进模范村。她的故事,就是寻求幸福感、寻求人的自尊自信的故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仁岸村美丽蝶变的故事是我自己发现的,当地政府没有主动向我宣传这个村庄。这使我想到,如果我们带着开放的心态,多到农村走走,会不会还有类似的美丽邂逅?
第五,乡村中国故事,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故事。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决议强调,“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当现代性渗入到中国当代文化的肌理之中,我们是否还能够保存农耕文明的文化内核?
我的观点是,农民就是中国的原住民,但他们不是北美保留地上的原住民,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是脚下土地的主人、乡土文化复兴的主体。今天,在原住民持续和顽强的抗争下,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怀着历史性愧疚,把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种种文化仪式、习俗、歌舞当作国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珍视和推广。在加拿大三十多年,我亲眼目睹原住民文化的主题是如何在我自己所在的大学一步一步被重视和得到呈现的。中国的农村仍然保留着丰盛的文化习俗资源,像缙云民间的“陈十四娘娘”女神崇拜、庙会、迎案、婺剧,不也值得认真留存?另外一个例子也值得关注。官店村每年的乡村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延续了六十余年,构建了官方话语、商业话语之外的替代性维度。2015年春节官店的“村晚”上,有一个婺剧小品《老鼠娶亲》,借用老鼠的视角,青年男女对“什么是好生活”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加以反思,也提出了在农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的生活道路选择。①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03期。这些源自乡村、民间、日常生活的多元文化,一旦能够逃离猎奇的凝视,完全可以成为对外讲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正如我在文章中写道,在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包括官店村“村晚”在内的四台来自浙江丽水市的“村晚”,就通过中国文化部的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向国外直播。②同上。2016年10月,在我组织的以“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第二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上,来自浙江丽水市文化局的林如豹处长关于丽水乡村“村晚”的报告,尤其是他描述的以乡村春节晚会为平台,复兴乡土文化的事业蓝图,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以城市为导向、以天价明星为核心的高度商业化的文化生产遭遇困境的今天,乡土中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
第六,乡村中国故事,还是一个生态被破坏又正在慢慢被修复的故事。
我生长在农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特别多,对环境的需求与消耗也极大,人们不断向山林索取,甚至把树根都挖回来烧火。早先“大炼钢铁”就曾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后来因为人口多,实际上把一根草、一根苗都拿来养家糊口。这是人从自然攫取的过程。从生态角度看,农村空心化、人口减少,也带来了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使自然得以休养生息。在浙江缙云,重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白鹭,池塘里的鱼回来了,山上的野猪也回来了,山上的树也非常茂盛。当然,农村经济发展也有环境副作用,如养猪、养鸡、兴建工厂、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也带来了地表和水源的污染。近年来,浙江搞“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溪水重新变得干净了。从长远来看,生态确实在逐渐恢复。
因此,乡村中国的故事还包含着重建生活家园、复原生态文明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有一句名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深刻认识到生态重要性的新发展观的通俗而生动的表达。在浙江缙云,凭借“后发”的优势,政府正在引领乡村打造以生态建设和旅游为基础的“美丽经济”。例如,在新建镇笕川村,村干部通过把农户的土地流转回村集体,开发了一片花海,希望把一个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的村庄,建设成集休闲观光、餐饮食宿、农事体验、科技示范于一体的“绿富美”的乡村。一条高架铁路在山区小盘地的平原上飞过,四周是青山,一辆名为“笕川号”的古香古色的小火车徜徉在万紫千红的花海里,你还能想象比这更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当然,笕川不是可以复制的,花海项目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观察。但是,这个村庄围绕生态建设,探索集体经济体现形式和产业形式创新道路的故事,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这六个面向的乡村中国的故事彼此交织,勾勒出一幅有足够吸引力的中国乡村画面。但它绝不仅仅是讲述农村,更指向城乡关系。如果没有政府的动员能力,如果没有工业反哺农业,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和农民主体性的互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企业家、技术人员的“新下乡运动”,如果没有新形式的“工农联盟”,怎么会有共同富裕、共同建设的美好景象?说到根本,乡村中国的故事,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故事。
如何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
乡村中国的故事拥有丰富内涵,值得浓墨重彩进行讲述,然而如何讲好这个故事,还需细细考量。
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受众分析。乡村中国的故事讲给谁听?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是上流社会还是普罗大众?是金融权力阶层还是劳工阶层?在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时,在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中,如果只针对西方国家,讲北京成为新纽约、上海成为新伦敦,这样的故事不仅缺乏吸引力,反而易招批评。然而,如果面向第三世界国家,讲中国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使多少人进入了小康生活,中国的基础设施如何借助国家动员和行政能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如何克服城乡差别从而获得协调发展,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又可以提供什么借鉴,这些故事不是更加精彩吗?在某种意义上,有些新闻报道总是关注西方,以其为参照,却忘记西方世界早已在资本主义进程中消灭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如果用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作为参照,那么,尽管有自己的问题,但中国的故事就不是一个农村衰败与城市产生贫民窟的故事,而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充满活力的故事。
受众分析的前提是阶层分析。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其受众的阶层亦很复杂。如果只是迎合西方所谓的主流媒体和上层社会,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不免流于片面。如果我们走的是一条人民的、大众的道路,走的是一条生态社会主义道路,讲给西方的精英,他们会感兴趣吗?如果我们中国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改变世界格局,讲给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听,他们会听吗?我们不可能以中国故事来迎合、满足、取悦西方的跨国资产阶级。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有针对性。讲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故事,美国人可能的确听者寥寥;但是生态断裂和生态修复的故事,美国人可能爱听。如果讲述如何走城乡互补发展道路的故事,我相信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感兴趣。我们还可以想象,如能讲述一些中国农村青年不再需要离乡背井,在“世界工厂”里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像以上提及的《老鼠娶亲》小戏里所憧憬的那样,能在农村安居乐业的故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釜底抽薪,使美国的右翼政客们再也无法在他们的“美国故事”中,煽动美国工人的种族主义,把中国农民工当替罪羊?
在受众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讲述的乡村中国故事,一定要有广度、深度和温度。首先,要有世界历史的广度。例如,乡村电影放映员是一个好故事,但要讲好它,就要观察整个中国电影业乃至世界电影业,看看电影业在漫长的发展史中,有没有预留乡村的位置,从一个放映员的故事可以见微知著。反过来,也只有从全球的、历史的广阔视角,才有认识高度,才能讲出好故事。
其次,要有深度。真正经过长期调研讲出来的故事才是有深度的,否则难免陷于猎奇,难免流于乌合之众的走马观花。例如,浙江农村的“五水共治”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省到市、到县、到乡镇、到村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故事。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来讲清楚生态的恢复,需要深入调研,还需要跟踪,要求记者像学者一样深耕田野,作专业调研。不能只追逐突发事件,而要作有主题性、策划性、专题性的报道。
再次,要有温度。好故事总是声情并茂的,是动人的故事。中国2.6亿农民工,前仆后继去工厂做工,这其中有多少背井离乡,有多少喜怒哀乐,从整体来看又是多么悲壮的故事。再看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我们看到的报道多是猎奇,常常涉及儿童集体自杀或者空巢老人的死亡,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人情味。有些留守老人含辛茹苦抚养孙辈,既不容易也颇有欢乐,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老人的成就感就在含饴弄孙,跟西方颇有不同。新闻报道是否能讲出更复杂和多元的感情?
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第三者叙事,或曰“借船出海”。换言之,应当让外国记者到中国乡村来调研,让他们能够写出充满理解和同情的、有温度的动人故事。同时,中国的传播教育也要培养学生从乡村的视角看问题,让他们既出得了国,也进得了村。
在2015年第一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的征文启事中,我和同仁们字斟句酌写下了四句话:“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乡村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乡村如此重要,乡村故事不容忽视。当中央与基层政府倾注心力建设新农村之时,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和教育者也应当超越城市中心主义,采取城乡关系视角,理解乡村,理解中国的独特道路。只要我们有自信,就一定能够吸引新时代的斯诺与韩丁。
(责任编辑:姬德强)
赵月枝,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张磊研究员对本文写作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