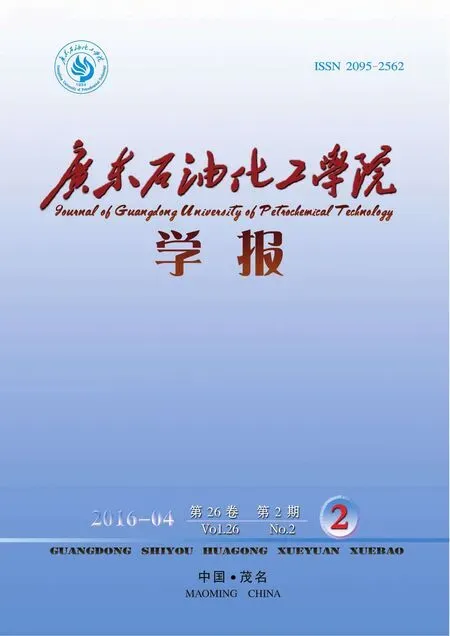莫言小说《变》英译本的叙事性解读
——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例
章心怡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莫言小说《变》英译本的叙事性解读
——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例
章心怡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变》是莫言最新的自传体小说,在叙事层次和叙事技巧上呈现出鲜明的叙事特色,针对叙事学对翻译的理论指导,译文需要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与原文达到对等,才能实现小说在艺术上的等值。运用叙事学理论对《变》的原文和英译本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时态、标点、斜体等手段显化处理了宏观层面的叙事层次;在微观层面上,通过直译或直译结合增译的方式,一定程度再现了原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技巧,创造了流畅且可读性强的译文,促进了小说在英语语境的传播。
关键词:《变》英译本;叙事时间性;叙事关联性;叙事选择性
叙事学起源于结构主义兴盛的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着重探讨文本内部的结构规律以及叙述技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学开始关注作品以外社会历史环境,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演变成了“将重心转向读者及其目标语境”的后经典叙事学[1]。叙事学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正如Whitebrook所言:“叙事理论能够帮助人们考察翻译如何在跨越时间和文本限制的叙述中起到重要作用”[2]。黄海军和高路的研究也证实了叙事学对叙事翻译的指导和促进作用[3]。张景华指出,应用叙事学能从“多种角度发现小说翻译中的假象等值”[4]。苏艳飞提出,译文必须在“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叙事策略”上达到对等,才能实现与原文在宏观上的对等[5]。郑敏宇强调要“恰当把握原著叙事技巧并准确再现其叙事风格,方能实现文艺美学功能的等值”;叙事技巧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宏观的叙事结构,如叙述层次、叙述聚焦主体等”,“二是叙述话语,如语言手段等[2,6]”。为探讨叙事学对文学翻译的理论指导和实际运用,本文将以莫言的自传体小说《变》(以下简称源文本)的英译本Change(以下简称目标文本)为例,利用叙事理论中的叙事层次和叙事特征,通过细读文本、双语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译文对原作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的承袭以及再创造,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文本的操控限度。
1小说《变》的叙事层次和特征
对叙事层次的梳理有助于理解原文;对叙事时间性、关联性以及选择性等特征的分析能更好的把握原作的风格。
1.1叙事的层次
叙事层次指“小说中叙述与被叙述这两个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7]”,在《变》中,尽管叙述者“我”和被叙述者“我”都以第一人称出现,但这两者实际处于不同时空层次上:被叙述者“我”是故事中的人,属于故事层次;而小说真正的叙述者“我”则在故事之外,属于超故事层次[7]。不同层次的叙述者向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叙事内容、时空距离、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7]。
1.2叙事的特征
本文探讨的特征包括叙事的时间性、关联性以及选择性采用。叙事的时间性(temporality)是指叙事中各个元素总是以某种顺序排列的。在自传体的写作中,叙事极少遵循严格的历时性(chronological order),《变》以倒叙的方式开头,在对往事的叙述中不时插入当下对过去的评价,并且在回忆的叙事中也包含了不同时期事件的穿插,造成了小说中叙事时态和叙事层次的不断转换。
叙事的关联性(relationality)指把一个叙事引入另一个叙事中时,源叙事和目标叙事都需要被重新构建以协调一致[8-9]。通过重新构建源叙事和目标叙事,以目标语境相对应的词汇和事物替代源叙事,或者通过增译等方式改变目标叙事,使两种叙事协调一致,是常用的翻译策略。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通过在目标文本中适当保留源文本的关键术语能避免被引入的叙事受到弱化或威胁,而这类不熟悉的词汇也能为目标读者创造更具挑战、变化性的阅读体验[8-9]。
选择性采用指叙事者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对事件进行筛选[8-9],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中文语境中的许多词汇和文化现象在英文语境中无法对应翻译,若通过直译、增译、注解的方式保留所有内容,必然会使译文丧失流畅性。《变》的英译本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选择性采用,以保障读者的流畅阅读和理解。
1.3译者对译文叙事的操控
译者对叙事的操控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等手段来调控源文本,目的是调和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差异,并尽量保留源文本中特有的文化内涵、叙事风格、叙述手法等等,从而再现源文本的艺术和美学价值。
译者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和改变源叙事,方法包括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等。时空建构是指将一段叙事引入另一段时间、空间截然不同的叙事中,从而突出这段叙事的方法。在引入源叙事时,通常采用直接引入或加工后引入这两种方式。译者需要把握度的问题,若一味地为了阅读的流畅感改变源文本,大幅删减文化内涵,则会破坏源文本的美学价值。在运用选择性采用改变原叙事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如果源文本的文化内涵参与构建了源叙事语言风格、甚至主题表达时,此时的删减则是不合时宜的。
2葛浩文版《变》的叙事风格再现
《变》是莫言第一部近似回忆录、自传体的小说,通过“我”及我的同学的人生经历,从民众的视角反映了中国1969年至2008年间的变化,语言通俗、风趣。小说发生在北方农村地区,地域色彩浓厚,大量使用民俗文化、历史典故。
“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10]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作品的“唯一首席接生婆[11]”,并被称许为对莫言获奖立下了汗马功劳[12]。“删节”“改移”“整体编译”等是葛译常被贴上的标签[12],在对其学术研究中,他的翻译也常被冠以“忠实”“创造性加工”“创造性叛逆”等标志[11,13-14]。
在《变》的英译本中,葛浩文基于“为读者翻译”的原则,删除和意译让目标读者费解的文化负载词,并通过直译、改写、增译等方式,保留文化内涵,捕捉浓郁的东方色彩和诙谐的语言风格[15],努力在“忠实意义”的同时“忠实字面/形式”。译文通过高度直译加增译的方式保留了源文本中的文化典故、俗语,并且用拼音和音译的形式保留源文本关键术语的手段,在译文中成功再现了原文中的异域风情,保留源文化特色,创造出了“不隔”的模糊美感[11]。
3多维度叙事性解读
3.1叙事的时间性和叙事层次
叙事的时间性决定了叙事中各个元素总是以某种顺序排列的,而在自传体的写作中,由于回忆的特点,叙事往往缺乏精确性的时间参照。这就造成了往事叙述中叙事时态和叙事层次的不断转换。
源文本:
(1)按说我要写的,应该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事情,但我的思绪,却总是越过界限,到达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下午。至此,我的回忆便与我混为一体[16]3。
(2)到达高密火车站时……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做那个介绍茂腔的节目时,我还提到了这件事。我买了……[16]45
目标文本:
(1)By rights, I should be narrating events that occurred after 1979, but my thoughts keep carrying me back to that fall afternoon in 1969….When it reaches that point, I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my thoughts[17]1.
(2)It was early morning when we pulled in to Gaomi Station…(I mentioned this incident a few days ago, during my introduction to Maoqiang opera for the Central TV drama channel). I went in and bought …[17]59
评析:叙事的时间性表明,回忆往事时存在时空的穿插,这在文本中就体现在插叙、倒叙的频繁使用,这同时也标示了叙事层次的变换,如上文的(1)(2)。故事由正在写作的“我”(超故事层次)开始,倒叙到1969年,叙事者变成故事中的“我”(故事层次);在回忆往事时,以插叙的方式,让叙事层次上升到超故事层次。不同叙事层次能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故事层次能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引导读者从“我”的角度看待往事;在超故事层次中,“我”则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故事本身,对事物的理解会更为全面、理性。译者主要运用了时态、括号、斜体、分段这几种手法,为读者明晰了叙事层次,通过叙事层次的不断变化,反映不同阶段的“我”思想的碰撞。而抽离出来的、突出标示的超故事层次,也营造了话外音、旁白的效果,从而带领读者跳出故事层次,跟随 “我”一起审视过去,对比事物以及“我”的眼界的变化,突出小说“变”的主题。
3.2叙事的关联性
叙事的关联性要求译者通过增译、删减等方式重新构建源叙事和目标叙事,使两种叙事协调一致,以促进目标叙事在目标语境的顺利传播。为了保护源文本中的文化因素不被目标语境弱化,需要适当保留源文本的关键术语以维持源叙事的独特性。
源文本:
(3)……他就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他自由了。学校的清规戒律再也管不着他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忍受老师的约束[16]12。
(4)……说姜子牙命运处于低谷时,卖面粉遇上了狂风,卖木炭遇上了暖冬,仰面朝天长叹一声,一摊鸟屎落入口中[16]22。
目标文本:
(3)He was like a bird leaving its cage, free, no longer governed by regulations or school discipline. The rest of us we had to keep putting up with the teachers’ suffocating control[17]13.
(4)…Once, when a down-and-outer named Jiang Ziya was selling wheat flour, a strong gale swept it out of his hand. Then he tried selling charcoal, but it was a particularly warm winter. Finally, when he looked up into the sky and sighed, bird shit landed in his mouth[17]26.
评析:叙事的关联性表明把源叙事引入目标叙事中时,需要重新构建,以使引入部分和谐融入目标语境。(3)的目标文本省译了源文本的文化内涵:“清规戒律”原指佛教徒所遵守的规则和戒条,喻指束缚人的繁琐的压抑人性的规章制度,此处暗指学校处处存在不合理的束缚人的制度,利用文化典故引申含义,并营造幽默感。目标文本翻译成“学校的规章制度”(regulations or school discipline),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幽默性。在紧接着的译文中,将源文本“约束”增译成了“让人窒息的约束”(suffocating control),对上文的意思丢失做了弥补。(4)是一段说书。源文本采用八字一句的格式,在动词、名词上对应搭配,读来朗朗上口。目标文本将原文的短句改写成复合句,并增加了逻辑连接词,以符合目标语言严谨的句法结构。这削弱了行文中的韵律感和民俗风情,在语言风格上并没能做到对等,也减弱了阅读乐趣。
小结:在本小说中,译者通过改写、增译、省译的方法,改写无法直接对译的部分,增加对源文本中文化典故、习俗的解释性说明,并删去会造成理解障碍的文化背景。这种追求流畅通顺、忠实意义的做法,有时会导致删减幅度过大,导致行文在写作技巧、语言风格上不能达到对等,造成了另一层次的不忠实,也削弱了小说原有的魅力。
源文本:
(5)他有一个外号叫“河马”,我们谁也没见过河马,蛤蟆也有一张大嘴,且“蛤蟆”与“河马”发音相似,于是“刘河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刘蛤蟆”[16]4。
(6)乡下人见惯了锣鼓家什,一鼓一锣一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16]15。
目标文本:
(5)One of his nicknames was ‘Hippo’. Now, none of us had ever seen a real hippopotamus, which in Chinese is hema, and that sounds like hama, for toad, another creature with a large mouth, so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we started calling him Toad Liu[17]3.
(6)Now, country folk are no strangers to cymbals and drums: a drumbeat, the clang of a gong and the crash of cymbals: bo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17]17.
评析:(5)是讲述刘老师的外号从“刘河马”演变成“刘蛤蟆”的选段。源文本的关键词“河马”和“蛤蟆”对于理解绰号的起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标文本在提供英文对应词(hippo,toad)的基础上,用拼音保留了源文本的关键术语,并通过斜体突出关键词,让目标读者通过对比两个词在拼音形态上的相似,体会它们在发音上的相似,从而理解“刘蛤蟆”(Toad Liu)的来源。在此处选择增译和保留关键术语,便于理解,并且保留了原文的音律感和诙谐性。(6)是描绘民间乐器的片段,译者使用音译法,通过拟声词,保留了器乐声这一关键术语,从而保持了源文本的音乐性,做到了意义和语言风格上的对等。此外,译者还通过斜体的方式突出了器乐声,迫使目标读者注意陌生词汇,营造出更具挑战性、多样化的阅读体验。
小结:为了防止在重新建构过程中对源文本造成的“污染”,译者可以通过保留关键术语的方式保留源文本特有的词汇。而对关键术语的保留还能迫使读者跳出阅读的舒适区,创造出更具挑战性、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上文两例中,译者即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又承袭了源文本的语言风格、文化内涵,使原文和译文的叙事在微观上达到了对等。
3.3选择性采用
选择性采用指叙事者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对事件进行筛选和采用的手段。在不影响主题表达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了选择性采用,能保障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促进目标文本的传播。
源文本:
(7)我将八千元钱点给了鲁天公,告诉他,我花高价买你的破车,是变相送礼。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6]71。
(8)……我没有别的理想——我只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鲁文莉的爸爸[16]7。
(9)简单点说,就是:汽车一到,鸡飞狗跳[16]13。
目标文本:
(7)When I gave him the eight thousand yuan, I said it was a gift and that I had a hidden motive-like Xiangzhuang performing a sword dance to cover his attempt on Liu Bang’s life…[17]97
(8)… I don’t have any other ideal-I only have one ideal-My ideal is to be Lu Wenli’s father[17]6-7.
(9)Simply stated, when that truck came along, chickens flew and dogs leaped[17]14.
评析:(7)对历史典故的翻译采取了直译典故和增译说明的策略,保留了项庄舞剑的典故,并改用刘邦的本名(更为人们所熟知)和增译项庄舞剑的目的(attempt on Liu Bang’s life)。译者选择保留这一典故,是由于直译典故已描述了整个故事情节,只需增译目的,就能让目标读者理解典故的含义。这样一来,不仅表达了源叙事的含义,也维持了源叙事在叙事技巧上的对等,并为阅读增加了挑战性、文化趣味。(8)是何志武一篇作文的全文,此处用直译法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句子实际上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去体会说话人的性格特质。简单直白的三句话,表现了何志武耿直、坦率、敢作敢为的性格,为何志武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后文的发展铺下了根基。(9)的原文采用了两个4字分句,而译文则采用了两个5句分字(增译了逻辑连接词when,and),在意思和字面格式、语言风格上都与源叙事达到了对等,堪称翻译中的理想状态,即同时达到意义的准确和形态的神似[18]。
小结: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根据需要选择性地采用源叙事:选择忠实原文大意,则使用意译法,忽视字面上的对等;选择忠实原文在字面上的对等,则选择直译,舍弃意义上的流畅表达;选择“为读者翻译”的流畅阅读,则删减源文本陌生的文化内涵;选择突出原文的文化底蕴,则保留关键术语、增译文化典故。这些策略可以同时应用,但必须保证译文在整体语言风格、叙事技巧上的一致。葛在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可读性的基础上,采用直译或直译加增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源叙事的叙事技巧。基于这个原则,对源叙事的改变和弱化有时在所难免。
4结语
葛译竭力做到了叙事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对等:在宏观层面的叙事层次上,通过时态、标点符号、斜体等手段,梳理了叙事层次,促进了小说在主题、情感、观点上的表达。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技巧、叙事风格上,通过直译或直译和增译的方式保留源文本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力求达到对等,并且为目标读者创造了更具挑战性、超越性的阅读体验。为了译文的流畅和整体的一致性,译者选择直接意译或省译隐晦复杂的文化典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原叙事,但不影响整体的翻译,从而创造出让目标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文,获得了较好的读者效应。
[参考文献]
[1] 申丹. 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J].外国文学研究,2005(4):110-113,175.
[2] 韩辉. 叙事学视域内的《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阐释[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7-91.
[3] 黄海军,高路. 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视角——以林语堂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4):90-94.
[4] 张景华. 叙事学对小说翻译批评的适用性及其拓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57-62.
[5] 苏艳飞.叙事学视角下的翻译——以《喜福会》中译本为例[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4):44-46,67.
[6] 郑敏宇.小说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视角[J].外语研究,2001(3):65-68,72.
[7] 黄希云.小说的叙述层次及其涵义功能[J].文艺理论研究,1992(1):16-23.
[8] 蒙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 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 Baker, 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M]. London:Routledge, 2006.
[10] 文军.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6):78-80.
[11] 邵璐.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中国翻译, 2013(3):62-67.
[12] 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3):6-17.
[13] 张琦.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本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 2014.
[14] 尹婷. 莫言小说英译策略的叙事学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 2014.
[15]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 2010(6):10-16,92.
[16] 莫言.变[M]. 北京: 海豚出版社,2010.
[17] Mo Y.Change [M]. Goldblatt H,Trans. Calcutta: Hyam Enterprises,2010.
[18] 许颖红.评Break,Break,Break两种译文的翻译风格[J].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1(5):47-49.
(责任编辑:骆磊)
A Narrative Account of Change——A case study of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change
ZHANG Xinyi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25, China)
Abstract:Changeis the newest work of Mo Ya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narrativity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tyle. According to narratologic theories, only when a translation version matches the original work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 can it fulfill its aesthetic value. Goldblatt applies explification to the narrative level by means of tense, punctuation and italics, and uses literal translation or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e to reproduce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strategy of the original text to some extent. His fluent and captivating translation promote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English version.
Key words:English version ofChange; Temporality; Relationality; Selectivity
收稿日期:2015-12-17;修回日期:2016-01-08
作者简介:章心怡(1989—),女,湖南浏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562(2016)02-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