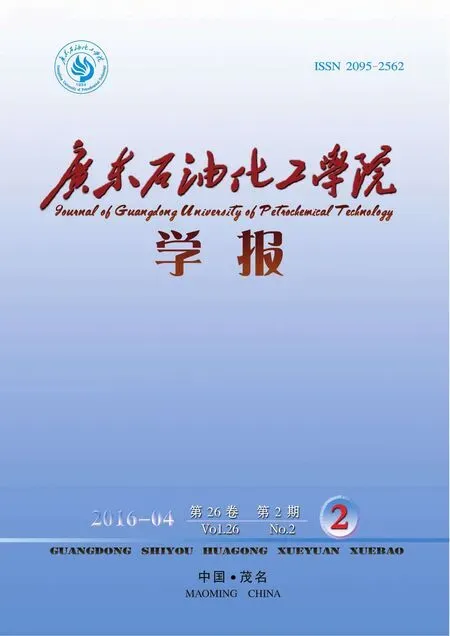拯救与献祭
——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再探
甘来冬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拯救与献祭
——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再探
甘来冬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悲剧,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悲剧的典范,从古至今,文学史上对它的解读不胜枚举,就其深层次的悲剧性而言,可以追究到人类的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个体既可以成为集体的救世主,拯救人类,也有可能成为集体的罪源,必须用个体来献祭方能保全集体。不管怎么说,人类的集体意识始终凌驾于个体之上,让个体生命的存在成为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因而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在于集体对个体的无情压迫。
关键词:俄狄浦斯王;悲剧性;拯救;献祭;个体;集体
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社会处在人类社会的童年阶段,其文艺也带有人类社会童年阶段的思想特点。诚然,在古希腊社会,尤其是在索福克勒斯生活的时代中,人类刚开始从思考自然转变到思索自身,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转向了道德哲学的研究,智者学派也高呼“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成为时代的命题,“我是谁”是那个时代哲学追问的根本问题。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索福克勒斯自然也不能摆脱时代烙印,他的《俄狄浦斯王》也正是对人自身思索的结果。古希腊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个体人对集体有着高度的依赖性,这就造成集体对个体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个体人就得承受着来自集体严重的压迫,更有甚者成为集体利益的牺牲品。例如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希腊人中流行的替罪羊风俗,“当城里受到瘟疫、饥荒或其它大规模灾害时,就选一个相貌丑陋或畸形的人,让他承担扰乱整个社会的一切邪恶。把他带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用火烧死,然后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1]。”个体随时都担心由于某种不确定因素而成为集体的替罪羊。
1五种典型的俄狄浦斯王悲剧性解释
长久以来,对《俄狄浦斯王》的接受和解释,使这部悲剧成为西方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围绕着这部作品的阐释,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范围,而成为西方人不断寻找和认识自我的文化探寻[2]。”其中有关《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性的认识,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这几种不同的说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人对《俄狄浦斯王》的阅读。
1)第一种观点是最为大家熟知的命运悲剧论。持该论点的人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之间的冲突是俄狄浦斯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俄狄浦斯王越是要规避不幸的神谕,越是一步步地实现神谕。因而张帆认为“‘命运悲剧’是指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同命运进行对抗,但结局往往是他(她)无法从命运的手掌中逃脱出来而不得不被命运毁灭[3]。”命运论者承认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是在神面前依然显得那么的无助,对自己的命运又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多数命运悲剧论者都强调悲剧带来的一种无奈和无助之感,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是无用功,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继而坠入了宿命论深渊。
2)第二种观点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在于他的过失,即过失论。这种解释肇始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人应该“不是十分善良,也不是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提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4]。”所以他认为悲剧人物遭受厄运是因为自己的某种过失。如19世纪的欧洲评论家,普遍认为俄狄浦斯的过失是因为他太自负、多疑,甚至是对神谕的怀疑,他太自负表现在他对祭司的无礼,对克瑞翁的暴躁,那就是他最大的过失[5]。事实上,这种过失,耿幼壮先生认为是“理智的错误”而不是“道德的错误”或“性格的缺陷”。就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来看,他认为俄狄浦斯之所以犯了杀父娶母的过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这个过失虽然可以原谅,但始终是一个污点。
3)第三类观点是仪式论。仪式论者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来源于杀王的仪式和替罪羊仪式。论者主要用费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人类学理论对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原因进行分析,如杨正喜教授就认为,“俄狄浦斯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是替罪羊仪式和弑君仪式的牺牲品[1]。”《俄狄浦斯王》不仅在原型上与替罪羊相似,即让牺牲者承担整个族群的罪过,惩处他而使族群得以洗脱罪名,也在形式上、含意上与弗雷泽《金枝》中的“弑君仪式”如出一辙。弗雷泽在《金枝》中介绍了意大利内米湖畔的一个习俗,通过新的奴隶杀死老王成为新王的行为,象征着整个族群的长治久安,繁衍不息。
4)第四类观点是弗洛伊德的情结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当时的—位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悲剧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在我们内心—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的[6]14。”至于那种能在观众心里引起震动,并且可以同俄狄浦斯一拍即合的东西就是一种共同的心理,即恋母情结。这种观点虽然有点主观色彩,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俄狄浦斯的悲剧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现代性解释。
5)第五类观点是反讽效果论。这类观点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效果是源于索福克勒斯反讽手法的运用。如安国梁教授认为“这种‘结构性反讽’渲染突出了《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性:敢于反抗命运、最终被命运打倒的过程是壮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勇迈的,造成的悲剧效果是强烈的……反讽在受众心中激起的怜悯和恐惧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7]。”同时,安国梁教授还对反讽效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俄狄浦斯王》的反讽模式至少有四大要件,分别是“狩猎者和被猎者同为一人;剧中隐在的‘发现’和‘突转’;集矛盾于一身并最终出现悲剧性转折的主人公必然是一个明眼的盲者,因而是一个善良而冥顽不化者;命运是这种反讽的最积极的因素, 是安排整个剧情秩序的看不见的手[7]。”正是这四点要素综合作用,才使得观众感受到了俄狄浦斯强烈的悲剧性。
2“失乐园”和“复乐园”两大范式
讨论拯救与献祭,首先要讨论两大文学范式,即“失乐园”和“复乐园”,“失乐园”在弥尔顿的文本里表现的是“人违反天神的命令,因而失去了乐园[8]2。”代表着人类从乐园里走出,遇到灾难(洪水)。《复乐园》讲述了耶稣为了拯救人类,经受住了撒旦的诱惑和试探最终完成了替人类救赎的大业[9]。“复乐园”代表人类为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的艰辛历程。在西方悲剧作品的大潮中,我们始终都能发现这样的一个范式,那就是对“失乐园”的悲鸣,以及对“复乐园”的希冀。在失乐园后,社会群体就会为复乐园展开努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秩序的混乱,理性的复乐园方式将被愤怒和蒙昧的方式取代,“社会群体将会自发随机地根据受害者的标记挑出替罪羊,并将危机和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的团体,来改变危机[10]29。”正是在“失乐园”和“复乐园”之间存在巨大的个体和集体相对立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生成的悲剧富有动人的魅力。“‘失乐园’与‘复乐园’的传说体现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结[11]。”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乐园”和“复乐园”的范式在后世文学中也经常出现,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马克·吐温的《天堂还是地狱》,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埃德加·爱伦·坡的《艾莱奥诺拉》等。
“失乐园”和“复乐园”之间存在着一种惩罚和崇拜的情结。人们会为了“失乐园”而找出罪魁祸首,并给以惩罚从而希望获得“复乐园”的机会,对于那种能为“复乐园”做出贡献的人,大家都起而膜拜,崇拜不已。长期以来人类都通过献祭的方式来祈求实现“复乐园”,巫师凭借能与神沟通的能力而获得极高的地位,并且凭借这种神化的地位把主观的群体意志客观化,通过惩罚带有污点的个体让集体获得拯救。与之相似的是那些在原始部落中流传的英雄叙事,主人公多是因保护族人或者是帮助族人实现了某种巨大成就的人物,这一类人成为了后人崇拜和效仿的对象。就像中国的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就是把那些为社会族群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英雄神化,之后辈辈祭奠,口口相传。相同的是,无论是群体的献祭行为还是英雄崇拜行为,都体现了群体意志。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悲剧中总离不开牺牲与献祭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悲剧艺术是人类原始信仰失落的产物,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由“失乐园”到“复乐园”所形成的悲剧模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演化和变异而已。在《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作品中,俄狄浦斯作为个体的代表,他可以帮助城邦“复乐园”,但是他也可能让城邦“失乐园”,最终在城邦的利害取舍中使个体陷入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狄浦斯王》所要讨论的问题,应该归于道德问题,即个体如何才能与集体和谐共存,个体如何能把握住集体的发展趋势,使自身避免在集体的大潮中成为被献祭的“替罪羊”。索福克勒斯用他擅长的戏剧,告诉人们,道德问题是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重大问题,《俄狄浦斯王》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3个体生存的焦虑——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再探
在《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作品中,俄狄浦斯身上所显示的悲剧性就是他作为个体的人既可以为城邦解除灾祸,也可以成为城邦灾祸的肇始者,他的过错不因为他曾为城邦解除灾祸而获得赦免,个体的人在集体面前一律平等,哪怕是国王也不能例外,这样就牵涉出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了,那就是人如何能同集体和谐共存,避免自身的悲剧。
在作品中,俄狄浦斯来到忒拜城,回答了斯芬克斯之谜,从而将忒拜城的臣民从惊恐中解救出来。斯芬克斯之谜说“一种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腿最多时最无能,谜底是人[12]114。”从斯芬克斯之谜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谜是对人类自身的追问,体现了人类哲学问题的一个转向。而俄狄浦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同时代的一般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对人类自身认识具有超前性的哲人可以帮助城邦摆脱灾难,恰巧俄狄浦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凭借超人的理性认识拯救城邦,他成了城邦里的英雄。那么英雄会不会在集体道德的规约上犯错呢?犯了错能不能躲避惩罚呢?索福克勒斯的回答是谁犯错谁就得接受惩罚,英雄也会犯错,犯了错也必须接受惩罚。
集体的利益是俄狄浦斯王探求自身悲剧的动因。俄狄浦斯成为城邦的君王多年后,他面临一个很糟糕的局面,那就是城邦里发生了瘟疫,“因为这城邦,像你亲眼看见的,正在血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来;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神降临到这城邦,使卡德摩斯的家园变为一片荒凉,幽暗的冥土里倒充满了悲叹和哭声[12]67。”城邦里的人再次将求助的眼神投向了俄狄浦斯,就像祭司说的“啊,最高贵的人,快拯救我们的城邦!保住你的名声!为了你先前的一片好心,这地方把你叫做救星;将来我们想起你的统治,别让我们留下这样的记忆:你先前把我们救了,后来又让我们跌倒。快拯救这城邦,使它稳定下来[12]68!”也就是这场瘟疫逐步推动俄狄浦斯不断去找方法拯救城邦,最终还原了他杀父娶母的事实。
神示表明个人行为与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那么克瑞翁带回来的神示是什么呢?克瑞翁说“那么我就把我听到的神示讲出来:福玻斯王分明是叫我们把藏在这里的污染消除出去,别让它留下来,害得我们无从得救[12]69。”这个神示即福玻斯王所指的污染就是那个犯了杀父娶母的道德大忌的人,这个人带来了城邦的灾难,只有把他清理出去才能让城邦得救。显然具有污点的个人会成为城邦灾难的祸源,只有清除了这个污点,城邦才会获得安宁,而那个犯了错误的个体就成了城邦集体利益的替罪羊,成为城邦利益的牺牲品。在《俄狄浦斯王》这里,神示就是一种集体意志,在这种集体意志里,包含着对个体的规约和惩戒。
个体在集体意志下卑微地生存着。无论俄狄浦斯王多么高贵与聪明,一旦他犯了杀父娶母的不伦之事后,他必定为整个城邦所不容,最终导致了他戳瞎双眼,自我放逐的悲剧结局。对整部剧的结构稍作梳理,即俄狄浦斯杀父(出于自卫)——回答斯芬克斯之谜后拯救了城邦——城邦再次蒙受灾难(源于他杀父娶母)——城邦再次获得拯救(通过俄狄浦斯自我流放而实现)。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再也不是那个躲不过去的神谕(杀父娶母)了,而是那无所不在的集体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他的荣辱并不是由他自己控制。索福克勒斯的另一部悲剧《安提戈涅》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安提戈涅作为一个妹妹,她有义务帮哥哥下葬,但是另一方面,以克瑞翁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又禁止她那样做,矛盾就此展开,最后安提戈涅违背国家意志,埋葬了波吕涅刻斯,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个体的意志受到集体意志无情的压迫,但是个体又显得无能为力,这或许才是索福克勒斯最终想要表达的内涵。
4结语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存在对乐园的迷恋,失乐园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必找出失乐园的原因来,多数情况下这种寻找都是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展开的,例如由于亚当夏娃的失信,人类被上帝从伊甸园中赶了出来,从此就开始承受苦难。另外,面对失去乐园的痛苦,人类还希望通过采取措施加以补救,使得再次复乐园,这种补救就是以牺牲犯错误的人作为悔过的表示,或者说是献祭,从而使更多的人复归乐土。正是在这一群体性的心理面前,俄狄浦斯作为个体的生命显得那么的无力,虽然他可以成为英雄,但是他也成为了被献祭的牺牲品,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体存在,显得那么缺乏安全感,此一恐惧可能是这部悲剧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杨正喜.命运·过失·情结·仪式——关于俄狄浦斯悲剧根源的争论[J].黑河学刊,2010(11):40-42.
[2] 耿幼壮.永远的神话——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批评阐释与接受[J].外国文学研究,2006(5):159-166.
[3] 张帆:命运的悲剧——以《俄狄浦斯王》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S1):292-294.
[4]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Dodds E R.论对《俄狄浦斯王》的误解[J].周嘉惠,译.文化艺术研究,2013(3):145-153.
[6] 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M].张唤民,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7] 安国梁.“不可能”的布局、结构性反讽及其他——《俄狄浦斯王》的艺术[J].郑州大学学报,2006,39(3):128-131.
[8] 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9] 弥尔顿.复乐园·斗士参孙[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0]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1] 司同.西方悲剧美学新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2):48-53.
[12] 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贺嫁姿)
To Rescue or Sacrifile——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Tragedy Oedipus the King
GAN Laid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colleg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OedipustheKingis a thought-provoking tragedy,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tragedy by Aristotle. From ancient times to now,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ofOedipustheKingin literary history, but in the deeper sense of tragedy,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l can either become a savior of a group, or become a source of sin to a group, and he or she must sacrific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group. Anyway,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s always superior to that of an individual, which makes individual life an uncertain one, so that the tragedy of Oedipus can be attributed to ruthless oppression from group to individual.
Key words:Oedipus; Tragic; Rescue; Sacrifice; Group; Individual
收稿日期:2016-03-20;修回日期:2016-04-13
作者简介:甘来冬(1989—),男,安徽霍邱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545.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562(2016)02-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