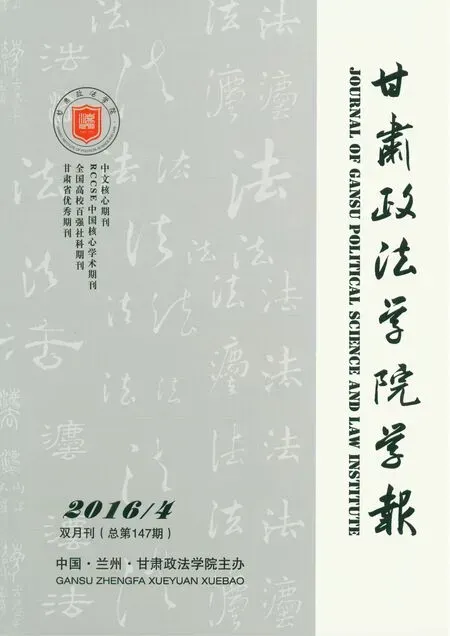欧洲人权法院Salduz案之评析与省思
刘国庆
欧洲人权法院Salduz案之评析与省思
刘国庆*
摘要:欧洲人权法院在2008年就Salduz案作出了具有标尺性的裁决,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赋予被追诉人接受初次讯问前的会见律师权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等。上述裁决促使欧盟制定通过系列相关指令以细化权利并增强其刚性,各成员国也纷纷以此为标准调试本国相关法律。Salduz案确立的原则有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提升其防御能力,实现平等武装。我国2012年刑诉修法提升了律师在侦讯阶段的参与能力,但与之相比仍略显不足,有必要省思完善。
关键词:自证己罪;在场权;法律协助;平等武装
欧洲人权法院于2008年就Salduz一案作出裁决,确立了系列重要的原则,对于各成员国产生重大影响,纷纷以此为标准调整本国相关法律规定。尽管距离此案已有几载,但此具有标尺性的案件至今尚未引起我国学界应有的关注,并展开系统的研究,不无遗憾。另一方面,我国侦讯程序中的律师协助制度与之尚存在一定的落差。有必要就此案进行一番研究,希望对我国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一、Salduz案及其拓展延伸
申诉人Salduz1984年出生在土耳其。2001年5月20日晚因为涉嫌支援库尔德工人党(PKK)违法抗议活动而被土耳其警察暂时逮捕。此外,申诉人也被指控2001年4月26日在土耳其某地一座桥上悬挂违法标语的横幅。申诉人被逮捕后,在无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警察对其进行了讯问。申诉人作出了自白,据此,2001年12月5日申诉人被定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又因为申诉人行为时为未成年人,因此减刑为2年6个月。申诉人对此不服,于2002年1月2日向土耳其最高法院提出法律审上诉,指出原判决有违《欧洲人权公约》(以下均简称“公约”)第5条及第6条,原审并没有进行公平审判的程序,且评价证据不当。2002年6月10日,土耳其最高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申诉人的上诉。2002年8月8日,申诉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指责土耳其违反公约第6条第1项及第3项第3款,主要理由在于接受讯问时,警方不让其接触律师。欧洲人权法院委员会首先就此进行了审查,发现此案并无侵犯申诉人所享有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主要原因在于申诉人在正式庭审与上诉审程序中均有律师协助,且其自白并非对其定罪唯一的根据,此外,法院还给予其质疑挑战检控方主张的机会。之后,欧洲人权法院第二庭在2006年3月28日以5比2票数认为申诉人在警察对其拘捕期间,阻止其与辩护律师联系以获得协助并无违反公约第6条第3项第3款之处。
申诉人不服此项裁判,2007年7月20日申请将全案移交至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经过审理,大法庭于2008年11月27日一致判定土耳其违反了公约第6条第3项第3款之规定。并指出公约第6条之规定尽管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的审判程序,但此举并非意味着公约第6条不适用于法院审判之前的侦查程序。公约第6条之规定,尤其是第3项,对于案件起诉之前的侦查程序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公约第6条第3项第3款所保障的权利属于公约第6条第1项公平审判程序重要的保障环节之一。任何被追诉人均享有辩护律师为其提供有效辩护的权利,必要时更应由国家依据职权指定律师,该项权利虽非绝对,却属于公平审判程序的基本要素之一。遗憾的是,公约第6条第3项第3款并没有就如何保障被追诉人行使此项权利作出详实的规定,而是由各成员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内自主选择保障的方法。不过,本院须审查各成员国所采取的方法是否符合公平审判程序的内在要求。公约无意保护徒具理论的权利,而要保障实实在在的权利。各成员国仅指定律师本身也不能确保为被追诉人提供协助的有效性。被追诉人在接受警察讯问之初的举动可能对其在后续刑诉程序的防御成效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上述原则符合国际法上普遍认同为公平审判概念核心的人权标准,存在有其必要性,旨在保护被追诉人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任何强制力的滥用,也有助于避免法院误判及实现公约第6条所追求的目的,尤其是实现追诉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的武器平等。侦查程序对于审判程序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此阶段获得的证据极有可能被法院作为对被追诉人定罪的依据。
大法庭接着指出在侦查程序中,被追诉人处于一种容易受到侵害的处境,而刑诉程序越来越繁琐,更加恶化其境遇。于是在大多数案件中唯有通过辩护律师的协助方能适当弥补,而此时辩护律师尤其需要注意被追诉人的反对强迫自证己罪特权是否得到公权力人员的尊重。被追诉人所享有此项特权的预设是控诉方须自己找寻能够证明支持其犯罪指控的证据,而不得采取强迫或欺骗等有违被追诉人意志的方式。当本院在审查某一程序是否侵犯了上述特权的核心内涵时,尤为注意程序保障措施的践行情况,被追诉人是否获得律师的协助是重要的环节。在此脉络下,本院认为欧洲预防酷刑委员会曾提出一些预防防范酷刑的建议,其中一点是被拘捕者接受法律协助的权利是防范酷刑行为的基本保护措施。倘若想对被追诉人的获得辩护律师协助权施加一定的限制,就必须通过法律清晰明确地规定,且还要严格限定限制的时间。这些要求在重大犯罪中意义尤为重大,被追诉人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刑事惩罚,民主社会必须采取上述措施保障被追诉人所享有的公平审判权。为此,为了使公约第6条第1项所赋予被追诉人的公平审判权切实得到保障与兑现,通常自其接受警察的初次讯问之时就应该允许被追诉人获得律师的协助,除非能够证明在考量个案全部特殊情况后,认为个案中存在令人信服的正当化事由,才可对此项权利进行适当必要的限制。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可基于此等事由,当然无论基于何种事由,均不得侵害被追诉人根据公约第6条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倘若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过程中没有获得律师的协助,而对其有罪判决正是基于在此过程中被追诉人作出的自白,通常会对其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并拒绝如下的主张,即在讯问之后向其提供辩护律师或随后程序的对抗属性可以有效弥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Dimitrios Giannoulopoulos, Strasbourg Jurisprudence, Law Reform and Comparative Law: A Tale of the Right to Custodial Legal Assistance in Five Countries, 1Human Rights Law review,p3(2016).
在2009年的Dayanan v.Turkey*ECtHR, Dayanan v. Turkey(2009),7377/03.一案中,人权法院又将此项权利进行了拓展延伸:指出一旦被追诉人受到羁押便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不限正在接受讯问前抑或讯问过程中,整个讯问程序中均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不限于获得其法律建议的权利,而且还涵盖与法律协助相关的全面服务。在2010年的Brusco v.France*ECtHR, Brusco v France,Application No 1466/07,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14 October2010.一案中,人权法院针对讯问程序中辩护律师的在场问题所引发的质疑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自被追诉人被拘押之日起便享有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整个讯问程序亦同。截至2013年3月,人权法院已有超过125个判决确认了Salduz一案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该原则主要为如下几点:其一,被追诉人在接受初次讯问前有权会见律师;其二,讯问时律师有在场权;其三,当被追诉人的上述权利受到侵犯时,自白应予以排除;其四,被追诉人有放弃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
二、Salduz案之影响评析
此案对欧洲各成员国的辩护制度产生不小的影响:一方面欧盟据此制定系列指令就Salduz案所确立的原则予以细化并增强其刚性。另一方面公约各成员国也纷纷调整自己的相关立法以符合人权法院对此方面的要求,推动了各成员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整体变革,详情如下:
首先,促使欧盟制定了系列指令。*在较长时间内欧盟(European Union)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其一个主要职能在于就欧盟范围内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制定标准。然而近些年欧盟在此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受到Salduz一案的影响,欧盟针对侦讯程序中被追诉人所享有的获得律师协助权问题制定并通过了若干指令,以强化并有效保护其权利。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欧洲人权法院在确保其各成员国执行其相关裁决决定的效果方面较欧盟稍逊一筹。此外,通过欧盟进行补充性的立法也被视为确有必要以确保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法所确立的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标准能够为各成员国有效贯彻执行。详情可参阅Anna Ogorodova & Taru Spronken,Legal Advice in Police Custody:From Europe to a Local Police Station, Erasmus Law Review,p192-193(2014).欧盟制定了系列相关指令以细化并强化被追诉人的上述权利:
其一,及时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根据欧盟制定的指令,被追诉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后应立即向其提供律师协助。该指令清晰无误地向外界表明被追诉人从开始被警方拘押之时便应享有此项权利。无论如何,各成员国均应在任何讯问开始之前使得被追诉人有可能私下与其律师会见接触。此外,还要求各成员国应积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被追诉人能够现实而有效地行使其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在被追诉人尚未与律师会见协商之前,警察无权启动讯问程序,除非被追诉人在讯问前已有效地放弃了此项权利。按照欧盟制定的指令,唯一具有正当事由可以减损被追诉人此项权利是在那些具有迫切地需要讯问被追诉人的情形中,比如为了阻止迫在眉睫的将对他人生命造成的危险或损坏证据的情形。
其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根据公约第6条规定,在整个刑诉程序中,被追诉人均享有亲自或通过他自己选择的律师来进行辩护的权利,倘若无力支付相关的费用,则为公平利益所需时,可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可见,被追诉人享有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然而上述规定并没有明晰如下问题,即被追诉人对于国家免费提供的律师是否如同自己出资聘请的一样享有平等的选择权。对此问题,人权法院视不同情况而分别处置,具体如下:1.就国家免费提供的律师而言,在2003年的Lagerblom v. Sweden*ECtHR,Lagerblom v.Sweden,No.26891/95,54(2003).Station, 7Erasmus Law Review,p193-195(2014).一案中,人权法院指出被追诉人对于由国家免费提供的辩护律师选择权并非具有绝对性,当局在向被追诉人指定某一特定辩护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时须考虑其主观愿望,此点十分重要,有助于强化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此举关涉到协助被追诉人的合法性问题。但当个案中存有充分与实质性的事由认为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利益也可以对被追诉人此种形式的律师选择权进行适当限制。2.就被追诉人自己支付费用聘请的律师而言,人权法院要求当局应更为严格地尊重其律师选择权,相对于国家免费提供的而言。然而,在2013年的Dvorski v.Croatia*ECtHR,Dvorski v.Croatia, No.25703/11,94(2013).一案中,人权法院指出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中,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权利也可以限制,比如为了司法正义或个案中存在正当且重大的阻碍事由,但对于何谓极其例外的情形在上述判例中人权法院没有详细论及。
其三,弃权的权利。按照欧盟所制定的指令,当局须以一种简单且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被追诉人清晰充分地告知获得法律协助的内容以及弃权的后果。此外,当局还必须确保弃权者的此举乃自愿的与明确无误的。有学者认为告知放弃获得法律协助权利的后果还应该包括告知涉嫌的罪名,这是尤其必要的,通过此举才能方便被追诉人作出是否要求获得法律协助,因为涉嫌犯罪的严重性是影响被追诉人决定是否要求获得法律协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Anna Ogorodova & Taru Spronken, Legal Advice in Police Custody: From Europe to a Local Police.根据欧盟制定的指令规定,被追诉人的弃权行为必须予以记载。此外,倘若侦讯人员试图阻碍被追诉人行使此项权利,则不应视为自愿的意思表示,比如提供不准确的资讯,无论主观上故意与否,或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误导被追诉人。倘若被追诉人为易受伤群体,其弃权行为需要更为严格的条件,比如在2008年Panovits v.Turkey*ECtHR, Panovits v.Turkey,No.4268/04,68(2008).一案中,人权法院指出倘若被追诉人为易受伤群体,当局应采取所有合理的方式手段确保其完全知悉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并尽可能地领会弃权的后果。
其四,侦讯时在场权。欧盟制定的指令还规定在由警察主导的整个侦讯程序中,辩护律师有在场权。此外,还进一步指出辩护律师应能够有效地参与侦讯程序,此等参与应遵循各成员国刑事程序法。各成员国的相关程序法不得损害被追诉人此项权利的有效行使,辩护律师有权提出问题,要求就某些问题予以澄清说明以及作出陈述。有学者指出根据人权法院的观点,考虑到讯问程序中获得辩护律师协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被追诉人的沉默权,那么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便是律师必须能够参与其中防止讯问过程中警方以违法方式侵犯上述权利。此外,在讯问程序中,律师应该能够向被追诉人提供私密性的建议,这是辩护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功能所在,并随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设法阻止讯问的启动或继续。除此之外,为了能与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另一个合理事由相契合,即实现双方的平等武装,辩护律师应该能够指出具体个案中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因素之所在,提供道德支持并确保侦讯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是准确无误的。*Anna Ogorodova & Taru Spronken, Legal Advice in Police Custody: From Europe to a Local Police.
其次,促使各成员国辩护制度的变革。Salduz一案对各成员国均产生不小的轰动,纷纷以此为契机强化提升此阶段法律协助的水准,推动本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变革。在此仅以法国的被追诉人初次讯问前与律师的会见权为例说明。在Salduz案之前的较长时间内,法国拒绝赋予被追诉人在拘押期间,接受讯问之前,享有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受到Salduz案的影响,法国宪法委员会于2010年7月指出在目前的警察拘留制度中,被追诉人没有被告知享有沉默权,在接受警察讯问时也无律师在场,该制度有违《欧洲人权法院》第6条之规定,并因此构成违宪。目前鉴于越来越多的被追诉人被羁押在警察拘留所(在10年中,人数已经翻了1倍),羁押已经被视为常规而非例外。被追诉人的羁押环境恶劣,并受到侮辱性的待遇(据报道,对被追诉人进行裸体检查是常规做法,即使是在轻微案件中)。最后该委员会裁决被追诉人在警察讯问之前以及讯问过程中应当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建议,并应当由警察向其告知享有沉默权。*[英]杰奎琳·霍奇森:《法国刑事司法的新发展》,载[英]杰奎琳·霍奇森:《法国刑事司法—侦查与起诉的比较研究》,张小玲、汪海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法国于2011年4月11日通过法律初次明确赋予被追诉人在接受警方讯问前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此项修法赋权行为,法国政府最初半推半就,热情不大,而法国的法院对于吸收Salduz案的做法热情似火。法国立法机构最后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确立了被追诉人的此项权利。
人权法院通过Salduz案在对初次侦讯中的被追诉人进行一些有益赋权的同时,还就限权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具有积极意义,详情如下:
首先,赋予律师在场权。侦讯一般在事先经过设计密闭且外界隔离的环境下进行,希望通过此举诱发被追诉人内在的压力及焦虑,打击其自信,强化侦讯人员的心理优势,最终达到突破被追诉人心理防线抗拒之目的,该过程涉及的不仅是法律规范,更是一种高度张力下的心理对抗及互动过程。整个侦讯空间变得极具压迫性,对于被追诉人而言,无论是对其心理上亦或精神上均是一种莫大的折磨与摧残,“审讯的场是一个压力的场,而且迫使真犯供认的审讯的压力同样会使无辜的人作出自白……审讯的场蕴含着把被追诉人吸引到有罪方向的强大的力量。置身于此的被追诉人在内心所感受的辛酸,我们作为第三者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即使见证审讯的审讯员,也不能充分地了解眼前的被追诉人的痛苦。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严厉追究被追诉人。”*[日]浜田寿美男:《自白的心理学》,片成男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为了克服上述弊端,人权法院通过Salduz案明确赋予律师在场权,具有积极价值,主要为如下几点:其一,见证过程功能。律师的在场可以借此了解对方的事实调查方向以及计划策略,弥补与对方的资讯差距。其二,促进程序司法性功能。律师的在场可以敦促侦讯人员恪守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其三,缓和功能。一方面,辩护律师侦讯时在场可以降低被追诉人的恐惧并提供法律上的协助。另一方面,通过律师的协调可以了解侦讯机关的意图,化解双方因为针锋相对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并借此消除对被追诉人的偏见。其四,还原真相功能。律师的在场还有助于促进彼此的沟通,实现侦讯的目的,还原真相,此即所谓“拼图理论。”*傅美惠:《侦查法学》,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91页。毕竟侦讯人员乃人而非神,难免会百密一疏,而律师的在场可以起到一种查漏补缺的效果。其五,人权保障功能。侦讯阶段最容易发生侵犯被追诉人人权情况,律师在场可有效地保障其权利,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警察讯问时有律师在场作为一种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措施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律师辩护增长了虐待的可能性。*[英]科纳·弗利:《对抗酷刑:法官及检察官手册》,梁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律师的在场可以成为自白任意性与否的证明者。
其次,赋予初次讯问前的会见权。人权法院通过Salduz一案赋予被追诉人接受初次讯问前与辩护律师会见权,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被追诉人突然陷入困境,惊慌失措,事先会见律师获得其法律协助才会在随后的讯问中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决定自己的反应模式,避免陷于不利境地而作具有自我归罪性的陈述,此举也有助于维护其程序性主体地位。德国赫尔曼教授曾就此指出:“对犯罪被追诉人的第一次讯问,必须被视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阶段。不论刑事侦查人员是否依法要求犯罪被追诉人如实回答讯问,第一次讯问对犯罪被追诉人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帮助和建议,犯罪被追诉人面对的将是刑事侦查机关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刑事侦查人员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任何问题;也可以毫无顾忌地适用任何技术和手段,直到犯罪被追诉人就范,作出自我归罪的供述。一旦犯罪被追诉人的口供被取得,生米便已煮成熟饭,这个刑事案件就已经基本定型。当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被追诉人完毕以后,辩护律师能够为犯罪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了。即使犯罪被追诉人在随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接受辩护律师的建议,拒绝再次供述,进行第一次讯问的刑事侦查机关取得的口供或者讯问录音,也可能被用作定案的证据。”*[德]约阿西姆·赫尔曼著,颜九红译:《关于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报告》,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
最后,赋予私密性会见交流权。辩护律师对被追诉人的法律协助不仅是一种形式,更应具有实质性,辩护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获取的案件资讯量,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律师对案情的获知程度取决于二者信息交流的畅通性,倘若被追诉人担忧被公权力人员偷听,那么将有所顾忌,面对律师要么缄默不语,要么避重就轻,使得辩护律师难以获知有效的资讯,将严重影响辩护的质量,危及案件真相的发现,也不利于维系二者之间的信赖度,久而久之也不利于律师业的良性发展。美国学者波斯纳曾指出“偷听不是一种有效率的发现事实的方法。如果人们了解有被偷听的危险,那么,他们的谈话就会改动,就会减少谈话对第三方的信息内容,而社会就会为此支付某些代价。”*[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王兆鹏教授曾就此指出“赋予被告律师权的目的,乃因为被告不解法律,对于诉讼程序陌生,所以由专业之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协助被告面对结果严重、过程慑人之诉讼程序。因此,律师协助权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被告得与辩护人完全充分及自由的沟通,被告得毫无恐惧、毫无疑虑地向辩护人吐实,不用担心今日所述成明日的不利证据。若被告恐惧其与辩护人间的沟通可能遭人窃听、可能成为证据,即不敢与辩护人充分沟通,此种恐惧越强,被告之律师权即越为虚无。被告得与律师完全充分及自由的沟通,应是律师权的核心价值。”*王兆鹏:《辩护权与诘问权》,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95-96页。可见,受到Salduz影响,欧盟通过制定法令赋予被追诉人此项权利,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彻底消除被追诉人的后顾之忧,使其能毫无任何顾忌地与律师交流,提升辩护的水准,维护其合法权利。
此外,就限权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在Salduz一案中,人权法院还就限制被追诉人侦讯程序中获得律师协助权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之前,比如在1994年的Imbrioscia v. Switzerland一案中*ECtHR,Imbrioscia v. Switzerland,17E.H.R.R.441,455-456(1994).,人权法院虽然认可申诉人审前享有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但认为此项权利并非一项绝对性权利,可以基于正当理由予以限制。在具体个案中,权利限制采取二元式的检验衡量基准:第一步检验施加限制是否具备正当事由。第二步,倘若具有,那么根据整个诉讼程序,此举不可以剥夺被追诉人所享有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使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此项检验基准存在一定的弊端,限制此项权利设置的门槛过低而足以对被追诉人的权利造成过度恣意侵害。有鉴于此,人权法院大法庭在Salduz一案中推翻了上述决定,而改采新的更为严格的检验基准以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此项标准内容如下: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对此项权利的限制标准从原来的正当事由(good cause)转为令人信服的事由(compelling reasons)。另一方面,即便个案中存在令人信服的事由,也并非意味着被追诉人的此项权利理应受到限制。倘若施加限制,也可能对其享有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造成侵害。至于何种情形,人权法院并没有指出,但倘若警察在对被追诉人进行讯问时没有让其获得律师的协助,在此情形下将获得的自白作为指控证据使用的话必然有违公约第6条之规定,由此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此举表明人权法院十分重视被追诉人侦讯程序中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此举也标志着人权法院对此问题的见解较之前发生重大的转变,对于限制被追诉人此项权利限制的条件较以往趋于更加严格,体现出人权法院希望通过此举切实保障被追诉人此项权利的良苦用心,即保障是原则,限制是例外。
德国Satzger教授主张侦查程序应是参与式的刑事程序,也就是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参与权,特别是讯问时的参与权,比如在场权。侦查程序的重要性已非当年立法者所认为的侦查程序只是为主审程序做准备而已。如今,审判程序的成败常常在侦查程序时就已经决定了。侦查程序已成为审判程序成败的转辙器的说法,早已是老掉牙的普遍看法,因而在侦查程序收集证据阶段,必须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参与权。曾指出侦查阶段强化被告及辩护人之参与权,是法治国之诫命,并非国家对被告之善行。*何赖杰:《侦查程序强制辩护之指定及违法效果》,载《政大法学评论》2009年10月第111期。笔者认同上述观点,鉴于侦查程序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此阶段极其容易发生侵犯人权情形,作为跨国性人权守卫者的人权法院通过Salduz一案明确赋予了被追诉人在讯问程序中获得辩护律师协助的权利,意义重大,此举有助于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尤其是保障其反对强迫自证己罪特权,有助于实现平等武装,提升被追诉人的防御能力。
三、对Salduz案之省思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曾指出整个刑事诉讼不断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辩护权不断拓展的历史。笔者深以为然,鉴于讯问程序在刑诉程序中的重要性,辩护权应贯穿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人权法院在Salduz中所确立的原则已有力地证明此点。而反观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个人认为尽管通过2012年刑诉修法我国在此方面已取得一些进步,比如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的地位得到确认,法律协助的范围有所拓展,延伸至侦查阶段等,但仍有些规定不无商榷之处,有些仍处于缺位状态,与域外仍存在一定的落差。此外,个人认为侦讯阶段辩护制度的完善在我国的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及迫切性,主要为如下几点:其一,正在进行冤假错案的治理,造成冤狱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其中侦讯阶段辩护律师参与受限是重要的因素。其二,审判中心主义是我国未来刑诉制度改革的趋向与重心所在,实现审判中心主义要做的功课很多,其中重要的便是强化并提升被追诉方在侦讯阶段的防御能力。其三,尊重与保障人权已写进刑诉法。我国侦讯程序中的辩护制度需要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检讨完善,详情如下:
首先,初次讯问前的会见交流权。我国1996年刑诉法第96条规定被追诉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才可以聘请律师。一个“后”字之差对于被追诉人权益的影响极大,司法实践中初次侦讯非常关键,也最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现象。为此,我国2012年刑诉修法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被追诉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追诉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被追诉人或者对被追诉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被追诉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看似赋予被追诉人在接受初次侦讯前会见律师接受其帮助的权利。其实不然,该项规定不无商榷之处,其中颇值得质疑之处为“自……之日起”的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不够明晰,容易引发歧义,可以作如下两种诠释解读:其一,“警察第一次讯问开始之时起”,被追诉人就有权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倘若想让辩护律师权成为防止侦讯人员采取暴虐不法讯问手段的有效屏障,就应作出此等理解,当然,这也是域外法治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做法。其二,“在警察第一次讯问之日但不必在第一次讯问之前”,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从法理上讲,应作第一种解释,但此等语义上的含糊不清就给公权力曲意释法提供了可能,即“公、检、法利用其解释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话语权’,故意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曲解刑事诉讼法条文的内涵,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辩方的解释,以扩张自己的权力而压缩辩护权行使的空间、抑制辩护权的行使。”*万毅:《“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刑事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域外有学者就此指出如果作第二种理解将拔去2012年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利齿,因为警察可以一直讯问被追诉人,而不受任何辩护律师的干预。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指出倘若要使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增设的禁止自我归罪的特权真正得到保障,就必须明令警察自其第一次讯问开始之时就应允许被追诉人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德]约阿西姆·赫尔曼著,颜九红译:《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带来多少变革》,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笔者认为对于此项问题的完善措施是解决立法规定含糊不清的弊病,明确规定被追诉人在被侦讯人员初次讯问前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并为其会见交流创设条件,当然作为配套条件要健全我国权利告知制度以及制定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对于侦讯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应进行程序性制裁,获得的自白应无证据能力。
其次,私密性会见交流权。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由于此项法条规定的含糊不清,比如何谓“根据案件情况”,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侦查机关均派员到场,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甚至在不告知律师的情况下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秘密监控。*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此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权,不利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与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之规定相悖,与域外法治国或地区的经验做法格格不入。为此,我国在2012年刑诉修法中进行了修正,比如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此举解决上述不足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但随之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针对何谓“监听”,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司法实务界坚持应从狭义上理解和解释“不被监听”,即认为立法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设备等进行监听”,其言外之意是应当允许“侦查人员在场。”而理论界则趋向于从广义上理解“不被监听”,即主张“不被监听”是指“律师与当事人谈话保密”,不被监听的精神在于维护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谈话的秘密性。参见万毅:《“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刑事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分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2条已对此作出明确回应:“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通过此举可以解决由公安机关负责侦办案件中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私密性会见交流权的保障问题。但公安部的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而对于由检察院负责侦办的案件面临类似问题将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没有提及。为了解决此等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等五部门于2015年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7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此举对于有效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私密性会见交流权,改善其执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遗憾之处,没有就公权力违反上述规定应承担何种后果作出明晰的规定,需要予以完善以增强上述规定的刚性。
最后,律师在场权。鉴于律师在场权具有多元价值,而且亦是域外诸多法治国或地区的普遍做法,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实有必要在侦讯程序中赋予律师此项权利。但法律移植需要虑及到我国的实际国情*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其一,尚未形成诉讼化的审前程序。其二,刑事辩护率低。其三,侦查对于口供仍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这些因素掣肘律师在场权的设立与运行。参见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2页。,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构应基于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理性思维而采取一种渐进式的路径,在目前可以将律师在场仅限于被追诉人为未成年人以及最高刑期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人,待时机成熟之际再推而广之。此外,个人认为律师的在场应保障其实质性参与,而非消极无为的看客,可赋予其提出意见的权利等。同时相关的配套制度也应及时跟进,比如健全的权利告知制度与值班律师制度,此外还应对于侦讯人员侵犯律师在场权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可考虑将由此获取的自白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指控的证据使用。
结语
人权法院通过Salduz案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积极推动了成员国辩护制度的变革,具有积极意义。而反思我国与之仍有一定差距,仍需继续改进以提升刑诉制度保障人权的水准与品质。法律规定不可含糊其辞、模凌两可,刑诉法关系民众重大福祉,需要尽量清晰明了,否则就会使公权力滥权有机可乘,从而导致民众基本权利的丧失。我国刑诉立法及司法实践已反复证明这一点。小处不可马虎,细节决定全局,我国刑诉法既需要宏观蓝图的设计,更需要具体细节的精心周密建构,只有通过点滴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整体的质变。
*作者简介:刘国庆,法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