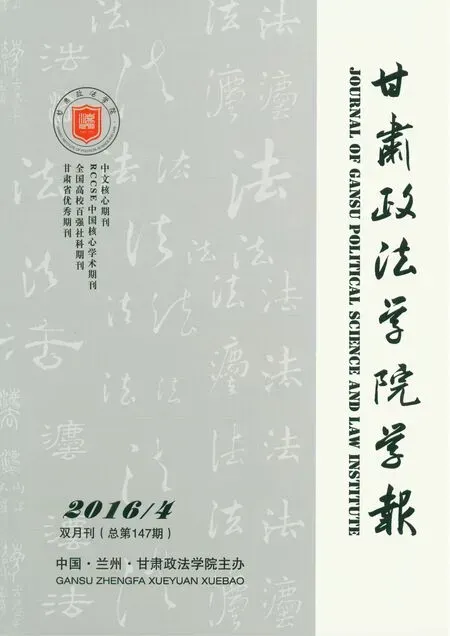强奸罪争议问题研究
——以英美普通法对强奸罪的改革为借鉴视角
赵桂玉
强奸罪争议问题研究
——以英美普通法对强奸罪的改革为借鉴视角
赵桂玉*
摘要:强奸罪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古老的犯罪,也是美国普通法中的一项重罪。就强奸罪而言,这是一项容易提出指控,但又难以提供有力证据的罪名,因此,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强奸罪都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甚至就同一起涉嫌强奸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指控强奸,而另一方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合意的性行为。英美普通法中的强奸罪理论的变革为争议的判断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评判标准,也为我国强奸罪理论研究和司法认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关键词:强奸罪;女权主义;男性受害人;刑法修正案(九);合理反抗
在英语中,“rape”(强奸)一词源自拉丁文“rapere”,意为“to take by force”,即“暴力获取”,*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 seventh edition ), Wadsworth Cengage Learing, 2010年版,第260页。这也预示着强奸行为的暴力性特征。十八世纪,英国普通法权威学者William Blackstone在其所著的《英国法释义》里把普通法中的强奸罪定义为“对妇女实施暴力和违背其意志的性交”(the carnal knowledge of a woman forcibly and against her will)。*刘士心:《美国刑法各论原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由“woman”和“her”两词可见,普通法中强奸罪受害人的女性特征。最初,普通法中的强奸行为在内容上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阴茎-阴道性交,并不包含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但是,在现实当中,性行为的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性交”的自然意义,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普通法对强奸罪的认定,从原则到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在行为的“罪”与“非罪”之间尽可能接近案件事实和裁判正义。
一、强奸的本质与强奸罪被害人主体的中性化趋势
在多数国家,强奸都是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罪。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即便没有接受过法学教育的普通人也不难理解强奸的涵义,而且法律文本对强奸罪的规定也较为明晰。正是这貌似简单的罪名,却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争议不断。强奸罪的法律制度源于古代男性的财产概念,*Joshua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third edition),Newark: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1年版,第573页。因此,强奸罪经历了从财产犯罪到人身犯罪的性质转变。最初的法律排斥妇女的独立人格,无论是父亲的女儿还是丈夫的妻子,女人都被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Catherine and Frances Quinn:《Criminal Law》 (third edition),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年版,第121页。这也意味着,从一开始男性便被排除在强奸罪的被害人主体之外。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男女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妇女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其独立的人格权得到法律的确证,在现代刑法中,强奸罪一致被认定为侵犯人身权利的重罪,其本质是对他人“性自决权”*所谓“性自决权”,即被害人自己决定与谁、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参见Joshua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fifth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9年版,第582页。的侵害。因此,强奸罪的核心问题不是性行为,强奸罪侵害的也不仅仅是被害人的身体,身体只是强奸行为达到侵害受害人“性自决权”的媒介,所有性行为都伴随着对当事人身体的“侵犯”,不同的是,强奸行为缺少被害人的“承诺”。
基于古代的财产观念,男性被认为是对女性这一“财产”的合法拥有者,亦或无耻偷盗者、掠夺者。当时社会中,性曾经被视为权利支配能力*有研究显示:强奸犯经常认为强奸带来的快感源于其刺激性与冒险性的结合,并不是因为纯粹的性因素或支配欲。但是,强奸确实侵害了男人对特定女性(妻子)的专属的性的支配权。的象征,因此,对男人来说,追求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无论主动出击还是被动接受,男人对性是求之不得的,起码不厌恶。特别是在父系社会,男人性交有整个社会赞同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他做的是整个社会赞美的事,而女人对他的接纳则代表了整个社会秩序,尤其是其他男人接纳他的象征。*[美]雪儿·海蒂:《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林瑞庭、谭智华译,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在社会中和法律上,女人才是值得保护的“利益”,恰恰强奸罪是对这种“利益”的一种保护规则,而男人则是这种“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对这一“利益”的拥有者。正如杰出女权主义法学家尼古拉·拉茜在她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主体》中所说的,法律完全是以男性主义为准则的。这是将男性的利益伪装成全人类的利益。任何法律改革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英]乔安娜·伯克:《性暴力史》,马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页。说到底,正是男人制定的“规则”将男性的“性自决权”拒之“规则”的保护之外。
在《法律史解释》中,庞德说道,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p.1: quoted from Cardozo, “The Growth of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4年版,第2页。即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的博弈促进了“法的成长”。
美国对普通法强奸罪的改革,源自20世纪60年代《模范刑法典》制定以后,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性价值观念的转变,加之女权主义运动的展开,美国经历了强奸罪改革运动,各州纷纷通过立法来改革强奸罪的相应规则,对强奸罪实体法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性交”范围的扩大;第二,犯罪性别属性的中立;第三,行为手段的多样化;第四,“婚内强奸”的承认。*同前引〔2〕,第91-93页。由此可见,改革突出了男女平等的保护意识,加强了对性无意识者(例如,未成年人,成年植物人或精神障碍者)的保护力度。除此以外,在诉讼程序中强化了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其改革意识和内容对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重新定义了犯罪,将(强奸)实施者和受害者的性别规定都修改为了中性的词语。*同前引〔3〕,第570页。本文认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重新定义了犯罪,将(强奸)实施者和受害者的性别规定都修改为了中性的词语,或多或少与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联,即同性恋人之间的专属性权利因同性恋合法化而取得刑法的保护。国外一些女权主义者也认为强奸法应该无性别之分。*国外女权主义者认为强奸法应该无性别之分,主要目的在于斩断“女性受害人本身也有过失”的暗讽。牢记“受害者促发”这一观点今天仍旧存在(而且不仅仅存在男人的思想中)很重要。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CM于2005年10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认为,举止轻浮的女人要为自己被强奸负部分责任或全部责任;有四分之一的女性认为,穿着性感的女人也要为自己被强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参见 [英]乔安娜·伯克:《性暴力史》,马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1-422页。我国刑法也已经开始了对“涉性行为”受害者中性化的立法尝试,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做出的修改,即将刑法第237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修改后本条的最大亮点就是“男性”成为了强制猥亵行为的“合法的”受害人之一。刑法学界和社会民众对此修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本文乐观地认为,这是我国刑法为强奸罪被害人主体中性化改革所做的一次预热和铺垫。
二、“性交”涵义的扩大与强奸罪及其他涉性犯罪的关系
一般来说,强奸行为往往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性侵害举动,例如,强行亲吻被害人、抚摸被害人的胸部、下体等等。本部分将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特殊的性行为与强奸罪的关系,例如,强制他人进行手淫、口交、肛交等行为是否属于强奸罪中的“性交”。二是强奸罪和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强制猥亵、侮辱他人罪等的关系或区别。
(一)“性交”涵义的扩大
传统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强奸,其涵义为违背妇女的意志而强行与之进行阴道性交。但是,性行为的形式绝对不仅仅是阴道性交一种,还包括手淫、口交、肛交等形式。我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将性的意义概括为七种:第一,为了繁衍后代;第二,为了表达感情;第三,为了肉体快乐;第四,为了延年益寿;第五,为了维持生计;第六,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第七,为了表达权利关系。*李银河:《李银河自选集——性、爱情、婚姻及其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我们不难发现,与阴道性交相比,其他形式的性行为除了不具备繁衍后代的意义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差异。在世界人口过剩(少数国家和地区人口仍然保持负增长)的时代,一味强调性的繁衍功能,势必大大限缩性的其他意义。而且强奸犯的犯罪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繁衍后代,无非为了满足肉体上的欢乐、精神上的刺激亦或寻求某种支配感。
在美国,《模范刑法典》将“性交”宽泛地定义为包括手淫、口淫和男性对女性的肛交。*Model Penal Code §213.0(2).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等的刑法规定中,“性交”的范围已经涵盖了以阴茎插入肛门、口腔或者以手指、舌头甚至物体插入肛门或者阴道等非常态性行为。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将强奸的形式局限于狭义的阴道性交,即强奸的形式应该包括违背他人意志的阴道性交、手淫、口交、肛交等等。否则,难免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形,例如,A采取暴力手段,强迫B与其进行(阴道)性交,构成强奸罪,在没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下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同样,A采取暴力手段,强迫B与其进行肛交,按照现行刑法可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他人罪,在没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下适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同样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暴力性侵行为,由于定性不同,适用的法定刑差别较大。另外,扩大并统一强奸罪中的“性交”范围,有利于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对卖淫嫖娼行为的明确认定,对维护我国法秩序的统一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英美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刑法典中规定了“鸡奸罪”,依据刑法典,我国并没有相关规定,本文也认为没有必要将“鸡奸罪”引入。在我国,两种鸡奸行为符合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他人罪的构成要件:一是鸡奸幼童;二是强迫鸡奸他人。如前文所述,如果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受害人范畴,并且扩大强奸行为中“性交”的范围,符合“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对刑法体系的完善大有裨益。
(二)强奸罪与其他涉性犯罪
1.强奸罪与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相比,我国刑法第358条的规定表述为“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由此可见,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的受害人包括男性,该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照现行刑法规定,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也是一般主体,但是女性不能单独成为该罪的正犯,妇女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77页。
在组织卖淫罪中,组织者和被组织者是自愿的合作关系,因此不存在违背“卖淫者”性的自主权的情形。问题是,在强迫卖淫罪中,以暴力、胁迫、虐待、其他手段等强迫他人卖淫的方式,被强迫的“卖淫者”对“性”的自主权的丧失等,与强奸罪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在司法实务中,如果组织者为了强迫被组织者卖淫而对其强奸,则按照强迫卖淫罪从重处罚,即强奸罪被强迫卖淫罪所吸收,强奸只是达到犯罪目的的手段,从量刑程度来看,这种吸收是恰当的。疑难在于,此时嫖客的加入,在不同情况下该如何定性?我们先看一则案例:
张某、李某共同经营一休闲场所,两人强迫新来的服务员小王卖淫,但小王不肯。一日,嫖客周某到该场所嫖娼,张某收取了周某的嫖资200元后,让小王接客。在包厢中,小王向周某言明自己不卖淫,是被老板强迫的,拒绝与周某发生性行为。周某即离开包间找张某和李某,说小姐不同意,要求退回嫖资。张、李二人闻听大怒,遂对小王拳打脚踢,并将其衣服扒掉,然后出来对周某说“已经同意了”。周某便进入包厢对小王说“这不能怪我哦”,遂与小王发生了性行为。事后,小王向公安机关报案。*马克昌:《百罪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页。
依照刑法第358条之规定,毫无疑问,上述案例中的张、李二人构成强迫卖淫罪,但是,对周某如何定性则意见难达统一。本文认为,对周某不能简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周某明知张、李二人对小王的强迫,因此可能构成强迫卖淫罪的共犯;另外,周某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明知性行为违背小王的意志。如果周某的强奸罪成立,那么张、李二人是不是共犯?如果构成共同犯罪,能否为之前的强迫卖淫罪所吸收?在司法实务中,强迫卖淫中的嫖客对强迫的明知或者不知,是否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诸如此类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2.强奸罪与强制猥亵他人、侮辱妇女罪。猥亵,意为:①淫秽;下流②做下流的动作;*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28页。侮辱,意为:欺侮,羞辱。*同前引〔17〕,第1498页。很难从语义上对猥亵、侮辱给予明确的界分,虽然强奸语义明确,但跟猥亵、侮辱仍有一定程度上的交集。从立法层面考虑,猥亵、侮辱他人排除了性交(广义上包括手淫、口交、肛交)等行为,但也属于对他人的性侵,只是与强奸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虽然强奸在语义上涵义明确,但是在犯罪形态上,包括预备、中止、未遂、既遂等。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定性犯罪分子的行为属于猥亵他人还是强奸的某种形态呢?此时,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恐怕难以奏效。例如,A于僻静的小路将B拦截,一言不发便上前强行摸其胸部和下体,并试图扒其衣服,到此A的行为被碰巧路过的C制止。对此,A否认自己有强奸的意图,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想摸摸对方占点便宜。如果依照强奸罪来定性,那么对A的量刑幅度在三到十年之间,如果依照强制猥亵他人罪来定性,那么量刑幅度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同样的行为,由于定性不同,则量刑幅度差别巨大。因此,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必然要求对犯罪行为的定性要准确。但是,除非强奸达到既遂才确定无疑,否则没有任何一种(或多种)方法能够准确区分猥亵和强奸(未遂、中止),因此,客观归责较之主观方面更接近事实真相。例如,在客观行为发生时,更多地关注对被害人暴力侵害的程度、犯罪环境、场所、行为人自身的生理状况(例如性无能)、有无前科劣迹等。
三、“婚内免责规则”与“婚内强奸”的确立
1736年,Matthew Hale 先生认为,“丈夫自己对他的合法妻子实施的性行为不能认定为强奸罪。”*1 Hale at *629.就这样,婚姻免责规则堂而皇之成为了普通法的一部分,被美国多州的立法机关采纳。Matthew Hale先生并没有为自己的言论拿出有力的支持,普通法中的婚姻免责条款则给出了明确解释,妻子是丈夫的确实的财产,*American Law Institute , Comment to §213.1.at 343.和钱物一样,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丈夫对妻子的性的权利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将女人视为财产的观念在历史上中外各国默契地达成了一致。
“婚内免责”这一缺乏法理依据的规则1991年在英国退出了司法舞台。在美国,不同的州对待该规则的态度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根据一个最近的调查,*Anderson , Marital Immunity, Intimate Relationship, Note 121, supra, at 1468-1473, 1486-1489(and citations therein).2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已经废除了所有性犯罪规则。在剩下的州中,一些司法辖区已经废除了特定暴力强奸犯罪的婚内免责规则,而保留了其他性犯罪的免责性……但是,通常当存在婚内免责规则时,如果双方从法律上被愤慨激发或者在发生强奸的时候处于分居状态,那么这个规则并不适用,*同前引〔3〕,第590页。即成立婚内强奸罪。
对是否成立“婚内强奸”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就该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种学说,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其一,“婚内强奸”否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婚姻是夫妻间的一种“契约”,概括地包含了同居义务(相互扶助的义务、满足对方“性需求”的义务等),因此,“婚内强奸”属于夫妻间民事范畴内的权利纠纷,称之为“婚内强行性行为”更为恰当,对于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而不宜认定为“强奸罪”。*朱丽芳:《婚内强行性行为之法律评述》,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第二,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在婚姻家庭领域,我国传统文化中更加注重“人伦关系”、“家庭秩序”,乃至将这种人伦秩序上升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主张“婚内强奸”是对西方“个体万岁”个人主义人权观的简单移植,而刑法的介入更多的是对被告人作出惩罚性的裁决,不利于对夫妻关系的改善和家庭内部的和谐,因此,在处理“婚内强奸行为”问题时,可以在法律中引入“调解”理念,包括第三人(亲戚朋友、单位领导、人民调解组织)参与下的“自愿调解”和法院介入下的“法院调解”。*周华山:《“婚内强奸法”的本土化研究》,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
其二,“婚内强奸”完全肯定说及特殊状态下的肯定说。完全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强奸罪的实施者为一般主体,行为人只要满足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即可,与性别、身份等无关,婚姻家庭法所确立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则不得因婚姻的缔结而被他人侵犯,因此,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而强行侵犯其性权利的,构成强奸罪。*欧阳涛主编:《当代中外性犯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特殊状态下的肯定说认为,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例如,夫妻因感情不合而分居期间或者离婚诉讼至法院离婚判决生效期间),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参见白俊峰案:载《刑事审判案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1页;王卫明案,载《刑事审判案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64页。
其三,折中改革说。之所以称之为“折中改革说”,是因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在当前强奸罪立法现状下,没有成立婚内强奸罪的余地;另一方面,“婚内强奸”的行为应该入罪化,但是应该通过立法来完善。陈兴良教授以解释学的视角否定了“婚内强奸”成立的可能性。从“奸”字的涉性涵义来讲,特指不正当的性行为,即颇具贬义的婚外性行为,因此,“婚内无奸”。*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宪权教授,他认为,第一,婚内不存在“奸”的问题;第二,“婚内强奸”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第三,离婚判决未生效则婚姻关系未接触,即不承认婚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在此期间,“婚内强奸”没有成立的余地。在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及刑法条文未作修改之前,不宜将“婚内强奸”的行为视为犯罪。参见刘宪权:《婚内定“强奸”不妥》,载《法学》2000年第3期。但是,婚内强奸犯罪化之不能的主张者完全可以同时是婚内强奸应犯罪化的主张者,对于特殊状态下“婚内强奸”肯定说所确立的规则陈兴良教授也表示赞同。*陈兴良:《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一种法解释学的分析》,载《法学》2006年第2期。
“婚姻免责”规则的支持者主张,强奸行为的危害性之一是给受害人带来的性的羞耻感,而婚姻的缔结则揭去了遮盖这种性的羞耻感的面纱,并且婚姻隐含了对性行为概括地默许,对此,本文并不赞同。虽然我国《婚姻法》第3条也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专属同居义务,夫妻之间有向对方要求性的权利,但是,该权利的行使不能依靠强权和暴力。
本文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婚姻关系处于什么状态(并不限于准离婚状态),婚内强奸都有成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理由如下:
首先,婚姻家庭往往因性爱而组建,没有爱的性违背了婚姻的初衷。*缔结婚姻关系的双方,未必都是因性或者为了组建生活共同体。有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不得已的手段,例如,为了获得某地的永久居留权、为了收养子女等等,此类婚姻往往徒具婚姻的形式。既然是强奸行为,那么无论婚内还是婚外,对受害者意志的侵害都确定无疑,“损害安全的一切行为应作为犯罪处罚。”*边沁说:“法律的所有功能都可以归入这四项或四项之一,即提供生计,求其丰足,鼓励平等和维持安全。”在法律调整的这四个目标里面,安全是主要的和最高的一个。安全的要求是:个人的人身、他的名誉、他的财产和他的身份受到法律保障,而且损害安全的一切行为应作为犯罪处罚。参见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学》,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因此,在婚内(哪怕是婚姻的正常存续期间),丈夫行为的强奸性质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婚姻不应成为犯罪行为的保护伞,但此时有必要坚持刑法的谦抑精神、公权力慎入,即不适用公诉原则,但是,受害人有权决定是否向司法机关追究强奸者的刑事责任。从实然角度看,依照现行《刑法》,强奸罪属于重罪,若将其作为亲告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故不宜成为亲告罪;从应然角度看,若祛除男权主义贞操观在强奸罪中的中心化地位,则强奸罪有可能成为亲告罪。我国目前不宜将强奸罪由非亲告罪改为亲告罪,但对“婚内强奸”可例外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方式。*张蓉:《对强奸罪应否作为亲告罪的思考》,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即把告诉的权利交给被害人一方。
其次,现行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妻子真包含于妇女之中(尽管同性婚姻中的“妻子”角色未必是女性),因此,“婚内强奸”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果将条文中的“妇女”限缩解释为“除了妻子以外的妇女”,则未必符合立法的初衷。
再次,依照“婚内免责规则”的原始论调“财产观”,妻子是丈夫的财产,未婚女儿是父亲的财产。无论父亲还是丈夫,都有处分“财产”的权利,如果丈夫强奸妻子不构成犯罪,那么父亲强奸女儿也只能接受道德和伦理的谴责了。现实生活中,父亲强奸女儿的案件时有发生,父亲仍然被指控犯有强奸罪,对此“财产观”却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最后,反对“婚内强奸”的观点认为,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框架下,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缺一不可,丈夫没有强奸妻子的主观故意。对此,本文认为,之所以认为丈夫没有强奸妻子的故意,原因在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命题:丈夫不能对妻子实施强奸。所以,丈夫在强迫妻子的时候其主观上也不认为这样的暴力行为是欠妥的。实质来讲,丈夫的暴力性行为客观上已经反应了其主观方面的故意——明知性行为缺乏妻子的同意。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并未缺失。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无论是婚姻非正常存续状态下的强奸,还是由于强奸而使婚姻陷入非正常存续状态,强奸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身心损害都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没有必要将成立婚内强奸的时间点限于婚姻状态非正常存续期间,无论何时、何地、婚姻关系处于什么状态(并不限于准离婚状态),婚内强奸都有成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彰显法治的进步。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丈夫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必然成立强奸罪。*同前引〔15〕,第777页。
四、被欺骗的性行为与“严格责任”
在美国,被害人在被欺骗下做出的承诺是否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基本达成了共识——“事实欺骗”不阻却强奸罪的成立;“诱因欺骗”阻却强奸罪的成立。
所谓事实欺骗,也称性质欺骗,是指在行为人的欺骗下被害人对自己承诺的性质没有明确认识,即不知道自己的承诺内容指向性行为。例如,男医生D通过“事实上的欺诈”,让女病人V同意在其被麻醉时放入阴道“治疗器具”,如果D所使用的“治疗器具”是他的阴茎的话,那他就犯有强奸罪。*See Pomeroy v. State, 94 Ind. 96(1883).因为V承诺的是一个治疗行为,而不是性行为。诱因欺骗下,被害人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承诺针对性行为本身。例如,宗教头目诱骗信徒,称只要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就能提高修行、祛病消灾,信徒深信不疑,于是和其发生了性关系。我们再看另一案例,A以恋爱之名欺骗B说,“我喜欢你好久了,渴望和你步入婚姻的殿堂”(事实上A是有妇之夫),B则信以为真,于是二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B才得知事实真相。对此,该宗教头目和A都不构成强奸罪(前提是案例中的受害人非14周岁以下的幼童)。问题在于,该欺骗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本文认为,诸如此类的诱因欺骗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公、私财物,受害人有所失、罪犯有所得,事实上,我们难以对“性”或者“性的自主权”做出属于“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解释。但是,在我国,无论事实欺骗还是诱因欺骗,如果涉及14周岁以下的幼童被害人则另当别论,“严格责任”不排除得到“承诺”的性行为仍构成犯罪——法定的强奸罪。
法定的强奸罪大概源自古老英国的重罪法规:禁止男性和10岁以下的“幼女”性交,*Thomas J.Gardner, Terry M. Anderson:《Criminal Law》( ten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2009年版,第295页。不论幼女对性行为是否有承诺。我国刑法也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依照强奸罪给予从重处罚。问题在于,强奸幼女罪中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严格责任”下刑法是否有必要设置这样的入罪障碍?本文认为,除非性侵幼女的行为人本身未成年,否则无需考虑其他被告人是否明知或应知被害人的幼女身份。行为人知或不知,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不会因此而增减,更何况行为人主观上的知与不知在司法实务中难以准确认定,*关于如何认定奸淫幼女行为中被告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幼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2013年10月23日 法发[2013]12号)认为:(19)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严格责任”的效力势必大打折扣。
五、遭遇强奸:反抗还是沉默?
强奸罪的本质在于性行为缺乏被害人的承诺。没有承诺,原本属于被害人的主观心态,必须将其外化为一种明显的意思符号——肢体反抗。被害人通过肢体反抗,向强奸行为人和法庭明确了性行为是违背其意志的。但是,当面对暴力强奸的时候,被害人应该沉默顺从还是积极反抗,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反抗,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第二种观点认为,反抗是必须的,而且要全力以赴;*普通法在暴力强奸案例中确实发展形成了对反抗的要求,因为反抗是对性行为拒绝的最好证明。但是,反抗的要求遭到了一些法院和许多学者的批判。第三种观点认为面对暴力性侵被害人应该做出“合理反抗”。*在美国,少数成文法或普通法解释中对司法权的规定已经取消了这个要求。虽然许多州看起来保留了反抗的要求,但趋势是减少这个规则的重要性或者完全废除它。如今,各州几乎没有要求女性“尽最大可能地”进行身体反抗,而只是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反抗是合理的。本文认为,面对暴力性侵,沉默未必是好的选项。理由如下:
第一,反抗的确可能给被害人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但这种伤害不是必然的,相反,不反抗的被害人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事实上,在面临危险时,抵抗是最有效的策略,能大大降低实际被强奸的几率。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内对22000名女性进行的一项“受害性”调查发现当潜在受害者尖叫、逃跑或试图规劝攻击者时,有五分之四的强奸企图会以未遂告终。与此相反的是,不试图抵抗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二最终遭到强奸。其他研究发现,利用一种以上自卫形式(尖叫、反抗)是减少被强奸危险的最有效方式。他们还发现“警察经常鼓励的策略(即哭泣和祈求)很少奏效”。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莎拉·乌尔曼(Sarah Ullman)和雷蒙德·奈特(Raymond Knight)调查了274名强奸受害者,发现有85%女性在面对性侵犯者的暴力时进行了身体上的抵抗。剩下15%在面对口头侵犯时进行了身体上的抵抗。那些进行了身体上抵抗的女性比起没有进行这种抵抗的女性更有可能避免被强奸。另外,“(进行身体抵抗的)女性受到身体伤害的可能性不会比那些选择其他抵抗方式或选择不抵抗的女性更大”。……和以前的研究一样,他们发现祈求和哭泣可能实际上增加了强奸行为完全得逞的可能性,因为它助长了强奸犯自觉强大无比且大权在握的心理。以上参见前引〔8〕,第440-441页。如果因为担心可能的进一步伤害而选择沉默,那么,第一,很不幸,强奸很可能达到既遂(除非行为人有生理或身体上的缺陷);第二,“正当防卫”的规定便失去了意义——对犯罪分子实施“正当防卫”当然可能导致防卫人遭受进一步的伤害。一方面,当公权力缺位的时候,刑法鼓励个人对正在实施的不法行为实施“正当防卫”;另一方面,社会中有些言论又鼓励被害人放弃抵抗,向犯罪分子妥协,这实在是一种不可取的懦弱者的选项。
第二,和反抗可能导致的伤害相比,强奸导致的伤痛可能永远挥之不去。正如《法医学与毒素学》中所描述的:那个男人(强奸犯)和整个强奸场景通过受害者的胡话再次从她紊乱的大脑里掠过。因为名声受辱和贞操不保带来的绝望可能使得受害者最终患上忧郁症,并由此产生强烈的自杀倾向。在有些案例中,强奸对受害者整个身体系统的打击足以永远摧毁她的健康,迅速导致她的早衰与早死。歇斯底里症、舞蹈症甚至癫痫都是强奸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精神紊乱后果。一次暴力侵犯企图经常成为致命的一击。*转引自前引〔8〕,第443页。从量刑方面来看,强奸罪的基本量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轻伤)的的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量刑范围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同样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量刑是一致的,既然如此,能否得出“被害人付出重伤以下的代价阻却他人的强奸行为是值得的”结论呢?对此本文持肯定态度。除非被害人遇到了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如果不幸遇到,即便被害人不对强奸行为进行反抗,往往也难逃被强奸灭口的命运。从一声轻微的“不要”,到歇斯底里的呼喊,甚至拼死的对抗,结果还能坏到哪去呢?反抗的确是一种阻却暴力强奸行为的有效手段。特别在遭遇熟人强奸时,积极的反抗尤为必要。当然,积极的反抗包括口头上的言语反抗和肢体的反抗,需要注意的是,口头抗议经历了“no”means“yes”*在传统社会的性行为规范中,男性居于主动、支配地位,女性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女性在性行为中总应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抗,才合乎社会规范。现代社会的女性也可能为了表示淑女、因为害羞或者为了促使同伴更具主动性而做出某种“象征性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说“不”也可能是表示“是”,即所谓“no”means“yes”。参见刘士心:《美国刑法各论原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到“no”means“no”标准的转变;肢体反抗经历了程度上的“极力反抗”到“合理反抗”或“真挚反抗”的转变,这些转变表明,随着社会发展,法律更加尊重强奸罪被害人的性自决权。
结语
在多数国家,强奸罪都是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罪。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当今英美等发达国家,所有向警察报案的强奸案件中,最终仅有5%*数据来源:前引〔8〕,第405页。的被告被判有罪,另外,不排除相当数量的强奸受害人选择默默承受而没有报案,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强奸罪是一项原告非常容易指控、但却难以提出有效证据的罪名,被告的抗辩往往也难以自证清白。即便一方能够证明性行为的确存在,或者暴力行为在原告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强奸的本质在于对受害人“意志”的侵害,不是“性”,也不是“暴力”。可以说,证明存在强奸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难问题,特别是与其他性侵犯罪相关联的强奸未遂、中止等情形,对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尤为重要,特别当涉及幼女被害人的时候,一方面,刑法在“严格责任”下对幼女进行绝对的保护,另一方面,刑法还要考虑被告人主观方面的认知程度。本文认为,除非性侵幼女的行为人本身未成年,否则无需考虑其他被告人是否明知或应知被害人的幼女身份。
强奸属于涉性犯罪,而性行为的形式并不限于传统强奸罪所指的(阴茎-阴道)性交,有必要对“性交”进行扩大化解释为包括口交、肛交、手淫等在内的性形式。扩大并统一强奸罪中的“性交”范围,也有利于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对卖淫嫖娼行为的明确认定,对维护我国法秩序的统一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被害人面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性侵时,反抗都是其否定意志最直接、外在的体现,“不要”就是“不要”!从一声轻微的“不要”,到歇斯底里的呼喊,甚至拼死的对抗,尽管都可能证明不了强奸行为的存在,但是,实证表明,无论女人还是男人,反抗的确是阻却强奸(既遂)的有效手段。当然,对于潜在的被害人而言,预防犯罪远远比对罪犯的事后惩戒更有意义。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你们想预防犯罪吗?那你们就应该把法律制定的明确和通俗;就应该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就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就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那你们就应该让光明伴随着自由。知识传播得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奖励美德……完善教育。 ”参见[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32页。。这个题目太宽泛了,它超出了我所论述的范围。*[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当然,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要继续探索的就是,在行为的“罪”与“非罪”之间尽可能接近生活事实和裁判正义。
*作者简介:赵桂玉,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