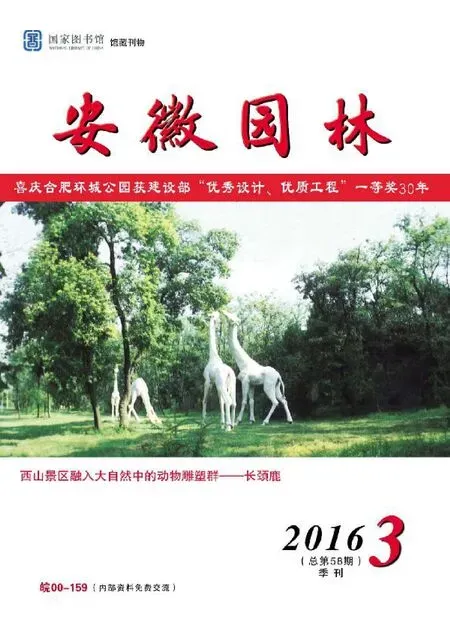美好的记忆永恒的怀念——贺安农大林学和园林学院80年诞辰
□尤传楷
美好的记忆永恒的怀念——贺安农大林学和园林学院80年诞辰
□尤传楷
我是文革前入学安农大林学系(林学和园林学院前身),也是学校办学以来唯一实行半农半读体制的一届。毕业后,一直在合肥这块土地上从事园林绿化工作,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试点城市、优秀旅游城市作出过自己应有的努力,并与母校始终保持着联系。我与母校的关系,半个世纪来,可以说水乳交融。林学当时是校内历史最悠久、师资和教学质量最好的王牌系之一。现在庆贺成立80周年,重温母校对我的培养与教育,心情特别激动,感恩之心由然而生。为感谢母校的恩情,现将我人生理想和绿色追求过程中撰写的有关论文和相关文章汇编成册,即《圆不完的绿色之梦——城乡园林一体化的探索》一书,作为学子向母校80年纪念活动的献礼。
一、难忘的专业启蒙教育
我进入安农,无疑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当时,在极左思潮背景下,要求试行半农半读教育,就是一半劳动、一半读书,而且当时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劳动。在那个大背景下,校系领导能够从实际出发,明确劳动课主要集中高年级结合专业课时实施,正因如此,我们基础理论学习未受到太大影响,仅在入学教育时,在校内林场(当时校内农林场很大)参加苗圃整地和林地养护管理。适度的劳动对于我这位城市长大的学生,既补上了劳动课又从劳动中初步认识到林学的概念,并提前接触到专业课老师。尤其,在校近五年时间,从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就以半农半读的名誉为我们争取到伙食费的全额补贴,解决了我们在校学习期间的后顾之忧,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正因为实行半农半读体制,我人生栽下的第一株树苗就在校园内。1968年底,还随学校下迁滁县琅琊山林场,在那里多次上山植树造林,开始体验到绿化荒山的艰辛。我们这届专业课基本没有学,仅在1967年上半年复课闹革命时接触到一点,好在班级激进分子不多,老师均有请必到。尤其与我交往最多的江家荣同学,他来自桐城县农村,自小就接触到植物,且树木认识的比我多,故空闲时常相伴到花园、树木园,甚至公园认树。我们凡不认识的植物均采下枝叶或花果,登门请教老师。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老师特别热情,有问必答。这种对学问的猎奇心态,应追述到我的少儿时代,那时南京小学教师每周有两个下午政治学习,我除了与同学踢小皮球外,常喜欢三五成群结伴到城郊雨花台南边的花神庙看花,那里曾是南京的花卉生产基地,建有许多玻璃温室,早被那里的奇花异卉所吸引,无疑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潜移默的影响。
二、难忘的军垦生活
我们这届同学除少数留校外,大部分被分配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艰苦的军垦生活延续了我们的学生生涯。我们去的是省军区农场,排以上干部均由军人担任,在那里除了体验军队生活,就是干农活。每人平均2~3亩地从种到收,而且多是水田,需种双季稻,全人工操作,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尤其收割期,一旦挑起刚刚割下的稻把就得一口气送到二三里外的打稻场,而且多为田埂上坡小道。百来斤的担子中途绝对不能休息,否则稻把垛落地就会洒脱掉粮食,那个时代更是绝不允许的。因这不仅仅看作浪费,而且要上纲上线,从政治上检讨你对贫下中农的态度,成为阶级感情问题。当然,这样的艰苦劳动能磨练人,尤其劳动的第二年春,我还被抽调窖建班。那里,阳春二月就得采用最原始方式,赤脚赶老牛踩踏搅拌黄泥土,准备砖坯的原料。艰辛的农场生活还可以洗澡为例,那里一年四季只有寒冬腊月才烧一、二次热水,300天以上都得到农场旁的淠河干渠洗刷,下河游泳则成为有水性同学的生活必须内容。因此,学生时期的艰苦生活,对走入工作岗位后不怕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难忘的师生感情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兴起,打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全面停课闹革命。残酷的阶级斗争,引导学生批斗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严重地破坏了师生感情。而我由于自1960年,初中期间就随父母由南京迁到合肥,而且父亲又是学校职工,全家生活在校内家属区。正是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没有卷入造反组织。那时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三秋”下乡劳动和外出大串联,其余时间多待在家中,成为典型的逍遥派。由于派性不强,与班上各派代表人物均能交上朋友,这也使我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人进行交往,寻找共同的话题。在朋友间逐步养成不乱传话、不搬弄是非,友善真诚待人的品德。这一良好的性格,让我受益终生。如1967年夏,学校因武斗成为一派大本营,为了同学的衣物等用品不受损失,我利用家在校内的优势,腾出家中里屋专门堆放同学用品,确保了安全。1966年秋,时任系总支副书记蔡其武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返校参加运动,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深入到学生中了解运动情况,曾个别找过我,我也如实报告了各人的观点。谁知1967年初,所谓一月革命风暴,造反派夺权后为了整当权派,通过校工作队要我交待蔡其武书记找我的情况,并以不揭发不让我参加军训相威胁。由于我始终咬紧牙关什么也没说,没有给蔡书记带来麻烦,从此我们结下了终身友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安农大(原安徽农学院)总院经中央批准,将从宿县回迁合肥原址,但最初方案并不含滁县的林茶蚕三个系。正是蔡其武书记听说时任省委书记万里同志夫人边涛曾到过合肥市苗圃,旗帜鲜明地支持发展被四人帮批判为资本主义毒草的花卉盆景事业,当时我正是苗圃的技术骨干,于是找到我通过边涛同志走了捷径,为母校回迁尽到我的微薄之力。
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全国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在旧社会有点情况的老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走资派都被集中关押接受审查。我作为群众代表,曾被推荐担任群专队员,参加看管和组织他们学习,协助组织落实政策,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多。由于我在履行职责中,能文明执法、秉公办事、友善待人、不坑人不害人,并实事求是、尽力帮人,因此曾经的“专政对象”大多成了我终身的良师益友。如,经受过磨难的树木分类学著名教授李树春,1987年帮助我运用拉丁文,为我撰写的《中国花径》重点长条目“石榴”一文的数十个品种进行定名,确保了任务的园满完成。刘世琪教授是树木病虫害权威,对我工作中遇到难题也总是有求必应。其他老师更不用说,如李宏开、吴诗华、康忠明等教授更是鼎力支持,多次通过我帮助合肥市解决各种技术难题。
四、共谋城乡园林一体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赶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四化要求,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园林部门的领导班子,为我情系园林、圆好绿色梦提供了机遇与平台。在领导岗位上我一蹲就是二十多年,没有养成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这应受益于母校老师好作风对我的影响。工作中凡我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让别人代劳,甚至讲话稿或汇报材料也自己动手。世纪之交时又主动学会开车,为退休后提供了方便与增添了幸福感。现在我一个人把《安徽园林》杂志办起来,正是受益于这种良好习惯的结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校回迁合肥,凡需要穿针引线,或直接要我办的事,无论大小均尽力为之。其中,接触最多的是彭镇华与江泽慧夫妇,因为彭镇华老师最早从事核辐射育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选择菊花作核辐射试验研究,需要合肥市苗圃合作。后来合肥市开展大环境绿化,又通过我积极参与和支持,还曾一道赴江苏泰兴、扬州等地考察银杏经济林和农田水网。1994年又力促合肥市成为国家林业部最早的森林城试点城市和世纪之交时的全国绿委开展的城乡绿化一体化试点城市。为加快发展安徽花卉事业,在他们夫妇力促下,由省绿化委牵头成立了省花卉协会,江泽慧老师担任安徽省花协常务副会长。1992年他们夫妇与我所在的合肥市园林局联合组团,赴香港参加一年一度的花展,并进行了境外花卉市场调研。紧接着又在他们夫妇倡导下省首届花博会在马鞍市举办,接着又由江老师亲自率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三届花博会。1993年5月,我还随他们夫妇一同访问与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紧接着的几年又与彭镇华教授一同参加了澳洲的国际花展、赴欧洲园林花卉考察和出访东南亚。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他们夫妇承担的跨市域、省域的科研课题活动,例如:兴林灭蜾、长江中下游滩地综合治理,森林生态网络建设等项目。在那段时间内,我除尽力为母校服务,还在1989年夏秋,江老师父亲江上青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受委托准备了鲜花花蓝,通过他们在蚌埠火车站工作的侄儿带到苏北墓地。
目前,我虽退休多年,仍在母校的关怀下,通过社会组织为园林绿化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主编的《安徽园林》杂志早己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刊物。甚至,在纪念长征70周年之际,母校90高龄的老红军、党委老书记张劲武还专门为我重走长征路,所著的《追寻峥嵘岁月》一书作序,成为我终身难忘的纪念。前几年,林学与园林学院时任院长黄成林还聘请我为学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省政府文史馆聘请我为特约研究员,这些荣誉鼓舞着我在有生之年更好地服务于我所热爱与从事的风景园林事业,不断地园着美好的绿色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