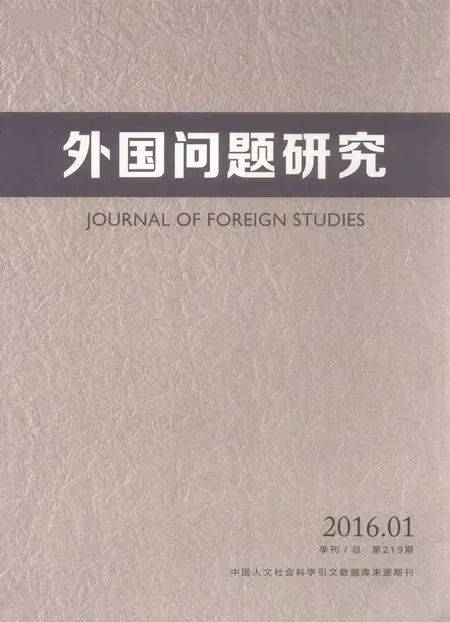从德川到维新初期的“攘夷论”之三重变奏
张 崑 将
(台湾师范大学 东亚学系,台湾 台北 106)
从德川到维新初期的“攘夷论”之三重变奏
张 崑 将
(台湾师范大学 东亚学系,台湾 台北 106)
[内容摘要]本文分三个阶段来阐释日本近世到近代的“攘夷论”之发展与变化,指出第一阶段的攘夷意识是在德川初中期阶段,此一阶段之“夷”是作为“在其自己”,相对的“华”乃指的是中华文化之“华”,特别是儒教文化之“华”,故一些德川知识分子极力洗刷这种“华彼夷我”的情节,这个阶段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华夷论战。第二阶段的攘夷论,是以“夷”作为“在其他者”,主要的“夷”是指“西洋”的侵扰,这个阶段的“他者之夷”在军事上构成威胁,文化思想上也牵动了武士思想的改变。在此阶段中,本文复区分“保守的”与“激进的”攘夷论两种类型,前者以后期水户学为主,“尊皇”与“攘夷”可以分别发论,后者攘夷论最后不得不与“尊皇”论联结合一,终结德川政权,故名“激进的攘夷论”。至于第三阶段的攘夷论,以西方为主的“文明论”取代了过去东方惯用的“攘夷论”,东西方文明之情势“逆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可为典型代表,在此本文也看到此波“文明论”与过去儒教的“华夷论”最大不同的两个转向,其一是以“智”取代“德”的伦理学转向,其二是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转向,儒教的“忠”、“孝”、“智”、“德”、“仁”等道德,在明治时代的文明论者与国体论者的脉络下,全都转向具有日本主体脉络意义的道德观念,成为以国体精神为中心的特有之“新文明论”。日本经过这一波转向的“新文明论”,不仅从中华文明脱逸而出,也超越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创出“东亚文明论”,而日本则自称是“东亚文明”的优等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依据,支配了明治以后至战前的意识型态。
[关键词]攘夷论、福泽渝吉、文明论、德川时代、明治时代
一、前言
古代中国对“夷”的定义,是指四方远国非华夏民族之称,如《春秋榖梁传·序》言“四夷交侵”,“四夷”即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在此“夷”的用法偏向种族而说。但种族的夷狄论,必涉及文化差异,“夷狄”与“华夏”所带有的文化价值差异,始自中国古代周人的文化天下观,周人“尚文”,以华美文化自居,又自创“华夏”一词,其“天下”观念即是由文化较高的华夏诸邦和落后的蛮夷所组成。*有关周人的文化天下观之研究,详参邢义田:《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3—41页,特别是第20—26页。因此,“攘夷”一词,即是由自认文化较高的族群对文化较低的族群所做的意识型态之排斥甚至采取军事行动,故本文所谓的“攘夷论”主要涵摄政治与文化意识两层面。就文化意识而言,“攘夷论”系预设“华夷对立”的文化相对意识,弱势文化遭受强势文化的“华彼夷我”的氛围下,希望扭转这种“华彼夷我”的局势,采取保护主义色彩,试图提高自己文化的优越意识。就政治军事而言,“攘夷论”往往预设“他我对立”的防卫意识,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以激化自我的独立意识。
本文用“攘夷”一词,企图解释日本从德川初中期、末期到明治维新三个阶段的“攘夷论”之不同性质,因此“攘夷”一词不过是论述理论策略上的一种概念上的运用,虽有转化传统“攘夷”只是作为“排斥夷狄”的意思,但其实根据“夷”这个对象内涵的不同,“攘”字意涵也有诠释的不同空间。“夷”若作为“自己”,则“攘”字可作为“使自我去除夷者之身份”之意,德川初中期的华夷论多以此类为主,强调自己亦是有礼乐文化的民族;其次,“夷”字的对象作为“他者”,又可区分针对“西洋”与“中国”,若“夷”指的是西洋,“攘”字有“使敌人退让、退却”之意,幕末阶段的勤皇志士则属此类;至于“夷”字若指涉的是“中国”,特别是儒教文明无法敌挡西洋文明,于是以西方进化论为主的“文明论”取代了过去的攘夷论,中国文明不再成为学习的对象,“东亚文明”概念被创造而出,最终日本文明足以取代中国文明成为东亚文明中心,甲午战争的转折是个关键,“华彼夷我”正式逆转为“华我夷彼”,并且在文化学习上,由本向东洋文明学习,如今“逆转”为向西洋文明学习。以上三个“攘夷”阶段都牵涉到与中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彼此国力的消长关系。本文在分析各阶段的攘夷论之际,无法一一列举,仅能选出几个代表性思想家的言论,因其有代表性,实则也可反应该时代的思想风潮。
本文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概念史研究,借着“攘”字概念,企图透视从德川到幕末、明治维新的知识分子对“攘夷”看法的变化。有关攘夷论之历史研究并不多见,多散见于个别思想家的研究中,就中藤田雄二所著《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國の比較研究》以及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可为代表,两者皆以东亚的宏观比较视野考察近代东亚的华夷衰长关系,前者集中讨论中日韩的攘夷论与守旧论之研究,*藤田雄二:《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國の比較研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1年。后者扣紧东亚架构的“华夷秩序”之政治与经济实力,在中日之间逐渐解体的过程。*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6期转载。唯本文采取跨越历史的纵深视野,企图理出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攘夷论”之变化关系,又不得不探讨明治时代的“文明论”之转折变化,呈现日本从近世到近代有关“攘夷论”到“文明论”的连续性关系。
二、“夷者之在其自己”:德川初中期的“攘夷”论争
近代以前儒教挟其文化、思想的强势,吸引诸多日本菁英,如出佛入儒的藤原惺窝(1561—1619)与林罗山(1583—1657),惺窝甚至在兵乱之际,于1596年亲自乘明船欲至中国,想一圆亲访圣人国度之梦,惜因遇暴风而吹回日本。*藤原惺窝有诗作描述此次登明船而未果的遗憾,诗云:“东方君子长诸侯,地隔中原天一陬。平日弦歌思鲁国,满城第宅置扬州。土峰云散兰全璧,武野波连奡荡舟。渔火远流萤稍去,客杯满引蛾空浮。”藤原為経編:《惺窩先生文集》第6巻,第96頁。与惺窝有笔谈深交的朝鲜儒者姜沆(1567—1618)在《看羊录》中如是描述惺窝对儒教文化的认同:“惜乎吾不能生大唐,又恨不得生朝鲜。”*姜沆:《看羊録——朝鮮儒者の日本抑留記》,東京:平凡社,1984年,第168頁。姜沆乃因壬辰乱事而成为日本俘虏的朝鲜儒者,被掳时间是1597年9月,1600年5月被释回。姜沆将其被日本拘留期间的所见所闻,撰成《看羊录》,收入在其《睡隐集》中。足见惺窝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即便不能生于中国,也愿生在邻近中国圣人故乡的朝鲜。
惺窝的例子可以反应出德川初期的日本文化氛围,儒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此后有林罗山(1583—1657)撰有《孔子浮海》,言东方有君子国,故孔子欲居之九夷,乃东方之“君子国”日本。*林罗山:“闻孔子曰:‘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按范史云:‘东方有君子之国’,三善相公以为日本国是也。仲尼浮海居夷,焉不可知其来于本邦哉?以世考之,则丁于懿德帝之驭寓也。所谓君子者,指懿德欤。我朝儒者之所宜称者也。乡曹盍言之。”林羅山:《孔子浮海》,《林羅山文集》第36巻,京都:京都史蹟会編纂,1979年,第408—409頁。
阳明学者中江藤树(1608—1648)亦奉儒教《孝经》为“上帝神明”之经典,崇拜不已;复有古义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尊《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古文辞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提倡“先王之道”,亦以中国《六经》先王圣典为圭臬。以上诸家都是江户儒学开宗立范的儒者,相当影响德川初中期的儒学氛围,但也因其带有浓厚的“中华主义”之色彩,遂有“华彼夷我”之讥,引起具有强烈日本文化主体性者的质疑与批判,如荻生徂徕曾说《日本书纪》称尧舜之国为“西土”,并非日本正史,被暗斋学派的人批评说:“天照大神敕曰:‘丰苇中国,吾子孙可王之国也。’非有我之得私也,盖有深意也。固非埋头异邦之书者所能识也。”*见于暗斋第二代弟子源安崇之《辨蘐园议垂加先生》一文,收入在《續垂加文集附錄》,《山崎闇齋全集》第2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372頁。其中最典型的反对者即是兵学者山鹿素行(1622—1705)、松宫观山(1685—1780)的批判,以下论之。
1644年满清入关后,由于统治者带有“满”族的“夷性”,动摇了传统东亚世界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华夷秩序,在朝鲜发展出更坚实的“小中华”甚至“唯我是华”的意识,在日本德川在并吞琉球之后更发展出自成一格的“天下”秩序,这可说本阶段排斥“华彼夷我”的政治背景。而批评上述这些“华彼夷我”者,欲翻转“华”与“夷”的认知,主张以日本为“华夏”,如山鹿素行常常批判这些业儒者“居我土而忘我土”、“食其国而忘其邦”。*素行说:“盖居我土而忘我土,食其国而忘其邦,生其天下而忘其天下者,犹生于父母,而忘父母,岂是人之道乎。唯非未知之而已,附会牵合,以我国为他国者,乱臣也贼子也。”山鹿素行:《中朝事実》,第366頁。素行在否定日本皇室之始祖为吴太伯之苗裔之时,如是批评佛教与“腐儒”:*山鹿素行:《中朝事実》付録·或疑,第370頁。事实上,德川初期反驳吴太伯是日本神武天皇者之论者,尚有朱子学者林罗山,罗山曾在《神武天皇论》提及吴太伯是日本人间天皇之始祖的论说,是来自僧侣中严圆月:“东山僧圆月,尝修《日本纪》(案:指《日本书纪》),朝议不协而不果,遂火其书。余窃惟圆月之意,按诸书以日本为吴太伯之后。夫太伯逃荊蛮,断发文身,与交龙共居,其子孙来于竺紫,想必时人以为神,是天孙降于日向高千穗峰之谓乎。(原汉文)《林羅山文集》第25巻,京都:京都史蹟会編纂,1979年,第280頁。林罗山本人在面对这类传说时的态度,也认为是荒诞不经。
如佛教者,彻上彻下,悉异教也。……天下终习染不知其异教,牵合附会以神圣为佛之垂跡,犹腐儒以太伯为祖。
以吴太伯为日本神武天皇之背后心态,即是“华彼夷我”,素行批评这些妖言惑众的学问僧与儒者,因此为去除自己本身“夷”的身份,必须对“华”“夷”进行翻转,以突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故素行所著《中朝事实》即是一部以日本为“中华”,企图逆转“妖僧”与“腐儒”们的“夷我”情节。*相关山鹿素行的日本文化主体性之分析研究,可参拙著:《德川日本“忠”“孝”概念之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第四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第179—183页。继踵素行这种努力洗刷“华彼夷我”者,则是松宫观山,在其所著有名的《学论》即说:*松宮観山:《学論》,《日本儒林叢書》第5卷卷上,第3—4頁。
佛有两部习合之妄作焉,儒有华彼夷我之非礼焉。其两部习合,将驱神入于佛,亦不经也甚矣。然而以其人观之,则浮屠唯知佛可奉崇,莫复知其他也。乃神与佛安置同龛,而均供香华,本是出于敬神之诚,如其情则有不可深罪者也。至于儒之华彼夷我者,本是出于贱恶我国之心,则不敬甚于浮屠者。非耶!窃稽上世称芦原中州,《古事记》、《日本纪》、《令》等,皆指我京畿为华夏,指彼云唐国、高仓之朝。《大外记》清原赖业讥之,近日水府儒臣愿介栗山子(名诚信)再论之,愿言曰:“自称曰中国,盖对外国之通称,而固非言此土在堪舆之正中也。”至其或为神州,或为神国,且海内为天下,而外为夷为藩,则虽俱非九九总域之通言,亦各国自称,彼此无相害。……”源亲房亦曰:“彼以我为东夷,犹我以彼为西蕃也。”近学堕乎市井,文不振乎搢绅,懵乎旧典而不之顾,或呼元明为中华,自称为东夷,殆几乎外视万世父母之邦,而无蔑百王宪令之著矣。确论可据,而儒者尚仍旧不改者多矣。
上述松宫观山有两要点:其一是点出儒教的“华彼夷我”论,比佛教的“驱神入佛”更令人有非议、可罪之处,乃因儒者系出于“贱恶我国之心”。其二是日本古代亦被称为“华夏”之国,而且“中国”往往是各国自称,非中国所独尊。松宫观山此论,诚属实情,因全世界称自己国家为“中国”的比比皆是,钱钟书(1910—1998)就指出世界各国多少以其所居之地为世界之中心,他说:“如法显《佛国记》称‘印度’为‘中国’,而以中国为边地;古希腊、罗马、亚剌伯人著书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92页。松宫观山旨在批评诸多儒者“呼元明为中华,自称为东夷,殆几乎外视万世父母之邦,而无蔑百王宪令之著矣。”借由批评“自夷”转而强化自己的“华”性。
由此观之,德川初期的“攘夷”之“攘”,系扣紧“使自己去除夷人的身份”而言,进而强调自己有与中国不同的“华”性,借此洗清自己“夷”之身份,甚至如山鹿素行直接改称日本为“中华”,以“夷”变“华”得到文化精神上的满足。由于“夷”的身份指涉自己,所以这个阶段并不涉及军事政治上的“攘夷”,全然是以“文化上”的“攘夷”而言,面对一个举国知识菁英多以“中华文化”为优势之际,从而担心日本自己文化主体性失落的问题,遂出现捍卫自国文化主体性的学者。然而无论兵学派的山鹿素行、松宫观山,乃至朱子学者林罗山、暗斋学派等,他们抬出日本文化主体性的内容,都是“神道”的主体信仰,这股被激发而出的“神道”信仰,在幕末维新之际,一跃成为压抑佛教、儒教的文化信仰。
三、“夷者之在其他者”:幕末“保守”与“激进”的两种攘夷论
本阶段“攘夷”的“攘”是作为一般所理解的“排斥”或“使人退让”,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夷”,此一阶段的“夷”是以“他者”的西洋为对象,所以“攘夷”即是“排斥西洋侵略势力”。但是,此一阶段的“攘夷”颇为复杂,丸山真男(1914—1996)曾区分为“诸侯的攘夷”(指后期水户学)与“书生的攘夷”(指吉田松阴),大意不差,不过都是在其分析日本前期民族主义形成的脉络下而发论。*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第356頁。中译可参王中江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89—290页。本文则扣紧前此华夷论来探讨,故以“保守的攘夷”与“激进的攘夷”论之,前者以后期水户学为代表,尚不致有倒幕之思想;后者则以长州藩的吉田松阴为主,最后发展出倒幕之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败给“洋夷”后,更动摇了“天朝”的中国天下秩序,作为武士国度的德川日本,深深注意时局的变化,魏源(1794—1856)在鸦片战争后所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很快地被日本武士学者所大量注意阅读。洋学者渡边华山(1793—1841)也早从海防的观点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动,他指出:“印度在释迦降诞之地,自古以来政度文物鼎盛,但莫卧儿人*“莫卧儿人”即是印度最后的伊斯兰教的Mughal Empire帝国,兴起于1526年,18世纪初曾全盛一时,以后帝国长期分裂,1858年最后一位皇帝为英国所逼退位,国灭。暗于航海之事,尤不严海防,终为英吉利斯所据。”*渡辺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第51頁。简言之,海防问题攸关国家存亡的课题,身为武士学者,不得不探究,尤其是在德川末期内忧外患的时代,儒者们的经世论,往往围绕着以海防论、开国论、勤王论为中心。光是《海防彙议》(1849年编)就收有八十几篇的海防论。
1853年美国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四只舰队抵浦贺港,要求和亲,打开日本近代史之扉页,有志之士,均忧国势之危,早已嗅觉出18世纪以后所陆陆续续来的外船,与以前不同,洋学者渡边华山(1793—1841)就区分“古之夷狄”与“今之夷狄”:*渡辺華山:《外国事情書》,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9頁。
因天下古今之变,古之夷狄是古之夷狄,今之夷狄是今之夷狄。以古之夷狄,难制今之夷狄。
复有论者说:*全楽翁:《鴃舌或問序》,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第79頁。
盖世运风移之会,沧海变为桑田,华夏扰为戎狄。斯道虽无古今,时势则今非古。
这些洋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波的“洋夷”来袭,可谓空前,稍知此时势者的洋学者,几乎均主张开国之论,迫切需要积极学习“西器”,不过这股“开国”之论伴随着朝、幕关系的紧张,使得“攘夷论”压倒了“开国论”,而在此“开国”与“攘夷”论争之间被利用的宗教意识即是“尊皇论”,后期水户学扮演了“尊皇攘夷”的主导角色。有关幕末的攘夷论之研究,藤田雄二的《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國の比較研究》一书中,以宏观的中日韩比较视野做出相当翔实的研究,不过藤田之书重点是采取与中国、朝鲜的比较研究,并未详细分析日本内部的攘夷论与尊皇论之关系,以及日本国内攘夷论的彼此之间理念的紧张性。*前引藤田雄二:《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國の比較研究》。本书用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有名的《历史研究》(第17卷)中的著名理论所用的两个希伯来语“Zealot”及“Hérode”,来说明文明冲突的挑战与回应的模式。Zealot主义,一般译为“狂热者”,系指处于两个同时代的文明冲突之际,不顾彼我之优劣情势,仍固守自己的文明,其模式如顽强抵抗罗马帝国统治而终遭消灭者。Hérode主义,是借用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希伯来大希律王(Hérode the Great)之名而来,意谓接受优势的先进文明而终能残留生存下来,如大希律王一方面接受罗马统治成为其帝国的一员,同时另一方面也维持并发展了犹太人的文化与社会。藤田雄二用上述汤因比的两个对照理论,贯穿全书来阐述近代中日韩的“攘夷论”所面临优劣势文明之取舍态度。例如日本的“和魂洋才”、朝鲜的“东道西器”、中国的“中体西用”之论皆不离上述两个理论模式,且两文明处处存有紧张关系。以下针对这两项议题发挥并补充。
关于尊皇论,根据一项日本古代传说之记载,早在应神天皇时代(约五世纪前后),首传《论语》到日本的百济博士王仁,已经碰到这类问题了,该记载说王仁解读神语之时,被住吉大神(海神)显灵给天皇说王仁“频为异解,谩神代轻皇代”,天皇召王仁问其所以,王仁曰:“如吾国之理,解此国文,著书持之以奉”,天皇即敕告之:“汝国,人国;吾国,神国。向后以汝国理,勿解吾国文”,王仁顿时愕然而惊。*以上王仁故事,引自山崎闇斎:《風水草》,《山崎闇斎全集》第5卷,第363頁。这个故事说明日本神国或神皇,与中国或朝鲜的人国或人皇是相异的。这类思维也充分展现在一些强调日本神国的思想家上,阳明学者熊泽蕃山(1619—1691)曾如是区分神人、圣人之别,他说:“后世不能无教,故其时之圣人付其名以为教,唐土之圣人,以此曰智仁勇之三德;日本之神人,则象之以三种之神器。”*熊沢蕃山:《集義外書抄》,《水土論》第38卷,第494—495頁。勤皇学者佐久间太华也说:“彼所宗之圣人之道者,亚我神皇之教者”,*佐久間太華:《和漢明弁》,《日本儒林叢書》第4卷,第4—7頁。而什么是“神人”,就是从天照大神(天祖)以降,派神孙(天胤)掌管日本国,到日本神武天皇建国,万世一系,圣神相承二千五百多年。“天祖”与“天胤”是一脉相承的神性血缘关系。按照这种“神”、“圣”有别的思维,则中国经典有关“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的王道政治思想,最令日本有强烈主体性的学者感到冲击与紧张,因二者都牵涉到“易姓”思想,亦即王位无法绵绵不绝,尤其是后一项“汤武革命”,更令思想家对于孟子大加挞伐。*有关德川时代神儒兼摄学者对“神人”与“圣人”差别的解释,可参拙著:《日本德川时代神儒兼摄学者对“神道”“儒道”的解释特色》,《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8期,2003年5月,第143—179页。
“尊皇攘夷”大纛的是由水户学者揭序,藩主德川齐昭(在位1829—1860)在《弘道馆记》曾说:“拨乱反正,尊皇攘夷”。“尊皇论”涉及“名份”与“国体”精神这两个主题,这种尊皇论又常伴随日本神道精神,如藤田幽谷(1774—1826)有名之《正名论》,严斥禅让放伐论,强调日本国体的“祭政合一”之特色,并对时势采尊王攘夷的态度,主张日本武尊之原始精神在于尊奉神道。其子藤田东湖特著有《孟轲论》,从书名可知,他不称“孟子”而谓“孟轲”,可见并不以孟子为圣贤。《孟轲论》中表达从正统论之“尊周”的立场,来区隔孔、孟之“王道”,故东湖特对孟子的易姓革命论大加挞伐,他说:*藤田東湖:《孟轲論》,《東湖全集》,東京:博文館,1940年,第237頁。
夫禅让放伐,姑置不论,周秦以降,易姓革命,指不胜屈,人臣视其君,犹奴仆婢妾之于其主,朝向夕背,恬不知耻,其风土然也。……独赫赫神州,天地以来,神皇相承,宝祚之盛,既与天壤无穷,则臣民之于天皇,固宜一意崇奉,亦与天壤无穷。而腐儒曲学,不辨国体,徒眩于异邦之说,亦以轲之书与孔子之书并行,欲以奴仆婢妾自处,抑亦惑矣。
根据东湖之论,首先他拿日本万世一系与中国的异姓革命对比,来强调日本对天皇的忠贞无二思想,这是典型的反孟思维。东湖更在《弘道馆记述义》,解释“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资以赞皇猷”时,说“禅让”与“放伐”这二事决不可用于日本:*藤田東湖:《弘道館記述義》,《東湖全集》,第156頁。
有决不可用者二焉,曰禅让也,曰放伐也。虞夏禅让,殷周放伐,而秦汉以降,欺孤儿寡妇,以篡其位者,必借口于尧舜,灭宗国,而弒其主,以夺天下者,必托名于汤武。历代之史,既过二十,不啻上下易位,或并内外之分而失之。所谓拓拔、耶律、完颜、奇渥温、爱亲觉罗者,何等种类,何等功德,而九州臣民,若崩其角,又从而赞扬其美,动比诸唐虞,不亦可悯笑乎?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孙,皇统绵绵,传诸无穷,天位之尊,犹日月之不可踰,则万世之下,虽有德匹舜、禹,智侔汤、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万一有唱其禅让之说者,凡大八洲臣民,鸣鼓攻之可也。况借口托名之徒,岂可使遗种于神州乎;又况腥羶犬羊之类,岂可垂涎于边海乎!故曰:资以赞皇猷,若资彼之所长,并及其所短,遂失我所以冠绝万国者,安在乎其为赞猷也。
东湖在上述之论,认为禅让是开启后世僭乱的理由,所以自秦汉以降,篡位、弒主、夺天下者,不外皆借口尧舜或托名汤武,而这种思想绝不可使之行于日本,万一有人提倡禅让、汤武之说者,就是日本臣民之仇,全日本臣民都要鸣鼓而攻之。由上述之论可知,在德川历史上,以儒者之姿来显扬日本主体性精神的最高峰,当非水户学莫属。
伴随上述的尊皇论,攘夷论也呼之欲出,但幕末的攘夷论颇为复杂,约而言之,依其地理位置与藩国立场,水户藩面对的是东北的俄罗斯之“夷”的侵扰,其攘夷立场亦多从德川政权锁国禁教的政策而发,因此“尊皇”与“攘夷”可以分别发论,笔者称此一立场的“攘夷”论为“保守的攘夷论”。至于西南藩是直接面对英、美的“洋夷”,其立场往往站在德川政权的对立面而发展,处处挑战幕府政策,因此“攘夷”论最后不得不与“尊皇”论联结合一,终结德川政权,笔者称此一攘夷立场为“激进的攘夷论”。以下析论这两种攘夷论。
史学界一般以水户学作为“尊攘”的发源地,尊皇论已如前所述,至于“攘夷”,因水户学的地理位置及其御三家的立场,“攘夷”论往往扣紧着延续德川政权的立场而发,如藤田东湖以下的“攘夷”之论:*藤田東湖:《回天詩史》,《東湖全集》,第39頁。
(德川家康)始设外夷之禁,凡蟹文之国,一切拒绝,不得复窥窬,独以和兰教法,与西洋诸夷异其宗,特许往来长崎,通有无,以为洋夷间谍,使其岁书西洋事情,以上于府。然虏之桀骜冥顽者,犹或犯禁而来者,不啻一再,当时国威方炽,必火其船,磔其人,无有□类,洋夷寒胆,不窥边陲者,百数十年。承平日久,武备稍弛,于是鄂(按:俄罗斯)、黯(按:英国)二夷,复垂涎于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谕而还之,至于其甚,则给薪水米果而遣之。微乙酉(1825)之令,则东照(按:德川家康)、大猷(按: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二公之贻谋殆荒矣。我纳言公(按:水户藩主),夙慨然有攘夷之志,深体祖宗之意,又洞察洋夷之谋,以为夷之出没海上,祸心不测,其守备不可严也。
按上述东湖的“攘夷论”,有以下二大可注意之点:其一是攘夷之策乃自德川家康禁教以来的政策,仅容许荷兰在长崎贸易,以晓知西洋情报;而1825年的乙酉年,鉴于英、俄船舰屡犯禁入港,将军德川家齐乃有“文政乙酉之令”,内容是:“外夷之船,至海滨者,发炮悉碎之。且渔民窃与夷人,贸易于洋中者,一切禁之。”(仁孝天皇条)可说是延续家康以来的禁教政策。其二是批评现有对“夷人”的宽待,不但未给予严惩拘禁,还给予漂流水手充足的饮水柴火及食物并放还归去,采用的是1842年比较宽松的“宽政文化之令”,东湖如是写下当时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感叹:“壬寅岁,幕府废乙酉攘夷之令,用宽政文化之令,于是滨海之国,不得辄碎虏舶。天下有志之士,索然而解体矣。”*藤田東湖:《回天詩史》,《東湖全集》,第42頁。值得注意的是,水户藩主要攘夷的对象是俄罗斯帝国,东湖的《回天诗史》中屡提及俄罗斯觊觎虾夷之地,而提出开拓虾夷之策。*东湖如是担心虾夷之地沦为俄罗斯所侵占,而曰:“夫虾夷千岛,本我神州之地,其加模沙斯加者,既出于虾夷方言,则其地亦安知非源豫州所经略。而今鄂虏傲然据其地千岛之多,我仅守久奈志利惠登吕府二岛,所失之地,何啻一寸一尺,岂非千古之愤哉!”藤田東湖:《回天詩史》,《東湖全集》,第40頁。同时,我们在此也看到水户藩站在延续德川开国的“攘夷”政策与立场,不断地向幕府谏言应彻底奉行“乙酉攘夷之令”。水户藩这样的“攘夷”论,实与德川幕府的延续政权直接相关,至于“攘夷论”与“尊皇论”之关系,企图使将军与天皇政权等视而观,在此前提之下抬出尊皇论,借此使幕府改革,而其中间的联结乃在“大义”精神。东湖说:
“苟明大义正人心,皇道奚患不兴起,斯心奋发誓神明,古人云毙而后已。”呜呼!我公之所以遭祸者,彪既粗言之矣。然则王室陵夷者,不可复尊乎?蛮夷猖獗者,不可复攘乎?幕府之政,谗慝日行,异端之说,浸淫益甚,而神皇所以经纶天地,控御宇内之道,湮晦否塞,不可复阐明开通乎?曰奚其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天尊地卑,日月昭明,彝伦犹存,苟能反其本,通其末,原其始,要其终,允执其中,以明大义于天下,则王室可尊,蛮夷可攘,幕府益昌,异端自衰,而皇道之隆,可企首而望也。
东湖看到了当前日本上下缺少的就是“大义”精神,幕府已经沦为小人当道且异端邪说橫行的政权,所以才导致皇道的“大义”精神晦而不彰,否则连“攘夷”这么明白的事情,幕府何以不做。至于奉行“大义”的尊皇论,其实质内涵则又与“尚武”精神息息相关,东湖如是发论:*藤田東湖:《回天詩史》,《東湖全集》,第47頁。
尊神之义明,则皇室自尊,异端自衰。忠孝之教立,而神皇之道兴矣。抑古者尚武之俗,冠绝宇内,亡论也;而释氏柔和忍辱之教,或折其锋;和歌者流,浮靡淫堕之习,又从而移其气。公卿百官,手不知兵,尚武之俗,一变移于武家,然犹亡于室,而存于堂也。故胡元之窥我也,先斩其使,以明示与彼绝,戒诸国,严兵备,遂歼十万之众于西海。朝鲜之无礼也,航海远征,八道惊溃,余威震明国。洋夷之藏祸心也,火其船,戮其人,丑虏破胆。今者承平日久,风俗偷薄,尚武之俗,或让古焉,而因循不察,万一失其存于堂者,则奸民狡夷,将有起而拾之者,岂可不寒心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曰武家,则尚武之风,不可以不振,曰弓马之道,则将帅之术,不可以不讲。当奖学之任,则五典之教,不可以不明,奉征夷之职,则膺惩之典,不可以不脩也。故尚武之风振,则幕府自昌,夷狄自远,天地之正气充,而神州之纪纲张矣。
由以上之论,约可略窥“尊皇论”的实质内涵其实就是“尚武精神”。东湖历数存于日本的佛教过于柔和忍辱,和歌者易于奢靡淫堕,导致公卿百官上下失去尚武精神,此后神皇之道幸存于历来的武家政权,但武家政权也因承平日久,尚武精神渐失。一旦失去了尚武精神,不仅丧失神皇古道,即连号称“征夷大将军”的武家政权也摇摇欲坠。以上发论,足可使我们理解何以“尊皇论”与“攘夷论”结盟之因,易言之,“尊皇论”与“攘夷论”的联结剂即是“尚武”精神。*这里提及的“尚武论”,颇如前引藤田雄二的书中,曾提及幕末攘夷论所出现的“死地之论”(即“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所拋出,齐昭所呈给德川将军《戊戌封事》及《十条五事之建议》两奏文中,齐昭成功地将“攘夷论”和武备联想在一起,从而逼出“死地论”的攘夷论,给文恬武嬉的幕府一记棒喝,且在当时幕末志士中传诵不绝,成功地助长幕末的攘夷论之发展。藤田雄二:《アジアにおける文明の対抗:攘夷論と守旧論に関する日本·朝鮮·中國の比較研究》,第101—102頁。
东湖提出釜底抽薪的“明大义”之“尊皇论”,希望神皇古道的尚武精神,挟“尊皇论”逼使幕府趋向“攘夷论”的改革,而其心中尚仍期许德川幕府昌盛之意。不过,西南藩接收了水户藩这套尊攘论之养分后,走的不是保守的尊攘论,而是激进的尊攘论,“攘夷论”与“尊皇论”已直接成为“一事”而非“两事”,幕府政权成为不得不去之后快的改革绊脚石。更激进的是,“尊皇”甚至不是“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天皇”与“日本国”已是一体概念,二者不可切离,吉田松阴最后的立场即是如此。*相关论点可参见本山幸彦:《吉田松陰の思想:尊王攘夷への思想的道程》,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第217—218頁。本书认为松阴的“尊王”是“目的”,不是“手段”,特别澄清论者有谓松阴是从“攘夷尊王”到“尊王攘夷”,似有二分之虞的论点,作者反驳此一说法,强调松阴是“天皇”与“国家”是一体概念,二者不可切离,其说甚是。
吉田松阴曾经考察东北,并访水户学者,受到水户学尊皇攘夷思想学风的洗礼,此后思想愈趋激烈,晚年著作几乎是在幽居期间完成,最后因组血盟同志十七名计谋刺杀幕府老中间部诠胜(1802—1884),因幕府发动安政大狱,松阴被押解江户处死,门人伊藤博文(俊辅,1841—1909)、木户孝允(初名桂小武郎,1833—1877)收其遗骸。有关松阴思想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笔者亦有相关研究,不再赘述。*张崑将:《吉田松阴〈讲孟余话〉的诠释特质与其批判》,《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第207—233页。以下集中松阴的尊皇攘夷之思想。
相较于水户学“尊皇”与“攘夷”论的保守性,仔细分析松阴的尊攘论,有时与水户学无大出入,仍是以延续德川幕府政权为主,如以下《丙辰幽室文稿》的言论:*吉田松陰:《丙辰幽室文稿》、《松下村塾記》,《吉田松陰全集》第3卷,第53頁。
君臣之义也,国之所最大者;华夷之辨也,今天下何如时也。君臣之义,不讲六百余年,至今时,合华夷之辨而又失之。然而天下之人,方且安然为得计,生神州之地,蒙皇室之恩,内失君臣之义,外遗华夷之辨,则学之所以为学,人之所以为人,其安在哉!
吉田松阴痛斥当前是不讲“君臣之义”与不辨“华夷之辨”的时代,“君臣之义”针对尊皇而发,“华夷之辨”是针对幕府而论,关键就在于掌权的幕府,有时松阴表达对幕府的期待,而说:“幕府真能一日感悟,奉皇敕,率诸侯,安兆民,驯群夷,细大之事,无非王事者。则今之征夷,古之征夷,今之国司,古之国司,今之臣民,古之臣民。制度有隆杀,委任有轻重,固无伤于皇国也。”*吉田松陰:《丙辰幽室文稿》、《復浮屠黙霖書》,《吉田松陰全集》第3卷,第47頁。期待着幕府扮演真正的“征夷”大将军的“攘夷”角色。但幕府一直没有作为、无法符合改革的期待之际,最终还是逼出了“尊皇斥幕”,比起水户学的言论,松阴更为激烈,如以下《外藩通略》之说:*吉田松陰:《外藩通略》,《吉田松陰全集》第8卷,第221頁。
自武臣擅国,古道渐废,如足利义满,至国王自处,称臣外域。人臣之悖,至是极矣。德川氏既代丰臣,宰割天下,几百制度,多步趋义满,然义满之罪,人能言之,德川之非,孰敢议之,固有待于隐居放言之士也。
《外藩通略》旨在突显幕府与诸外国之文书,幕府无视天朝(天皇)之礼,故松阴斥之曰:*吉田松陰:《外藩通略》,《吉田松陰全集》第8卷,第225頁。
德川氏……独朝鲜遣使通聘,事体颇重,而其来为德川氏贺袭职,而未尝为天朝贺登极,且德川氏亦未以是请天朝而奉敕旨。人臣、外交之罪,德川氏其何以辞之哉!
上述两条历数武家政权的不是,痛斥德川武家与足利武家政权的不尊皇室。松阴举出德川的两大罪状,其一是“人臣”之罪,直指外国使臣(除了朝鲜以外)来向日本祝贺世袭登基之礼,只向幕府祝贺,却从未向天皇的登基祝贺,这当然是畏于幕府权威之故。其二是“外交”之罪,从幕府与外国的“外交”往来,看出德川的僭越之罪,系指德川武家接待或遣使外国使臣,是否均呈报给天皇,或对外国的种种決策是否请示过天皇,因为一旦涉及“两个国家”的外交来往,就会出现谁代表“日本国主”(是幕府将军?或是天皇?)—也就是“国体”的问题,1853年美国的培里舰长当初呈给日本的国书对象是“日本国王”也就是“天皇”。因此,德川将军的任何对外国的决策是否“奉敕旨”这件事情,成为幕末倒幕的主要理由之一。
以上“人臣”与“外交”之罪,是“尊皇斥幕”及“国体”论的引爆点,而“攘夷”之“夷”,在这些激进武士与德川政府官僚的交涉过程中,无形中也是成为勤皇倒幕的“帮手”或“理由”,其一是幕府直接与“夷”人谈判,失其“征夷”大将军之职;其二是幕府跳过“皇敕”而与“夷”人谈判,不尊“国体”。如此具体地指出德川氏违反人臣、外交之罪,我们在水户学者的尊攘论中比较少见,故笔者称松阴是激进的尊攘论,而事后也证明这种激进的尊攘论压倒了保守的尊攘论,成为倒幕论的主流。
四、由“攘夷论”到“文明论”:明治维新的两种“文明论”之转向
“华夷论”本带有文明相较于野蛮的意思,故幕末维新之际,由于西力东渐,旧有的“华夷论”一变为“文明论”。以英美为主的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家的作品则又扮演承续介绍西学的重担,如福泽谕吉(1835—1901)的启蒙书《西洋事情》刊于1866年、《文明论之概略》撰书于1875年,中村正直(1832—1891)的《西国立志篇》成于1870年,西周(1829—1897)在1880年著有《百学连环》,是一本集欧洲诸学艺的百科全书。当中国尚在洋务运动之际,日本已然历经明治维新,进而西学全开。
明治维新,初时尊攘论还甚嚣尘上,但终究形势比人强,终于认清“攘西洋之夷”是不可行的局势,有识之士也开始觉醒昔日之洋夷才是真正“文明”的象征,而东洋的一切(专制、封建、权威、阶级…),反成为“不文明”的代表。于是在此又有了第二波“华夷变态”的转折,原被视为“夷”的西洋人,翻转为“华”,而改用“文明”与“野蛮”的新词语取代过去的“华”与“夷”,无论是中国张之洞(1837—1909)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日本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都企图固守自己的“体”时,也都无法挽回在当时无论是“体”也好,“用”也罢,皆输给“洋夷”的事实,从而走向“全盘西化”之路,积极学西方的“文明”。这一波与德川初期满清入关的“华夷变态”最大的不同,是西洋文明取代了中华文明,成为“华夷”的指标。福泽谕吉是当时代的指标人物。
明治时期虽不说“攘夷论”,但在语境上转换成为“文明与野蛮论”,各种“文明论”的书籍与文章纷纷出笼,福泽谕吉是其中的启蒙者与宣扬者。如果用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的“文明开化”为标准所区分出三种国家,一是“最文明”的欧美国家,一是“半开化”的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一是“野蛮”的非洲、澳洲等国家。*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页。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进化到“文明开化”的先进国家之列,而中、韩两国成为福泽笔下无法进化的文明停滞国家。*这充分地表现在福泽著名的“脱亚论”,福泽说:“我日本的国土虽然位于亚洲东边,可是国民的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支那,一个是朝鲜。…据我观察,在当今西风东渐之际,这两国很难维持其独立。如果很幸运地,这两国出现开明志士,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大刀阔斧地从事改革,一新全国人心,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地,从现在起不出数年,这两国就会亡国,而且国土也将被世界各文明国家分割。……若是如此,则我国就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携手复兴亚洲,而是应该脱离他们,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参1885.3.16福泽在《时事新报》的言论。
过去,中国有长远的时间向来以“倭”或“倭寇”蔑称日本。幕末期间,随着“天朝”被“洋夷”戳破其外强中干的表象后,日本开始渐渐出现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在明治维新成为正式蔑视中国的称呼。昔日文明中心的“中国”成为被日人鄙视为文明落后的“支那”,“华”与“夷”之间在中日形成逆转关系,且在日本看来成为“事实”。不过,华夷变态在近代成为“事实”之前,十七世纪满清入关已经撼动这种华夷关系的绝对观,用福泽谕吉对“文明”的“相对”概念,今日之“文明”国家若不能持续“进步”,将成为明日之“野蛮”国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处处充满相对论之观点,如他说:“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线。但是,这些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的时期,也不妨以半开化为最高阶段。这种文明对半开化来说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页10)又说:“即便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尽善尽美了。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展,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页11)虽然如此,切不可将福泽视为“相对主义者”,丸山真男对此特有解析,丸山认为福泽的“相对论”应是一种不断抵抗斗争的进步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价值可以分化与多元,例如对自由、文明的追求即是如此,永远呈现一种不至于停滞的进步状态。参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8—59页。易言之,没有永恒的“文明”或“野蛮”国家,不与时俱进的结果,就等着成为被新进文明国家宰制的野蛮国家。
但是,福泽的“文明论”之最大问题在于以进化论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定义“文明”的涵意,即偏向外在物质进步取向的“文明”意义。虽然福泽也说“文明”包含“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精神”,但其所谓“外在的事物”指的是饮食、衣服、器械、居室乃至于政令与法律,而“内在的精神”指的是“人民的风气”,也就是“一国的人情风俗”,并特别强调“智力”的展现,而非“德”的发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2—14页。依笔者粗略的观察,明治时期的“文明论”相较于过去基于儒教道德的“华夷论”而言,明显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转向”现象:
1.以“智”取代“德”的伦理学转向
此一“伦理转向”指的是“伦理学”向“物理学”的转向,福泽谕吉是这个转向的翘楚者。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批判儒教的五伦常理,常以“道德伦理”渗入自然物理(如朱子理学),故有如下之批判:“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而论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36页。按福泽的原著是《文明论之概略》,译书去掉了“之”字。根据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的研究,他指出福泽谕吉反对汉学的原因,是因为“无数理教育”及“无独立精神”,这两者都可反应在福泽强调“智”的表现。“智”既是福泽高举“独立自尊”,扫除专制权威以“道”或“德”为主的伦理要素;“智”同时也是福泽提倡科学之本的“数理教育”的根本。*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9—30页。
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专辟两章论述《论一国人民之“智”“德”》及一章讨论《“智”“德”的区别》、一章解说《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足见“智”的展现是其文明论的核心,且福泽谕吉强调一国人民“智”的展现就是“内在的精神文明”。严格言之,福泽所谓“内在的精神”极力排斥个人“私德”的部分,特别强调“团体”、“整体”智力或舆论的展现,他特区分“公德”(与外界接触的德行行为)、“私德”(内心活动的一己德行行为)、“公智”(聪明大智)、“私智”(机灵小智),又区分“德”属内,“智”属外。*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六章《智德的区别》,北京编译社译,第73—79页。如实言之,福泽倡道的新思维,取代了过去中华儒教文明以“德”、“智”兼摄的取向,同时也转化“德”与“智”的内涵。殊不知在传统儒教道德的“德”不仅包括“私德”与“公德”,且“私德”与“公德”彼此之间有其连续不可分割的关系。又“德”、“智”也都同时涵摄“内”与“外”,故有“闻见之知”与“德行之知”,“德”与“智”可说内外互涵、公私连贯且体用兼摄,但透过福泽的用法,都成为两分境界,且仅成为“实用主义”并独厚“智力”的展现。昔日德川儒者荻生徂徕重外王轻内圣之学的实用儒学充分展现在福泽的思想上。
福泽“以智代德的伦理转向”,似乎矫枉过正,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造就一个“重智轻德”的实用主义之社会,也将导致“智力”收束不住而成为科学主义挂帅的倾向。吊诡的是,福泽如此强调一国之民“智力”的舆论展现,但现实上福泽也无法挽回以下“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的重重问题,“智力”在此不但退缩,而其瓦解儒教道德的“伦理”转向后,特别是对“仁”德的解消,如今被填入以天皇为信仰的“忠孝一体”的国体观。表面看来,“伦理转向”与“超越原理”的被取代,二者似乎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仔细推敲,似乎与“重智轻德”的思维有关,因为在福泽看来的“德”,就只是儒教的尊卑的纲常五伦与阶级的上下关系,却漏掉了儒教最核心的普世价值之“仁德”,“智”与“仁”之关系,如同山与水之体用关系,缺一不可,如今过度重“智”的结果,故能轻易地被置入以“忠孝一体”的国体观成为超越一切道德的道德原理,或成为超越一切宗教的宗教原理。
2.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之转向
此一“超越原理”指的是“忠孝一体”的国体论,取代并超越了“仁本体”论的普世价值。
这方面以国体论及武士道论者为代表。国体论者表现出日本文明既超越中国文明也凌驾西洋文明,成为万邦中最优秀的文明。并把对中国的甲午战争解读为“文明与文明”战争,日俄战争解读为“东方文明(或人种)胜过西洋文明(人种)”的战争。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以后,有关“忠孝一本”或“忠孝一体”的“国体”论的书籍如潮涌般出版。更不用说1895年甲午战以及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十年之间战胜了东西两大国,更强化了“国体论”精神是日本文明最优良的代表,上述福泽谕吉那种扫除权威且基于个人主体的独立自觉之“文明论”远远被拋在脑后。
有关“国体”,就中竹越与三郎所著《二千五百年史》(1896),洋洋洒洒从远古日本文明的独立性、大和朝廷的建立,一直到明治维新,全书以神武纪元,充满人种进化论的色彩。*竹越与三郎:《二千五百年史》,東京:警醒社書店,1896年。1902年的教科书,也明定“国体”、“大和民族”之由来,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本邦ノ風土国体》均提及万世一系的天孙民族以及对天皇的“克忠克孝”之“国体”精神。*中島半次郎:《教育史教科書》,東京:金港堂,1902年,第6—8頁。以下根据国会图书馆,简单罗列明治到大正初期出版书中之目录中有“国体”与“文明”者:
从上表简列,约可略知,与国体所涉及“文明”内涵,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政治、教育、种族、宗教,也扩及农业、医学(卫生)等。我们以井上圆了的《日本政教论》为例,说明如下结合“国体”与“文明”之通说:*井上円了:《日本政教論》,東京:哲学書院,1889年,第7—9頁。
余曾曰:日本文明是从神儒佛的混合化成分解而成,又若无日本文明,则日本文明之精神、日本性质之基本在此三道之中,故日本风之与外国异,日本人心之与外国异,日本国之独立于东海之上,自我皇室开国以来,皆无不受此三道之结果影响,故维持日本人心,保存日本独立,此所以养成我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日本国之所以为日本国也。……我旧来之宗教,系在我皇室国体之下千数百年间流布。我皇室国体在此宗教之上,千数百年间连续,以其宗教渐渐改良发达,而取最适合我国体之形质,成为永续我皇室最有力之宗教。
以上的“日本文明”指的是杂糅神儒佛三教的独特文明,但三教之上是日本的皇室国体,故以皇室为主的国体是超越所有宗教的宗教,即被指为“国家神道”是也。宗教领域被如此强迫性地结合或压抑,其他领域更不用说。
只是,这样以“忠孝一本”的国体论,并将之超越化或宗教化,确实是日本独有。但这种超越性,看似用的是儒教伦理,实则“忠孝”内涵已与儒教大异其趣,毕竟在传统的儒教内涵的忠孝只能是“二元”(血缘的与政治的无法混同为一),不能是“一本”。其次,“忠孝一本”的国体论与儒学最重要的核心“仁体”也出入甚大。笔者曾为文指出儒学的“仁义”的内在超越思想,在日本德川武士国度的学者的脉络解读下,成为唯政治义所理解的“仁义”,导致出现以下两种道德连续的断裂,其一是斩断个人道德与政治道德之关系,而以“政治道德”凌驾“个人道德”,这是对仁德的去内在化;其二是切断宇宙与人生道德之关系,这是对仁德去超越化。*拙著:《德川儒者对中国儒学道德价值观念的转换:以“仁义”、“忠孝”概念为中心》第一章,《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职是之故,“忠孝一本”的国体论道道地地是日本特殊主义的产物,本身的伦理理论缺乏“普世价值”之理念,强化自身的优越性与神圣性,而强以政治意识型态进行“超越”伦理的控制。
仔细观察上述明治时期的两种文明论,不论是“智德的伦理转向”或“仁德超越原理被取代”,都可以追溯到江户时期。福泽的文明论所抱持的“德”、“智”转向观点,几乎都可在荻生徂徕的论点中找到。而以“忠”超越“仁”的观点,在武士国度的家训中也仅突显“忠德”优先,认为“仁”德有碍武家的忠德。不过,勤皇论的“忠”德就不只是如此,他们将儒教基于血缘关系的“孝”德纳入后,透过“拟血缘”的想象超越联结关系,融入到“忠”德中,从而创出“忠孝一体”的国体论,这在幕末水户学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及吉田松阴的著作中皆可看到其理论的原型。*相关研究可参拙著:《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五、结论
本文分三个阶段来阐释日本近世到近代的“攘夷论”之发展与变化,指出第一阶段的攘夷意识是在德川初中期阶段,此一阶段之“夷”是作为“在其自己”,相对的“华”乃指的是中华文化之“华”,特别是儒教文化之“华”,故一些德川知识分子极力洗刷这种“华彼夷我”的情节,这个阶段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华夷论战。第二阶段的攘夷论,是以“夷”作为“在其他者”,主要的“夷”是指“西洋”的侵扰,这个阶段的“他者之夷”在军事上构成威胁,文化思想上也牵动了武士思想的改变。在此阶段中,本文复区分“保守的”与“激进的”攘夷论两种类型,前者以后期水户学为主,“尊皇”与“攘夷”可以分别发论,后者攘夷论最后不得不与“尊皇”论连结合一,终结德川政权,故名“激进的攘夷论”。至于第三阶段的攘夷论,以西方为主的“文明论”取代了过去东方惯用的“攘夷论”,东西方文明之情势“逆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可为典型代表,在此笔者也看到此波文明论与过去儒教的华夷论最大不同的两个转向,其一是以“智”取代“德”的伦理学转向,其二是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转向,儒教的“忠”、“孝”、“智”、“德”、“仁”等道德,在明治时代的文明论者与国体论者的脉络下,全都转向具有日本主体脉络意义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以国体精神为中心的特有之“新文明论”,而这一波经过转向的“新文明论”,不仅从中华文明脱逸而出,也超越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创出“东亚文明论”,而日本则是“东亚文明”的优等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依据,支配了明治以后至战前的意识型态。*最可代表的著作即是1930年最初刊行出版的滨田耕作(青陵)所撰《東亜文明の黎明》,東京:刀江書院。相关分析可参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第8—14页。
(责任编辑:董灏智)
[收稿日期]2015-08-31
[作者简介]张崑将(1967-),男,台湾台南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1-006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