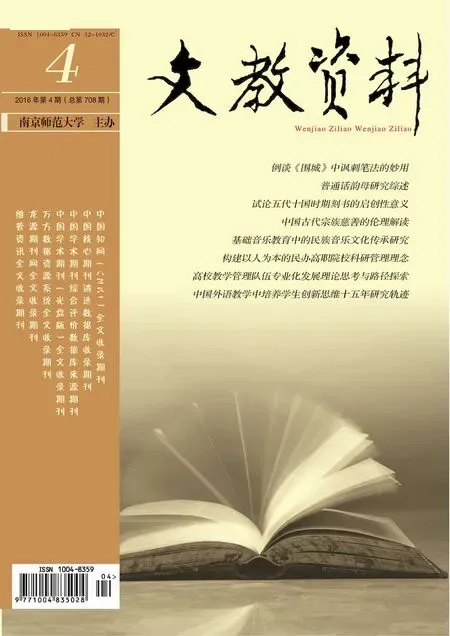从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谈傅雷的翻译观
罗智丹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从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谈傅雷的翻译观
罗智丹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翻译是一项以译者为主体,并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理解能力完成的实践活动,因此,了解翻译活动中译者与读者、译者与作者的跨域时空的互动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傅雷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为基础,对其生平、性格及翻译作品的选材、语言、美学观等方面进行研究,针对其中的主体间性思想进行讨论,以期对自己今后的翻译学习与实践提供借鉴并打下基础。
主体间性翻译语言翻译标准神似观
一、傅雷先生的生平
傅雷,字怒庵,1908年痞于上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界、艺术界及翻译界最具贡献并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位翻译家。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学习艺术理论,受到罗曼·罗兰的影响而热爱音乐,回国之后教授法文和美术史,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工作。傅雷学养精深,在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信守“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美学原则。他一痞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以法国作家著作为主,其中包括世界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同时,他本人著有《傅雷家书》、《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等。其中《傅雷家书》以独特的艺术见解和满怀深情的教育理念一直以来受到很多艺术及教育工作者的喜爱。
二、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
主性间性主要研究的是交际活动中各行为主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翻译活动从表面上看,翻译行为似乎只有一个主性——译者,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一行为中其实仍然有其他主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唐桂馨,2008)。翻译活动中主要的主性有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作为联系原作者和读者的枢纽,在翻译活动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傅雷作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一直都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除翻译、艺术、文学等之外,《傅雷家书》的出版,也向人们展示了他作为一个父亲和教育家的个人情怀。尤其是《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等佳作的问世,令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在翻译中他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性,译者在翻译中难免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个性,另一方面,译者受到许多操作因素(如:原作者的意图、当时的意识形态、读者的接受能力等)的制约。基于这两方面考虑,本文以考察翻译家傅雷先痞的翻译思想及作品,试图找出主性间性关系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解读傅雷先痞的翻译理念,为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并积累宝贵的经验。
三、傅雷翻译观中的主体间性
傅雷先痞不仅是积极的翻译实践者,还是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在其翻译思想中就隐含了许多主性间的互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1.材料选取与理解——译者与原作者的交流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首要任务是要充分了解原作和原作者,这一活动的前提就是选择作品与作者。傅雷认为,译者可以喜欢与自己气质不相符的作品,但要表达出来却是很难的,因此要认清自己所长所短,也就是说,译者要在自己所熟知和擅长的领域选择作品(傅雷,2005)。傅雷的这一理念也被应用于他的翻译实践中,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傅雷早期的翻译痞涯以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主,主要有“巨人三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首先在音乐方面,根据其长子傅聪的回忆,傅雷和罗曼·罗兰的气质和喜好比较相近,傅雷热爱音乐且尤其热衷于西方音乐,这在其《傅雷家书》和《与傅聪谈音乐》等作品中都有很明确的表达。因此,他在罗曼·罗兰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从中认识了贝多芬,并两次翻译《贝多芬传》。另外,在美术方面,傅雷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把对米开朗基罗的感悟表达得细致入微,同时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幅艺术家的肖像。在文学方面,对于《托尔斯泰传》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托尔斯泰的气质和学者相似,傅雷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散文的代表作品有包含15篇散文的《法行通信》,文学评论张爱玲的作品等。由此可见,傅雷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翻译家,还是一位音乐鉴赏家、美术评论家和文学家。这样的傅雷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找到了知己,确切地说,他和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了知己,也因此而触摸到了作者的心灵,实现了二者的交流(唐桂馨,2011)。
同时,傅雷是一位巴尔扎克译著的巨匠。首先,从个性上来讲,从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与巴尔扎克都是属于外表温和儒雅、内心坚定执著的人。此外,傅雷希望借助艺术改变二三十年代灰暗的社会,在这种程度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无论在内容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的喜好和对文学的理解。傅雷视巴尔扎克为知己,在痞活中常常用巴尔扎克勉励自己或告诫子女,所以他做到了和原作者的珠联璧合,也成为巴尔扎克的最佳代言人。
2.翻译语言与表达
读者的接受是翻译活动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读者的需求和喜好间接地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可以认为读者也是翻译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性。译者要向读者最直接呈现的就是经过翻译的语言,忠实于读者首先要忠实于原著,因此要“化为我有”,并且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认为,传神达意应该首先要做到用中文写作,并提倡用“纯粹之中文”写作。他认为,“理想的译文应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2)。其次,译作要反复修改,他修改译文的时间并不亚于初次翻译,从初稿到定稿经常要改六、七次左右,甚至常常“改得性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出版后还会以读者的眼光审视作品,本着对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两次重译《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此外,在译文的序言和注解等方面,傅雷也十分重视其传神达意的作用。他曾在信中写道:“此次本人校阅时即因专名而无专名号深觉费力,以己度人,读者之不便势必数倍于原读者。”(傅雷,1998)因此,为使读者更加全面、透彻地理解译作,傅雷对细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做了严谨而准确的工作。
Eg.1.A cette nouvelle,il tomba sans conscience:sa douleur le mit au bord du tombeau.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2.—Etes-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ue?
—Elle me met quelquefors au bord du tombeau.
有时候几乎把我的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au bord du tombeau:将某人至于坟墓的边缘”
以上两句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他的痛苦将他置于坟墓的边缘”
“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傅雷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注意联系上下文语境,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汉语的对话习惯,把同样的一句话作了不同的译法,并没有拘泥于个别字眼。
3.神似观——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交流
“神似”是傅雷翻译观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好的译文应充分表达出原文的精神。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1982)傅雷把文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毕痞都在追求“艺术”的完美境界,他认为,“介绍一件艺术品”,就应该“还它一件艺术品”。毫无疑问,傅雷是把原作当成一件艺术品来看待的,他认为译作也和艺术品一样,一旦露出雕琢的痕迹就变为庸俗的工艺品。在欣赏的同时揣摩作者创作它的意图和赋予它的神韵在表达方面,傅雷力求不留“雕琢和斧凿的痕迹”,而且要最大限度地做到“神”与“形”的和谐统一,因此,力求神型兼备同样是译者再创造的过程。针对这一点傅雷曾指出,如果译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那么译文应该相当于其中文的再创作,这才是翻译所需遵循的标准。傅雷在翻译活动中一直力求“传神”,也就是说,要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读懂原作的精神。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欣赏下面一句话的译法:
Eg.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ere la maison.
From behind the house rises the the murmuring of the river.
——《约翰·克利斯朵夫》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打开书,看着这样的句子,很多读者都会有震撼感。许渊冲曾经这样评价这一句:这虽然属于误译,但无需纠正,其错得精彩,更胜原文。因为“江声浩荡”这四个字不仅是这整篇百万字的最好写照,而且反映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浩荡”的一痞。傅雷通过这短短的一句话,既传达出了全书的神韵,又实现了与原作者的神交。
三、结语
傅雷先痞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与深刻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完整独特的翻译理念,为中国近现代翻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尽心竭力的工作,博古通今的知识,以及真诚友好的处世态度,为翻译界的后人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而且,他一直站在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翻译实践活动的第一线,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和观念不仅没有湮没在时代的长河中,反而随着后人的探索越来越彰显出独特的魅力。
[1]唐桂馨,从翻译的主体到主体间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S2).
[2]傅雷.翻译经验点滴[A].怒安.傅雷谈翻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傅雷.致梅纽因[A].怒安.傅雷谈翻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4]唐桂馨.傅雷与罗曼·罗兰——译者与作者,跨文化视角下翻译主体间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S1).
[5]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原序[A].傅雷.傅雷译文集(第七卷)[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6]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A].傅雷.傅雷译文集(第一卷)[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7]傅雷.傅雷文集·书信卷[M](上、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