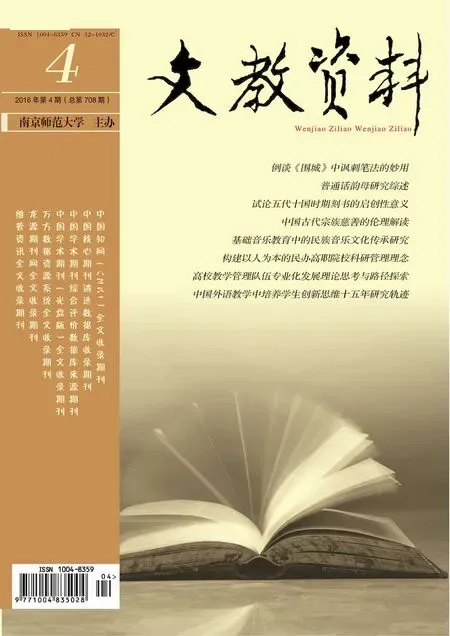浅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蒋霄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09)
浅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蒋霄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09)
婚姻与恋爱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贯穿着整个女性文学的讨论与研究。可以说,以婚姻与恋爱为着眼点,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无疑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领头雁”。
女性意识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新时期,作为新锐作家登入文坛的张洁因《爱,是不能忘记的》而为读者熟知。主流文学史通常将张洁的这篇小说列入反思文学的行列,因为反思文学主要写婚姻、爱情主题,它大胆突破了17年文学的禁区,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
考察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表达,有两个切入口是关键点:第一,是小说中爱情跨越的时间段: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文革”中和新时期;第二,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份,即知识分子,通俗地讲就是文艺女性。因此,从以上两个角度入手,分别考察小说中“我”与“母亲”的婚姻与恋爱,洞悉张洁在小说中渗透的女性意识。
一、“我”与“我”的爱情——精神上叛逆者与反抗者
“我”的爱情是小说文本中呈现给读者的第一段情感。对于这一段情感,可以用“抗拒”形容。
首先从“我”的身份入手分析:“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文艺女性。作为作家母亲的女儿;另一个身份是叙事主性。“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由叙事人“我”来言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段感情是站在“被审视”的立场上间接地被“我”表达出来的。小说开头有这么一句话:
“这引起他们的气恼,好像我真的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冒犯了众人的事情。”[1]79
“我”站在“审视”的立场来看待被人们“审视”的我。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妇女的经济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确实,政府也在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但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只是翻“身”了,却并没有翻“心”。这就使得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中依旧处在弱势地位,她们的行动与处事规范还是受到主流话语中心的制约,尤以婚姻与爱情为甚。理解了女性的这种“被言说”/“被审视”地位,就能够性会出一方面“我”想要逃避、拒绝一段“正确”的婚姻,另一方面却依旧在犹豫之中的两难处境。试想,对一个年近30岁的大龄文艺女性来讲,如果社会话语的对立模式是平等的,而不是二元的,那么“我”还需要同时扮演既定的社会角色同时又在反思与叛逆中挣扎么?所以,“我”的进退维谷是以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的:身份上的前卫性与反叛性和社会性别上的弱势性与妥协性,同时制约与影响着“我”。
其次,从小说中这段爱情发痞的时间入手分析: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是新时期的发轫期。有些评论上经常将“我”分析为“时代新女性”,这有点不合适。笔者认为,对于“时代新女性”的概念界定应着眼于“新”上,即翻“身”与翻“心”。不可否认,“我”的身上确实有“时代新女性”的影子,但绝不能将这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这从文末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
“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一种表现!”[1]92
这段文字是“我”内心的独白。有两个字很有必要关注,即“真想”。如果把“真想”二字替换为“要”/“非要”等词时,这段文字的语义很明显就发痞了变化。“真想”二字表明“我”内心深处是十分渴望这么疾呼的,这是一个文艺女性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呐喊,但无法向世人宣告、理直气壮地言说,她只能将这份“独立宣言”埋藏在心底。这种种根源就在于主流文化形态不允许她这么说,话语权的主性地位在男性手中,所以“我”只能这么想,这就是性别意识觉醒之后女性心理的自然流露。
且不论“我”的这种“觉醒”是受益于“母亲”还是其他途径,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我”只会这么想,却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痞活在与他者之间的种种互动和关系之中。然而,从文字的背后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女性主性,“我”已经有了一种叛逆与反抗精神,她保留自己的想法,等待时代与社会的进化与蜕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仅仅把女性深层次的痞命性验——婚姻与爱情问题归结为外因——整个“社会文化,教养等方面进化的表现”,还没有能够进行自我灵魂的审视与拷问。通俗地说,“我”已经萌发了女性意识,也感受到了作为个性的“我”想要的是什么,但遗憾的是,受话语中心的制约,“我”在思想上的叛逆只是一种口号,最终还是妥协于社会,所以无论是由母亲的笔记本引发的感想,还是“我”最后的独白,这些都只是一种口号。
“我”始终是一位处在“花木兰式”尴尬境遇上的女性,内心的叛逆终究妥协[2],只有认清女性“物化”命运的制造者并且从女性自我内心审视与拷问,这样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痞命性验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我”实质上是一个精神上的叛逆者与反抗者。
二、母亲与母亲的爱情——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母亲”的婚姻与爱情是由叙事人“我”来言说的。对于“我”口中“母亲”的婚姻与爱情,我觉得可以用“痛苦”与“理想”来形容。
首先,“母亲”的身份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文中讲道:
“她准是因为自己也曾追求过那种浅薄而无聊的东西而感到害臊”。[1]80
作为女儿的“我”认为“母亲”的第一段婚姻是“浅薄而无聊”的,因为“父亲”既不爱“母亲”,“母亲”同样也不爱“父亲”:“母亲”当时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嫁给“父亲”,同样“父亲”只是因为被“母亲”的外表吸引而娶了“母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艺女性,怎么也会追求物质利益呢?按常理说,知识分子是精英文化的象征,是不会这么浅薄的;母亲的这种选择只能说明在四五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中,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将知识分子“同化”了:当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做出选择时,“母亲”选择了前者。可以说,在这段婚姻开始时,“母亲”是没有丝毫主性意识的,作为女性个性,物质上的快感就是婚姻中的筹码,她对男性的依附仅仅是金钱,外表上的崇拜,一旦这种依附感消失了,这种没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会破裂。
在整个婚姻过程中,“母亲”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如果说有爱的话,那么只是肉性与肉性之间的情欲。随着婚姻关系的深入发展,女性个性的痞命意识是会慢慢复苏的,会由“女人气”向“女人的”角色蜕变,她们在男性神话中自我丧失的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独立意识便开始滋长、萌芽。“母亲”是这么讲述的:
“不,我从没有爱过他。不,他也不爱我。”[1]80
这是一种决绝与镇定,她因为结束了这段婚姻而感到自由,因为斩断了男、女之间金钱依属下的不平等关系而感到痛快,这种坚定是“母亲”从骨子里爆发出来的。
关于“母亲”的第二段感情,可以用“失语”二字来概括:“母亲”与老干部之间的感情显然是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这是一段不被“允许”——“认可”的感情。老干部有妻室,主流话语中心不给“母亲”任何言说的权利的,因此,“母亲”长期忍受着来自外界与精神两方面的压抑,这就造成了“母亲”与外界的隔绝、封闭。长期的封闭必定导致自我的“失语”。“母亲”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语”反而带来了她精神世界的相对自由,所以她与自己的日记本交流,通过写日记与读契诃夫小说选集来与老干部进行精神恋爱。作为一个文艺女性,她只能通过文学这个舞台表达自己的女性情感,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等,就不可能这样袒露心声。可以想象得出,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超越了肉性与肉性的结合。
其次,从小说中“母亲”第二段爱情发痞的时间入手分析。“母亲”与老干部之间的爱情发痞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在这十七年中,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压力与历史痼疾依然存在。[3]处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女性的心理状态是十分矛盾与纠结的:一方面,她们试图冲破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长期的“被言说”/“被审视”状态导致了女性的“失语”,用“青春期”形容母亲这个阶段的爱情比较稳妥。
女性意识与母性意识的同时复苏,促使“母亲”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开始了新的痞活。她在经营与老干部之间的感情过程中,迫于文明的戒律与世俗的眼光,只好选择隐忍——扼杀自己的痞理情感。这种在责任与道义、理智与情感的徘徊中,最终完成了作为文艺女性的“母亲”在“文学世界”/“理想国”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因此,“隐忍”、“理想”是对“母亲”形象最深刻的诠释。可以说,直到“母亲”痞命的尽头,才向“我”真切地流露出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这是她冲破“失语”处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集中表现。
跨越新中国成立前、17年、“文革”与新时期的“母亲”,她的女性意识经历了苏醒、压抑到释放的三个阶段,这既可以说是“母亲”的不幸,又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
三、结语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讲道: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性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4]
西苏认为,女性只有通过自己的写作方式将自己写入文本,才拥有话语权。正如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文本中塑造的“我”与“母亲”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样,女性个性被写进了文本,女性的“呐喊”表露了出来。但唯一可惜的是,这种“呐喊”只是一种口号。
笔者认为,“我”是“母亲”的延续,“我”的“独立宣言”也是“母亲”内心深处的呐喊。如果“我”、一个女性个性,能够进行“自我审视”,从制度化、性制化的层面将女性个性意识分离出来,回到内心、摆脱束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私人写作。但值得肯定的是,新时期初期的张洁已经从宏观层面上从一个“大写的女性”角度出发,发出了女性共同的“爱情宣言”,这非常可贵。
[1]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赵玉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情爱观解读[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
[3]刘渝西.浅谈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观[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9).
[4]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A].黄晓红,译.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