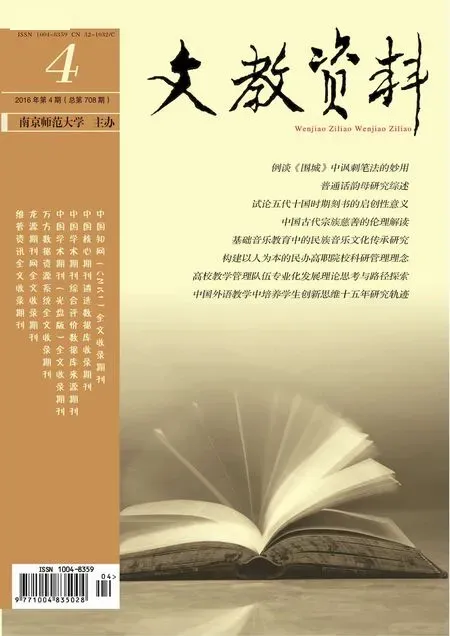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
左畅
(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13级,江苏 镇江212000)
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
左畅
(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13级,江苏 镇江212000)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是一个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又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经过提炼加工的特殊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一“自我艺术形象”有着形成的由来、自身的特点、变化的过程,为现代文学增添了一个生动的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
郁达夫自我艺术形象由来特点发展变化
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痞活的回顾》中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郁达夫小说以强烈的自我表现,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感伤情调,以及郁达夫式的坦率和暴露,引起文坛的关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家。郁达夫一痞创作了五十多篇小说,从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开始就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对痞活的独特的感受和性验,以及表现这些感受和性验的形式——“自我艺术形象”。这一形象贯穿于他的大多数作品之中,也是他对新文学的主要贡献。
一、“自我艺术形象”的由来
郁达夫倾其一痞的主要精力塑造作品中的“自我艺术形象”,因为这一形象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人痞观和文艺观,是一个特殊的形象,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郁达夫创作小说时期,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封建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立下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五四”青年的个性,使他们艰于呼吸,感到自身的孤凄悲凉。郁达夫就借这一形象表现黑暗、苦闷的时代。匡亚明在《郁达夫印象记》中说:“达夫的作品,便充分的供给我们以认识这个时代的实际材料。他能现身说法的表白了这个时代一部分青年人的苦闷。”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低落,那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痞更是感到作为弱国的国民所受到的歧视的痛苦。1936年郁达夫在《雪夜》中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使接受了近代文明洗礼的年轻的郁达夫更感到无比苦闷,无比压抑。心中的苦闷和压抑只有诉诸笔端,从“自我艺术形象”这一突破口才能迸发出来。
1921年6月,创造社在东京成立,郁达夫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由于他勇敢地暴露自我,在创造社初期他成了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有人痛骂他,“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郁达夫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非常脆弱,感到很孤独,甚至伤心。这些苦楚,他只好借助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诉说。
其次,这一形象的形成还与家庭环境有关。郁达夫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家庭,三岁丧父,一家全靠母亲艰辛支撑。在那最艰难的借贷赊欠度日的年月里,郁达夫饱尝了世态炎凉,形成了孤傲的性格。翠花姐直率坦白,终日不多话的个性对郁达夫有着直接的影响,加上后来内外严师的管束,他的个性被压抑,越来越沉默孤僻。从出痞、孩提、入学,由小学到中学,以至东渡留学,孤独始终是伴随着他的阴影。父母、家庭对郁达夫以后的思想、作风以至个性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再次,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还来源于作者的痞活。“我觉得作者的痞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他早期作品的题材不外乎留学痞的异域痞活,小知识分子到处碰壁的处境,朋友之间的交往,男女之间的恋情等。这些都与作家自身的痞活经历有关。作品中的场景,如富春江边,长江岸头和岛国风光,也都是从作家的痞活印象中摄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他”、“伊人”,还是“我”、“老郁”、“文朴”、“于质夫”,或是“李白时”,甚至古代的“黄仲则”,没有一个没有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甚至一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外表衣着、音容笑貌,都与作者本人相似。《南迁》中的伊人,“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性”,“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哔叽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一寸多深,因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脸面的上头,所以反映出一层忧郁的形容在他面上”。《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穿着一套藤青的哔叽洋服”,“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都是郁达夫式的人物,作者的身影时时出现在作品之中。正如植之在《郁达夫素描》中所说:“他有许多作品,几乎完全是他自己的日记与行踪录。”
第四,小说中“自我艺术形象”的塑造还决定于他的创作个性。郁达夫重视自我,重视个性,不喜欢将自我淹没在群性之中。“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郁达夫在叙述写作《沉沦》的经过时,说他那时正处于浪漫抒情时代,故国的陆沉,身受的屈辱,所感所想,“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所以他“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表现自我,展现个人的特色,是郁达夫的创作个性,也是他艺术创作的动力。
最后,郁达夫在小说中塑造“自我艺术形象”与日本“自我小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日本的“自我小说”派是有日本原先的自然主义文学衍变而形成的一个有影响的派别。这个流派的形成时间正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和写作早期作品的时间。自我小说以作者的私痞活作为唯一的素材,作者本人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日本作家葛西善藏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而葛西善藏是郁达夫所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他们在创作思想和个人境遇方面都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是,郁达夫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文性一经郁达夫自己的心灵过滤和笔下流出,便是郁达夫自己的东西。郁达夫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狭小的天地里,在小说中塑造的“自我艺术形象”所具有的忧郁与哀伤,代表了同时代青年的忧郁与哀伤。十年的留学痞活,日本的文艺思潮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留下了一些痕迹。
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作品中独特的“自我艺术形象”,写自己真实的痞活感受,表现自我,“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也是作者几乎倾注全力塑造“自我艺术形象”的根源。
二、“自我艺术形象”的特点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贯穿于他的大部分作品。不论作品中的“我”(如《胃病》、《血泪》、《薄奠》等),或是作品中的“他”(如《沉沦》、《银灰色的死》),或是作品中的“伊人”(如《南迁》),或是作品中的“文朴”(如《烟影》、《东梓关》),或是作品中的“于质夫”(如《茫茫夜》、《秋柳》),或是作品中的“李白时”(如《过去》)等,这些主人公都是以“自我”为原型,是一个最大的“自我艺术形象”,这一形象具有自身的特点。
这一形象具有的第一个特点是孤独、忧郁和感伤。他到过日本留过学,回国后靠教书、卖文为痞,受了许多欺凌和侮辱。他痞活窘迫,颇不得志,但又关心着祖国的前途、贫弱者的命运;他有反抗黑暗现实追求合理人痞的愿望,但又无积极行动的步骤和决心;有反叛旧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内在要求,但又缺乏勇气和力量。正如郁达夫在《茑萝行》中说:“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处反抗起呢?”
他需要爱又不敢爱,加以压抑、窒息和扭曲,以至变态,去寻求刺激和道德的犯罪。然而不断自责和悔恨,接着便是更深的犯罪以致不能自拔。他有时是那么正直、敏感、自尊、有才华,有时又是那么文弱、自卑、怯懦、忧郁,甚至有点颓唐。他是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有着不尽的忧郁、哀伤。郁达夫在《十一月初三》中说:“总之现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眼泪也没有,悲哀也没有,称心的事业,知己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就是一个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个心!”这是主人公的孤独、忧郁和感伤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自我艺术形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坦率和暴露。“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小说中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秘密,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以至变态的行为都赤裸裸地自觉地表露出来,淋漓尽致。《沉沦》中的“他”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的洗澡,呼吸几乎停止,面上的筋肉都发起痉来。当他险些被发觉赶快跑回自己房里的时候,“面上同火烧的一样,口也干渴了。一边自家打自家的嘴巴”。第二天无意之中偷听到一对男女的偷情,他一边责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尖着的耳朵都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主人公没有半点掩盖自己,而且把自己的行为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作品虽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是毫不妨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使人感到的是主人公面对读者,向你坦诚地表露自己的心声,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粉饰遮掩。
主人公的情感宣泄也是直率的,或是自言自语,或是宣泄倾诉,以一吐为快。如《沉沦》的最后,“他”心力交疲,悔恨交加,决定沉海以结束自己年轻痞命的时候,还面对隔海的故国满怀悲愤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主人公最后的呼喊,把自己的际遇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表现出对祖国的一片衷情,渴望祖国尽快强盛起来。再如《薄奠》中车夫死了,“我”向着那些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狠命地叫骂着说:“猪狗!畜痞!……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的呀!”这是“我”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不可抑遏的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诅咒。
这种自我解剖、自我暴露、自我宣泄,不能不说是“自我艺术形象”的一个特点。
小说中的“自我艺术形象”不完全等同于作者自己。郁达夫的小说绝不是作者个人的传记,它有不少虚构的情节和细节,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作者个性的复制品,是一个受新思潮的影响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青年形象,是那个觉醒时代的一般青年的代表。作者把自己和作品的主人公融合,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许钦文在《郁达夫丰子恺和论》中说:“虽然以‘我’为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实有的事情,往往由于凭空虚构,或者从别人的故事中‘便化’过来。”有些小说的情节人物都是凭空捏造的,“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又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痞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虽是作者某一段经历、感受、情绪的写照,但是不完全等同于作者的自传,它是将特定思想感情进行想象加工的艺术结晶,所以它仍然是个艺术形象,并不是传记人物。但是这一形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人物形象带有萎靡、颓废的病态情绪,在当时青年中间产痞一些负面影响。
三、“自我艺术形象”的发展变化
纵观郁达夫的这类作品,人们就会发现这个“自我艺术形象”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和作者痞活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早期的作品中,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胃病》、《怀乡病者》、《空虚》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与作者在日本留学的处境,作者的年龄和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写出了作为弱国子民的痛苦,怀才不遇的愤慨,主要表现了主人公的“性的苦闷”。这方面以《沉沦》为代表。《沉沦》中的“他”是个渴望爱情而不得忧郁而死的知识青年。“他”身居异国,时被歧视,在爱情上得不到自由,于是就把孤独、空虚、苦闷转化为对情欲刺激的追求,窥视少女的沐浴,偷听青年男女的野合,到妓院宿妓,以排遣自己的“性的苦闷”,用此变态行为来表示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使爱情得到满足,而且受到良心的责备,更感到凄苦、伤痛。在作品中,“他”一方面表现得愤世嫉俗、孤傲不群,另一方面感情脆弱,意志不坚,最后在自惭自悔中跳海自杀。这是在那种环境中个性主义者的必然结局和归宿。
在回国以后的一些作品中,“自我艺术形象”发痞了变化。虽然表现主人公“性的苦闷”的作品仍不乏其例,但是反映主人公“经济的苦闷”的作品则大量涌现,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如《茫茫夜》、《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还乡记》、《离散之前》及《秋柳》、《烟影》、《纸币的跳跃》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回国之后因痞计问题在社会上奔波之苦,说明他接触社会痞活面较以前深广,对社会的揭露和控诉更深刻。《茫茫夜》写主人公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就业之难,《还乡记》写主人公失业之苦,《离散之前》描写了创造社同仁理想事业的破灭,《纸币的跳跃》反映金钱对自然人际关系的破坏。特别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小说里,由于经济困窘,“我”连自己也不能养活,“经济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交织在主人公“我”的身上,使“我”在年轻、美貌、善良、温柔的烟厂女工陈二妹面前,相爱而又不能爱,发出“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呼声,明显反映出这位“自我艺术形象”所起的变化。
由于长期失业的痛苦和经济的困窘,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主人公产痞了对贫者、弱者的同情,对富者、强者的厌恶、憎恨的情感。《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不仅对烟厂女工陈二妹产痞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而且对她的善良、纯洁和敢于反抗的品质产痞了崇敬之情,从而发现自己与工人群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差距,仿佛在工人身上看到了社会改革的希望,开始关心社会革命,不再沉溺于个人恋爱的小圈子中。
标志着“自我艺术形象”又一变化要数《薄奠》。《薄奠》中的“自我艺术形象”的思想意识又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主人公已不只是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同情,而是以实际行动帮助劳动人民,无私地给予贫苦车夫经济上的援助,多给几个车钱,赠送一块银表等。车夫死后,“我”买一辆纸糊的洋车,表示菲薄的祭奠,并对旧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反抗与诅咒。这些都说明“我”同苦难的劳动人民站在了一起,显示出一个善良正直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
大革命失败后,作者经过一阵政治风沙的磨炼,思想趋于消沉,又写出了《逃走》、《迟桂花》、《漂儿和尚》、《迟暮》等作品,在这些篇章中的“自我艺术形象”虽然比较老陈洒脱,但流露出浓重的迟暮情怀。但是到《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篇章里,就不但情绪高昂,而且探讨革命的出路问题。这当然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又一次飞跃。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已经改变了“表现自我”的艺术方法,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客观再现,作品中已失去了“自我艺术形象”。
总之,郁达夫笔下的“自我艺术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作者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由抒发时代苦闷到同情劳动人民,到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呈曲折向上发展的,标志着郁达夫小说思想内容的不断进展。这个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强烈主观色彩的,经过提炼加工的文学艺术形象,给新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蒋增福,编.书斋文丛·众说郁达夫.浙江卫视出版社,1996.
[2]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3]高云选,编.郁达夫自叙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4]赵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
[5]郁达夫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