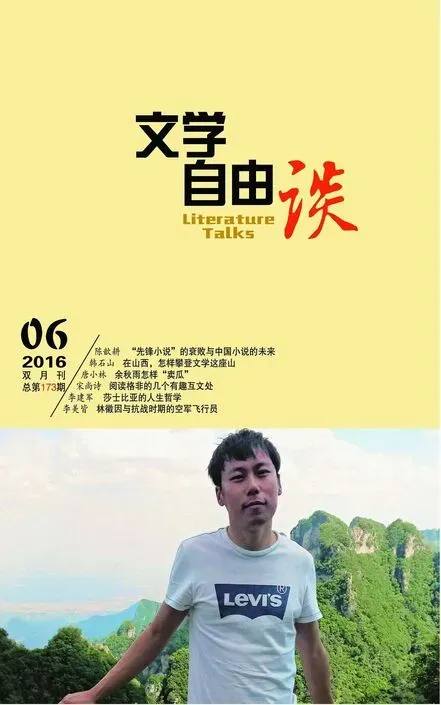贴地而飞的朱山坡
□武 歆
贴地而飞的朱山坡
□武歆
1
与朱山坡相识是在广西,他的家乡。很多年以后,我依旧会认定,与一个人的相识,地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符号。
与朱山坡一起参加的那个比较热烈的活动,是在6月潮湿、闷热的桂北地区。我是一个每逢活动更愿意站在后面的人,所以能看清许多人的肢体动作和真实的侧面表情。我发现,同样喜欢站在后面的朱山坡是一个不言不语的人。或是骄阳下或是人群中或是餐桌旁的朱山坡,始终都是面色平静。“面色平静”似乎不太准确,应该是“不动声色”。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无论怎样的环境,无论怎样的天气,也无论怎样的场合,一个始终不动声色的人,肯定是一个能做大事情的人。眼下朱山坡做的大事,从他镜片后面那若有所思的眼神中,基本就能揣测出他在做什么——肯定是在屏声静气地写小说,安静地打造自己的“小说宫殿”。大凡深陷创作状态中的写作者,目光好像都会有些恍惚。那略带恍惚的目光,在其他写作者看来,则是令人无比艳羡的状态。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广西有个“写小说的朱山坡”。虽然在70年代作家中,朱山坡不是一个大红大紫的人,但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应该承认,经过十年的思考、写作,朱山坡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景。大概发表于十年前的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让朱山坡在中国文坛“七零乐队”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山坡乐声”。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朱山坡用百多万字的短、中、长篇小说,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压住了自己的写作阵脚,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了飞翔的姿态。
2
朱山坡的小说,从题材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但即使写城市生活的《灵魂课》、写大学校园生活的《驴打滚》等,也依然在字里行间弥漫着来自乡村的一丝气息。那种桂东乡村的气息挥散不尽,氤氲在他的文字中,似乎也只有把自己弥漫在乡村的气息中,他才能更加叙述自如;也只有如此,他小说的内在意蕴才能更加饱满、丰盈。
坦率地讲,我还是喜欢朱山坡书写小镇生活、小镇人物的那些短篇小说,尤其是书写“过去时的桂东乡村”,文字精致、叙述大气、视角诡异,在不事声张的如低声般的讲述中,却又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凌厉攻势。
短篇小说《天色已晚》的故事很简单。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带着母亲给的六块钱去镇上买肉,了却 “可能是最后一次吃肉的、86岁祖母的人生愿望”,同时也包括“我的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当然还有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日子的热烈向往。但“我”还是因为从没有进过电影院的长久诱惑,忘记了母亲“把地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而换回来的六块钱,同时必须用“六块钱买来三斤肉”的郑重嘱托,在不堪电影院收票人的奚落下,竟然花了两块钱,自尊地看了一场将要散场的电影,了却了多年来只能在电影院外面“听电影、想象电影”的遗憾。但最后镇上卖肉的屠户在知道“我”只剩下四块钱的情况下,依然给“我”称了三斤肉,并在镇上所有店铺已经收摊的情况下,委托那个电影院收票人把三斤肉给了“我”。
这是朱山坡近期的一篇小说,虽然在这篇小说里,他的小说内涵“电影—理想,肉—现实”充分暴露在外,他想要表达的“小镇少年的理想、普通人内心温暖”的想法也是直面显现,但我还是异常喜欢——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潜藏在每个文字内部的叙述力量,喜欢他自由营造的那种怅然、忧伤、感人的文学气氛。
“邻居家传来的肉香,引起了我们一场舌头上的骚乱”;“午饭后,我把钱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撒开双腿,像一匹第一次离开马厩的小野马,往镇上飞奔,我的身后扬起了滚滚黄土”;“暮色从街道的尽头奔腾而来”;“安详的祖母躺在床上,她见多识广,老成持重,不像兄妹们那么急不可待,但也伸长了脖子”……朱山坡用这样简练而又韵味无穷的语言所构建的生活场景,会让心烦气燥的阅读者很快就能沉静下来,即使没有经历过那段困苦岁月的人们,也能从这样感情充沛的描写中,想象出来“能够吃上一块肉犹如人生大事”的那不堪回首的困苦岁月。
这篇小说也就五千来字,但每个有名字的人物都是活灵活现:“说我妄想用六块钱买一头猪回家”的肉行屠户老宋;“大家来认识这个小偷,今天偷看电影,明天就会偷看女人,将来会偷遍全镇”的电影院收票人卢大耳;当与银幕上《伊豆的舞女》中的熏子相遇时,“下意识地直了直身,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这将是我和熏子的初次相见,我还快速地整理了一下仪表,双脚相互搓掉了对方的污垢”的“我”。
朱山坡在“紧迫的时间”和“逼仄的空间”里,不仅关照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了营造小说的氛围,也让那些没有名字的背景人物独立鲜明地出现。譬如“卢大耳说了,只对你收费,因为你‘听电影’听得最认真,电影里的门门道道都被你听出来了,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没有多大区别”的那些屠户老宋的同行们。这些屠户们虽然是以“声音”出现,但是每个人的肢体动作、脸上的表情,阅读者都能在心里把他们准确地描绘出来,并且栩栩如生地站立在面前。
朱山坡书写小镇上的各色人物,总会让人想起曾经影响过斯坦贝克、塞林格和阿莫斯·奥兹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想起十多年前曾被中国作家反复提起、挂在嘴边上的《小城畸人》。我是读过舍伍德·安德森,再读朱山坡的,因此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种感受,相信依照如此顺序阅读的人,心中都有那种感受——朱山坡的气势并不逊于舍伍德·安德森。尽管这样比较毫无意义,也不具备类比性,甚至也有可能对于低调的朱山坡不是一件好事,但莫名其妙地,我还是想这样讲,况且讲出这样的阅读感受,也不会天塌地陷。记得徐则臣在“确立自己阅读标准”的进程中曾经这样说过:要快速远离阅读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那种“基本上见了大个儿的就当神儿,见了神就拜”的“阅读萌芽期”,从而才能快速走上 “三、五年过去,你未必就比他们差,已经不比他们差,至少作品中一度神秘莫测的部分在你已经了然于胸的”那种“残酷且快意的阅读征程”。这样的阅读标尺,其实也是作家写作进程中如何测量自己水准的内心标尺。
3
朱山坡描写苦难、描写艰难的“乡村小说”,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锐利”。但这种锐利,绝不是一味地展示贫穷、绝望、困境,而是深入人心;而穿过绝望、困境之后,最后朱山坡真正想要书写的,还是人的内心柔软,还是人的理想憧憬、温暖怜悯、意志尊严。尤其是对尊严的抒发,朱山坡总是荡气回肠。
在朱山坡所有的小说中,“尊严”永远隐蔽在那些独特文字的背后,永远是他书写的主题,就像他的小说《回头客》里那个自尊的父亲。面对村子里的流言蜚语,哪怕从来没有人面对面跟他讲过什么,但父亲也绝不允许,甚至绝不苟活,宁可把自己和船一同沉在水底,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用生命抗争命运、挣回尊严,是朱山坡心中永不倒下的一杆大旗。在阅读朱山坡小说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想象朱山坡在来到广西首府南宁之前的日子。在没有看过他的自述之前,我认定他过得并不愉快。看过之后,更加认定了这样的想法。
“我极力按照父亲的期待去做。参加工作后,我到了政府机关上班,我的目标是尽快当上一名副乡长,以满足父亲平生之渴。为了这个目标,我付出了十年之功却没能实现。”在朱山坡的自述中,“十年之功”被他轻松带过,但我相信有过“直接感受”或是“间接感受”的人,都能想象到在他内心深处的波浪翻滚。在诸多生活的波浪中,只有尊严的波浪永远不会停歇,永远击打心灵的堤岸。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做十年最重的活儿、可以十年不吃肉、可以十年不买一件新衣服……这一切,都不能让一个人永生铭记,唯独尊严,一生之中哪怕有过一次尊严被人践踏,你都能永生记住。为了“尊严”这杆大旗,朱山坡尽情挥洒自己的想象力,书写自己的生命主张。应该承认,朱山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但是他的想象力,都起飞在他命运的雪橇上,不是天外来物。我能理解朱山坡。在我18岁那年,曾经掌握我命运的一个领导,用手指着我的脸说:“你还想写小说,我让你一辈子在我这里抡大锤!在我这里没有‘飞鸽牌’,都是‘永久牌’的!”就是那个人的这句话,愚笨的我才歪歪扭扭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许多时候,那个曾经侮辱过你的人,会让你的尊严在日后变得异常坚固。那个曾经用手指着我脸的人早已消失,但他狰狞的容貌我至今还记得牢固清晰,每当读书、写作出现慵懒、懈怠的时候,那张脸都会神奇地飞到我的眼前——无论窗外冰雪、寒风,抑或闪电、惊雷——让我拥有不可抑制的写作力量。
朱山坡是一个谨慎的人,所以他“起飞在雪橇上的想象力”不会漫无边界,肯定贴着地面疾速飞行。许多时候,一个作家写出怎样的作品、能够写出怎样意境的文字,完全是一种宿命,是早已放在那里的东西,你只不过取来使用罢了;它永远等着你,不会因为你的迟到而让别人拿走。
我始终觉得,貌不惊人也不高大伟岸的朱山坡,面对小说、面对小说里的人物,却像一个强硬的铁腕人物,始终居高临下地掌控着叙述进程。他做得不错,就像他的为人处事,尽管内心孤傲,但总能做到不动声色。掌控小说的那双手,总能恰到好处地隐蔽起来。就像刚才说的,朱山坡对他小说叙述进程的有力掌控,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具有“贴地飞行的姿态”。我在阅读朱山坡的小说时,总是感觉他的小说具有《十日谈》一样的文学气质——“虚构的情节”,让他的小说“连着天”;“真实的细节”,又让他的小说“接着地”。离地而飞,但又绝不虚张声势。因此,在他大气、从容的笔下,经常会出现怪异的人和怪异的事,比如“与鸟住在一起的父亲”,甚至最后“父亲”“跟随鸟儿,离家越来越远”的《鸟失踪》。这篇小说,让他的文学气质具有插上翅膀的傲然气势。这是一篇越写越飞扬的小说,虽然在我看来,它截止到“最后讨厌父亲但又始终寻找父亲的母亲,最后忍着对鸟毛的过敏,也在鸟儿中间”时,我以为小说到这里已经很好了,不应该再有后面“大约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多余的内容,但瑕不掩瑜,我还是觉得这是一篇“畅然飞翔”的小说。当然,这只是个人之见。
4
我不了解朱山坡的阅读范围,但从他的小说能够看出,他被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两口大缸同时浸润着。他的故事是中国的,但讲述方法是西方的,最为难得的是,他把二者极为“友好”地融和在一起,看不出“隔”,也看不出“拿”,似乎就应该这样,才能“看上去很美”。
朱山坡在《鸟失踪》里这样讲“父亲”:“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人在山里看见过他,他就躺在树上,那只鸟和一群形形色色的鸟在树冠上叽叽喳喳。”我记得很多年前看拉什迪的《羞耻》,拉什迪在描述那位做了18年鳏夫的老沙尔克时,也是这样如此地想象、描述:“他声音激烈,连床头的空气也沸腾起来。”《鸟失踪》里写了住在树上的“父亲”:“母亲有些担心,想把父亲拖回家,但他不肯从树上下来”。她甚至不断给那个与“父亲”相好的贵州女人钱财,让她找回“在乌鸦岭接近峰顶的地方,在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上”的他。大师卡尔维诺也曾把那个著名的男爵狠心地放在树上,那个男爵也是不愿从树上下来,因为“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但是讨厌的原因非常简单:“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鸟失踪》里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位“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的人,像极了那位男爵。
如同其他70后作家一样,朱山坡曾经受到西方文学很深刻的影响,从他的小说构思乃至叙述方式,都有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子。但“70年代作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深陷其中,没有邯郸学步,而是矫健地踏浪前行;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在他们身后飞溅起的不是“卡尔维诺浪花”,而是地道的“中国浪花”。
从叙述方式、构思方式以及想要表达的思想,朱山坡都是一个充满耐心的人。他具有极大的耐力,绝不着急,慢慢地靠近经典。就像他自述讲的那样:“我突然变得不急,变得只有理想而没有野心。”但我想,“理想”过于书面,还是“野心”来得蓬勃、澎湃;况且写作者拥有野心,也并非一件坏事。你说呢,山坡兄弟?
朱山坡曾经崇拜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是他接触到的第一部文学经典。他曾经对天发誓:“想在《伊豆的舞女》身边立起另一座丰碑,但那么艰难那么遥不可及。然而,我的心一直在蠢蠢欲动,像一只蟾蜍要跳到月亮上去。”
其实,现在的朱山坡已经不仅能跳了,还能自由地飞翔。飞翔的姿态有很多种,有人喜欢盘踞在高空,耀武扬威。但朱山坡的飞翔,属于贴地而飞,而这样的飞翔更具野心,因为他的家乡广西有着魅力无穷的山水,贴地而飞,恰能让家乡的山水成为自己的美丽背景。
可是,无论如何,朱山坡终将都是一个谨慎的人——“我肯定成不了大师,但努力成为一个一丝不苟的匠人。”我想要解读的是,只要转换一个角度来看,“谨慎”也是匠人走向大师的必要操守。
同时,朱山坡也是一个具有孤独气质的人。对于作家来说,孤独并非不好,它甚至还具有高冷的哲学气韵,就像写出了《阿克拉手稿》的巴西著名作家保罗·柯爱略说的那样:“爱是神的状态,孤独才是人的状态。”
《两个少年的长征》
李秀儿著晨光出版社
两个少年的长征路,一段曲折的成长史。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火线从军的两个少年,经历过哪些战火的淬炼,内心的煎熬?他们身上的“缺陷美”,更能逼近那一段鲜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