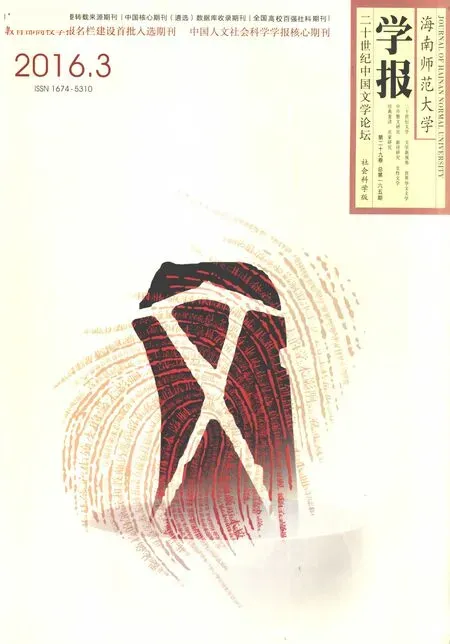艺术禅趣与形上本体
舒志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艺术禅趣与形上本体
舒志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艺术禅趣的空灵之境的形成,除了根植于中国传统的诗论之外,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是佛学中的形上精神。此种形上精神的渗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思想的问题域由“道”向“理”进行了更换。文章对于艺术禅趣的考察同样置入了这样一个视域。文章同时认为,佛学的形上精神对意境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佛学;形上精神;禅趣;意境
艺术禅趣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兴趣、妙悟均有甚大的关系,可见禅化诗性思维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成熟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诗性思维中国自古有之,意象理论、言意之辨中国也早已萌发。那么受佛学浸染甚深的禅化诗性思维及所营造的空灵之美到底与儒道的德性思维主导下的诗性理论有何区别呢?对于此问题的探究,我们不能单纯局限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视角而应该越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范畴,才能厘清其中的关系,寻找其中的脉络。
佛教的东传,从中国古代思想交流史上而言,是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经过近一千年的流变,儒释道终于在宋代左右完成了各自对对方的吸收、兼容。而此种互动,与中国先秦思维相比,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重新排列组合。这种根本性的变动,其所辐射的不局限于宗教信仰方面,更达致于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层面。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现象,在艺术、文教、政治各个层面荡起涟漪,开花结果。艺术禅趣的产生同样也应该置入此思想史上的大变动的视域中,方能得到根本性的检视。
一、 由“道”到“理”:形上精神的凸显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界的分期大抵上是宋之前为“道”,宋之后是“理”,一“道”一“理”,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域。由“道”向“理”的转变,其中便有许多机窍,而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动因素,即是佛教的东传。在宋明理学中,佛教的超越性思维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思想生发出了超验的一维。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先秦思维一直是以德性思维为中心,其孜孜以求的是总体性的“道”。“道”与“德”无疑是先秦思想的两个内核。《庄子》论道,《老子》分为“道篇”与“德篇”,《论语》中的“德”亦是“仁义礼智信”所要趋向的。但是无论是道家的“道”还是儒家的“德”,其都没有超验维度的出现。在《庄子·知北游》中有这样一段著名对话:
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陈鼓应:《庄子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4页。
同样在儒家经典《中庸》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儒道二家虽然都是追求“道”,但是这一个道始终未脱离生命现象,亦即道不离器,我们需要于万事万物中去求得此道。
但是对于佛教而言,则并非如此。李泽厚认为:
佛学禅宗的化出的确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形上性格。它突破了原来的儒家世界观,不再是“天行健”、“生之谓易”,也突破了原来的道家世界观,不再只是“逍遥游”、“乘云气、骑日月”,这些都太落迹象,真正的本体完全是超越于这些生长、游、动静、有无”。*李泽厚:《华夏美学》,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3页。
所谓“形上性格”,所谓“不落迹象”,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哲学中的超越维度。佛教的总体指向是超越尘世,哪怕是在如此世俗化的禅宗中,也仍然是离尘出世的。“道”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是生命展开的一种总体态势。正如“道”之本义为“道路”一般,“道”的整体性呈现是离不开生命的自觉展开的,“道”的指向是一种实存指向,充满生命活力。而在禅论中所言的“空”、“无”,却比“道”更为“超迈”,这里明显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在起作用,是思维对杂质的完全摒弃,对生命现象的提纯,而追求一种远之又远的绝对“澄明”,类似后世理学所言的“太极”。由“道”向“理”转变的关键所在,即在于此种“太极”思维的加入。朱熹的理学体系区分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所谓:“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即是太极之全体。”朱熹明确主张“理在气先”,而且万事万物的根据即在此理。格致修身的目的即是谓了达到这样一个“理性”境界。这种将理与气进行明确分野,并在哲学地位与道德价值上分出秩序的做法,在先秦儒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此种转变,钱穆先生认为:“孔孟虽不言阴阳,然并不抹杀外界事物,盖孔孟所重在人生境界,易庸则越入自然界,而分创一套形而上学之意见。如再深细言之。易庸所涉,大体仍在宇宙论范围内,而宋儒如横渠、朱子,则富于形而上学精神,此种转变,实受佛学影响。”*钱穆:《中国学艺术思想史论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发掘佛学中的形而上学因素,并进而研究此种形而上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宋明理学的哲学构建,实在是一件十分艰巨但又极富意义的事情。这也是解决中国思想史上三教融合问题中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个巨大的课题,笔者在此只能挂一漏万。但有一点无疑是无法否认的,即是佛学对中国思想史的形而上学贡献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关键性维度的置入,可以说在整体上改变了国人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序列与排位,实现了福柯意义上认识型的转换。
二、 形上精神对艺术禅趣的本体支撑
我们所言的艺术禅趣实际上是离不开这样一种形上维度的支撑的,禅趣的空灵与玄远得以可能是因为首先预设了这样一种本体的存在。正是基于此,我们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如诗文、绘画、雕塑等艺术样态作为形式指引,才能逐步靠近那个绝对的澄明之域。本体的在场或者缺失,构成有无禅趣的关键,也实际上是后世主导宋明艺术创作的境界论的根据。本体维度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艺术中体味出“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禅妙境界。此种维度的缺失则就滑向先秦美学中的“言外之意”了。对于这种分别,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有着相当的敏感:
所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便是道,而非禅。“空山无人,花开流水”(苏轼)便是禅而非道。因为后者尽管描写的是色(自然),指向的却是空(那虚无的本体),前者即便描写的是空,指向的仍是实(人格的本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是禅而非道,尽管它似乎很接近道。“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采菊东西下,悠然见南山”(陶潜)却是道,而非禅,尽管似乎也有禅意。*李泽厚:《华夏美学》,第214页。
从李泽厚所引之诗可以看出,近禅之诗大抵空灵澄明,而近道之诗则不离生命的亲切。中国先秦诗学恰恰是在大生命宇宙视角下的一种构建。生命的感发、阴阳的相荡,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先秦诗学中处处不离生命,处处以生命为底色。无论是《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页。;还是庄子的“以天合天”,“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陈鼓应:《庄子今注》,第133页。的“天籁”;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9页。;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5页。,无不有生命的在场。中国在先秦的致思方式中,始终不离世间,着眼点始终是这一人文大群。在后世的诗论中,仍然如此,如钟嵘:“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周振甫:《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页。抑或是刘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4页。他们都是以自身生命对万物的接纳而产生的无限体验。
相比而言,佛家的视角是彼岸的,虽然经过禅宗的世俗化改造,信众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层面修行成佛,但相比儒道而言,其视角毕竟是“更高了一层”(钱穆语)。佛教的出世倾向,其理据在于设定一个洁静精微的西土世界的存在。这种设定的存在,使得与之对照的人世间变得无足轻重,也正是以此为视域,佛家才认为众生沉沦于苦海,不得解脱。世间种种多为幻象,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劝告世人的即是要放下对世间的种种执念,而趋向于一个无有挂碍、无有牵念的空无境界。这里的关键之点,还是在哲学价值序列层面对于彼岸性的东西给予了较高的位置,而在世间价值层面则认为是无意义的。对于世间万物的种种姻缘牵念,以佛教的视角观之,并没有发出儒道似的生命的亲切与可爱,看到的却是众生烦恼之根,其产生的是另一种崇高的情感——慈悲与怜悯,故而立志普渡众生。可见,在生命这一复杂的生命面前,儒释的分野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出这样的质疑:道家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陈鼓应:《庄子今注》,第205页。的反智式的举措,不亦是一种出世态度吗?然而细辨之,可以发现,道家的这种离经叛道式的宣扬,其实仍然是对生的执着,其视角仍然是世间的。所以道家看到人的天性因为礼法而受到禁锢,其发出的并不是佛家的慈悲之心,而却是愤世嫉俗、要求返璞归真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这一点,李泽厚看得比较清楚:
庄所树立、夸扬的是某种人格,即能作逍遥游的“至人”、“真人”、“神人”,禅所强调的却是某种具有神秘的经验性质的心灵体验。庄子实质上仍执着于生死,禅则以参透生死自诩,于生死正真无所住心。*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24页。
然而,正是禅化思维对于一个超越俗尘的本体世界的设定,正是观审世界种种幻象的彼岸视角的存在,使得其与庄子似的道家“逍遥游”境界而言,而高超也更深刻,这种高超与深刻,为审美想象延宕出一种极深而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回荡中,韵味才得以充分的酝酿,艺术的禅趣才得以可能生成,所以李泽厚同样认为:“(禅)这种与宇宙合一的精神体验,与庄子更深刻,也更突出。在审美表现上,禅以韵味胜,以精巧胜。”*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25页。
三、 艺术禅趣与意境
艺术的禅趣世界是高度意境论的,甚至可以说,这即是一个意境世界。意境理论的形成与佛教的渊源甚深,境界一词,最早即来源于佛教。然而,相比于词语的借用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支持。意境的核心即在于在虚实之间的配置,其见功夫处在于以精到的写实去触发无限的虚灵世界。这样一种空灵世界的绽放与敞开,给人无限的回味。庄子式的奇诡想象,是一种时空上的无限扩展,物类比例上的悬殊,然而这只是一种平面的铺展与推陈。相比而言,禅化思维所绽出的这个世界却有着无尽回响,这种回响预示着无限的深度。这种纵深感的存在,正说明了在此岸与彼岸之间距离的存在。在这里,很显然是因为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之间的那道“鸿沟”的存在使然。
所以,可以看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为何要“以禅喻诗”了,因为正是在禅的这种延宕与回荡中,“兴”才有可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唐人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严羽在这里所强调的“兴”不尽然与孔子所言的“赋比兴”之“兴”相同。对“兴”之较为公允的阐释,是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严羽这里所强调的“兴趣”的“兴”不在于物类横向的联想,而是一种纵向的跃进,要达到的是一个清明洁净的世界。所谓“不可凑泊”强调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的超感性性质。严羽认为这是“向上一路”,“向上一路”的说法正是来源佛教:“《传灯录》卷七:宝积禅师上堂示众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所谓“向上一路”,即是一种形而上的路向,而这种路向得以可能的前提是对形上与形下的理论的自觉,即“影”与“实”的深刻区分。
可以看到,严羽强调“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严羽的诗学之所以异于前人的独到之处,恰恰是因为其深受释家的理论影响而对诗境纵深拓展的强调。当然,这种影响是思维方式层面的,严羽了无痕迹地将其化用到了其诗学理论中。
四、 结语
审美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的哲学与美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柏拉图开始,历史上重要的西方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总体上诗与艺术在哲学家那里经历从驱逐、否定到逐步认可,最后取哲学而代之的历程。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艺术的本质的历史相应于真理之本质的转换”。*[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此言确实不虚。然而在中国的思想家那里,“美”与“真”之间并不这样的剑拔弩张,二者往往是水乳交融。这是中国哲学之幸,然而抑或亦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使得我们对于哲学的超越维度一直缺乏自觉,而对于诗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也局限于体悟层面。从这一点而言,佛教对于中国艺术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异质化而言,则尤为可贵。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Artistic Taste of Chan and the Noumenon of Metaphysics
SHU Zhi-feng
(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intangibility in the artistic state of Zen is theoretic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metaphysical spirit in Buddhism apart from its rootednes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while the infiltration of this metaphysical spirit is the key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history, thus having led to the shift from "Tao" to "truth" as to issues concerning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In this paper,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rtistic state of Zen within such a framework. Moreover, as is opined in the paper, the metaphysical spirit of Buddhism has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aturity of the artistic appeal theory.
Key words:Buddhism; metaphysical spirit; the artistic state of Zen; artistic appeal
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90-04
作者简介:舒志锋(1989-),男,江西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方艺术与美学。
收稿日期:2015-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