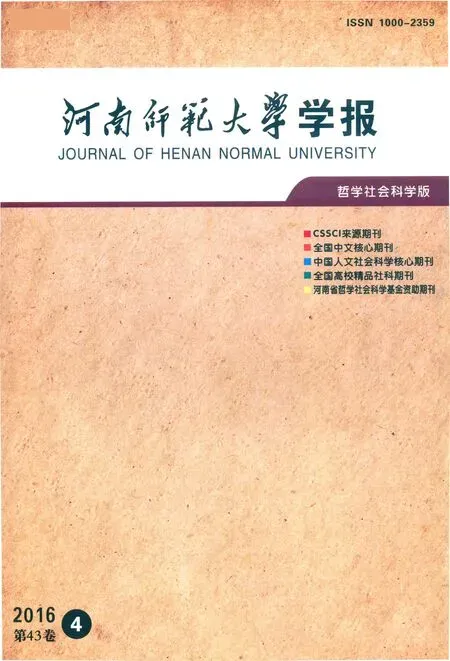技术变革视域下的国外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刘 春 荣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技术变革视域下的国外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刘 春 荣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技术变革导致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生产工作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劳动关系运行环境为其研究提供更多视角与领域。文献简要分析了基于技术变革的宏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职业结构,个体劳动者的技能需求、工作特征,以及微观组织内部的技术选择、工会化程度、雇佣规则等变化。中国经济转型关键在于技术的转型与升级。形态各异、交叉重叠的技术环境使中国劳动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多变,需要学者充分重视并给予细致深入的研究。
技术变革;劳动关系;宏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工作特征;微观组织就业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其和谐稳定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劳动关系运行受到多种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当前,技术变革的影响尤为显著。劳动关系发端于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漫长的市场经济历程以及交替重叠的技术革命为劳动关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劳动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就业、职业结构、工作特征、工人技能、工会和人本主义雇佣规则等六大方面。本文将对此进行系统梳理,为国内劳动关系研究提供新思维。
一、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
技术变革必然引起组织内部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变化,引起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宏观劳动力市场和微观组织两个层面。
(一)宏观劳动力市场
研究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首先要明确技术变革的性质。技术变革包括技术进步与技术退化,绝大多数的技术变革都属于技术进步,本文中的技术变革与技术进步同义。技术进步有中性与非中性之分:前者不会引起要素生产效率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与供求关系不变,要素市场维持原有状态;后者则会引起要素生产效率变化,要素相对价格、投入比例与市场供求关系均发生变化。
Acemoglu(2002)将非中性技术进步称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并将其细分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技能偏向型三种[1]。当某一地区大范围推进劳动偏向型技术变革时,必然会引起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供求关系失衡,这不是技术变革的主流;当资本偏向型技术变革成为主流,资本需求增加,劳动需求萎缩,大范围失业即将开始;当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成为主流,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结构性失业开始凸显。很显然,技术变革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技术变革在带来劳动力市场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同时,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催生新的劳动需求,此即为熊彼特等人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学说。Claudio Michelacci & David Lopez-Salido(2007)认为,工作毁灭主要受两种相反的力量影响:一方面,相对于新创造的工作,原来的旧工作变得更加过时;另一方面,工作毁灭与相应的工作创造都是有成本的。新创造的工作通常体现尖端技术(leading-edge technologies)[2]。技术变革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可能是扩张性的也可能是紧缩性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性质与推广力度。
除此之外,技术变革还会引起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分布趋势变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变革属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Acemoglu(2002)认为,如果工资是按照工人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支付的,这种变革势必导致工人相对工资的变化,以及工人之间的工资不平等[3]。Katz & Autor(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技能差异和工资不平衡的缩小,80年代开始由温和到较大幅度地上升,英美两国的上升幅度比较大[4]。长此以往,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什么?Gregg & Manning(1997)悲观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趋势(指工资不平等趋势)不会持续到未来,我们必须预期到,非熟练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将继续恶化。”[5]然而,Matthias Weiss(2008)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技术变革并不必然导致工资不平等提高。因为工资的决定不仅取决于相对劳动生产率,而且取决于产品价格。换句话说就是,要素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技术,而且取决于消费者偏好(例如,许多消费者对传统手工艺品的热衷)[6]。的确,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不平等性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尚不能定论。毕竟,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还可能受到劳资之间谈判力量和谈判结构(如集中谈判、分散谈判)的影响。
(二)微观组织
技术变革对微观组织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需求数量、需求结构和工资形式三个方面。
1.劳动力需求数量
技术变革对微观组织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其一,组织的技术革新性质。研究证明,大规模流水线作业使工作场所劳动力需求增加;先进制造技术(包括计算机数控技术、机器人等)可能使生产车间的工作岗位更少,劳动需求量大幅减少[7]。其二,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的相互作用。技术进步可能使资本的价格相对便宜,组织对劳动要素的需求减少;由于先进生产技术使产品价格降低,产品需求增加,劳动力需求自然增加[8]369;组织的劳动力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最终取决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相互作用。
2.劳动力需求结构
技术变革对组织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包括性别结构和知识技能结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新机器设备的推广使用,许多工作突破了性别限制。组织中许多劳动强度大、过去只能依靠男性劳动者完成的工作任务如今也能被女性劳动者轻松完成。由于女性劳动者的工资率通常低于男性,参加工会组织的倾向较弱,在工作中容易被管理,许多组织开始大量雇佣女工和未成年工来替代男性工人,从而改变了组织内部的性别结构[9]。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机械操作向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新机器往往承载着比较先进的技术水平,客观上要求工人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在新的技术环境下,组织必须对工人技能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或者对原有工人进行技能培训,或者从外部劳动力市场招聘新工人。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主要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修复成本(renovation cost)。Mortensen & Pissarides(1998)认为,公司可能通过支付一定的修复成本来更新他们的技术和组织,进而调整劳动力。这些成本包括购买新设备及其他内部调整成本,如在新的技术和组织环境中培训工人去操作等。如果修复成本低于创造一个新工作岗位的成本,公司将通过培训工人来更新现有工作,否则就会雇佣新工人[10]。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自动化生产技术发展阶段。
3.工资形式
工资支付形式主要包括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个人工资和团队工资等。在手工劳动阶段,工人负责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产品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单个个人的技能水平,工资支付多以计件工资为主;随着生产技术改变,产品生产被分割为若干环节,劳动成果变得不易明确统计,工资支付开始转向计时工资。不论是计件工资还是计时工资,它都建立在个人工资支付基础之上。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工人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工作中的团队合作要求越来越高,工资支付更加倾向于以团队为主的方式。
二、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
在不同的技术变革阶段,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呈现很大差异。在20世纪之前,技术变革主要围绕机械、机器的发明创新进行,产品生产依靠工人操作机器完成。由于技术创新速度比较缓慢,劳动力市场以中低技能职业为主。进入20世纪之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将生产任务分割为无数个工序,操作技能要求大大降低。技术与技能之间呈现出替代性关系,技术变革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特征极为明显。一大批技艺高超的技师、工匠瞬间沦为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低端操作职业。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技术如信息技术、计算机等推广使用,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者完成相关工作。劳动力市场高技能职业的需求逐渐增加,工人也开始从低技能职业流向高技能职业,技术变革凸显出技能互补性特征。从理论上讲,随着技能互补型技术变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上应该出现一种“高技能职业需求增加、中低技能职业需求减少”的变化趋势, 然而,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主要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变化呈现一种新的变化趋势——工作极化(job polarization),即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呈现“U”形格局,中间职业的就业份额开始下降、两头(高端和低端)职业的就业量逐渐上升[11]。例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1988-2004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极化特征[12]。在发达国家,高端职业就业份额增加,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等环节,高质量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中间职业就业份额下降,是因为大量的常规化工作被编为计算机指令由机器代为执行,或者通过贸易渠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低端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呈现上升趋势,有点令人费解。通过进一步研究,学者给出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主要缘于某些低端工作的非常规性质,它们必须由具有较强的互动机能和情景适应能力的“自然人”完成,而不能由缺乏情感色彩的智能机器人所代替。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变化,Maarten Goos(2009)等人给出了概括性总结,认为工作极化主要缘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常规化工作和工作机会的离岸外包[13]。前两个解释都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而第三个解释则与全球化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紧密联系。
三、技术变革与工作特征
技术形态不同,人类的劳动过程大不相同。Toby D. Wall(1990)等人认为,技术本身是工作特征的主要(但不是绝对)决定因素[14]204。换句话说,工作特征变化是技术变革的结果之一。技术变革对人类工作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方式、工作类别、工作自主性等方面。
(一)工作方式
技术变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手工生产、机械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每个阶段,工人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在手工生产阶段,工匠亲自完成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生产的整个生产流程,产品质量取决于工匠的技能水平,工匠在生产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机械化生产阶段,生产的重心由人转向机器,任务被分为一个个简单而专业的工序,技能要求大幅降低。技艺高超的工匠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之一,要么操作机器,要么维护机器。工人虽然在直接生产产品,但不知产品的最终形态与价值所在。对工人而言,工作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到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动化生产阶段,人们的工作本质发生深刻变化。电脑网络改变了人类劳动的本质,工人不需要手工触摸,工作依靠认知而非感觉,数字经济将围绕人与信息机器组织生产[15]。产品的生产跨越了组织边界甚至国界,人们对产品的认知更加支离破碎。总而言之,技术变革正在逐步拉大工人与产品的距离。
(二)工作类别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们只能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绝大多数劳动都属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较少。工业革命发生之后,随着各种机械、动力机器的普遍使用,体力劳动被细分为手工劳动和机械操作。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一系列新技术广泛应用中,人类劳动划分标准被再次改写。许多学者通过对不同职业的任务内容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常规化任务(routine tasks)和非常规化任务(non-routine tasks)。前者主要指能够被计算机软件精确编程并由机器完成的工作,反之即为后者。Autor(2003)等人又将非常规化任务进一步细分为抽象任务(abstract tasks)和手工/体力任务(manual tasks)。抽象任务是指需要解决问题的,有直觉、说服力和创造力的活动,这种任务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管理性、技术性和创新性特征,例如法律、医学、工程师、管理、设计等职业,从业者通常需要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在工作中与计算机互为补充。与抽象任务不同,非常规的手工任务则需要较强的情境适应性、视觉和语言识别能力以及人际互动能力,从业者只需要接受较少的正规学校教育;职业以个人服务为主,如食物准备和服务、清洗和清洁工作、地面清洁保养、个人健康援助等[16]。在前人的基础上,Daron Acemoglu & David Autor(2011)利用象限法将所有职业划分为四类:非常规认知任务、常规认知任务;常规手工任务,非常规手工任务[17]1078。由此可见,学者们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始终都离不开技术这一关键变量。
(三)工作自主性
技术变革对工作特征的影响还表现在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方面。Toby D. Wall(1990)等人将工作中的控制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时间控制,意指工人能够决定何时完成既定任务,其内涵与工作进度自主相同;第二,方法控制,意指工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工作;第三,范围控制,又称为角色宽度,其实质是对工作范畴的界定[14]204-205。
生产技术不同,工作控制程度也不同。海曼(1975)认为,“管理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过程本身实现的”;“技术可能对管理者和工人的相对权力产生重要影响”[18]77。工业革命之前,产品生产以手工制作为主,工匠(英文翻译为artisan,专指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对整个生产过程全权负责,在工作方法、进度安排、任务分配等方面有很高的自主性。工业革命初期,生产活动由手工作坊转移到拥有机械工具的工厂,生产中心从“人”转移到“机器”。工人的劳动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任务被分割为无数个工序;人体机能被割裂,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彻底分离,“概念先于执行,并且支配执行”[19]。劳动者不再需要“思维”,只需要承担“执行”职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标准”的动作即可。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工艺流程、工作内容,还是工作节奏,工人都遭受着严格的控制,而雇主也正是通过去技能化的技术革新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来实现对工人的直接控制。近年来,随着大量先进制造技术的问世,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再是单纯的机器操作者,而且还是监管者;一些辅助性的生产任务,如调试和维修工作,也逐渐被划归到一线操作人员的工作范围之中。事实充分证明,先进制造技术有降低操作工人被控制的潜力。
除此之外,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工作环境都有较大影响。蒸汽、电力等动力技术的问世催生了一系列大型机械、机器。新的生产工具使过去许多重体力劳动变得更加轻松,许多依靠人力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也能够轻松完成,人类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也使人类的工作环境更加安全。电力技术使工作场所更加清洁明亮,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许多“苦、脏、累、差、险”岗位上的工作,如机器人灭火、清理污水道、水下打捞、排爆等。总之,技术变革不仅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解放出来,还使人们的工作环境更加安全舒适。
四、技术变革与工人
技术变革在给人类工作特征带来重大变化的同时,也对工作的完成者——劳动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目前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人技能、工人认同以及工作场所工人互动等三个方面。
(一)工人技能
在工业革命之前,产品生产主要依靠工人手工完成,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技能得到不断提高。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变革使生产工具中不断融入技能元素,工人的技能需求开始降低。流水线技术使工作被分割成若干任务单元,生产技能需求降至最低,工作过程、劳动成果越来越趋向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高度分工(包括程序分工和机能分工)使工人及其劳动都发生了异化。“在制造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手足的活动习惯,既与思虑无关,也与想象无关”[20];“工人们很少被视为有特殊需求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更多的被看作非人性化的‘生产要素’”[18]13。在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中,企业不再需要技艺高超的工匠,需要的是大量的能够完成简单动作的熟练操作工人。“去技能化”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并被广大学者普遍认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观点开始被人质疑。Schumacher认为现在的技术变革属于技能互补型的,工作需要使更多的技能劳动者从事工作。Kemp & Mueller认为,先进技术的使用,既不会使工作始终如一,也不会使工作单调不变。Chakravarthy(2006)也提出相同观点,认为在未来,僵化的、重复性劳动会不断减少,与生产有关的不同任务单元和工作将变得更加一体化、更加复杂。因此,技术变革需要工人具备更多的技能和知识。Roger Penn & Hilda Scattergood(1985)则从辩证的角度分析技术变革对工人技能的影响,认为技术变革会同时产生强化技能(enskilling)和去技能化两种效应。如果生产所使用的技术属于半自动化,劳动者需要掌握的技能就会增加;如果属于完全自动化的,劳动者需要掌握的技能就会减少[21]。
由此可见,技术变革导致工人技能是增加还是减少,主要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性质以及学者对技术变革的研究假设。主张技能变化的学者大都假设技术变革属于技能偏向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技能影响是有所区别的,替代型技术变革使劳动者技能水平降低,互补型技术变革使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高。例如,Goldin & Katz(2008)就认为,在20世纪早期的制造业企业中,技术与劳动力是互补关系,之前可能是替代关系[17]1046。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技术变革与技能形态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随着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标准化技能要求越来越少,工作中需要更多的难以衡量和监测的技能,如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危机处理能力等。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岗位任职资格需求中,显性的任职资格需求比重如知识、技能等将会越来越少,但隐性的任职资格需求比重如个性、价值观、自我形象、态度和内驱力等则会越来越多。在未来,技能形态的无形(intangible)特质将会越来越明显。
(二)工人对技术变革的认同
众所周知,在技术变革过程中,组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起着主要决定作用。然而,作为技术的最终使用者,工人对技术变革的认同及其在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则从根本上决定着先进技术的效力发挥,进而对企业的劳动关系性质及市场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动荡。
其一,工人对技术变革的认同影响着其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态度决定行为,而行为是工作绩效的重要载体。Krishnan(2010)专门就技术变革与工人认同关系提出“技术接受模型”,认为工作态度与技术接受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新技术的引入会严重影响工人对工作的认知,进而导致其工作满意度的变化[8]373。加拿大学者Brian Bemmels & Yonatan Reshef(1991)的研究也发现,在技术变革中,如果工人可以参与(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执行),将会比没有任何角色更加支持技术改进;参与技术变革决策的工人将会产生一种因为新技术而主动进行技能转变的承诺和责任[22]243,234。因此,组织在技术引进之前首先应该取得工会与员工的认同(一般可以通过信息沟通、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实现)。
其二,工人对技术变革的认同影响着组织内部劳动关系状态。在一些特定技术变革阶段,技术与劳动要素表现为显著的替代关系,即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将导致大量基层操作人员失去就业机会,解雇、裁员等使组织的劳动关系变得比较紧张。William Mass(1985)提出,在引进先进技术时单纯地降低劳动成本是不可行的,企业必须首先得到工人的认同,这样才能既增加利润又巩固劳动关系[23]459。
总之,关注工人在技术变革的反应非常重要,尤其是当技术变革可能导致大量岗位减少时,管理方和政府必须关注工人的反应,从而确保劳动关系的稳定运行。
(三)工作场所工人互动
工作场所工人互动主要研究技术变革对工作场所中工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技术变革类型不同,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有很大区别。 一般而言,大规模生产技术制约着工作过程中的工人互动。例如,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中,由于工作内容单一且节奏较快,工人们忙于完成标准化生产任务而无暇进行沟通交流,工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少;在大规模的自动化系统生产中,由于每个人都需要负责多台机器,负有较高的监管责任,从而制约了员工之间的互动关系[24]。最近几年新出现的另外一些技术形态,尤其是小批量生产(batch production)技术,需要员工之间充分合作的应用技术,可以使操作者与所有层次的同事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更加频繁的工作联系。例如,Blumberg & Alber(1982)的研究就揭示了灵活制造体系如何在操作者与其他需要密切合作的人员之间就生产、维护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形成更大的相互依赖性[25]。
在工作场所中,积极有效的工人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增强工人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提高工作绩效,还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工作热情与满意度。因此,企业必须选择合适的生产技术,为高绩效工作提供良性互动氛围保障。
五、技术变革与工会
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之一,工会在技术变革过程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而技术变革对工会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工会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作用
工会作为重要的工人组织,在组织的技术变革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工会可以促进或阻碍组织进行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势必导致组织的雇佣数量与雇佣结构变化。此时,工会就要发挥其代言人功能与组织进行沟通。例如,组织引进的技术属于劳动替代型的,如自动化生产线,工会可以就雇员裁减问题、技能培训等相关问题与组织进行集体谈判。如果谈判顺利进行的话,工会能够促进组织技术变革,反之,工会则会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行动以抵制技术变革。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19世纪的绝大多数罢工都源于企业推进技术变革。可以说,工会的强势地位直接影响着技术变革能否推行。
其次,工会对组织技术选择有着显著影响。William Mass(1985)在分析英美两国自动化纺织技术的推广差异时,得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技术选择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二是技术选择取决于产业关系结构,尤其是工资谈判结构。由于工人是技术的最终使用者,劳动的努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关系,除非企业能够极大地改变其他要素的投入质量。因此,工资谈判(effort-wage bargain)不仅决定着单位劳动成本,而且也决定着其他成本。实现高生产能力设备(主要依靠新技术而实现)的成本减少潜力主要依赖于产业关系结构[23]460。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Brian Bemmels & Yonatan Reshef(1991)在对206个进行过技术变革的制造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工会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不仅与其自身力量相关,而且还与一定的制度立法密切相关。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产工人的工会化并不意味着管理方受到的技术变革阻力就一定比较大[22]232。在工会化企业中,集体协议虽然增加了关于技术变革的条款(主要集中在工人替代、就业安全方面),但这并不能消除劳资冲突,有时候反而会创造一些新的冲突理由。
由此看来,工会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依据国情、技术性质、产业关系结构等进行具体分析。
(二)技术变革对工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得工人进入企业,集体劳动、共同利益使得工会快速成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技术变革交替进行中,劳动者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工会的职能发挥也在悄然变化。自20世纪中后期信息革命发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生产方式开始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改变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工作内容、工人技能的异质性,工人阶层内部分化加剧。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以集体目标为谈判宗旨的工会逐渐失去优势,随之而来的是分散化谈判在工作场所的盛行,以及非工会化工人正在取代工会化工人[26]。多个西方国家的工会化密度都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技术变革在其中的贡献不容小觑。
六、技术变革与雇佣规则
(一)雇佣规则的经济目标
以分工为基础的技术变革能够快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组织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围绕着经济目标,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雇佣规则,为获取利润最大化提供制度保障。在追逐经济利润的过程中,绝大部分企业过度关注技术的影响。Yassin Sankar & Samuel Natale(1990)提出,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物理工作环境中,企业通常强调产品、技术和市场,重构一种组织来迎合成员的心理需求,通常被放在次要地位,高层管理者对“让人去适应工作(fitting the person to the job)”而不是“工作去适应人(fitting the job to the person)”表现出更大的兴趣[27]92。Vries(1980)通过分析以往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从历史角度看,组织对工作中的技术的关注度要远远超过社会投入与人类财富[28]。
(二)雇佣规则的文化意识与伦理意识
当雇佣规则的经济功能被发挥到极致之时,学者们逐渐开始探寻技术之外的生产率来源。Marshall(1992)认为,企业应该追求有竞争力的战略(其特征是产品创新、质量以及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创新),而不是企图追求更低工资水平的竞争[29]。Gertler(1995)认为,生产率最好产生于生产过程,在这中间,技能工人的工作与先进机器密切结合,这就需要基于稳定、信任、信息自由交换的劳动关系的支持。为此,他还对比了先进技术在美、德两国的推广情况,认为在德国的推广难度小,主要缘于德国特有的工业文化(culture of industrial practices),即工厂工人较高的技能水平、雇佣关系的稳定性、生产车间的协同决策机制以及对培训的强烈关注[30]。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Cooke & Morgan(1991),他们认为,后福特主义经济制度使用一种灵活方法去生产,而这通常反映在雇佣关系、公司内部的工作安排以及更广泛的劳动的社会性分工[31]。
不难看出,先进技术要转化为真正的生产率,必须有适宜其发挥效力的制度文化环境。基于此,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技术变革中的雇佣文化与规则,关注技术形态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工作场所的技术异化及其带来的劳动异化现象,开始关注技术变革背后的伦理问题。在技术变革中,组织必须关注“人”的因素,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作用。Eric Trist(1978)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对人”或“人对技术”的调整,它由人-机相互作用的安排构成,以便于能够获得双方的最佳配置。更确切地说,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实现有效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而人和技术都是其中的一部分[32]。
(三)人本主义雇佣规则
明确了“人”与“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学者们开始倡导技术变革中的人本主义雇佣规则。他们认为,在新的技术环境中,组织必须注重工作设计,注重工作中“人”的效力发挥与多元化需求。Florida(1991)认为,这种技艺通常是指一套新的灵活性工艺技术,其可编程特性能够为生产商提供这样一种前景,即广阔的通用性、有限的故障时间、无与伦比的精度以及优越的品质,拥有这样一种潜力,即释放工作者的创造潜力、促使生产者在生产车间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机制[33]。Yassin Sankar & Samuel Natale(1990)的研究主要从“人”的需求出发,认为工作简单化、工作具体化、工作碎片化、限制工作深度和范围都在摧毁个人的需求,这都是以往技术变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为了矫正这一现象,技术变革必须确保,工作设计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允许个体需求的表达。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工作设计都必须给雇员实现他们需求的机会,如自我实现、自尊、地位、自我提高、归属感、爱和安全等等[27]91-92。
其实,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对劳动者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涉及技术本质与技术伦理问题。技术变革的起源与初衷是为了将人类从危险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应该是“为人”和“人为”的,而不应该奴役人类、控制人类。技术变革涉及技术专家、代理人、管理者、工程师和科学家等,他们的行为都将影响劳动者及其从业生态系统(ecosystem),其行为都应做出适当调整。作为先进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企业应该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使劳动者能够以社会期望的方式实现自我潜能。
七、研究启示与未来展望
理论来源于实践。西方国家漫长的工业化过程给技术视域下的劳动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专门的劳动关系研究至今不过20余年,研究内容以制度规范建立完善为主,技术变革引起的劳动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学者关于技术变革下的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可以为中国的劳动关系理论与实践提供宝贵借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体制及发展轨迹、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学者的研究变量控制、主体行为假设并不十分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学者在借鉴时需要辩证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如“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等将快速融入生产领域。技术变革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分配,引起劳动力市场的连锁反映。劳动关系学者应该充分意识到技术变革即将产生的一系列劳动关系问题,如技术转型对劳动力需求(如数量、素质和结构)的影响,技术转型对劳动关系力量(包括劳动力市场力量和岗位力量)的影响,技术转型对劳动者组织意愿的影响,由于技术转型导致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在技术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技术升级导致的工作过程变化、工作场所氛围变化,技术升级导致的微观劳动关系管理方式问题,等等。可以说,伴随着技术转型升级,中国面临的劳动关系问题将更加复杂多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需要劳动关系学者进行详细系统的研究。
[1]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 781-810.
[2]Claudio Michelacci, David Lopez-Salido. Technology Shocks and Job Flow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 (4):1195-1227.
[3]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1): 7-72.
[4]Katz, Lawrence, Autor, David. Changes in the Wage Struct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M]. The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Amsterdam, 1999.
[5]Gregg, P., Manning, A. Skill-Biased Change, Unemployment and Wage Inequality[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 (6):1176.
[6]Matthias Weiss.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There Hope for the Unskilled[J]. Economics Letters, 2008,100, 439-441.
[7]Hirschhorn, L.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M]. MIT Press, Cambridge, 1986.
[8]T. N. Krishnan. Technological Change &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India[J]. 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 45 (3):367-381.
[9]William Lazonick.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Self-acting Mul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 (3): 231-262.
[10]Mortensen, Dale T.,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998, (1):733-753.
[11]Alan Manning. We Can Work It Ou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The Demand for Low-Skill Workers[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51(5):581-608.
[12]Viki Nellas, Elisabetta Olivieri. Job Polar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OL]. http://www.iza.org/conference_files/ESSLE2011.pdf
[13]Maarten Goos, et al.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9, 99(2):58-63.
[14]Toby D. Wall, et 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Work Design: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1(3): 201-219.
[15]Daphen G. Taras, Ames T. Bennet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002, (3):335-338.
[16]Autor, Levy and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279-1333.
[17]Daron Acemoglu, David Autor.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M].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4b:1043-1171.
[18]海曼.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M]. 黑启明,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77,13.
[19]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47.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52.
[21]Roger Penn, Hilda Scattergood. Deskilling or Enskill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ecent Theories of the Labor Process[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36 (4): 611-630.
[22]Brian Bemmels, Yonatan Reshef.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991, Xll (3):231-246.
[23]William Mas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Diffusion of Automatic We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5, 45 (2):458-460.
[24]Argote, L., Goodman, P. S. and Schkade, D. The Human Side of Robotics: How Workers React to A Robot[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3, 24:31-41.
[25]Blumberg, M., Alber, A. The Human Element: Its Impac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Advanced Batch Manufacturing Systems[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ystems, 1982, (1):45-53.
[26]J. S. Sodhi, David H. Plowman.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 Changing Field[J]. 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2, 37 (4):459-485.
[27]Yassin Sankar, Samuel Natale.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stress, and Industrial Human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Based Management, 1990, 3(1): 91-103.
[28]Ket de Vries, M. F. Organizational Stress: A Call for Management Action[M].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0.
[29]Marshall, R. Unions and Competitiveness[J]. In Empowering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labor agenda for the 1990s, 1992:75-98.
[30]Meric S. Gertler. Being There: Proximit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J].Economic Geography, 1995, 71(1): 1-26.
[31]Cooke, P., Morgan, K.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Regional Industrial Research Report. 1991,(8)
[32]Trist, E. 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J]. Labor Gazette, 1978.
[33]Florida, R.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J]. Futures, 1991, 23, 559-576.
[责任编辑 张家鹿]
2016-02-12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4.016
F240
A
1000-2359(2016)04-0088-08
刘春荣(1979-),女,山西芮城人,经济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讲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