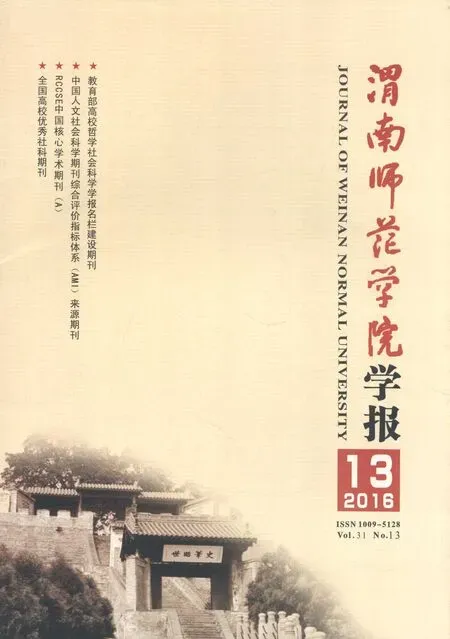《史记》增饰的叙事策略
芮 文 浩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史记》增饰的叙事策略
芮 文 浩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史记》的历史叙事有明显的增饰成分,司马迁在传达“天意”与表达己意时虽有增饰却又不悖史实,达到了实录与增饰的完美统一。《史记》的增饰既有出于历史叙事的需要,也是“整齐百家之语”的表现,同时也是出于追叙秦楚及楚汉之际风云变幻的需要,更有实录西汉本朝史事并传达己意的需要,体现出其极为高明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史记》;实录;增饰;叙事策略
“增饰”见于古典文献中的年代甚早,如《风俗通义·声音》记载:“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乐官多所增饰,然非雅正,故继其条畅曰声音也。”[1]267又如《论衡·是应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驎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2]45而明确指出《史记》增饰问题的是唐代史记学家司马贞,其《史记索隐》称《滑稽列传》之优孟谏楚庄王事有明显的增饰之词:“此辩说者之词,后人所增饰之矣。”[3]3201此注列于正文“韩魏翼卫其后”之下,观文中优孟以人君之礼葬楚庄王爱马之辞,实有反讽意味,因而《史记索隐》所言之“后人所增饰”,不仅包括以大夫之礼、人君之礼葬之不宜,而且涵盖后文优孟所言只适宜葬此肥马于人之腹肠。
章太炎先生曾言:《史记》所记鲁仲连、苏秦等人事迹“于事实或有增饰”,至于“叙蔺相如奉璧秦廷,怒发冲冠,秦王即为折服,事亦难信”,此类记述是由于“史公好奇,引以入列传耳”,而扬雄称《史记》为“实录”,“实录者,实录当时传记也。苏秦有《苏子》,鲁连有《鲁连子》,魏公子有《兵法》,史公皆取以作传,故曰实录,事之确否,史公固不负责,须读者自为分辨耳”[4]157-158。以现存的传世文献比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廉颇、蔺相如事迹多为他书未载之事。《史记会注考证》称,《战国策》记载廉颇事迹颇为简略,并无一语提及蔺相如。对此,钱钟书先生明确指出《廉颇蔺相如列传》有“叙事增饰”之迹:“(此传为)《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5]516施伟忠先生指出,史家要表达的是历史的真实与其对历史理解的真实,因而,在理解历史、参与历史的基础之上,史书叙述往往采取偏离原貌的渲染、夸张甚至增损、改观等叙事手法,从而揭示历史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特殊的摹写手法就是叙事增饰。[6]
若依《史记》所载史实时限为序,其中的叙事增饰略可分为三种情形:其一是对先秦经史的增饰;其二是对秦末及楚汉之际史事的增饰;其三是对西汉及武帝本朝史事的增饰。
一、《史记》对先秦经史的增饰:“以训诂代经文”及其再创作
从《史记》内容来看,司马迁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史料,其中对夏商周三代史多采自上古文献。三代史事多是司马迁对此类文献甄别后所作记载,《史记》虽未列出其所采书目,但其所涉文献不下100余种,若依据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来划分,其中有关六经及其训解著作23种。[7]21采择先秦典籍时,司马迁对其中“文不雅驯”者多不予采信,而是“择其言尤雅者”入史,《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便是如此:“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3]46《史记》记五帝而以黄帝首,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旨在突显黄帝勘平诸多部落战乱的功勋,肯定了黄帝统一的功业。[7]341《史记》采择先秦典籍时,或录其全文,或节其一部分,运用“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变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在“以训诂代经文”的同时,司马迁或适当剪裁摘要,或增文补史,或训释古文,或熔铸改写,这一过程中就有着文学构思的成分。为尽可能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行状,《孔子世家》在援引《论语》材料时均为相关对话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文学构思的痕迹十分明显。[8]201-202如此一来,司马迁不仅解决了时空悬隔所致的语言障碍,而且使得《史记》的叙事更趋合理,有时甚至具备了戏剧化的特征。
“以训诂代经文”是司马迁历史编纂中的重要方法,在运用此法时,司马迁往往会在已有史书文献和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史记》对于赵氏孤儿的记述便是增饰中极具戏剧化的典型实例。《史记·赵世家》载,春秋晋景公三年,赵朔遭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赵朔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侥幸免祸,赵武成人后,得到韩厥等人的支持恢复了赵氏宗位。以现有传世文献相较,《左传》对赵氏孤儿有过粗略的记载。据《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9]833-834
《左传》叙述的中心在于,韩厥劝晋侯以明德为要以保住赵氏后代。赵氏遭戮是源于晋君与晋卿赵氏家族的矛盾,而赵盾之孙能够幸免于难是由于其母庄姬和韩厥的保护,文辞简短,相比之下,《史记》赵氏孤儿故事不仅篇幅较长,而且细节传神,情节动人,虽多增润生发,但并未背离赵氏终于平反、赵武终得继任晋卿这一史实。
二、《史记》对秦末及楚汉史事的增饰:传达“天意”
较之于先秦史,记载秦楚之际与楚汉史事时的语言障碍则要小得多,而西汉史尤其是西汉武帝朝史事,应该说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的。然而,我们发现,《史记》对秦末及楚汉史也有增饰,《史记》对张良“博浪狙击”反秦义举的描述便是增饰的明证:“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3]2034刘辰翁指出:“从仓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举于旷野,而正中副车,虽架炮不能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并隐力士,此大怪事。卒归圯上老父,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乃今人以为小说不足信者。”[10]435-436《留侯世家》中对张良与力士狙击秦始皇的记载极富传奇色彩,《史记》此处叙事有增饰是不言而喻的。
《史记》述楚汉之际史事的增饰主要体现在刘邦身上。刘邦平生曾数次遇险:鸿门宴上险遭不测、彭城大战几难逃脱、广武大涧暗弩伤胸而扪足、平城之围万难生还、征讨黥布时伤于流矢。其中前三次遇险均在楚汉相争之际,三者相较,《史记》对鸿门宴与彭城大战的增饰更为明显。
《史记》所述鸿门宴的是一场暗藏杀机的宴会,在《史记》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樊哙的传记等篇目中均有记载,而以《项羽本纪》所载最详。据《项羽本纪》载:刘邦攻占秦朝都城咸阳后,驻军霸上,并派兵扼守函谷关。不久,项羽命黥布攻破函谷关入三秦,项羽40万大军进驻鸿门,范增建议项羽抓住战机进攻刘邦。项伯深恐其故友张良在刘邦军中遇害,当夜策马至刘邦军中道楚军意图,经过一番斡旋,刘邦携张良、樊哙等至鸿门会见项羽,项羽留饮。宴会上,范增多次示意项羽决心除掉刘邦,但项羽均未予理会,于是,范增命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借机刺杀刘邦,不料项伯的拔剑起舞,使其计谋落空。最后张良出帐招来樊哙,樊哙带剑执盾闯入,一番责问使得项羽几乎无言以对,刘邦则趁机离席,逃离鸿门返回霸上。《项羽本纪》之鸿门宴无异于是“沛公历险记”:刘、项集团先后入秦,但实力悬殊,项羽兵力是刘邦的四倍,项羽两番大怒之下,读者不禁替刘邦的安危捏一把汗。曹无伤告密,项羽大怒声言发兵,刘邦危在旦夕,然而项伯夜告,沛公约婚并言愿至项王军中谢罪,复有转机。鸿门谢罪时,项庄舞剑,沛公几乎命悬一线,然若无项伯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沛公难免血溅当场。遂后樊哙闯帐,对项羽怒目而视,历数项羽之过时,读者不禁替樊哙担心,进而更为刘邦担心,因为项羽在沙场上喑叱咤千人皆废,此时又身为诸侯上将军的,而且刘邦一行还是在项羽的军营之中!只要项羽一声令下将樊哙擒下或推出斩首,鸿门宴还能平静吗?然而,不料鸿门宴上的项羽一反往日的喑叱咤,使得历史的发展、人物的命运在瞬息之间发生了巨大转折,极具张力的叙述话语不仅体现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内动力,也交代了历史人物命运的神秘转机,使得文章在尺幅之间波澜起伏。即便沛公借口如厕招呼樊哙出帐,并与夏侯婴等人从小路回到霸上,此时若楚军发难,汉军和沛公也将会命悬一线。然而历史容不得的假设,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洪流在两千多年前的新丰鸿门并没有卷起滔天狂澜,而是在樽俎之间泛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涟漪。[11]600-601对于这一段历史,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虽对秦末反秦义军中的刘邦破峣关入咸阳后的约法三章有明确的记述,但紧接着叙述的便是项羽入秦后屠咸阳焚秦宫而火三月不灭之事,对鸿门宴会却只字未提。[12]31抛开古今史家甄别史料的标准各异不说,《史记》关于鸿门宴的叙述的确太富于戏剧性了,后世不断演绎“鸿门宴”戏曲和近现代以之为题材的影视便是明证。
汉王趁田氏在齐地叛楚反击项羽于城阳时进军彭城,遂后,项羽率骑兵三万由齐地经萧县从彭城以西猛攻汉军,是为彭城大战:“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汉军已有胜势在项羽铁骑面前霎时溃败,汉王也身陷重围,此时,汉军连同汉王危在旦夕。孰料,“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3]321-322。此役项羽以少胜多,然而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因为汉王逃脱了,而且此役后,诸侯时而助楚时而为汉,有些干脆明确地叛楚。若依当时突如其来的大风暴毁屋拔树之实际情形而言,《史记》也当然可以写成“大风逢迎楚、汉军”,《史记》虽没有如此叙写,但我们仍能推想当时两军对阵的情形:楚汉两军在迅疾的大风暴不得交战,战斗力极强的楚军骑兵在强沙暴中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汉王趁机与数十骑遁逃后,楚军虽派军追击至沛县,但除拿获刘太公和吕雉及审食其外,并未能追到汉王刘邦。虽说灵璧突如其来的大风来得太过蹊跷,恶劣的沙暴天气实属少见,但毕竟自然界的确有这种灾害性天气,碰巧的是这次灾害性天气对楚军的毁伤远远大于汉军,使得楚军瞬间丧失了战斗力。
三、《史记》对武帝朝史事的增饰:表达己意
《史记》对武帝朝史事的增饰集中体现在李广身上。《太史公自序》谓:“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3]3316明司马迁尤其看中李广之“勇”及其“仁爱士卒”,检视本传又突显其善射之能。
《史记》对李广优异的品质有明确的记述:“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李广不仅廉洁,而且爱士卒,“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3]2872。不过,《史记》对廉洁奉公、关爱士卒之将多有记载,如战国时赵之良将赵奢,“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3]2447。而汉大将军卫青更是一位廉洁奉公、仁爱士卒的将军。淮南王意欲谋反,又虑及若举事汉武必定起用大将军卫青弹压,因向伍被询问卫青的为人,伍被回复:“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3]3089伍被以其友人黄义的亲身经历告诉淮南王——大将军卫青是个勇于当敌、仁爱士卒、才干超群的人。可见,廉洁奉公、仁爱士卒是李广具有的优秀品格,但却不是李广独具的品格。
对李广的仁爱士卒,《史记》是极其赞赏的,但这自古便是重要的为将之道。《黄石公》书称:“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恩不倦,以一取万。”[13]20而相传姜尚所著的《六韬》陈述了为将者服礼、力行、止欲对治军的重要性:“太公曰:将有三胜。武王曰:敢闻其目?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14]123《黄石公书》与《六韬》都认识到,为将者服礼方可知士卒冷暖、身体力行方能深味士卒劳苦、遏制物质私欲则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因感于主将与之同滋味共安危,因而,实战时他们便甘冒矢石、前赴后继、蹈死不顾,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也必将由此得到大大提升。
再来看看李广射石的记述。射石非独李广一人,王充《论衡》:“儒书言楚熊渠子出见寝石,以为伏虎,将弓射之,矢没其卫。或曰:养由基见寝石,以为兕也,射之,矢饮羽。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主名不审,无害也。或以为虎或以为兕,兕、虎俱猛,一实也。或言没卫,或言饮羽,羽则卫,言不同耳。要取以寝石似虎兕,畏惧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寝石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没卫,增之也。”[2]17后世学者对“射石没羽”之说多持异议,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引用多家之言力辩其妄:“射石一事,《吕氏春秋·精通篇》谓养由基,《韩诗外传》(六)、《新序·杂事》(四)谓楚熊渠子,与李广为三。《论衡·儒增》以为‘主名不审无实也’。《黄氏日钞》亦云‘此事每载不同,要皆相承之妄言也’。”并引《文选》鲍照《拟古诗》注所载宋景公射石之事:“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援弓而射之,其余力犹饮羽于石梁。”[15]1378-1379很显然,梁玉绳认为李广没矢饮羽之说不足为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无疑是一个能与士卒共甘苦的好将军,但射石没羽、与士卒共甘苦,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广才气有余而纪律不整,如虎豹虽雄豪绝世,然羁縻于文物之中,有不如立仗之马、驾车之牛者。”[16]132再看看《史记》所载李广实际的战例,更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点。李广经历了汉代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景帝时,“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于景帝朝参加过平定吴楚叛乱,“取旗,显功名昌邑下”[3]2867-2868;但《史记》并没有写出李广的实际战功如何,不过,若浏览《史记》他篇,如窦婴、周亚夫等人的传记,我们会很容易发现:窦婴、周亚夫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的功勋十分卓著。李广于景帝朝还有一次和匈奴交兵的经历。为了报复匈奴射手射伤中贵人,李广率百骑追射匈奴射雕者,归途突遇匈奴数千骑兵,于是,李广令士卒下马解鞍示为诱骑来迷惑敌兵,从傍晚一直僵持到半夜,匈奴骑兵方退。这一次,李广射杀了匈奴射箭高手而且全身而退。
武帝时期,李广参加的抗击匈奴之役计有四次:第一次是在马邑之谋之后的元光六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结果,匈奴“破败广军”,李广亦被匈奴生俘,《史记》对此在《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予以再三表述,其中李广本传中称:押解途中,“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李广所率部卒多败亡,李本人又被生俘过,按律当斩,赎为庶人。[3]2870-2871这一次的李广因射杀追兵后逃归汉营。李广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击匈奴在武帝元朔年间。“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这一次是诸将多有功封侯,而李广无功。元朔八年,“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李广与其子李敢与匈奴四万骑兵遭遇,第一天激战后,汉兵死伤死者过半,第二天再战,张骞亦引军而至,匈奴遂撤兵,此时,“(李)广军几没”,“军功自如,无赏”[3]2873。这一次,李广虽“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但并未能战胜匈奴兵,而且所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由李广参加的上述三次战役来看,李广虽然善射,但在率部与匈奴骑兵的交战中难建军功。
李广第四次出击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这是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也是他生前最有可能在征伐匈奴时建功的一次,然而这一次的李广非但无功,而且其所率之师几近徒劳。究其原因,有外在的客观因素,更有李广自身的内在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武帝的用人方针。临战前,武帝认为李广“数奇”遂密令卫青不得让李广军作前锋,“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当李广得知自己不能作前锋时向大将军力争,未果,“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与此同时,“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李广和前将军公孙敖、右将军赵食其相遇时,汉军主力与匈奴单于骑兵的激战早已结束了。诚然,沙漠本无路而难以行军是客观事实,然而这也恰恰反映了李广自身的严重不足。与往返荒漠沟通西域的张骞相比,李广在沙漠行军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李广军在沙漠中失去向导而迷失方向,说明出他在沙漠中骑兵实战的能力相当薄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卫青。卫青亲率汉军进行的漠北之战有声有色:元狩四年春,汉武帝令大将军出定襄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驘,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3]2935。卫青的漠北之战“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可见匈奴军众此役遭受的重创前所未有,以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2910-2911。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李、卫二人孰优孰劣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史记》的增饰与实录:“天意”与己意的统一
班固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2738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史记》中的实录与增饰呢?《史记》在增饰中体现了实录的选择性艺术,做到了天意与己意的统一。
清人万斯同有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如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成人后游学四方,求耆老遗书、郡志、邑乘、私家撰述,皆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18]1345-1346“实录”几为历代修史之通则。钱钟书先生指出:中国《左传》等史籍长于记言、黑格尔所称苏锡狄德士史纪中记言,二者均出于作者增饰。[5]273钱氏以会通中西的学术眼光,透视了中外史著中所共有的增饰是现象。
章学诚指出,史才、史学、史识三者得一已然不易,兼三者得更难,而具备史识之人必知史德,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着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19]219章氏正是着眼于“实录”而言“史德”的。西晋时,杜预曾揭《春秋》义法有五,其中之四为:“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钱钟书先生进一步申说:“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5]269《史记》叙事虽时有增饰,但多不违史实。如赵氏孤儿对赵武立为赵卿并不违背《左传》所述赵武继任晋卿的史实;对李广和卫青征伐匈奴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对李广多舛的命运多有怜惜,对李广善于守城和短兵相接的小规模、近距离对战射杀多有斩获大加赞赏,同时司马迁并不掩饰李广在大规模的骑兵长途奔袭式的运动战和沙漠行军中的短板。在处理李广与卫青这两个武帝同时代的人物时,关于卫青廉洁爱士,《史记》在卫青的本传中并无一言提及,但司马迁却在记述淮南王刘安意欲谋反时,借伍被之口道出了卫青的这一优秀品质。由此一来,《史记》不仅通过“互见法”使卫青的为人得以完足,既不违“实录”之史德,又体现出《史记》选择性叙事的高超艺术。
这种“史才”不仅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刻画相关人物多样性格的需要,也是《史记》著述过程中对相关史事予以特定选择的结果。司马迁对西汉当代史表述的重点非常突出:高帝时以靖乱安邦为重点,武帝时以征伐四夷为重点。[7]363而李广生逢西汉三代皇帝,然而皇帝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却大不相同:文帝在平定诸吕后即位,根基未稳,施政宽仁,景帝亦多守成,因此,文景之世政治上奉行“无为”的治国之策,军事上则对匈奴的袭扰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武帝建元以后,大汉天朝志在用兵四夷,对四夷的军事策略为之一变,武帝元光元年的马邑之谋虽未取得预期战果,然而却是西汉变以往的和亲政策为军事斗争、变被动防御而作主动出击的转折点。在用兵匈奴的问题上,武帝采取的总体战略是:主动出击,用大兵团强骑兵长途奔袭,对匈奴王庭采取战略纵深包围,对匈奴骑兵完成穿插并与之决战。如李广其人,游击战、运动战是其长处,率领一支小部队可以发挥其长,若委以堂堂之阵,则非其能力所及。[20]5456若此,李广非唯自身长技不足以退匈奴而立功受封,而且也不能领会文、景之世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更不得武帝对匈奴的大兵团、远距离、奔袭战的用兵要领。然而,在品读李广传时,读者多对李广的命运不济感慨良多,如“卫霍深入二千里,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明人黄震指出,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正是得益于太史公“抑扬予夺”的写作手法。[21]673
相对于先秦史的编纂来说,司马迁对西汉朝,尤其是武帝朝史事进行再创作的空间要小得多,再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西汉朝当世之史,尤其是汉武帝朝的史事,司马迁是见证者、甚或是亲历者,同时,修撰《史记》时还可以发金柜石室之书,因而,西汉史没有再行标新立异的必要,也无大规模再创作的空间。但是,我们注意到,《史记》在叙述楚汉及西汉史事的过程中还是有增饰成分的。这种增饰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选择性叙事艺术,而且在增饰中体现了“天意”和司马迁的个人意志。
彭城大战汉军溃败,逃至灵璧时“大风从西北来”,楚军遭受恶劣天气影响,战斗力骤减,汉军连同汉王遂虎口余生。对此,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反复致意“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760然而《史记》述楚汉变局是围绕刘邦如何一统天下这一中心,因而在田儋扰动西楚时,司马迁称“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3]365。《史记》在叙述楚汉之际史事时,详细记载了田横死后,与之共同流亡海岛的五百部下皆自杀一事,梁玉绳认为此处记载出于传闻而非事实,是司马迁的溢美之词。[15]1338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司马迁修史时重人物尤重于其事的史学精神。[22]122-124因此,《史记》无论是叙写“大风从西北来”暗含的天意,还是记载田横及其五百壮士的义烈之举,均是围绕楚汉之际风云变幻展开,叙事核心是靖乱安邦。如果说强沙暴纯属“天意”,而消弭战乱、德治天下则是人心所向,这才是真正的天意。
参考文献:
[1] [汉]应劭.风俗通义[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汉]王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3] [汉]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 施伟忠.论《史记》叙事增饰的形成[J].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75-80.
[7] 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1] 芮文浩.《史记》鸿门宴对古代史传小说的影响[M]//赵生群,王增文,陈曦.史记论丛:第十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12]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魏汝霖.黄石公三略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
[14] 徐培根.太公六韬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15]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21] 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朱正平】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13-0016-07
收稿日期:2016-05-1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古代史传评注与小说评点关系研究(AHSK11-12D186)
作者简介:芮文浩(1974—),男,安徽肥西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史传文献整理与史传文学研究。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Exagger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RUI Wen-hao
(Chinese Literature School,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There is apparent fic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While exaggerating, Sima Qian conveyed providence and expressed his own opin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but not contrary to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Records is perfectly unified with its exaggeration and faithful records. The exagger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is in need of not only historical narrating, but also unifying the view of hundred schools, and telling about the past of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and Chu, and Chu and Han. What’s more, the exaggeration is out of the necessity of faithfully recording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conveying his own wishes. Thus, Historical Records reflects its superb narrative strategy.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faithful record; exaggeration; narrative strategy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