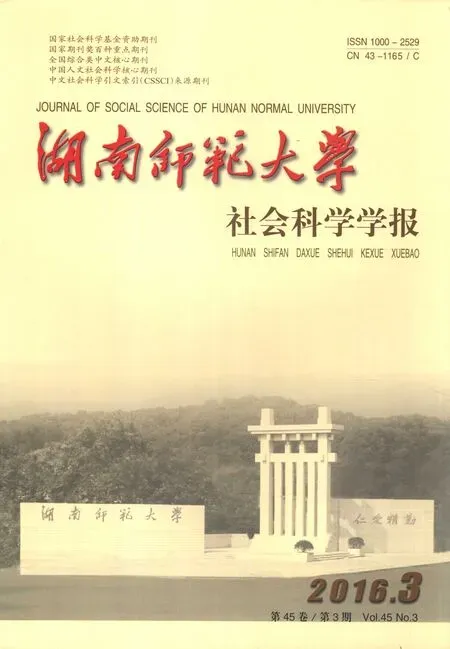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视角
张雨,敖双红
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视角
张雨,敖双红
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网络之于公民言论自由不限于媒介作用,还会实质影响该项基本权利与其他权益之间的关系。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对网络言论进行限制与保护,其核心在于如何协调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间的价值冲突。因而,探寻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当前我国网络言论监管体系在灵活性与适应性方面仍无法完全因应网络发展的需求,需要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立足于本国特点建立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机制、统一立法标准、充分运用“法律”与“网络技术”等综合监管手段,以平衡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
网络言论自由;权益衡量
敖双红,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3)
言论自由是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平台,其不仅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件提供了更为快捷、方便的场所,也在事实上扩大了公民言论影响的范围。网络虚拟世界让一种现实社会不能实现的绝对自由环境得以形成——言论自由且公开,言论发表者匿名且身份隐蔽。但因网络言论自由而引起的现实争议却不断增加。因而,与传统的言论表达自由相比,网络言论应当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一、网络对言论规制机制的挑战
法学上的“规制”具有通过法律法规进行监督管理的涵义,主体一般为代表公权力的政府,目的在于维护利益均衡与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合理。①可见,“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监管”通用。政府规制某一特定社会活动就是为了协调活动成员之间的价值冲突、平衡成员之间的权益关系。尽管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极易与其他权益(如名誉权、隐私权、社会秩序等权益)发生价值冲突,而网络通讯技术的蓬勃发展则在无形中加剧了该项基本权利与其他权益之间的价值冲突。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对规制主体、规制理念、规制方式、规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网络迫使规制主体不得不转变理念,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舆论事件。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隐蔽性与公开性为言论侵权与犯罪行为提供了潜在的庇护。通过这种“隐秘而匿名”的途径,网络为敏感的社群及个人发表攻击性或者具有挑衅字眼的言论提供了可能。②攻击性或者具有挑衅字眼言论的负面作用经由网络无限扩大,因此而产生的侵权与犯罪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出了传统侵权与犯罪的范围。例如,某些网络用户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发布诋毁他人名誉、侵害他人隐私的言论,其不良影响经由互联网可以跨越国界;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恐怖、邪教、仇恨等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论,甚至可以导致某一地区出现社会动乱。政府如果不能对以上不当言论及时进行引导,长此以往,就会给人们形成一种恶性思维——即在网络空间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相较于“面对面”言论,网络言论对政府所造成的舆论压力要更大,影响范围也更广。因为网络不当言论一旦被反复转载、快速传播,就会成为极具冲击性的网络舆论。这就要求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时,不仅要迅速、及时,还应根据言论传播特点而采取一定的策略,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其次,网络迫使政府监管标准必须与网络技术标准相结合。网络信息发布、传输和接收有赖于互联网数据传输物理线路、通用计算机技术标准以及服务协议等互联网技术架构的支持。政府监管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与规则必须融合互联网技术标准或至少不与之相违背。例如,政府在识别网络不当言论过程中必须将其确立的法律文本标准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程序代码,并设置文本过滤系统以供互联网用户自愿进行选择。可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政府很难实现对数量庞大的网络言论进行监管之目的。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传播路径去中心化、网络言论发表者与听众自愿性的特点,政府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与多个国际互联网行业组织合作。这些互联网行业机构因在其专业领域的垄断性而对政府监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网际网络赋值当局、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万维网联盟、国际互联网协会等非政府性机构因享有互联网资源分配权而实质控制了网络数据传播路径。
再次,网络打破了传统“政府VS个人”的二元对抗模式,增加了政府规制目标实现的难度。在传统言论规制机制下,个人是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体,而政府被视为对该项基本权利的最大威胁。这是因为受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公民言论的影响力处于一种分散、隔离的状态,彼此没有互动与响应,从而不能产生有效社会反响。与政府行动博弈,公民基本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③然而,网络媒介打破了言论传播的时空限制。人们的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很快凝聚成足以影响整个现实社会的力量——如网络群体性事件会使得政府对言论传播渠道难以管控、加重政府及时应对的负担并导致政府机构公信力的下降。④例如,郭美美“炫富”事件使得中国红十字协会失信于民,并使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⑤因网络言论而引发的价值冲突还会跨越国界而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例如,美国导演纳库拉·巴塞利导演的《穆斯林的无知》在互联网的传播造成叙利亚班加西地区的血腥暴动,并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与反对。⑥这是因为互联网在广泛传播言论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言论发表者与接收者间的价值冲突,进而加深了现实中的矛盾纠纷程度。传统的政府监管被限定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言论发表者与接收者间的价值冲突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媒介因素就能得以解决。但言论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传播,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接入服务提供、电信运营服务提供等多个主体服务支持。政府监管的客体从政府——个人的二元法律关系向电信运营——网络服务提供——接入服务提供等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扩张。
二、网络言论自由的范围与程度
传统的言论自由之所以能得到较高程度的保护,是因为其有民主自治、真理追求、自我实现与社会安定等多元价值。⑦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可以在多大范围与程度内被监管既与一国的宪政价值理念有关,又与言论自由同其他价值如平等、人格尊严、隐私等之间的位阶关系有关。言论自由价值的多元性使得其非单一不变,而是与其他权益有着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⑧权利不仅可以从义务的角度来认识,还可以从为他人设定义务的权力角度来认识。⑨从义务的角度来看,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损害与之相关的其他公民权益,意即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负有不侵害他人权益之义务。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公民言论自由的界限是与“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权力所保护的其他权益”相互博弈后的结果。于此,探寻网络言论自由之范围与程度实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权益衡量的过程。
1.纵向的权益衡量
纵向的权力—权利衡量表现:一为代表公权力之政府介入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范围与程度,此为监管的常态;二为公民网络舆论对政府公权力执行之监督范围与程度。众所周知,价值冲突的解决首先需要确立的是一些指导性原则或准则,如价值位阶原则、比例平衡原则、功利主义原则以及个案平衡原则。⑩在纵向上,公民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最有可能与政府所保护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发生价值冲突。政府如何协调该价值冲突,既需要遵守依法行政与法律优先的原则,也需要综合考虑个案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即个案平衡原则的运用。首先,政府监管方式的选择是判断某项权利价值位阶的重要依据,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监管的强度。台湾学者依据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的不同,将权力介入权利的方式划分为“强制当事人为一定的私法行为”、“禁止或排除私法行为效力”、“以行政处分作为私法行为的生效要件”、“行政许可处分”等。⑪根据这种分类,政府干预网络言论行为之程度由强至弱表现为强制性干预、禁止性干预、授权性干预、许可性干预。在强制性干预模式下,网络言论自由之行使被严格限定于特定行为模式之下。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行为,政府机关均可对其进行干预,并给予处罚。例如,某些关乎国家利益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必须经过特定的程序,隐藏在这一行为背后的价值冲突是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较量。政府需要判断公民行使网络言论自由而产生的价值是否与其所保护的国家利益有冲突,并且优先保护何种价值。在禁止性干预模式下,公民的言论自由行为被严格禁止或者无任何法律效力,其监管强度最高。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采取这种模式,因其存在损害言论自由权的嫌疑。在授权性规范下,公民享有作出或者不作出言论自由行为的自由,但受到其他条件的限制。与授权性规范不同的是,许可性规范要求公民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网络言论自由需要得到权力机关的登记许可,例如,我国从事营利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需要得到信息产业部门的许可,从事非营利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需要备案。其次,政府对网络言论自由保护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对言论自由享有的限制空间就越小。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采用禁止性规范的形式限制美国政府规制言论自由的权力,而公民则获得较高程度的言论自由保护。显然,在美国言论自由的价值要优于其他权利价值,如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与名誉等。再如,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思想与观点的自由交流是公民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任何人都享有自由表达、自由书写以及自由出版的自由,但是任何滥用该项自由的行为都应承担法律责任。法国刑法典第645-1条则规定展示、交换或出售与纳粹有关的物件构成犯罪,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表达。在授权性规范的形式下,网络言论自由在法国获得保护的前提是该项自由权利不得滥用——即不得侵害其他如国家公益、人格尊严、名誉、隐私等权益。
在某种程度上,公民通过网络也能对政府公权力的执行进行监督。相较于“面对面”言论,网络言论具有去中心性、跨地域性、低成本性等特点。诸上特点使得往日话语权受限的普通民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参与公共生活、评论公共事务、表达利益诉求、监督政府决策的机会。网络不仅为公民行使宪法保护之批评、建议与监督等政治性权利提供了更直接与便利的平台,也为公民创造了与政府进行博弈的机会。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谣言等现象足以对政府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公民事实上获得了与政府谈判的机会,这是传统的“面对面”言论环境下所无法实现的。然而,政府却并不能以监管的名义彻底关闭公民“批评、建议以及监督”的网络渠道,或者仅以网络言论内容为监管依据,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因为政府不能禁止任何观点的表达,仅仅是因为其发现这个观点具有敌对性或者令人厌恶,只有这种敌对性或者令人厌恶的观点已经上升为“攻击性言论”或者“煽动违法行为的言论”时政府才能对其进行屏蔽。但如果等到网络言论上升为“攻击性”时,其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事实已经出现,且难以恢复原状。可见,纵向的权益衡量不仅对政府有要求,还对权利享有主体的公民有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应同时发挥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能力。言论发表者的自我治理与自我控制能力构成言论自由的内部心理界限,而他人的权利、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秩序等权益则构成该自由外部界限的端点。因为言论表达实质上是一种将内心的思想观念公诸于众的活动,除了应有内在的思想观念之外,还必须有将这种内在的思想观念公诸于外部的行为。行为与观念并不能百分之百衔接,所以存在权益冲突之可能性。⑫
2.横向的权益衡量
言论自由意味着“凡是值得被表达出来的,都应该被表达出来”。“判断是否值得”内含有价值判断、价值衡量与价值选择过程,须与其他相关的权益比较才能明晰。⑬判断政府的监管手段是否会造成对言论自由造成侵犯,需要将言论自由与其他关涉的权利价值之间进行平衡操作。⑭网络言论自由最容易与名誉权、隐私权、声誉权等精神性权利发生价值冲突,如何衡量需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首先,对网络言论侵害之客观结果因素判断。例如,在2008年初爆发的陈冠希与多名女星之间的“艳照门”事件中,由于视频主角为当红明星,其隐私照片一经上传就被广泛传播,其负面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上传者与受害者两者。从言论行为引发的侵权后果来看,上传者与传播者行使言论自由的价值要远远低于对受害者隐私权以及对社会秩序价值之侵犯。其次,对网络言论侵害之主观目的因素判断。以公务员为例:某些网民出于私愤而在网络平台发布诋毁公务员的言论,网络推手捏造公务员贪腐的事实或者利用照片处理技术传播其虚假不雅照片等。从发表言论的目的来看,言论针对的是特定的公务员个体,带有主观上的故意且具有人身攻击性。从言论的影响结果来看,言论一经上传网络不论受害者是否知晓该言论就已经构成了侵权既遂,因为快捷、互联而公开的网络传播言论不受时空限制。在此情形,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就要低于名誉权的保护,政府对这种言论的监管就应更加严密。然而,在现实中也存在非以“侵害他人权益”为目的的内容中立性言论,例如网络公布的关于某一少数民族特殊的婚俗言论,公共机构在网上公布的某一地区公民工作行业偏好调查报告等。言论发表者并不以攻击他人人格尊严为目的,而只是听众因自身的主观理解而认为其存在侵犯其权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能否对言论自由进行监管还须考量言论发表目的与已发生之客观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确实造成了受害者权益的损失,且这种损失的价值不低于该言论发表所带来的价值,那么政府就有权对该言论进行规制。从以上分析可知,网络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之间的较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能够对衡量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主观目的因素、客观结果因素以及因果关系因素。
三、美国与德国网络言论规制比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民主国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求,在原有的言论规制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网络言论规制机制。其中,美国与德国的网络言论规制机制最具代表性。
第一,政府规制网络言论是一种必然趋势。美国学界对于政府监管网络言论广为争议:有学者主张如果政府监管网络言论的内容,那么网络独一无二的交流可能性就会丧失;⑮也有人主张网络空间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且不局限在任何特定的地理位置,网络空间的言论界限只能被限定于密码与屏幕。⑯而以詹姆斯·J.布莱克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政府监管网络言论具有必然性。争议产生原因与美国传统的宪政环境有关。因为在美国言论自由一直都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护,并被视为美国民主宪政的基石,是维持自由社会秩序的必要因素。⑰美国言论自由的价值一般优于其他民主价值,如平等、人格尊严与隐私等,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绝对不能监管网络言论,只是要受到严格的违宪审查制约。与美国相比,德国政府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要相对较低:一方面其承认某些言论不受基本法保护,政府对其进行监管不致于引发违宪问题,另一方面基本法自身规定了某些国家利益优于言论自由。因此,德国法律监管网络言论的理由既可以是因该言论完全在宪法保护的范围之外,又可以是因某些优于言论自由的利益而被监管。由此可见,政府规制网络言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只是监管的方式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国宪法的制约。
第二,权益衡量是政府规制网络言论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不论是德国还是美国,违宪审查是判断政府监管网络言论自由行为是否得当的必要程序。宪法法院通过违宪审查确立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标准。网络言论社会价值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监管的强度。在美国,法官在审查政府对网络言论监管的合宪性过程中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双轨理论”与“双阶理论”。双轨(two-track)理论,⑱将监管区分为“以内容为依据之监管”与“针对内容中立言论之监管”。“以言论内容为依据之监管”以监管言论内容的传播为目的,法院需要判断受监管言论的内容是属于受保护/不受保护抑或价值高/价值低,以此判定言论监管的范围与程度。“针对内容中立言论之监管”目的则不在于言论的内容,而是为了追求其他的政策目标,如公共利益的保护。法官在判断政府监管言论自由行为的合宪性时,除了依据判例,还会进行多元价值比较。“双阶(two-layer)理论”以“双轨理论”为基础通过衡量言论之社会价值而对言论价值进行排序。低价值言论内容保护的核心在于“意见或观点表达”。言论内容社会价值越低,政府监管程度则可以越高。与低价值言论相比,政治性言论这种符合民主社会需求的高价值言论自由则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政府监管的程度就相应降低。
与美国类似,德国将言论区分为“事实陈述性言论”与“价值判断性言论”。《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众人皆有表达并传播其观点之权利,而不论其表达途径为何,均不受任何阻碍。言论自由权之行使被严格限定于“观点表达”。同一法条之第2款又指明:诸权利之行使均受法律限制——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尊重其他公民权利范围内受限。这意味着损害未成年人及其他公民权利的言论被排斥在基本法保护范围之外。基本法并没有如美国一样将所有的言论自由纳入保护范围,而是直接禁止那些显而易见或明知是非真实的言论,如种族仇视言论、淫秽言论、暴力言论以及恐怖言论等。联邦宪法法院解释了原因:言论表达的目的在于向周围之人传达智慧效果,使之受人信任,并有助于形成观点。价值判断性言论应受保护,而不论其表达是有价值或无价值,正确或错误,情绪化或理性化;事实性言论也应受保护,因为观点自由表达这一基本权利需要以之为基础才能得以形成。只有虚假的事实性言论才被排除在基本法保护的范围之外,因为其不能形成宪法上预期应得到保护的观点表达自由权。⑲可见,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是狭义的观点表达自由。政府监管网络言论自由的空间也相应地扩大,而免受严厉的违宪审查标准限制。在德国违宪审查过程中,法官适用“权利衡量”⑳的方式来监管网络言论。“权利衡量”之关键在于比例原则的运用,即将言论自由与其他受基本法保护的权益进行价值衡量。依据基本法第5条规定,真实的事实性言论以及观点陈述均受保护,除非其涉及其他被宪法保护而又值得获得优于言论自由保护的权利。未成年人权益以及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就是基本法规定的值得获得优于言论自由保护的权利,但仍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只有当表达行为侵害了人格尊严时,言论自由才必须让位;只有当言论以“侮辱性言论”形式表达时,个人名誉权、隐私权才优于言论自由得到保护。“侮辱性言论”被狭义地定义为“不是意图与人辩论而是攻击他人”的言论。“侮辱性言论”标准只是一项基本原则。通常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条法定规则能够提供明确答案,因为评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相互冲突的价值孰轻孰重,仍离不开法官主观经验及其价值选择倾向。
第三,两国均构建或尝试构建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的政府规制法律体系,并积极融入“网络技术”监管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传播净化法案》、《未成年人色情保护法》、《未成年人在线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等法案。然而,政府的立法尝试一直遭到违宪审查的挑战,原因在于以上法案是通过“限制成年人的言论自由”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当信息侵害”的目的。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Reno V.S ACLU”案件㉑中,法院判决1996年《传播净化法案》违宪,其理由为:该法案对成年人言论自由的监管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政府监管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政府不能以增加成年人言论自由行使的负担去推进“政府关切的重大利益”。㉒因为除了限制公民言论自由之外,尚有其他代价更小的替代性措施可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继Reno案之后,美国上诉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又判决《未成年人在线保护法》违宪,随后该案件一直上诉直至2009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判。该法案被判决违宪之理由在于:法案在判定网络言论是否构成淫秽事物时采用的标准过于宽泛与模糊,有导致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被禁止的危险。法案规定言论是否对未成年人有害须依据“临时社区标准”进行判断,即适用控诉法院所在州的法律来对“淫秽事物”进行界定。㉓“临时社区标准”的适用使得某些言论在法律相对宽容的州被允许,而在法律严厉的州则被禁止。违宪审查的败诉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寻求其他途径以实现其监管目的。2003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规定学校与图书馆只有在其网站上使用内容过滤软件并采取其他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有害网络信息侵害,才能获得联邦基金资助。该监管机制引入“互联网内容选择平台”作为网络内容分级的技术标准,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使用信息过滤软件以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但在内容分级标签中,“淫秽”、“暴力”、“仇视”等关键词被植入,事实上起到了监管网络言论的作用。由此可见,即使在严格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政府也有必要综合采用法律与网络技术之方式监管网络言论。
由于德国各州在电信服务方面具有单独的立法权,德国网上服务监管的法律多达二十余部。除了刑法、民法外,其中与网络言论监管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多元媒体法》、1997年《信息与传播服务法》、《州际媒体服务条约》、㉔《联邦电信服务法》、以及《联邦电信服务连接数据保护法》等。《多元媒体法》将互联网活动者划分为五类:内容提供主体、网络接入服务提供主体、网络服务提供主体、电信运营商与网络终端用户。言论内容提供者与终端用户颇似现实中的演说者与听众,接入服务提供主体为用户提供入网链接,服务提供主体为用户服务器提供软件、链接与电子邮件账户等服务,电信运营商则运用其电信线路连接所有服务器以使内容提供者与用户的电脑介入互联网。同一主体在网上可能会扮演多个角色。例如,某手机通讯公司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接入服务而成为接入服务提供者,同时也可以为了商业目的而在网上建立推荐公司产品的网站主页而成为内容提供者。因此,政府在判断某一主体因发表或传播不良信息或言论而应承担之责任与义务范围时,首先应考虑该主体在特定环境中所扮演之角色。1997年颁布的《信息和传播服务法》则规定了接入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提供者在两种情形下对非法言论负责:一是当网络接入服务提供主体与网络服务提供主体为言论之原始来源时;二是服务提供主体明知内容违法且技术上具备限制该内容的能力而又未采取限制措施的。㉕显然,德国网络言论监管法律体系建立在互联网主体架构之上,并建立了统一各州的监管立法标准,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四、我国网络言论规制机制之不足与建议
除民法、刑法以外,我国目前约有二十余部含有网络言论监管条款的法律法规。其中位阶较高的有《电信条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侵权责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15年6月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网络安全法》草案。㉖与美国的《传播净化法案》以及德国的《多媒体法》以及《信息与传播服务法》相比,《网络安全法草案》强调维护国家网络主权与保护网络安全。草案从整体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其首要价值目标在于主权、安全与秩序。政府监管网络言论之目的在于协调因网络言论自由而引发之多元价值冲突,以达至公平与正义。不同国家网络言论监管机制之差异,并非是任意或由其他非重要性因素决定,而是直接受限于特定国家所关注的核心价值。基于此,我国网络言论监管机制相较于美、德两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违宪审查机制的缺失,使得政府监管网络言论不会受到违宪审查标准的严格限制。而相应地,就很难形成相对统一的、适用层级较高的权益衡量准则。网络言论监管权益衡量标准主要源于基层民事、刑事乃至行政司法实践,极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地方政府利益保护、行政官员与法官的价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二是现有的网络言论监管法律法规效力层级低,且立法标准不一。尽管不乏监管网络言论的法律法规,但并未形成效力层级分明的法律体系。各级地方行政法规与规章中对某些关键词的解释不一致,导致适用结果的任意性;三是技术性手段与法律手段的融合度不够,导致政府监管机制在适用过程中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鉴于此建议如下:
第一,政府应确立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标准,灵活协调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定的宪政环境使得我国暂时无法建立美、德那样的“违宪审查制度”,要确立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标准主要依靠的是立法的价值引导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的经验判断。缺陷在于灵活性与适应性不够,但又容易导致结果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法律先天的滞后性使得立法机关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可能会落后于网络的发展需求,但网络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之间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尽管政府很难建立量化的权益衡量标准,但可以通过树立榜样、提供针对性强的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指引价值选择方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颁布关于网络言论侵犯名誉权的典型案例指导,在判决理由中对网络言论自由与其侵犯的名誉权进行比较,为基层法官进行价值衡量提供参照;或者政府专门针对现实影响较大的网络言论侵权事件发表指导性意见。价值判断有赖于主体的主观经验判断并受限于自身道德素养与良心,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机制的构建需要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
第二,梳理现有的网络言论监管法律体系,统一立法标准。我国目前有关网络言论监管之内容散布于各种“委员会决定”、“政府条例”、“规定”、“实施办法”、“意见”、“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之中。㉗尽管数量众多,但每个条款的立法标准却并不统一,且存在适用模糊性。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颁发且专门针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行为。该办法第十五条采用的是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分别针对九种不当言论进行了列举。㉘《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由公安部颁发且专门针对接入服务提供者之行为,其第五条同样也采用的是禁止性规定的形式,也列举了九种不当言论。㉙尽管二者之目的均在于监管网络不当言论,但在适用中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第6款中规定“封建迷信”属于不当言论,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却并未将其涵括。这就导致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传播了有关“封建迷信”的言论属于违法,但信息服务提供者传播则不违法。此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使用的“淫秽”、“色情”、“暴力”等关键性词语缺乏清晰的界定,完全取决于适用机关的自由裁量,也容易造成规范性法律文件适用的不确定性。基于此,我国应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对各级政府部门关于网络言论监管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建立统一的立法标准。
第三,注重“法律”、“网络技术”等综合监管手段的运用。当前我国网络言论政府监管机制缺乏灵活性与适用性,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量网络媒介之技术特点。网络言论要产生外部影响力,须经历发布—传播—接收三个阶段,至少要获得五个主体活动的支持:言论发表主体组织言论内容、网络接入服务提供主体提供入网链接、服务信息提供者通过网络传播、电信运营商提供网络基础通讯服务支持、言论接收者接收言论内容。㉚网络言论发表者与接收者的行为可以通过一般的监管手段得到控制,但接入服务提供者、服务信息提供者与电信运营者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并受限于计算机代码技术。可见,只有在法律规则中融入互联网技术标准,才能真正实现网络言论之监管目标。政府除了限制网络访问资格以外,还可强制性规定接入服务提供主体、网络服务提供主体、电信运营商必须开发先进的计算机信息过滤软件以供网络用户使用。信息过滤软件通过植入政府所限制的不当言论关键词,如“淫秽”、“暴力”、“恐怖”等,对含有该类关键词的信息事先进行筛选,软件用户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其接收言论的内容,以保护特定人群免受不当言论的侵害。其次,互联网自诞生以来就已形成了特有的行业规则与运行标准,政府监管机构应当与互联网行业协会进行共同的技术开发与合作,利用行业协会之自律规范也能实现监管之目的。
注释:
①(英)安东尼.奥格斯(Anthony I.Ogus):《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文学国主编、何辉副主编:《政府规制;理论、政策与案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②谢晶仁:《论网络突发事件的非对称性困境及其对策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③朱海龙、彭鑫:《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嬗变对政府行动的影响———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④李金龙、黄峤:《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⑤百度百科:微博炫富事件,http://baike.baidu.com/link?ur=0iQ3bMz7Y7dIHD_Xi01h_iEeY5pNFnAWrcI_bvf9197z3qxnANRJvxBjLVL09z19JQAmSjCjIgtd32vJ_vVvua,2016年1月24日。
⑥Wikipedia,Innocence of Muslims,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nocence_of_Muslims,2016年1月24日。
⑦赖祥蔚:《言论自由与真理追求——观念市场隐喻的溯源与解释》,《新闻学研究》2011年第108期;James J.Black:“Free Speech&The Internet:The Inevitable Move toward Government Regulation”,Richmon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winter,1997.
⑧刘静怡:《政治性言论与非政治性言论》,《月旦法学教室》第30期。
⑨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⑩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72页。
⑪林佳和:《行政法与私法:私法形成之行政处分、合法化效力与构成要见效力》,《月旦法学杂志》2015年第151期。
⑫秦前红、陈道英:《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信息网络安全海外资讯》2006年第5期。
⑬Peter E.Quint:《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德、美两国比较》,余履雪译,《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⑭Joshua Spector:“Spreading Angst or Promoting Free Expression?Regulating Hate Speech on the Internet”,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Fall,2002.
⑮Gerd Rollecke:“Der Rechtsstaat für einen Störer!——Erziehung vs.Internet?”,NJW 1996,at 1801.
⑯David R.Johnson:“Taking Cyberspace Seriously:Dealing with Obnoxious Messages on the Net”,http://www.eff.org/pub/ Censorship/content_regulation_johnson.article〉,2016年1月24日访问。
⑰Kitsuron Sangsuvan:“Balancing Freedom of Speech on the Interne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 Regulation,Spring,2014.
⑱秦前红、黄明涛:《论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以美国经验为参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黄铭辉:《言论自由司法审查体系之检讨——双轨理论的反思》,《公法新课题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25日;刘静怡:《言论自由的双轨理论与双阶理论》,《月旦法学教室》第28期。
⑲Lothar Determann:“The New German Internet Law”,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Fall,1998.
⑳权利衡量的观点第一次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在著名的Lüth决议中提出。See James J.Black,Free Speech& The Internet:The Inevitable Move toward Government Regulation,Richmon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winter,1997.
㉑Reno v.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521 U.S.844(1997),该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针对网络言论规制的违宪审查案件。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no_v._American_Civil_Liberties_Union,2016年1月24日访问。
㉒董媛媛、王涪宁:《美国防止互联网色情信息侵害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评述》,《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
㉓Miller v.California|US Law|LII/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413/15,2016年1月24日访问。
㉔德国各州均有权制定法律,为了协调网络言论规制的法律适用问题,16个州签订所谓的“州际条约”(State Treaty)。联邦政府在1997年8月1日颁布了适用于16个州的统一法典《州际媒体服务条约》。
㉕James J.Black,“Speech&The Internet:The Inevitable Move toward Government Regulation”,Richmon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winter,1997.&Lothar Determann,“The New German Internet Law”,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Fall,1998.
㉖网络安全法(草案)全文,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2015-07/06/content_1940614.htm,2016年1月24日访问。
㉗陈纯柱、韩兵:《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㉘《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㉙《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六)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的;(七)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八)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九)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
㉚㉛尹建国:《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责任编校:文泉)
The Limit of Freedom of Speech on the Internet:——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Rights
ZHANG Yu,AO Shuangho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is a basic right for citizens,but the internet i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vector for citizens,but also the substantial factor of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Whether and how governments,on behalf of power,can regulate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lies on the coordination with rights,value and interests.Hence,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goes with a process of value judgments and value choices.The existing regul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not enough to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the aspect of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and needs to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native feature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it needs to establish a special internet legal system with clear effect structures,and also a relatively fair judgment mechanism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fully using the legal means,internet technology means as well as other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ghts and other interests.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weighing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张雨,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舆情下政府公信力的法律重构研究”(13CFX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13&ZD032);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研究”(2013M5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