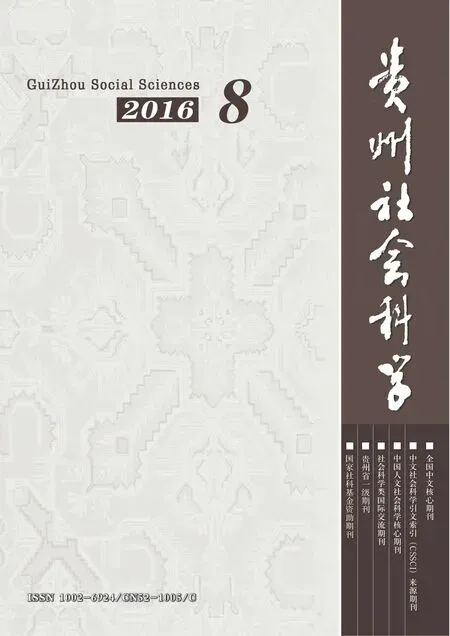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民族文化产业模式分析
邢启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民族文化产业模式分析
邢启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西南山区具有典型立体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蕴育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的格局,在历史积淀中创造出的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产业资源基础,所衍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产业,是主导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经济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普遍性和民族文化产业选择的特殊性,决定了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性和独特性。而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产业选择的内在适应性,决定了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新型城镇化产业选择的合理性。
民族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原生态
所谓“模式”,即遵循一定规律的具有某种既定特征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从系统角度理解,是系统内结构性要素在系统内的作用差异的外在表征。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模式”是指在特定地区和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时间里都在看西方、学西方,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即便到建国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对大都市总是怀揣梦想,引发了我国在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大都市充满向往,整个国家都在都市化的招引下走现代化道路。针对中国实际,也有人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途径,主张中国的城镇化战略,但很长时间里并未得到积极回应。在都市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中国社会面临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城镇化逐渐取代城市化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到21世纪初期,城镇化被定位为我国的发展战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规划术语标准》中将“城镇化”定义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镇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镇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城镇化模式就是城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在城镇化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发生的动力机制、呈现的外部形态及特征的总和。”[1]很快,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理论成为学术争论的热点,专家学者们在批判城镇化(包括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新型城镇化是在批判“城市化”(都市化)或城镇化发展道路基础上提出的概念。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特征决定了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日益深入发展的影响下,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特征,从经济的核心发展要素来看,文化经济和区域经济具有独特的代表性,民族文化产业成为西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模式之一。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事实上,这个数字反映的主要还是在城市而非城镇,处于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的城镇发展水平并不高,城镇化战略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表面是对城镇化概念的肯定性发展,实际是对城市化概念否定性的重构,产业选择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一、新型城镇化模式研究述评
新型城镇化模式可以概括为:“C模式”、“差异化模式”、“福利论模式”、“人口论模式”、“综合论模式”。其中,综合论模式(或层次论模式)囊括了前面几种模式,张占斌(2013)将其概括为四大方面: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四化”协调互动,通过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三是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2]综合论的核心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包括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新型城镇化理论上的发展,具有普遍性,而针对各个地区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则需要提出适宜的模式。
二、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性
都市化、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都离不开经济发展和产业驱动。都市化发展早期主要依托工业化驱动,尤其是工业革命奠定了现代国际性大都市的基础,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多有诟病,主要因为工业化带来人口聚集,并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空间狭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增大、经济失衡、社会转型矛盾激化、文化不适应等系列“城市病”。没有世界性的工业化大发展奠定的物质生产基础,就谈不上以物质文明为前提的现代化。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发展都是依托工业发展带来物质财富的积累,这奠定了我国从积贫积弱到奔向小康的物质基础累积,这个过程是在漫长的100多年里才逐步走过的,并且还在继续。早在1930年代,费孝通等一批学者提出中国城镇化战略,到了21世纪初期,它才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个转变意味着中国逐步迈入新型工业化国家,都市化发展的红利逐渐向乡村延伸,最终带动乡村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边界越来越模糊,我国每一个城镇都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分工带来了区域经济和城镇经济的特色化,每个区域或者城镇出现了相对明显的独特产业,并成为其主导产业。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选择必然要考虑地域因素和民族因素,使之成为适合地方发展需要的特色产业,因此出现了以某种产业为代表的产业模式代称的特色新型城镇化模式。比如,李柏文《中国旅游城镇化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一文“旅游城镇化模式”指出:“民族地区具备旅游城镇化条件的旅游城镇应当立足旅游的产业优势,围绕旅游做文章,依托旅游兴镇和立镇,使旅游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形成与生态环境和本地区实际相适应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针对西南民族地区而言,民族特色村寨、城镇都卷入新型城镇化浪潮中,其新型城镇化模式也必然是与西南山区民族经济特色产业相适应的特色新型城镇化模式。民族文化产业,指依托某种具有 “民族性”或“族群性”文化特征的经济活动,涵盖特殊的信仰、经济行为、法规制度、文学艺术、节庆、生活风俗等广义的文化范畴。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是在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基础上,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逐渐兴起的新兴产业。桂林、拉萨、景洪、大理、丽江、凯里已经发展成区域性民族文化产业中心城镇。这些城镇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典型代表性,是新型城镇化模式之一,是区别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特色新型城镇化模式。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偏重于“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3],文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而不是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产业模式,如花键提出“文化产业要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做出贡献,必须突出四个重点:发挥文化引领和提升作用,推动产业和城镇双转型; 壮大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新型企业家群体;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推动产业要素的流通和各种财富的涌流; 再造城镇空间形态,从产业园区走向文化城区。”[4]民族文化产业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区域性和民族性兼顾的特色产业,是新型城镇化主导产业,并由此可代指新型城镇化模式。
三、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原理分析
以民族风情旅游业为代表的初级模式逐渐转化到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高端模式,直接推动了西南山区大批文化旅游城市或城镇以及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村寨的诞生,并最终集聚而成新型城镇,创造了新型城镇化的独特模式,这是近40年来西南民族文化产业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于多民族集聚的西南山区而言,民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型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民族文化产业能够带动区域民族经济的良性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更是当地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缩小地区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区域民族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则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与产业化开发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与制度保障。”[5]即便这样的作用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近40年的民族村镇文化旅游业发展足够说明一切,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地的民族风情旅游显现的优势,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为世人津津乐道。桂林、昆明、景洪、大理、丽江、拉萨等地成为知名的旅游城市,傣族园(橄榄坝)、和顺、喜洲、新华、泸沽湖、青岩、肇兴、郎德、天龙屯堡、西江、阳朔、凤凰等相继成为经典的文化旅游村镇。民族文化产业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带动了城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和改善,空港和高铁逐渐在西南地区普及,令人兴奋不已,这些发展也得益于民族文化产业的直接贡献。民族文化产业成为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产业,是“新型”的根本所在。1930年代,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倡导的小城镇道路,主要是依托手工业发展,这在1980年代时期的东部地区显现出明显优势。在国家层面主导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实际依靠工业化道路来推动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生产,小城镇实际是被动发展的。而当城市化发展出现系列“城市病”的时候,小城镇凸显出优势。西南民族地区和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总体上表现出这个一致性的同时,但也表现出特殊性,就在于西南山区历史积淀出来的综合特征,决定了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独特道路。这个特殊性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发展出现特定的功能型全球化分工锁定,区域经济的互补性,让后现代中的文化消费行为把西南民族原生态文化作为天然的消费对象之一,成功探索出西南山区独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互补性区域经济的出现呢?肯定地说,就是区域文化的差异性。中国近40年的经济发展,从东到西逐步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从而带动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转型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发展,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和民族原生态文化形成强烈的互补型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仅局限在国内,也是全球性的文化消费结构之一。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区域化发展,亚太-中国-中国西南-(次区域)形成互不分离的共同体。发达国家也滋养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从而和中国西南民族原生态文化形成全球性文化消费的互补。就新型城镇化的主体而言,在早期,“老外”带动了中国西南山区新型城镇化起跑,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成为西南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半工半农的农民工逐渐转化成“市民”,成为新型城镇中的主体。由民族风情旅游业发展而来的民族文化产业,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成为互补型经济,带动了当地就业从业人员成为新型城镇的新主体,支撑了新型城镇化主体的发展。
四、新型城镇化模式普遍性和民族文化产业选择特殊性
西南山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有其普遍性意义。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决定了中国西南不可能脱离全球化浪潮而置身事外。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到了历史的关节点,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中,这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西南具有普遍性,而在全国则具有特殊性。这种模式最基本的核心结构性要素包括:工业化为基础的物质生产、一定体量的经济规模和相对完备的城镇体系、全球性人口流动和集聚、适度的环境承载力。
物质生产的相对富足是城镇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谓“新型”也不能抛开物质性生产退回到物质匮乏中去。这也并不等于说,要在每个城镇都有大大小小的工厂来进行每个人所需要的物质生产,而是在高度社会化的物质大生产中,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这个交换不仅是全国的也是全球的。除了服务水平相对低下的比较偏远的地区以外,有现代交通和信息条件等支撑,相对富足的物质生产基本都能实现。某个高原山地社区的村民可以用山羊或牦牛直接或间接通过世界市场进行交换,从而享受到远在欧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生产的产品,如独具异域特征的饮料、红酒、大米等等,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获取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海量信息,西南山区大小村寨的每个人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流通到世界各地。在现代世界市场条件下,西南山区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了物质的相对富足,使之具备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条件。
新型城镇化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对完备的城镇体系,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与普通城市的基本特征一致。人类的群居形态从几十人的村寨到几千万人的大都市,应有尽有,但都各不相同。而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是人类群居生活的特征所决定的,也是人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因而具有普遍性,新型城镇化也不例外。西南山区的新型城镇化也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城镇体系,并且和世界体系密不可分,从属于世界经济体系和相适应的规模。从目前看,西南地区还没有上千万人口的城镇经济体,从规模最大的重庆看,2013年主城区常住人口795万,总数2936万,全市经济总量在1.5万亿左右。普通地县级城镇相对较小,人口在3-5万左右,经济总量在50—1000亿元左右。城镇规模越大,城镇化体系越完备。在这些城镇中,无论以何种产业为主,都需要城镇体系要素基本完备。即便不十分完备的偏远乡镇,也完全可以在世界性市场中进行充实。
人口和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困境,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城市病、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困扰人类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理念概括起来就是: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存环境和愉悦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中,生存环境被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优雅的生存环境需要高成本才能保障。人居环境的相对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增强,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组矛盾,要确保良好的生存环境对短时间内人口快速聚集的磁吸效应行为适应,是人类社会的复杂巨系统工程。西南山区城镇规模普遍较小,部分石漠化地区环境承载力非常有限,人口的全球流动和经济的全球性补充,在外部世界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在一定时段内确保“城镇-人口-经济规模-环境承载力”的“恰到好处”,而一旦外界波动,城镇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城镇本身的依附性导致自我恢复和调节能力的极度脆弱。
民族文化产业选择特殊性指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产业选择的地域性、民族性、产业互补性以及特殊的人口聚集模式和新型环境承载模式。民族文化产业化是民族文化在高度现代化的全球社会中的一种经济活动,准确地说,是以文化内容为基础,充分融入到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建构过程。西南区域经济相对中国经济地理板块而言,具有天然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同时根据相邻区域的特点和经济发展需求,又与周边区域经济融合,云南和西藏东部地区属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圈,广西和贵州属于珠江流域经济带或北部湾经济圈,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西南地区以重庆和四川为代表,大部分属于长江经济带。从中国文化产业分布格局来讲,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总体形成四大民族文化产业走廊:藏羌彝民族文化产业走廊、南岭民族文化产业走廊、武陵民族文化产业走廊、苗疆文化产业走廊。这些具有民族性特征的文化产业和地域性特征结合,与全球文化消费市场形成互补,从而推动西南新型城镇化发展,使之具备城镇化的普遍性特征外,还具有特殊的人口聚集模式和新型环境承载模式。
西南山区的新型城镇化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多样多元的。自1980年代以来,青壮年劳动力资源普遍向东部和中部外流,这个过程持续30多年才逐渐有所改变,一些具备新型城镇化条件的村镇,在民族旅游业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带动下,出现人才回流现象,同时,这些依靠民族文化产业驱动发展的城镇里,除了当地留下来的农民工以外,还包括不确定的游客及外地流入的外来从业者。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制度性障碍的逐渐破壁,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聚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口在全国大小城市落脚,也包括西南的诸多新型城镇,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外来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贵州凯里市为例,1980年代初期,外来人口仅占10%不到,到了2010年,外来人口接近30%。类似的还有拉萨等中型城市,藏族文化产业及藏区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来者常驻拉萨,从事餐饮、酒店、导游、交通运输等行业,带动城镇纷纷改善环境条件,改善自然环境资源和打造人文景观,以争取和吸引更多游客的到来。旅游业首先选择自然环境良好的地方发展,随着旅游业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改善了城镇环境承载力状况。
五、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产业选择的内在适应性
民族文化具有双重功能,其一是满足民族内部精神文化需要,是民族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支配着民族一体化共同的精神世界认同;其二是满足民族外部文化消费需要,是全球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必然。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自在的文化,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了自觉意识,在与它者的比较中才发现自我的价值。就民族文化产业而言,它具有“经济性”、“文化性”、“民族性”,“文化产业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族文化的新的存在样态,是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的呈现方式,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的结果。”[6]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进行相互建构,作为民族文化主体,既不孤悬于全球文化之外,也不局限于民族文化之内,在民族文化产业市场中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包括对新型城镇化产业的选择,也天然具有内部的适应性。
民族文化产业是基于民族文化做为资源基础的产业化的文化再构,对新型城镇化产业选择具备内在适应性,主要表现为:通过自动调节文化内部结构,达到总体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民族原生态文化基本精神元素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和重构。新型城镇化产业选择是多样的,对于每个城镇而言,产业选择具有某种偶然性,也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一旦以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产业,必然具有内部的适应性。原生态文化舞台展演的“真实性”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旅游人类学等学科的质疑和诘难,似乎这是不可饶恕的欺骗,但这样的展演却依旧长期存在,在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领域大行其道。如何理解这种存在的合理性呢?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如波拉尼所言:“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7]对于一个族群以及他们的个体而言,他们违背本族群外的文化的观看者所需要的“原真性”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个双向的文化经济活动中,遵循的不是纯粹的经济规律,而是社会文化发展规律,表面看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通过深层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非功利的目的。
这种适应性一方面融合到公共文化供给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市场的组成部分,适应全球文化市场需要进行调整,民族文化的价值正是通过该民族文化交往中进行扩展得以体现。通过自动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的文化适应能力,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既不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也不会导致民族原生态文化内部萎缩,在互动过程中促进民族原生态文化迸发出活力和创造力。文化产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产业,民族原生态文化功不可没,必将继续发挥其内在适应能力,为新型城镇的建设作出贡献。
[1]郭斌,李伟.日本和印度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探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5):23-27.
[2]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48-54.
[3]路雁冰,刘俊娟.贵州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5-21 .
[4]花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J].东岳论丛,2013(1):124-130.
[5]刘文颖.民族文化产业化与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研究--以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2008(5):83.
[6]马翀炜,晏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产业[J].思想战线,2010(5):18-23.
[7](美)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9-40.
[责任编辑:明秀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12XJY010)。
邢启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经济、民族村镇旅游、民族文化产业。
G124
A
1002-6924(2016)08-06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