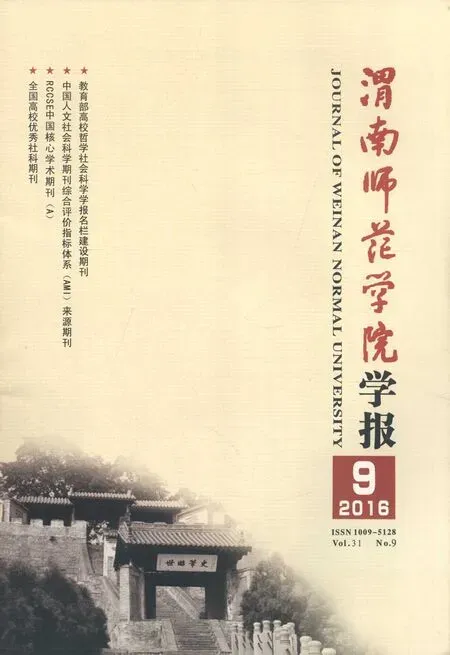《史记》与秦汉之际淮河流域军事地理初探
张 文 华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史记》与秦汉之际淮河流域军事地理初探
张 文 华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史记》兵学色彩浓厚,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秦汉之际淮河流域尤其是淮北地区成为群雄竞逐的主要沙场,文章以此作为研究的基本地域范围,充分发掘和利用《史记》的相关记录,从军事地理的视角较为细致地分析不同时段的军事争夺和攻守形势,期望以此为个案,引起学界对《史记》军事历史地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史记;军事地理;淮河流域;秦汉之际
司马迁是一位精通兵略的历史学家,《史记》具有浓厚的兵学色彩,其对战争格外关注,诚如张大可先生所言:“《史记》对于战争的记载,内容更丰富,评论更深刻,堪称古代最完备的一部战争史。”[1]291其实,《史记》不只是一部完备的战争史,更是一部周详的军事地理杰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2]891顾炎武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史记》的重要军事地理价值,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近400年来似乎并未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目前关于秦汉时期军事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德龙《汉初军事史》[3]1-255、颜吾芟《中国秦汉军事史》[4]1-242、慕中岳、武国卿《中国战争史(二)》[5]1-280、傅仲侠《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6]191-242等,其主要从军事史角度出发,或勾勒军事活动的历史演变,或以战争为主线叙述军事争夺过程,或着重分析描述具体战争始末及交战双方有关情况,或编列具体战事。客观地说,这些成果因各自研究目的和任务的不同,有的较为宏观,有的又失之具体,尤其是鲜有充分挖掘《史记》的地理价值,从军事地理角度阐释分析战争进程及军事攻守形势的。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7]1-553、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8]1-313虽然是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古代战争,前者主要针对军事“衢地”个案,后者则着重宏观的军事地理布局,其时空范围都十分广阔,但对秦汉之际的淮河流域涉及甚少。秦失其鹿后,以陈胜、项羽和刘邦为主的三大政治集团展开竞逐争夺。这三大集团,从其成员构成主体的籍贯看,主要分布于淮河流域;从其政治、军事活动的地域空间看,亦主要是集中在淮河流域。可见,淮河流域在秦汉之际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司马迁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对淮河流域的军事活动与攻守形势作出精彩的记述。笔者曾在《秦汉之际淮河流域战地的分布及其兵争路线》[9]中从总体上勾勒出诸多战争的地理分布形势,并最大可能地复原出当时的行军路线,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仍以《史记》为基本依据,从军事地理视角出发,试图细致梳理秦汉之际淮河流域的军事地理部署及其攻守形势。期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史记》军事地理价值的深度发掘与研究。
一、陈胜的军事部署与攻防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对秦末楚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作了十分精彩而又确当的总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0]759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高度,精辟地指出了这段为时短暂,但却纷争扰攘、急剧变化的历史的根本特征和地位,另一方面又以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其间政治形势鼎革变乱的特殊性。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采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方式率领戍卒900人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武力翦灭暴秦的序幕。作为一个毫无政治背景和社会基础的下层农民,陈胜得以发动起义,主要是利用了三方面的优势:其一,秦行苛政,不得民心,“天下苦秦久矣”[10]1950;其二,赵高等诈杀公子扶苏,而“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10]1950;其三,楚怀王死于秦,而楚将项燕为秦所杀,楚人至今怀念于心,“或以为死,或以为亡”[10]1950。如果说第一点是起义的客观条件,那么后两点则是起义军领袖的主观努力了,它充分显示出陈胜的聪明才智和独特领导智慧。应该指出,义军领袖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是“从民欲也”[10]1952,其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陈胜、吴广是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市南蕲县集)大泽乡首先起事的,其军事部署和进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大泽乡起事至攻克陈县,是义军初步发展阶段。义军攻陷大泽乡后,既而又攻克蕲县。占领蕲县后,在此进行了第一次军事集结和部署。陈胜分兵两路,一路为东线,由符离(在今宿州市东北)人葛婴率领,攻略蕲县以东地区;另一路为西线,由陈胜本人率领,是为义军主力部队。西线主力进军顺利,所向披靡,从蕲县出发,沿途先后攻克铚(今宿州市西南)、酂(今永城市西)、谯(今亳州市)、苦(今鹿邑县东)、柘(今柘城县北)诸县*《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云:“攻铚、酂、苦、柘、谯。”按,太史公叙陈胜西进路线,当是混而言之,未以其先后为次,观诸县地理位置,其序当以铚、酂、谯、苦、柘为是。,进而攻杀陈县(今淮阳县)守丞,并占领陈县。东线葛婴军一直渡淮攻至东城*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东城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也。”此则当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后还军陈县复命。
陈胜的这种军事安排和行军情况,有颇可值得注意之处。其一,蕲县北距彭城不远,又地处秦驰道近侧或就在驰道上*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巡,“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史念海先生《河山集四集·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指出,此处之“衡山”不在今日湖南,当在今江淮之间的六安一带,甚确。始皇此行是从彭城出发,西南渡淮的,渡淮处在九江郡治所寿春(今寿县),因史文简略,彭城至寿春间所经路线不太明确,但蕲县就在彭城与寿春之间,揆诸形势,当在驰道上,或在其近旁。,有交通之便,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应该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但陈胜并未取道彭城(今徐州市),亦未派兵攻打彭城,其间秘密何在呢?考究当时形势,这主要是由于义军初起时势单力微,仅九百人,攻下大泽乡和蕲县后,兵力虽又得到一些补充,但仍然很是弱小。而彭城为东楚重地,交通四达,秦的统治实力必然强大,且容易得到补给救援,义军自然难以抗衡。可见陈胜不从蕲县北上彭城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强就弱,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战略。
其二,陈胜本人率主力西攻,向秦的心脏挺进,但观其沿途所向披靡的情景,此线当为秦统治力量的空虚处。对于此点,还可从其他方面得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战国以来至于汉初的重要经济都会和政治中心,铚、酂、谯、苦、柘五县没有一个预列其中,这表明诸县在秦汉之际并未有若何的重要性。既然地位不甚重要,秦的统治力度自然要较其他地区松弛些、薄弱些,同驰道相比,其间的交通道路也应该不会太为宽广畅达,但这正为小股兵力行军作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不过,攻克陈县的情形与此五县有所不同。这是因为陈县为陈郡治所,地处“楚夏之交”[10]3267,地理位置特殊,水陆交通便利,自然成为秦控制一方的重要据点。陈县统治力量的强大,也确实引起了陈胜的足够注意。在攻打陈县前,陈胜对部队作了一番调理整顿,史书称之为“行收兵”[10]1952。因史文简略,“行收兵”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详知,但从攻克陈县时义军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11]1787的规模来看,招纳士卒、严明军纪、调整作战方略等项内容当在其中,否则要集结起数万人的部队,将其率领好、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是有一定困难的。陈胜对攻打陈县的这种小心谨慎态度,正是从反面说明了此地秦的统治力量是较为强大的。但在正式攻打时,义军并未花费多少气力便已攻克,这是因为“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10]1952,陈胜由此取得了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
其三,陈胜派葛婴东略地,葛婴行军路线的特点与陈胜颇为相似,即均未取道大路,而走的是小路。蕲县以东有一条贯通江淮的大道,其走向大致是沿广陵(今扬州市)、东阳(今盱眙县东南)、盱台(今盱眙县东北)、下邳(今睢宁县西北)、彭城(今徐州市)一线,项梁北上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不过,对刚刚起兵、势力微弱的葛婴军来说,取道此途南下确有较大难度。有鉴于此,葛婴便改从他道。葛婴行军的具体路线司马迁没有作出详细记载,只是说“葛婴至东城”[10]1954,但从后来项羽垓下(今灵璧县南)败退的路线看,二人走的乃为同一条道路。项羽渡淮后,经阴陵(今定远县西北)、东城以至乌江(今和县东北),及项羽败死,灌婴又从历阳(今和县)渡江而平定会稽诸郡,而这一条道路,“仅为彭城与江东间之一捷径”,“此捷径初非通衢”[12]552。正因为此非通衢大道,秦的统治势力也当较他处为虚弱,反而成为实力本不强大的葛婴义军的最佳进军路线。揆诸形势,葛婴渡淮处当在钟离(今凤阳境内)一带。渡淮后,攻克阴陵、东城,并在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只是后来得知陈王已立,才杀襄强回师复命的。此等情势,也表明取道于此行军较为顺利,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第二阶段:从陈胜称王至其被杀,是为义军发展至辉煌顶点并走向败退时期。陈胜在陈县称王,既表明义军已经有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和领导中心,也标志着义军的发展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前期,陈胜义军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一则其本身兵力已发展至数万人,兵车、骑士亦足称道,二则外部形势一片大好,“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10]1953于是,陈胜顺应形势,抓住机会,以陈县为中心,遣将纷纷四出徇地,史称“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10]1956。就见于史籍记载者言,有如下10条出兵路线:(1)以吴广为假王,监领诸将西击荥阳;(2)周文西击秦;(3)武臣、张耳、陈余率军北上徇赵地;(4)周巿北徇魏地;(5)邓说将兵居郯*《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和《汉书》卷三十一《陈胜传》均作“郯”,颜师古以为是东海郡之郯县,司马贞《史记索隐》则云:“章邯军此时未至东海,此郯别是地名;或恐‘郯’当作‘郏’,郏是郏鄏之地。”按,司马贞说为是,观《陈涉世家》上下文意,郯地当在陈县以西而不在陈县以东。;(6)伍徐将兵居许(今许昌市东);(7)宋留将兵攻南阳(今南阳市),欲从武关入关中;(8)邓宗东南下徇九江郡;(9)召平徇地广陵;(10)命武平君畔为将军,东出东海监郯(今郯城县北)下军。这10条路线,以陈县为原点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涉及范围宽广,大有燎原之势。此10条路线的分布,若以淮河为界,则在淮河以北者有8条,淮河以南仅2条;若以流域为界,则局限于淮河流域者有6条,溢出淮河流域者有4条。这种布局,是与当时的军事形势相适应的。秦国都远在关中的咸阳(今咸阳市东北),淮河以北是义军灭秦最重要的根据地,所以必须首先以较多的兵力稳固住后方,方可并力西向灭秦。溢出淮河流域的四条出兵路线,其中有3条就是直接指向关中的,显示出义军威猛的气势。尽管吴广军围攻荥阳(今荥阳市东北)时遭到了三川郡守李由的强力抵挡而未能攻下,但周文所率数十万大军竟然攻至咸阳以东的戏(今临潼东北),直有灭秦之势;宋留军南下攻克了南阳,但旋即为秦所有,终未能入武关。另外一条则指向燕赵之地,此即后来演变成为河北军者。
陈胜遣周巿北徇魏地,及“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巿为魏王”[10]2589,但周巿固辞不受,要求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当时魏咎在陈县,使者多次前往迎接,陈胜才立其为魏王,遣就国。陈胜之所以委曲求全,主要是不想树敌,因为魏地与陈县近在咫尺,为陈县北边的门户,对陈县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诸将擅自立王之事,陈胜主观上是不能容忍的,但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陈胜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如葛婴在不知陈王已立的情况下于东城立襄强为楚王,既而得知,便立杀襄强而还报命,但还是为陈胜所难以容忍而杀之。至于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胜得知后,先是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第2576页)观其前后态度之变化,与对魏王颇为相似,均系不得已而为之。。
东线武平君畔前往东海监郯下军,主要是想稳定和控制东方的局势,但事实上,这对于陈胜在西线的攻守似乎未发生若何明显的作用。因为陈王初立时,秦嘉、董緤、朱鸡石、郑布、丁疾等人已异军突起,并攻占了东海郡治郯县。陈胜是得知这些情况后才遣武平君畔为将军,监理郯下军的。然而,秦嘉不但不受命,反而借口矫陈王命将武平君畔杀害。
陈胜派伍徐将兵居许、邓说将兵居郯,一则为稳住陈西颍川地区的局势,二则可防止秦军南袭,既保护陈的安全,也为宋留顺利南下起着屏蔽作用,因为许、郯就处在从洛阳南下经方城至南阳的大道两旁,地理位置重要,颇有战略价值。后来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秦将章邯击败周文大军后,即遣别将击破邓说,“邓说军散走陈”;而章邯本人则亲率大军击破伍徐,“伍徐军皆散走陈”[10]1957。邓说、伍徐的败退,使陈县西北的门户洞开,义军的形势随之急剧恶化。章邯乘胜逐北,直攻陈县,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既而又引兵击陈西张贺军,陈胜亲自监战,结果失败,张贺战死,陈胜亦退兵至汝阴(今阜阳市)。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二月,陈胜为其御庄贾所杀而降秦。已克南阳的宋留听说陈胜已死,得地复失,无法进入武关,便引兵东至新蔡(今新蔡县),遇到秦军后以军投降,结果宋留车裂而死。这样一来,陈县以西皆为章邯所攻占,陈胜领导的义军活动亦至此宣告结束。
二、陈胜死后淮河流域的军事攻守形势
陈胜死后,淮河流域的军事形势发生了若干变化。从秦军方面说,章邯军自从将周文部队赶出函谷关,并彻底破军杀将后,咄咄逼人,几乎所向无敌,声势特别壮大。从义军方面说,陈王死后,楚王又立,亡秦活动为其他新生力量所取代。这一时期,双方争夺的地域空间也发生了转移,陈县以西既已为章邯攻下,陈县以东的淮北东部地区自然成为交锋的重点,薛(今滕州市南)与彭城也因此成为新的领导中心。
当陈胜初起之时,天下云集响应,“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10]1953仅就见于史籍记载者而言,大体有如下11支:
(1)刘邦初起于丰(今丰县),聚众数百人,及诛杀沛(今沛县)令,立为沛公后,收沛中子弟3000人。[11]9-10
(2)项梁斩杀会稽守,在江东起事,得精兵8000人。[10]297
(3)东阳(今盱眙县东南)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强立东阳令史陈婴为长,县中从者达2万人。[10]298
(4)六(今六安市)人黥布和番君吴芮叛秦于江淮间,聚兵数千人。[10]2598
(5)高阳(今杞县西南)人郦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人。[10]2661
(6)昌邑(今巨野县南)人彭越常活动于巨野泽周围,为“群盗”,陈、项初起时,持“两龙方斗,且待之”的观望态度,岁余后即立为长,聚泽间少年百余人,旋又收得千余人。[10]2591
(7)淩(今泗阳县西北)人秦嘉[13],铚(今宿州市西南)人董緤,符离(今宿州市东北)人朱鸡石,取虑(今灵璧县东北)人郑布,徐(今泗洪南)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于郯(今郯城县北)。[10]1957
(8)张良在下邳(今睢宁县西北)聚少年百余人。[10]2036
(9)沛人王陵聚集党徒数千人,居于南阳。[10]2059
(10)赵佗在南海“稍依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待诸侯之变。[10]2967
(11)蒲将军军*《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云:“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按,蒲将军也曾起兵应涉,只因史文阙略,对于其身世及起兵地点不得详知,观其入项氏军后,屡嘱重任,亦一将才也。。
这11支义兵,集中分布在淮北东部及淮河以南地区,历经归属合并,最后形成三大支骨干力量,即项羽、刘邦和彭越,其中项羽的实力最为强大,刘邦次之,彭越最弱,游荡于刘、项之间,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如前所说,陈胜死后,淮河流域的争夺重心转移至淮北东部地区,但陈县一带也还发生过若干值得一提的战事。章邯破陈后,陈王故人、将军吕臣率苍头军从新阳(今界首市北)起兵,一举攻克陈县,诛杀庄贾,复以陈为楚。但旋又为秦左右校所破。吕臣败走,复收兵。时值黥布引兵北击秦,遂与吕臣军合,破秦左右校军于青波(或作清波),复以陈为楚。[10]1959-1960
此时淮北东部的局势是:秦嘉听说陈王败死,便于秦二世二年(前208)正月在留(今沛县东南)立景驹为楚王。[10]766雍齿据丰反沛公,沛公攻之不下,乃前往留从景驹。陈县攻克后,章邯别将引兵北向,欲以平定楚地,攻屠相(今濉溪县西北),至砀(今砀山县南)。景驹遣东阳宁君*按,关于东阳宁君和秦嘉的关系,历来说家多有纷争。或认为是一人,或认为是二人。综观诸家之说兼及史实情况,当以二人为是。参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三家注及《汉书》卷一上《高帝纪》颜师古注。和沛公引兵而西,与秦军战于萧(今萧县西北)西,结果失败。收兵回留后,再次出兵攻砀,激战三日乃克定。攻下邑(今砀山县),克之;攻丰,不拔。[10]352
淮南地区的形势是:召平为陈王徇略广陵未下,听说陈王败走,秦军将至,于是渡江,矫命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遂率8000精兵渡江而西击秦。及至东阳,陈婴以兵属项梁,项梁兵力因此大增,达3万人。[10]298
既而项梁渡淮,淮北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项梁渡淮后,黥布、蒲将军以兵属项梁。及行军至下邳,兵力已增加到六七万。面对项梁实力的迅速膨胀,颇有野心的秦嘉不免多有狼顾之心,于是从方与(今鱼台县西)还军彭城,意欲抵挡项梁继续北上*《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云:“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据《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是在秦二世二年端月(正月),地点是留,是时章邯围魏王咎,临济告急,秦嘉当是从留引兵救魏之急的。但当他看到项梁气势汹汹地北上时,狐疑对己不利,遂不再继续前往击秦,仅行至方与而返,驻军彭城以待项梁,故《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秦嘉“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遂以“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10]299相号召,发兵攻灭秦嘉,收编其部属,景驹亦走死梁地,项梁则引兵入薛(今滕州市南),兵力达十余万。至此,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欲以号令诸侯的局面仅维持了短短四个月便昙花一现了。
秦嘉败死,号令大权便归于项梁。二世二年(前208)六月,项梁“召诸别将会薛计事”[10]300,拥立楚怀王孙子心为楚王,都于盱台(今盱眙县东北)。此时尽管楚王在盱台,但真正的领导中心还是项梁所在的薛县。
这个时期淮北地区的攻守形势是这样的:一是项梁遣项羽西攻襄城*按,因史文简略,项羽西攻的出发时间和地点不得确知。但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羽西攻是在二世二年(前208)四月项梁攻灭秦嘉之前;据《汉书》卷一上《高帝纪》,项羽还报命在是年五月;据《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项梁渡江是在二月。项梁攻秦嘉前曾屯军于下邳,考虑到广陵至下邳也有较长一段距离,行军略地尚需一定时日,因而估计抵达下邳当在三月左右。襄城远在淮北西部,城又久攻不下,且来回往返亦需较多时间,故此推测项羽当是在三月从下邳出发西攻的,前后历时两月余。(今襄城县),先是久攻不下,既而攻克,项羽屠城而归,还至薛报命。二是项梁自胡陵(今鱼台县东南)遣别将朱鸡石、余樊君至栗(今夏邑县)击秦军,结果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归。[10]299三是刘邦两次攻丰不下,遂至薛见项梁,项梁益沛公卒5000人,五大夫将10人,还攻丰,拔之,雍齿逃奔于魏。[11]13四是章邯大军围临济,魏王派周巿请救于楚,楚遣项它前往救魏,结果为章邯所败,魏王咎投降,自焚而死。[10]2589-2590五是章邯破楚、齐救兵,降魏王后,田荣率齐余兵东归,章邯直追,围于东阿(今阳谷县东北)。项梁得知田荣之急,乃引兵北至东阿,大破章邯军。章邯溃退西撤,项梁乘胜追北,欲与田荣合力西击,但田荣不肯。追至定陶,项梁再破秦军,遂乘胜占据定陶。[10]2644六是秦军西溃,项梁遣沛公、项羽别攻城阳(今菏泽市东北),破军屠城。又西至濮阳(今濮阳市南)东再次击破章邯军,于是回师攻定陶,攻之不下,遂转而西向略地,与秦军大战于雍丘(今杞县),三川守李由被杀,秦军惨败。雍丘攻克后,又回头攻外黄,外黄未能攻下,于是转攻陈留(今开封市东南),陈留亦坚守不下。[11]14-15七是项梁在李由被斩、再破秦军、攻占定陶等的军事胜利面前产生了轻敌心理,“益轻秦,有骄色”,不听劝谏,将骄卒惰。结果秦“悉起兵益章邯”,章邯军威复振,卷土而来,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战死。[10]303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到,自秦嘉、景驹败死以来,淮北的争夺集中在以薛县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下邳、彭城、萧县、相县、砀县、栗县、下邑、留县、沛县、丰邑、胡陵、方与、亢父、昌邑、定陶*定陶位于济水南岸,菏水从其东北分济水而出,东至胡陵入于泗水,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济水流域。但定陶就在济、菏水交汇处,即淮河流域与济水流域的交界处,且其水陆四达,自战国以来就有“天下之中”的美誉,实在是淮河流域北方的一个重要门户,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定陶也归入淮河流域来。、城阳、东阿、陈留、雍丘、外黄、襄城等均为战略要地,争夺激烈,战事频繁。这些要地,除城阳、东阿不属淮河流域外,其余均位于淮河水系的睢水、汳水、获水、泗水、菏水诸水两岸或近旁,同时又处在陆路交通的重要位置,交通便利自不待言,因而其军事价值和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于章邯军而言,只要完全攻占和控制了这些重地,就可以说是置义军于死地了;对于义军来说,也只有占领了这些要地,稳住其局势,才能有稳固的后方基地,才能有迅速便达的军事通道,才能谋图西向灭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军与义军在淮河流域你死我活的搏斗,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战略要地控制权的争夺。关于这一点,从双方的进攻方向中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秦军的进攻从陈县出发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章邯率领,是为主力部队,直捣魏地临济。临济在济水岸边,定陶的上游,降下临济,抢得上游,既有回旋余地,也可以高屋建瓴之势,东北向则攻齐地,东南向则攻楚地。后来章邯击败齐、楚、魏军,攻下临济后,直指东阿,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另一路由别将司马卬率领,北上攻略相、砀、萧、栗诸地,而这既是楚地西部的要害之区,也是义军西出北上最便捷、最重要的一条通道。秦军的这种攻夺,就是要扼控义军西出的门户。面对秦军的攻势,义军也正是从这两条战线出兵应战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义军出兵的这两个方向,并不是面对秦军的围攻才被动地作出的,而是其从一开始就主动地选择了这样的发展方向*项梁在渡淮后,即遣项羽西攻襄城,其所经路线虽然不得详知,但西向发展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襄城在洛阳通往南阳的大道上,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军事价值重大,南下经方城可入南阳,进而由武关入关中;北上可至洛阳,进而由函谷关入关中。至于定陶一线的出兵方向,刘邦早在斩杀沛令、收得沛中子弟3000人后,就北向攻胡陵、方与了。。这些情况表明,此期双方争夺的焦点无非是位于这两条战线上的关键性的战略据点,难怪章邯在定陶破灭项梁后,就以为“楚地兵不足忧”[10]304而北上渡河平略赵地了。
项梁死后,淮北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一,章邯军从定陶北上,撤出了淮河流域。其二,项羽、沛公与吕臣军自陈留引而东归,吕臣驻军彭城东,项羽驻军彭城西,沛公驻军砀县,大有三足鼎立之势。其三,迫于形势,楚怀王从盱台徙都于彭城,亲自将领项羽、吕臣军,并封项羽为鲁公,吕臣为司徒,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至此,彭城成为新的领导中心。其四,楚怀王分兵两路击秦,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号为卿子冠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英布、蒲将军为将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沛公率领,收陈王、项羽散卒西向略地入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0]356。北上一路的军事活动已经不在淮河流域,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下面仅将西路军的活动作一简单叙述。
当时秦军强大,常常斩将杀臣,攻城克地,乘胜逐北,诸将莫有以先入关者为利的。唯独项羽有家仇国恨,强烈希望与沛公一道西入关击秦,但在楚怀王诸老将的反对下,项羽卒未能如愿。同北路军相比,刘邦所率西路军的实力是非常弱小的,但其行军转战的成绩却颇值得称道。刘邦从砀县出发,辗转抵达成阳(今菏泽市东北)、杠里(或作扛里,在成阳附近),击破秦二军。[10]357随之回军,于二世三年(前207)十月,又在成武(今成武县)南攻破东郡尉军。[10]769-770十二月,还军至栗(今夏邑县),夺刚武侯军4000余人并为己军,与魏将皇欣、武满*按,“皇欣”于《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作“皇”,“武满”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作“武蒲”。军联合攻破秦军。[11]17二月,刘邦又从砀北上,“击昌邑,彭越助之”,但未能攻下,遂引兵而西。[10]2592刘邦西至高阳(今杞县西南),用高阳人郦食其之计,攻占陈留,得秦积粟甚多。[10]2692-2693三月,攻开封(今开封市西南),将赵贲军围于城中,城未克下。[10]2023又西上与秦将杨熊会战于白马(今滑县东)、曲遇(在今中牟附近)东,大破之。[11]18四月,南攻颍阳(今许昌市西南),因张良略韩地,“下韩十余城”[10]2037。此时赵别将司马卬欲渡河入关,刘邦于是“北攻平阴(今河阴县),绝河津,南,战洛阳东”[10]359。洛阳一战,刘邦失利,遂从缑氏县东南的轘辕隘道南下进入颍川,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今禹州市),自己则与张良等人由方城南下,约降宛城(今南阳市),西入武关。
综观这个时期刘邦的军事行动,虽然为时仅9个月,但涉及地域十分广泛,大致彭城—砀县—陈县一线以北的淮北重要地区,都留下了刘邦的足迹。其攻城略地不以必克为是,能破则破,不能则引兵而去,要以保存实力为重。流动作战,攻略方向飘忽无定,但大体上先是以砀县为中心上下游动,既而西攻。在淮北西部,攻下陈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发挥了后勤保障的作用,实际上成为刘邦军事活动的重要后方基地。淮北西部的攻略趋势总体上有函谷关和武关(或南阳)两个方向。刘邦的根本目标是要入关灭秦,这里的“关”,既可指函谷关,也可指武关,因为由山东地区攻入关中,非此两关莫属,所以刘邦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地方进行的。当刘邦正在攻略韩地的时候,得知赵别将司马卬欲渡河入关,于是火速北上,攻平阴,绝河津,结果在洛阳东吃了败仗。刘邦此行,既有阻挡他人抢先入关的意图,也有自己从函谷关入关的打算。倘若洛阳之战刘邦获胜,或许刘邦就此取道函谷关而入,秦汉之际的历史也将因此而增添一些新的情况。洛阳战败后,刘邦毫无反顾之意,迅速取道轘辕关,直奔南阳方向而下,就是要取道武关而入的,因为他不想看到因不能从函谷关入关而导致自己后他人而入关的被动局面。刘邦的这种急切心情,张良看得最为清楚,所以就劝说他不要因为急于入关而不顾后方的稳固。
相比较而言,经由函谷关一线入关路途较为近便,对此,刘邦并不是没有积极努力的,只是因为条件不够成熟,时机对己不利,所以只好作罢。而刘邦南下南阳,取道武关的进攻路线,正好是当年宋留所欲进取的方向。
三、楚汉时期刘、项对淮河流域的争夺及防守
楚汉战争时期的主要战场在关东地区,而淮北又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封地所在,因而此期刘、项双方对淮河流域的争夺也是格外激烈的。
(一)项羽分封及其对淮河流域的争夺
刘邦和项羽对淮河流域的争夺是从项羽分封诸王开始的。项羽入关后,杀子婴,屠咸阳,无意留都关中,只是一心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10]315于是分封十八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之地九个郡,几乎将整个淮北地区据为己有。项羽分封,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压制和打击刘邦,牺牲他人利益,分化潜在力量,扶植亲己势力,确保自己对淮北地区的控制权,这从其所封诸王的实际情况中便可看得十分清楚。
十八王之中,汉王刘邦是项羽的头号“敌人”。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关者王其地,但由于项羽北上救赵,对付的是秦军的主力部队,所以后刘邦而入关,这使得项羽在“约束”面前已经被动一步,而此时能与其分庭抗礼者也唯有刘邦,故而对刘邦的分封,项羽还是伤了一番脑筋的。尽管项羽自己不愿留在关中,但关中毕竟有优越的经济、军事形势,王于关中者自然会有诸多优势,对其所在的关东也会形成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一点项羽当然是清楚的*当时就有人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按,关中地区的优势,时人多有评论。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云:“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而汉初娄敬更有一段至为精辟的分析,《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云:“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这就是说,项羽一则要打着“约束”的名义,二则要遏制刘邦的势力,于是就想出了“巴、蜀亦关中地”[10]316的计策,将刘邦封于巴蜀、汉中之地,都南郑(今汉中市)。巴蜀虽亦有经济上的富饶,但其僻居西南,有秦岭、大巴、米仓诸山的阻隔,路途悬远,交通险恶,不易北向扩张和发展,相对于关中而言,是要大为逊色的,所以当时韩信就对刘邦说:“王独居南郑,是迁也。”[10]367
刘邦既封巴蜀,项羽乃立三秦王,将关中一分为三*按,《史记》中所见关中的范围有广狭之义,狭义的关中指今宝鸡和潼关之间,广义的关中则既可包括今陕北地区,也可包括巴蜀及汉中地区。不过巴蜀、汉中属于关中是项羽首先提出的,后来鲜有人遵用,我们这里所说的关中是包括今陕北在内的。另参见史念海先生《河山集四集·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第145、146页。。项羽封立三秦王,其目的至少有三:一是扶植亲信势力。雍王章邯原是秦军主帅,后因战败投降项羽,而翟王董翳是劝章邯降楚的,塞王司马欣则曾与项梁有故,因而尽管三人均为秦降将,但项羽认为其政治立场已经倒向自己,分封三王既可安抚三将,也可作为亲信势力来培植。二是分割关中天然形胜,以免造成对关东的威胁。关中为四塞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又居于上游,对关东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项羽便将其一分为三,章邯王咸阳以西,司马欣王咸阳以东至于黄河,董翳王上郡(今陕西北部),互相牵制,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样就大大减弱了关中天然的军事优势,对关东地区就难以有若何的威胁了。三是拒塞汉王刘邦北上。刘邦虽被迁于巴蜀、汉中,但项羽还是心有余悸,担心其卷土重来,所以他封立三秦王的另一个目的,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抵制汉王的北上,这一点司马迁已经指出来了,他说项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10]316,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成为刘邦所指斥的十大罪状之一的根本原因。
项羽对魏王豹和瑕丘申阳的分封情形刚好相反,但其根本目的一致,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魏王豹原封于魏地,按理说可以不动,但项羽欲占其地而有之,遂徙封魏豹为西魏王,王河东地。河南之地号为“天下之中”,交通四达,北濒大河,西有函谷,南有熊耳、伏牛诸山,内有伊、洛平原之富庶,可谓关东之“善地”。照理说,项羽应该据为己有,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封申阳为河南王,王河南地。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居于重要位置,容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尤其是它为关中出关的第一站,势必成为多事之区,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一则可由其承担各方面压力,二则可使自己的封地受到屏蔽,不直接暴露,其良苦用心是可以想见的。
位于淮北地区西北一隅的韩地,虽然经济比较差,但其地理位置特殊,军事价值很高,在战国时曾被人们称作是“天下之咽喉”[14]239,因而也就成为项羽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项羽先是名义上令韩王成仍都于阳翟(今禹州市),但旋又以无军功为由,不遣之就国,而是将其带至彭城,废以为侯。韩王成不久便被杀害,韩地实际上就为项羽所控制,只是后来为抵挡刘邦的进攻,才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项羽的这种反复做作,正是其争夺西北一隅之地的直接体现。
齐地被山带海,膏壤千里,素有大国之风,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项羽自然不希望在自己的头顶上有一个强大的齐王出现,于是就将齐地一分为三,分王田都为临淄王(先称齐王)、田巿为胶东王、田安为济北王,这实际上是分化瓦解潜在势力,与分关中为三王的做法如出一辙。
项羽封立黥布为九江王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形。当阳君黥布是楚军中最为得力能干的一员大将,项梁、项羽屡屡嘱以重任,经常充当前锋军,在击秦嘉、降章邯、破函谷、入咸阳中屡建奇功,“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10]2598。因此黥布在诸将中功劳最大,也最得信赖,项羽封其为九江王,王淮南地,一则慰抚功臣,扶植亲己势力,二则以其为南部之藩属和后方基地。关于这一点,在后来项羽对黥布的态度中有所反映。当齐王田荣叛楚时,项羽向九江王征兵,黥布仅遣4000人北上助楚伐齐;当汉王刘邦乘楚击齐,国内空虚,便劫五诸侯兵攻入彭城时,黥布又称病不佐楚。这两件事使得项羽对黥布大为恼火,但只是遣使者予以责让,终不发兵击之,就是因为黥布毕竟是自己最为信得过的重臣,“又多布材,欲亲用之”[10]2599。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窥知项羽当初封立黥布的真实意图所在了。
总上可见,号为“沐猴而冠”的项羽在封立诸王时却是精心设计了一副蓝图。这副蓝图的基本格局是他自己奄有几乎整个淮北地区,其重臣黥布则拥有淮南地区,作为最忠实的屏藩;淮北周边之地则或予以利用,或化大为小,要以不为己患为是。换言之,通过分封,项羽几乎将整个淮河流域控制在手,淮北为其根基,淮南为其辅翼,俨然一派霸王气象,只是由于后来历史形势的迅速变化,他的霸王梦想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二)淮北地区的攻守形势
淮北地区地势平衍,一望无垠,几无天然形胜可言,因而从军事地理形势的角度看,它是远远比不上四塞为固的关中的。项羽以淮北诸地自封,可能是只从经济的角度着眼了,但却因此而导致在军事上处处被动、受敌。对项羽而言,楚汉时期淮北的军事压力主要来自齐地、荥阳(今荥阳市东北)和南阳三个方向,其军事攻防也自然集中在这三条线上。这三个方向的军事争夺,或相继而来,或同时并举,常常令项羽措手不及,疲于奔波,不遑应付。
1.齐地方向的攻守
项羽的分封,引起最大不满的要数田荣,而其祸端也就首先由此而起。如前所说,项羽对齐地心存顾忌,遂将其一分为三,欲以削弱威胁,但这正成为田荣反叛项羽的基本口实。齐地与淮北接壤,是项羽的北方门户,其间又有便利的交通,因此它的稳定与否及同楚的关系状况,都直接关系到淮北的安全。
汉元年(前206)四月,项羽下令诸侯各就国,田荣趁机起兵杀田巿、田安,赶走田都,并三王之地,自立为齐王。田荣合并三齐称王,无疑是在项羽的北邻出现了强大的敌人,这也正是项羽当初所担心的。因此当项羽得知田荣反叛时,遂亲自引兵北上伐齐。结果田荣兵败,逃至平原(今平原县南),为平原人所杀。项羽击灭田荣后,纵兵烧杀抢掠,所过无不惨灭,引起齐人的极大反感。于是田横趁机收得齐散兵数万人于城阳(今菏泽市东北)反击项羽,时刘邦已攻入彭城,项羽只得撤兵南下保卫都城,田横遂立田广为齐王,项羽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10]2645-2646
齐地的形势变化很快,田广立为齐王三年后,楚将韩信引兵击齐。齐向楚求救,项羽担心韩信平定齐地后击楚,遂遣龙且前往救齐,结果龙且中计,军败被杀。汉乃立韩信为齐王。韩信立为齐王后,齐地成为权衡和决定楚、汉双方前途命运的重要砝码,诚如时人武涉对韩信所言:“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10]2622武涉的说法颇为有理,也符合当时实际,后来刘邦就是在齐王韩信的援助下才于垓下击败项羽的。这是说,在楚汉时期,齐地作为项羽的北邻,实际上有居高临下的态势,它无论是对刘邦的争夺淮北,还是对项羽的保护淮北,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自然成为双方出兵争夺的重要方向。
2.荥阳方向的攻守
荥阳方向的攻守,也可称为函谷关方向的攻守,因其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关西。这是此期为时最长、最重要的攻守方向。荥阳位于出关之后的东西大道上,又有地形之险,敖仓之富,故而楚汉鏖兵,多萃集于此。刘邦还定三秦后,即出兵关东与项羽争夺天下。汉二年(前205)四月,刘邦劫持五诸侯兵56万人东伐楚,直入楚都彭城。时项羽正在齐地,得知彭城攻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师彭城,大破汉军于谷水、泗水、睢水上,杀20余万人,睢水为之不流。[10]322刘邦吃了败仗后,返回荥阳,楚兵追击,结果在京(今荥阳市东南)、索(在今荥阳市)一带被汉军击败,楚军由此不能越荥阳而西。[10]372其后楚汉在荥阳(在今荥阳市东北)、成皋(在今荥阳市西北)争夺相持,一直到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才告一段落。
荥阳、成皋一带,实际上是淮北地区的西北门户,因为自此而东,即为平衍无际的淮北大平原,根本无险可守。从某种意义上说,楚汉相争的胜负,关键就取决于荥阳一带归谁所有,这也是为什么双方不遗余力地争夺这一地带的根本原因所在。相比较而言,在争夺荥阳方面,刘邦是有着较多优势的。刘邦的本部在关中,出关争夺荥阳,有利则可进,不利则可守;萧何经营关中,源源不断地供给士卒粮秣;且刘邦居于上游,有居高临下之势。而项羽则刚好相反,既无险可守,彭越又屡屡反于梁地,截断楚军后勤补给线,且属于仰攻,形势自然对他不利。也正因如此,当项羽引兵东归,而刘邦却听从张良、陈平之计负约追击时,楚军就从此陷于被动,再也没能挽回败退的命运*按,楚军的这种不利攻守形势,其实早在汉二年刘邦劫持五诸侯兵东伐之时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刘邦所以能直捣楚都彭城,除了兵力强大、项羽在齐地外,楚地自身易攻难守也当为事实。也就是说,一旦荥阳一带克复,楚地即暴露于外,要想保全,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和坚实的后勤保障。。
3.南阳方向的攻守
刘邦出兵关东,不外经由函谷关、武关两途。尽管函谷关近便,且有高屋建瓴之势,武关迂远,属于仰攻,但刘邦曾由此道入关定秦,故而对这一条路线不仅熟悉,而且还有着特别的感情。楚汉时期,刘邦方面就先后两次从武关南下,经由南阳而入关东。一次是在汉元年(前206)九月。此时刘邦刚刚返回关中平定章邯,便派将军薛欧、王吸南出武关,同南阳的王陵一道前往沛县迎接太公、吕后,结果被楚发觉,遣兵拒之阳夏(今太康县),终未能得逞。[10]368刘邦的此次行动,表面上是要迎接亲人,实则是对项羽态度及其军情虚实的一次试探。另一次是在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刘邦从荥阳逃归关中,收整士卒后准备再出函谷关赴荥阳,此时袁生劝谏说:
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10]373
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遂由关中出武关。行至南阳,项羽果然引兵南来,刘邦坚壁不战。这时彭越渡过睢水,大破楚军,项羽于是又引兵东击彭越,刘邦便趁机出方城,过叶县,北上成皋。项羽击败彭越后,得知刘邦已驻军成皋,于是又引兵西向,攻陷荥阳,复围成皋。[10]374袁生的这个建议十分奏效,使得项羽南下北上,东出西进,疲于应对,而刘邦此次出兵武关而至于成皋,正好走的是当年他入关灭秦时的老路。
参考文献:
[1] 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2] [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 李德龙.汉初军事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 颜吾芟.中国秦汉军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慕中岳,武国卿.中国战争史[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2.
[6] 傅仲侠.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7] 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9] 张文华.秦汉之际淮河流域战地的分布及其兵争路线[J].求索,2009,(11):201-204.
[10]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史念海.河山集四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3] 陈业新.秦嘉籍贯考辨[J].安徽史学,2003,(4):105-106.
[14] 战国策[M]. [汉]刘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朱正平】
A Study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ilitary Geography of the Huai River Basin during Qin and Han Periods
ZHANG Wen-hua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sm,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 has important value in military geography and its military color is very strong, while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Huai River Basin, particularly Huaibei Regions, became a major battle pack during Qin and Han peri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the Huai River Basin. Military geography as the angle of view, the paper makes the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postures by exploring and making full use of Historical Records. As a case, the paper hopes that academic circl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ilitary geography.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military geography; Huai River Basin; during Qin and Han periods
作者简介:张文华(1975—),男,陕西靖边人,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史及历史地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6-03-28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46-10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