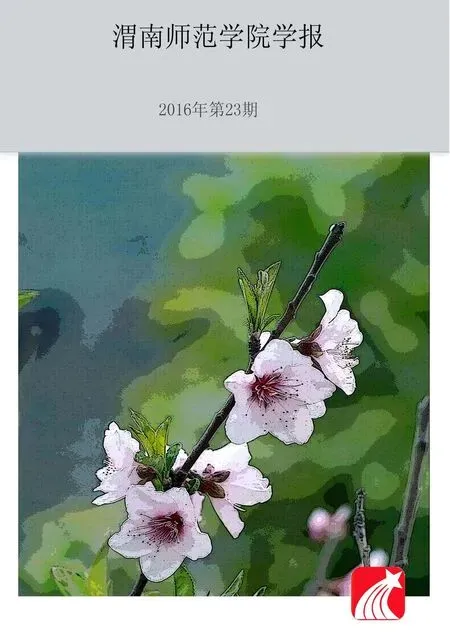佛教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本土动物变形故事的新变
张 瑞 芳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南京 210096;2.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历史文化研究】
佛教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本土动物变形故事的新变
张 瑞 芳1,2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南京 210096;2.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魏晋及至隋唐,佛教宣教故事借助于本土动物故事,将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观念逐步渗入其中,使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出现了新变。在原生故事注重祖先崇拜、强调变形化生的基础上,因果报应观念成为人与动物互相变化的重要原因,轮回转生更加强化了此类变形。同时,动物意象群和动物王国开始被建构,海外大物故事进一步发展,源于域外文化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变形故事也逐渐受到普遍接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在佛教影响下呈现出更加人情化的一面。
佛教;魏晋隋唐;动物变形故事;新变
我国本土的动物变形故事与始祖类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受到巫方文化的影响,魏晋以降,这类动物变形故事多被视为怪异现象进入志怪记载。与此同时,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佛教徒一方面利用此类动物变形故事来宣扬其戒律教条,劝导人们行善修持,另一方面则将因果报应、转世轮回观念运用于动物变形故事中,编造出新的故事类型。这使我国魏晋以至隋唐时期的动物变形故事在主旨意义与情节模式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佛教教义、教旨的核心理念,成为其时动物变形故事“升级换代”的重要依据。
一、佛教初传时期对变化法术的利用 及其对动物变形故事的重视
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传播的方式是极其曲折而艰难的,外来的佛教徒为了传教的需要,不得不当众玩弄一些西方的幻术,以吸引受众,而大量涌入的胡人商客——其中当有一些来自佛教国家——也可能在街市上排演一些他们所熟悉的本民族的杂技,以便买卖交易或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么,这些幻术和杂技演出中就可能包含一定的佛教内容。[1]117张衡《西京赋》和《搜神记》“天竺胡人”条中都对此类情况有所记述,足见佛教借助幻术在当时所受到的关注。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依附于道士、方术,被认为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是求神祈福的祠祀,其修行的方法也等同于黄老养生之术。为了在中国立足,扩大影响,一些前来传教的外国僧人都重视学习中国的方术信仰和谶纬迷信,并以此吸引教众。这样,早期来华的佛教徒一方面以幻术为起点,向本土道教巫方法术借鉴靠拢,同时,又结合自身善于利用动物故事阐述哲理的特点,把变形法术与动物故事相结合,改造本土原有的涉及动物变形的故事,利用本土民众猎奇、好奇心理,开启了借助动物变形故事宣传佛法的历程。
不同于本土文化对动物变形作为怪异事件的重视,佛教更注重借助动物变形阐述教义、教旨。受此影响,魏晋及其之后的动物变形故事开始呈现出寓含佛教文化、宣传佛法思想的发展趋势。劝善惩恶以及戒杀生、轮回转生等观念逐渐成为这类变形故事发生的主导因素,人与动物的转化模式也与之前原始观念之下的变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人变为动物成为主要变化趋势。
二、佛教对本土动物变形故事的影响与改造
(一)“人变动物”故事在志怪中的大量出现与佛教果报观念下的惩戒行为
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多围绕“动物变化为人”的怪异现象进行描述,除溯祖传说和以道教升仙、炫术为主题的故事外,“人变化为动物”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以宣传因果报应、惩戒观念为目的的“人变动物”故事的出现,则是佛教思想在初传时期对民众观念意识影响最大的体现之一。
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就其初期在中国的实际传播情况而言,其借用并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孝”的强调。佛教主张人们应摒弃情感困惑,这本身与忠孝观念存在矛盾,但在传入中国后,为吸纳教徒、立足本土,佛教逐渐向中国本土的孝文化靠拢,成为其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借助于动物变形故事在至孝方面的深厚基础,佛教徒们以宣扬“孝”为依托,在动物变形故事中将因果报应、转生轮回等观念渗入其中。
1.不孝而现世变形为动物
围绕惩戒“不孝之人”的故事,佛教徒在宣教故事中将“人变动物”的情节巧妙植入: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切蚯蚓为羹以食,姑怪其味,窃藏其一脔,留以示儿。儿还见之,欲送妇诣县,未及,而雷震失其妇。俄从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头为白狗头,言语不异。问其故,答云:“以不孝姑,为天神所罚。”夫以送官。时乞食于市,后不知所在。[2]56(《冥报记》)
祁连休先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对这类不孝故事按时间顺序归为两类,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蛴螬炙型故事”和隋唐五代时期的“逆妇恶报型故事”。尽管这两类故事在结尾处理上存在差异,前者突出盲目复明,后者重在指出不孝妇遭受惩罚,但依据不孝妇奉养盲母这一基本情节来看,这两类故事在最初应有同源性。上引“河南妇人”故事即为逆妇恶报型故事的代表,晚唐李亢《独异志》“狗头新妇”条与此类同。祁著中对于恶报的方式强调了被雷电击毙,或变为牛、狗、猪、驴、虎一类牲畜的情况,并以敦煌遗书《孝子传》“向生妻”中逆妇遭雷劈故事为其源头:
向生者,河内人也。慈母年老,两目俱盲,时遇贼寇相陵。向生遂被讨征。新妇在家,向生厌贱,好食自飡,粗食将与向母。向母自嗟叹云:“不种善因受艰苦。”新妇大怒,乃取猎粪和食与飡,又更辱骂。天具(见)不孝,降雷霹雳至死。又书背上曰:“向生妻五逆,天雷霹雳打煞。”阿家再明。诗曰:“向生养母值艰苑(危),被射(征)边(疆)未得归。新妇家中行不孝,天雷霹雳背上亡。”[3]1265(《孝子传》)
然而,考察更早时候出现的“蛴螬炙型故事”则不难发现,这两个类型的故事同为逆妇、不孝主题,后者在报应方式的处理上,使用的是上天垂怜不幸之人的模式,并无过激的如遭雷劈、变形等惩戒内容: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彦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闻彦暂行,取蛴螬炙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于此遂愈。[4]135(《搜神记》)
可见,含有“人变动物”情节的“河南妇人”故事,作为逆妇恶报的代表,在故事的结尾具有明显的刻意增加的痕迹:不孝者由婢女换作儿妇,结尾增加了对于逆妇惩罚的处理——其先为遭雷劈,稍后的故事中更换为雷雨之日变为白狗——惩戒意义被突出,故事震撼性更加强烈。利用民众对于不孝之人的唾弃心理,不仅巧妙地将这种暗含因果的内容植入其中,更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将严苛的惩罚加诸于上,虽然仍套用“天神所罚”的传统说辞,但“自云”“书背上”等带有说教解释成分内容的出现,以及“变为白狗”之恶果的特殊处理,则突出强调了因果报应和佛教式的极端化惩戒。表面上看,这仍与传统的怪异变形等现象类似,但“因果报应”在这里被作为解释工具,佛教文化的渗入十分明显。
这样看来,我们将祁著中分为两类的故事合并看待并不突兀,这两类故事在结尾处理方式上的不同,正反映出“人变动物”情节在佛教思想影响下被逐步改造的痕迹,也可见佛教果报观念、惩戒意识逐渐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情况。
诚然,人变动物在我国志怪中并不少见,但在本土故事中,这类变形大多具有追溯始祖来源的传说性质,带有强烈的神灵显示色彩。我国较早的宣扬至孝的故事,接近于史料,记述简单,如:
罗威字德仁,八岁丧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后授其处。[4]138(《搜神记》)
耳熟能详的孝女曹娥入水寻父、死而复生的故事更是在史书、志怪中都有记载。在一些仍然带有原始神灵显验、含有预示征兆性的至孝故事中,动物成为引起主人公注意、避免灾祸的通灵物,如:
衡农字剽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获免。[4]138(《搜神记》)
虚幻情境中的动物现身,成为孝子获得上天垂怜的奖励与恩赐,因至孝而感动“上天”的重要背景也在这类记载中被强调。同样因至孝行为而由动物现身、获得意外收获的故事,还有见于《搜神记》之“王祥”“王延”“楚僚”三则。[4]134-135可见,将动物作为带有神灵使者或显灵意味的神话角色,是传统文化中宣扬孝道的重要凭借对象。而佛教文化传入后,则将这种显灵式的怪异故事用因果报应论来解释,将主人公是否尽孝与果报内容关联起来,劝善与警示目的得到凸显。
另一方面,我国本土一般意义上的人变动物故事中,动物的神灵意义仍然是主导因素,如:
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撅儿”。方四岁,刘渊筑平阳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儿应募。因变为蛇,令媪遗灰志其后,谓媪曰:“凭灰筑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遂投入山穴间,露尾数寸,使者斩之,忽有泉出穴中,汇为池,因名“金龙池”。[4]171-172(《搜神记》)
同样著称的还有“陈仓宝鸡”故事等,都是神灵化的人在特殊情况下变化为动物。
由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后,“人变动物”这一情节在神化灵异的基础上,增加了警示意义,尽管惩戒方式较为极端,在情感接受方面难免令人抵触,但对于宗教背景的佛教文化而言,正需要这种深刻的现身说法来达到震慑目的。在借用至孝观念的基础上,使民众对于守法奉戒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使传说中“人变动物”情节有了更为世俗的意义。
2.偿债等因惩戒而转生为动物
除了现世受报变为动物,佛教轮回转生说的传入,亦配合果报观念,将转生为动物作为惩戒方式来劝戒教众。
相对于因果报应,转生观念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一种陌生、全新的认识论。我国先民尽管认为万物有灵,祖先或亲人的灵魂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仍然会庇护子孙,但并没有灵魂再生、转世重回人间的观念。因此,佛教传入后所宣扬的六道观、轮回转世等内容,对于国人来讲极其新颖,因作恶受罚而转生为动物的构思,更加引人注目。尽管佛教宣扬万物平等,动物与人之间同为修行伙伴,但人转生为动物的情节模式,对国人来说仍然较难接受,也正因此,转生为动物的故事,成为佛教惩戒方法的重要内容被构建,如: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5]3753-3754(《原化记》)
由于观念的全新,佛教文化对人转生为动物故事的改造,缺少本土固有的认知基础,唐以前,此类转生故事数量较少,质量也很一般。此类故事在早期多依附于道教宣教故事,如《异苑》中有戒杀意义的猎户“彭世”条中,猎户变白鹿而走失,其孙所射白鹿“两角间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乡居年月”,近于转生故事。但考究起来,并未出现明确的转生字眼,与后期宣教故事中转生为动物的情节尚有所差距。唐代开始,转生为动物的故事大量见于记载,故事中涉及的转生变形原因,也不单限于触犯杀生戒律,而有了诸如宣扬守信、批判贪吝、批判不敬佛像等内容,一些故事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男尊女卑的强调等问题,如: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值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 :“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 。”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6]180(《广异记》)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其寺亦僧以太守终不敢言。未几而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如缕,织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且异曰:“崔君为吾郡太守,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复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亦竟归其寺焉。[7]26(《宣室志》)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与我一头驴”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所伊水东,欲渡伊水,驴不肯度。鞭其头面,破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轻捶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讫出,寻之不见,其母兄既而还,女先观驴,头面伤破流血,如见其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怪问之。女以状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还得之,言状符同,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啼泪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即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粟送王五戒处。后驴死,兄妹收葬焉。[8]420中(《法苑珠林》)
与早前志怪中出现的动物能够说话、预示吉凶等怪异事件相比,人转世为动物的故事,配合着佛教转生轮回说,将人的命运框架在行善积德等社会规范之中,即使现世并未受罚,但也同样无法逃脱来世偿债。比起现世报应,借助转生轮回说对于来世的惩戒,此类故事更加彻底地将果报观念进行了宣扬,警示意义更加突出。
另外,在对于所化形或转生之动物的选择方面,除了尊崇原有文化体系中对于动物情感的喜好之外,也将佛教本身对于动物所代表的人性特征等认识作为重要参考。《搜神记》所记“人化鼋”“人化鼈”和“宣骞母”[4]175-176,变形主人公都化为水族龟类动物,虽然并未交代化形原因,但“不敢食鼋肉”等显示的戒食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这类故事流传的文化背景——表面看来,近似于佛教的戒杀生、戒食,但变形的主体皆为年长的母亲、所变动物本身具有水族图腾动物的特征,这与远古时代夏族的水族动物祖先崇拜、祖先能够死而复生等原始信仰有一定的联系。配合佛教所强调的戒杀生、戒食酒肉等观念的广布流行,这种久远且模糊的信仰与意识,有了更为切近的解释。佛教观念的注入,为原始文化中具有独特意义的龟类水族动物故事的继续流传,提供了全新的内涵支撑。
(二)对类型故事的整体性影响与后续改造
1.人化虎故事的演变
“虎”是人变动物故事类型中最常见的变化动物。佛教传入之后,本土人变虎故事也受到果报、轮回观念的影响,但由于“虎”在动物种类中的特殊性,使一般的惩罚、劝诫故事并不将虎作为变化对象,而多以狗、龟、鳖等替换。同时,具有原始图腾意义的人虎婚配故事的深入人心,也使得佛教对于人化虎故事的改造,难以发挥更多突破性的影响,表现为选择性的接受与渐进式的改进。
佛经中与虎有关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菩萨本生鬘论》中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事。对于讲求孝道的中国人来讲,“舍身”行为实难接受。因此,这一故事在中国的流传主要体现在佛理文化中。近于“舍身”却较为常见的人变虎故事,宣扬的仍然是戒杀生的观念,如《齐谐记》“吴道宗”条,记吴道宗之母无故变化为乌斑虎食人,自言“宿罪见遣”;同卷引《广异记》“牧牛儿”条,记众人杀牛、食牛而变化为虎。
入唐以后,佛教与本土文化进一步融合,人变虎故事在情节设置上并未有大的改变,直白的说教之词,将宣教意图表露无遗;同时,变虎故事的情节内涵也由围绕原始婚配的内容,向“虎报恩”“虎为媒”“虎妻子”等方向发展,“虎”在民众心中的文化意义不断丰富。佛教所宣扬的动物与人平等、此心同彼心、因缘既定、宿命观等观念,成为此类故事的主题,在经历了一系列中国化改造之后,佛教的这些教义逐渐与本土传统观念融为一体。动物由神话中神的形象,开始以人情化、人性化的角色示人。
2.精怪变形故事中因果观念的渗入
精怪变形故事在佛教因果、报应等观念的影响下,也开始改变最初单纯的变形作祟模式,将人与变形精怪之间的矛盾加以突出,用因果解释精怪变形、作祟的原因,故事情节也趋于复杂。相较于魏晋志怪,唐人小说中这类故事逐渐增多。如《柳毅传》中龙女化身的卢氏,《任氏传》中狐女任氏,以及《灵怪集》“王生”(人狐互化)、《续玄怪录》“薛伟”(人鱼互化)等等。唐人对于这类故事的加工创作,已经将动物变形作为构建传奇、进行文学虚构的一种手段。此类故事在情节变化、新内容的增加方面,也十分突出。这里仅择其要点加以略述:
《灵怪集》“王生”之人狐互化,延续了此前志怪中对于精怪作祟内容的描述而有所增益,动物精怪显示出更多的作祟手法。主人公“王生”在违背精怪要求之后的无法安生,尽管也可勉强用因果论进行解释,但精怪作弄王生的目的,却并无伤害之意,与魏晋志怪中精怪害人、奸淫妇女等恶行有了巨大的差别。精怪法术的高明、王生被整治的无可奈何,读来不禁令人捧腹,一改以往作祟精怪令人厌恶、惧怕的形象。狐狸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叙述情感上开始表现出向这类变形精怪的倾斜。《续玄怪录》之“薛伟”故事,以梦中化形为鱼、经历被捕生活,醒来自叙经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人鱼互化的神异事件,暗中宣扬了佛教戒杀意识。这种以第一人称自述变鱼及在此之后的种种经历,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与佛教宣教故事中最常用的自述“地狱经历”、皈依佛教的方式如出一辙,与之前的精怪变化故事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
唐人宣佛小说之化虎故事中也有这种自述情节。在精怪的人化故事中,继早期的精怪作祟、人怪婚配等套路之后,将戒杀观的宣讲借助人化形为动物、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方式来加以表现,为人变化动物之类型故事增加了新的讲述方式,较之魏晋时期一般的戒杀、戒食故事,无疑令人耳目一新。
同类精怪故事在唐代及后世创作中不胜枚举,佛教对于本土故事的影响可见一斑。至于像《任氏传》之表现狐女任氏与人的爱恋故事,虽然并不见相应的宣教或惩戒寓意,但其作为精怪变形为人、与人结为夫妻的模式,无疑上承自传统的人兽婚配题材,又对后世如《白蛇传》等故事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后者故事中大量佛教因素的渗入、佛法戒律的宣扬,则是十分醒目的。《柳毅传》中的龙女卢氏,其与佛教的渊源就更加深厚,以之为代表的龙王、龙女故事,也成为佛教影响之下,我国动物故事新题材建构的典型代表。
三、新故事类型的创造及意义
(一)动物王国故事的构建——借助梦境来强化因果报应观念
“在汉代以前人的观念中,梦乃灵魂为鬼神牵引出行有所闻见而形成,故被视为天命或神意的载体。”[9]264动物在梦境中代表神意的情形,与远古的动物崇拜有关。随着佛教文化因果观念对民众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动物及动物王国开始在想象世界中被逐步构建。《搜神记》“董昭之”条,以传统的动物托梦形式出现,对蚁王和蚁族世界生动勾勒,主人公最终在蚂蚁的帮助下脱困。同样见于今本《搜神记》的“审雨堂”故事,虽然简略,却为后世黄粱梦、焦胡庙祝等以梦中在动物王国经历人生起伏、醒来幡然醒悟的故事打开了想象空间:
夏阳卢汾,字士济,梦入蚁穴,见堂宇三间,势甚危豁。题其额曰“审雨堂”。[4]123(《搜神记》)
动物形象由单纯的被用于述说因果、宣扬道德教化,逐步成为现实生活的缩影,梦境世界的描述实则喻指现实社会。动物世界作为整体对象进入文人视野,既是动物意象长期对民众影响的结果,也是文人有意识地借助幻想世界折射现实的表现。
在动物王国幻想世界建构的过程中,龙王、龙女故事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代表之一。“龙”是我国特有的图腾崇拜动物,佛教惩戒、修行、护法、宝藏等意识的输入,成为我国龙王、龙女形象在传说故事中进一步丰富的重要组成。龙王、龙女形象群和故事系统的形成,将具有动物外形的人性化的动物故事与神仙故事结合起来,仙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缩小,龙王、龙女也逃不开疾苦的困扰。人情化、人性化神仙世界的构建,既是动物故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显示出创作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宣教的同时,这类故事对人性的关注愈加明显。
佛教文化促进了动物形象的成长,使动物故事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后劲,为动物形象由精怪向人的过渡指明了途径。以搜录怪异事件为特征的志怪故事,逐渐表现出脱离宗教掌控、超越宗教束缚的态势,并最终完成了这些蜕变。动物形象在唐代以后的人性化、借助动物王国来反映社会问题的叙事作品的成长,正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
(二)海外大物故事的发展——文化碰撞的独特表达
先民对于域外世界的探索向来不缺少勇气和智慧,在徒步旅行与巡海探索方面的成绩也同样值得称道,而这些行为产生的背后动力,除了政治、军事、商贸等直接目的之外,相对隐蔽的宗教文化传播也是其重要原因。先民早期“海外大物”之想象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变,新的故事应运而生。在魏晋搜奇猎异之风大盛的文化氛围下,海上大物故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继先秦神话想象如《庄子·逍遥游》之鲲鹏、《庄子·外物》任公子所钓之巨鱼等意象之后,《神异经》之北海大鸟,《玄中记》所记北海之蟹、东海巨鱼、东海巨龟等天下大物,都成为志怪者们关注的对象。这些内容在带给人们惊惧的同时,为其后鲸鱼搁浅、大鱼吞舟以及航行中遭遇大物等纪实性的奇遇故事、自觉的文学虚构等相关故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积累了最初的故事素材——从神话式的巨型动物,到传闻式的海外大物,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这类以动物为中心的志怪的成长,成为动物意象在海外大物故事中脱离单纯的神话想象、渗入奇遇经历与其他精彩内容的有力推动。
(三)域外变形故事的输入——以“板桥三娘子”故事为代表
《板桥三娘子》初见于唐代薛渔思《河东记》,《太平广记》卷286有辑录。描写一家客店店主施用法术,让旅客食用自制的烧饼后变成驴出售;后被其中一个旅客识破机关、巧妙躲过,旅客返回客店设法让店主自食其果、变成驴子,店主若干年后路遇神异老人,破除驴皮才恢复人形。这则故事的域外输入起源已被学界普遍认可,“中国古代人变驴及还复人形的故事,不仅来源于古希腊罗马,而且辗转经波斯与印度文化的融汇,具备了浓厚的宗教观念,这就是业报观。”[10]3“变驴”在我国古代故事中多见于因不孝、偿债等原因而变化的故事中,前面的引文中即有此类。“驴”之所以被作为变化对象,主要是为借助繁重的劳作来作为惩戒,而通过法术将人变形为驴的故事套路,也以佛教译经故事为先。常任侠《佛经文学故事选》中所载《变驴》,本自《出曜经》卷15利养品下,公元4~5世纪东晋十六国时期姚秦凉州竺佛念译,讲述的便是因与咒术家女人私通而被变为驴子,最终食草复还人形的故事。这与“板桥三娘子”之故事结构已十分接近。可见,佛教文学对于这类全新变形故事在译介方面的贡献。
《板桥三娘子》传入中国之后,唐代小说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动,相对于该故事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版本,主要表现为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运用,其原因除了受传统的纪传体叙述方式的影响外,佛教故事突出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是产生这种变动的主因。故事中,店主三娘子为聚集钱财,暗施法术加害往来旅客;旅客偶然窥见其法术,用同样的方法使其变为驴身、遭受报应。第三人称限知叙述视角下,故事人物变驴后的哀怨、辛劳被忽视,着重强调“变驴”这一情节,突出了惩戒规劝的道德寄寓。
我国的小说创作在唐代进入“有意识”的阶段,小说家们对变化故事本已十分重视,对于这类域外传入的变形故事的改造,已经不单局限在情节本土化和习俗、姓名等内容方面的微调。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经过漫长的中国化之后,其教义内容也开始被自觉地运用于对这类故事的改造中。来华之初以变化之术吸引教众、求得立足的佛教,除了带来新的故事类型和题材内容之外,其教义、教旨也逐渐成为诸多变化故事背后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动物故事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吴焯.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J].中国史研究,1994,(4):115-120.
[2] [唐]唐临.冥报记[M]. 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卷8[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4.
[4] [晋]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59[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唐]戴孚.广异记[M].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唐]张读.宣室志[M].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5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 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阎伟.“驴眼看人”与“人眼看驴”——《金驴记》与唐《河东记·板桥三娘子》叙述视角之比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1):1-4.
[11] 徐军义.《山海经》的生命意识[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54-57.
【责任编辑 梁红仙】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to the New Change of the Deformation Stories about Animals in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NG Rui-fang1, 2
(1.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s: In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Buddhist disseminated their religion through the native deformation stories about animals, and new changes appeared in these stories which absorb the ideas such as karma and samsara. Based on the original stories which focus on the ancestor worship and lay stress on the change of the animal’s body, in these new stories, the idea of karma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o explain why body changed between people and animals, and samsara strengthened these changing st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up of animal images and the world of animals were constructed; stories about the huge things of oversea were depleted; new stories about the changes between people and animals that originated from abroad were accepted at that time. The native deformation stories about animals showed more human feel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Buddhism;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eformation stories about animals; new changes
K235
A
1009-5128(2016)23-0069-07
2016-10-25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唐前志怪小说研究(14XZW04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变迁与文化阐释研究(13YJC751078);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唐前志怪小说的图像学研究(1601178B)
张瑞芳(1982—),女,山西灵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先唐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