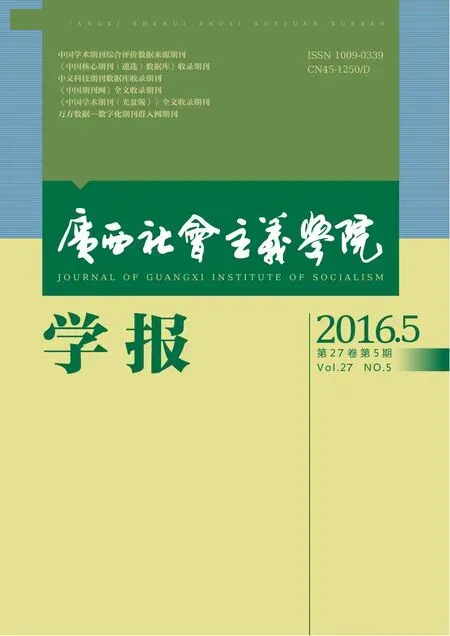儒家政治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章再彬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儒家政治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章再彬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儒家文化走的是一条“内在超越”的突破路径,其政治信仰与西方寻求外在超越的天国信仰不同,表现出很强的现实趋向。儒家政治信仰的内容随时代变迁有所不同,然“王道政治”的核心信仰却一以贯之,成为历代儒者努力追求、极力达成的理想政治状态。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信仰在封建社会曾经历过与专制王权既契合又紧张的双重关系。从儒家政治信仰中汲取优秀内容,运用到当代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实践中去,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也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儒家政治信仰;道统;政统;理想信念
在“轴心时代”,中西方世界虽然都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但二者突破的方式和途径却有所不同。古希腊的哲学认为人的感官所能触及的是一个缺陷的“现象世界”,因而,总是要寻找一个价值之源,即一个永恒不变、至善至美的“本体世界”[1]6。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最先的动因”,其实都包含了这种“二分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及至中世纪,基督教将世界分为“天国”与“俗世”两途,上帝是完美全能和完全理性的化身,而带有“原罪”的世人只能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救赎。不难看出,这种哲学上的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之分以及宗教上的天国与尘世之分,都说明了西方走的是一种“外在超越”的道路。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方式却走的是一种“内在超越”的途径。中国古代哲学虽也有未知的“本体世界”与可知的“现象世界”分别的意识,然古代哲人们并不纠缠于对本体世界的探究与揭秘之上,而是抱着一种“六合之外、存而不议”态度将其搁置。中国虽也有“天”的概念,然“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显然,在儒家语境中,“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1]8。这种内在超越的路径催生了中国古代政治浓厚的人文性,因此中国不需要搬出一个“上帝”来对人进行“启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们通过“修身”而达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儒家文化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儒家文化却和宗教一样能给人以信仰,特别是政治信仰。儒家的政治信仰是什么、这种信仰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有没有现代价值?如何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儒家政治信仰的发展历程及核心内容
如上所述,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在超越式”文化,它没有将人的理性交给一个外在权威——上帝,因此,它不是宗教。那么,既然人保有了理性,是否就意味着人没有信仰呢?笔者认为,理性与信仰之于人而言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性的人更需要信仰。身处政治场域中的人更需要政治信仰,否则就不是政治人。
(一)儒家政治信仰的发展历程简述
人类社会的成长是一个逐步发展进步的历程,其间,政治观念也会经历一个变迁过程。三代时期人们的政治信仰是“上帝”“天”等神秘之物,但这些信仰大多带有极其浓重的祖先崇拜观念,且往往被王权借用来作为愚昧民众、加强统治的工具。及至周公提出“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天命”便丧失了不可把握的神秘性,对“天”的信仰必须以实践中“保民”的政治价值取向来体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鬼神及死后世界始终持一种避而不谈、谨慎对待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孔子也不是个宿命论者,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环境,他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四处奔走呼号,试图力挽狂澜、恢复礼制。然而,每当面临重大危机或陷入困境之时,孔子都会诉诸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在谈及“天”时虽然大多是为了表达一种面对艰难而自信、乐观的精神境界,但从中也可看出他是相信有“天命”存在的,并将其作为决定成败的最终因素。战国时期的荀况是第一个明确摒弃“天命观”政治信仰的儒家学者。“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有自身的规律,不因人世间统治者的优劣和世道的好坏而发生任何改变”[2]。社会的治乱并非由天命决定,而是人的因素所致。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由圣人来制礼作法,“化性起伪”,教化民众。及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意识形态化,儒家信仰也便落入“三纲五常”的统治教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逐步兴盛,而儒教却日渐式微。为了恢复儒家的统治地位,韩愈针对佛教的“佛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认为儒家有一个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道统,从此便成为历代正统儒者的政治信仰。后来程朱理学中的“天理论”、阳明心学中“心性说”,实际上都包含于“道统论”之中,或者说是其变种。以上是对儒家信仰发展历程的粗线条的勾勒,虽然忽略了许多细节,但也大体能够得其要点。
(二)儒家政治信仰的核心内容
与释、道寄希望于来世不同,儒家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伦和纲常。其政治信仰虽也有“天”“太极”等本体论内容,然其核心内容仍然落脚于现实政治。儒家的政治信仰虽几经演变,然其核心内容却具有较强的延续性,这些“一以贯之”的内容可称之为“核心信仰”,也可以认为儒家政治核心信仰便是“道统”。儒家的道统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同之世的政治理想及仁政、德治、礼制、爱民等政治主张。道统在儒家圣人们中代代相承,及至唐朝的韩愈才得以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之后儒家士人恪奉遵守的信仰准则。韩愈的道统论可归纳为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三个方面。首先,从认同意识方面看,儒者不仅要对古圣先贤怀有无限崇敬之情,而且要从理智上认同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思想与学术方面坚守圣人的学说立场。其次,正统意识就是要坚持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要努力消除佛、道异类教派的威胁。再次,弘道意识就是儒者都应有一种传播、推广、实现“王道政治”的义务与使命[3]。
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历代正统儒者皆有一种强烈的弘道意识,即以王道政治理想指导现实政治实践,努力在其所处的时代实现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内容的王道政治。孔子十分崇尚“先王之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生为了实现“有道”政治而四处奔波,游说诸侯,虽四处碰壁,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始终未放弃这一政治理想。其门生曾参也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视弘道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儒者,使他们不但获得了“道”之信仰,而且竭尽全力地在现实政治中践行“道统”。
二、儒家政治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浅析
(一)儒家的弘道意识决定了其政治信仰的实践倾向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实属一种实用主义经验哲学,它具有很强的践行性。信仰“道统”的儒家士大夫必然会努力将“圣人之道”在现实政治中付诸实施。孔子就认为只有恢复“先王之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当时“王纲解纽”“诸侯纷起”的社会失范状态,因此,他率领门徒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心与使命感的孟子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儒者要扮演“帝王师”的角色。此后,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儒无不是“代圣人立言”“为君主出策”。正是这种弘道意识与现实关怀使儒家信仰并未成为束之高阁的空洞哲学思想,而是获得了不竭的生命力,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二)儒家政治信仰中包含许多合理性内容是其被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
儒家“道统”信仰中没有什么玄之又玄的天神鬼怪,也不包含残忍无道的厚黑权术,而是充满了小康之世、大同盛世的美好社会理想以及仁政德治、亲民爱物等温情脉脉的政治主张,确实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与很高的道德感,总能给人以正能量。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植根于现实社会之中,直面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改造现实社会、重构理想社会的愿景和路径。简言之,儒家政治信仰不玄远、不空洞、不脱离政治现实,源自现实政治需要,回答了现实政治问题,又高于现实政治,能够激励并指导政治行为者为达至更加美好的政治愿景而奋斗。这是其在众多的政治信仰流派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
(三)统治者的提倡与支持是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力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4]“马上得天下”的封建帝王却难以“马上治天下”,因此,不得不寻求一种意识形态来论证王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中国的封建帝王既没有选择道家“清静无为”的“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治理哲学,也没有选择法家“一断于法”的强权式治理方略,而是选择了“崇道”“尊王”与“爱民”兼而有之的儒家政治学说。极富道德性与积极入世精神的儒家政治信仰恰好契合了封建王权的怀柔和进取并用的统治需求。因而,王权便将其上升为国家的统治哲学,并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性以及科举考试的方式使其获得了崇高的思想地位。与王权相结合是儒家政治信仰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原因。
三、“道统”与“政统”的现实冲突
马基亚维利曾对“应然”与“实然”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怎样行动与实际怎样行动存在着巨大差距,不懂得二者间的区别将会造成重大灾难[5]。儒家政治信仰也碰到了如何面对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显然,封建王权只是将儒家政治信仰作为了一种统治工具,王权并不受此信仰的束缚。实际上,汉武帝之后实行的是一种“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儒家高尚的政治信仰只是一种“装饰品”,国家的制度还是大体沿用秦朝的所谓“法度”,正如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两千年之制,皆秦制也”(《仁学》之二十九)。统治的实质还是法家的强权政治。对此,汉宣帝毫不讳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6]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自有一套以驭下权术和严刑峻法为核心内容的统治方略,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政治主张。
那么,在这种现实政治环境中,儒家的“道统”必然会与君主的“政统”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既崇道又尊王的儒家士大夫就会陷入一种行为两难困境之中,他们的行为选择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从道不从君
如前所述,儒家有着很强的“弘道”意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家士大夫自然会把实现王道政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在圣人的心目中,“道”是高于“君”的。孔子宁可放弃官位、颠沛流离,也不会屈从“无道”之君的淫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也曾说过,“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恪守圣人教诲的儒家士人往往会选择从道,而从道的方式有如下两途。
1.隐以求“道”。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不止一次提及如果在“无道”的政治环境下,可以选择隐居以求道,他在晚年甚至产生过飘洋过海去寻找施行“王道”的世外桃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受其影响,后世许多儒者发现混乱的现实政治无法承载“王道”之时,便会选择隐居以独善其身,潜心研习道学。纵观我国的古代历史,确实出现过一些不屈王权、遁世求道的“不召之臣”。
2.以“道”谏君。另外一些儒家士人在发现君主的言论、行为或政策有违王道时,则会对其进行谏诤,用圣王之道与王权进行分庭抗礼。这些敢与皇帝叫板的士大夫一般都是几朝元老、托孤重臣或无所畏惧的耿直之臣,但综观整个历史,这种人毕竟寥寥无几。
(二)从君忠君
中国的君主制度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7]。在“利出一孔”的高度同质化社会里,帝王垄断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思想文化的权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王权无所不包、无处不及。在这种情势下,任何人挑战君主的权威,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打击。王权甚至发明了一种“以言定罪”的判案方式,宋代的“乌台诗案”、明清两朝的“文字狱”皆属此类。奢谈仁政王道的儒家士人稍不留神,就会因言获罪。这样,连人的思想与言论都纳入了王权宰制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王权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之术,试图将士人纳入体制之内,科举选士就是王权常用的方式。科举考试尤其明清的八股选士只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机械性记忆与教条式理解,不能测试出考生的道德人品、真才实学与独立思想,“它不仅距离经世致用的治国知识越来越远,距离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教化之学也越来越远了”[8]。但统治者需要的正是这种既能有效地束缚士人思想、又能为自己培养大量人才的制度,正如唐太宗在得意忘形之时一语道出的实情:“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
总之,在王权软硬兼施的两套手法面前,大多数儒家士人都会俯首听命于王权,而不再纠结于君主施行的是否为“王道政治”。深谙“权变之术”的儒家士人运用道家“此亦彼也,彼亦此也”的相对主义哲学对王道与霸道进行了重新诠释:王道亦霸道,霸道亦王道,霸王道同也。于是乎,道即君,君即道,尊君就是崇道。这是汉代以后大部分儒家士人的现实选择。
四、儒家政治信仰的当代意义
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有用、如何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我国进入近代以来便争议较大的问题,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主流答案是不同的。其实,宣扬“抛弃历史、全盘西化”与主张死守“本位文化”的态度都是极端而非理性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并列为“四个自信”,强调“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9]。习近平不仅本人深具传统文化学养,而且善于把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精华和智慧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政治发展不能割裂传统文化的基因,我们的政治发展要善于运用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封建时代的主流政治文化,儒家政治信仰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世易则事异,它不可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但儒家政治信仰中又蕴含了许多超越时代的因子,对之进行挖掘、转型和改造,可以为推进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支撑。
(一)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文化底蕴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圣人为治“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这种对理想社会的描摹虽然还停留在一种空想的层面上,且带有人治社会的痕迹,但先辈们对大同社会无限向往的情感与不懈追求实践是值得今人继承并发扬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期盼实现的理想社会状态,每个时代的政治精英也应该提出符合时代特点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善于用政治理想团结和引领人民、凝聚民心,使党提出的政治理想不仅成为全体党员的奋斗目标,还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较长一段时间内,党、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价值多元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弱化。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执政党本身建设和政治治理的主要软肋或者最薄弱的环节”[10]。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意识形态需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整合社会普遍道义价值,进一步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结合,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与认同。在这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不仅可以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现代价值的有益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当代化,而且还可以借鉴儒家政治信仰的务实性,不过于抽象,不脱离实际,找出可以激发广大民众为之奋斗的具体愿景及其实现的可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一百年”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来源于传统社会理想的精华部分,只是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已不是几千年前古人所能想象的了,它具有了现代内涵,是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逐渐明晰化、具体化的,有具体的指标体系;第二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共同孕育的梦想,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追逐的梦想,有利于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党的政治主张有效整合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成功典范。
(二)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文化支持
儒家政治信仰中有一种圣人崇拜传统,圣人是站在人类道德至高点的完美化身,是士人们尊崇和效仿的人生导师、道德楷模和行为标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号召人人通过努力修身争取达至圣人的境界。然而,尧、舜、周公、孔子等圣人毕竟是传颂中无法企及的至善至美的幻影,现实中“孰能无过”,成仁成圣的毕竟是少数。从一定意义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其积极意义,但其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政治浪漫主义的体现,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从一定意义上讲,“崇圣”是符合人治需要的,人治传统倾向于信任领导人的善性、道德与能力,而缺乏对制度权威的信仰,这方面必须要转型,尽快从对圣贤能人的追崇转变到对法律制度的信仰上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其实,崇圣尚贤的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并不必然冲突,在注重法治的大前提下,完全可以进一步弘扬德治,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依法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治军才是最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因此,崇圣的传统不能完全丢弃,但需要对其进行扬弃,使其在现代法治的框架下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儒家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修身为善的传统不仅符合法治精神,而且可以推进法治建设。因为法治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践行,儒家强调人皆可以为善,主张“求仁由己”,这就是号召人人从我做起遵纪守法的善因,对于推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积极意义。
(三)为助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儒家的“王道”政治信仰是以古代圣王为中心的。在儒者心中“圣王”的典型代表是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他们既有德又有位,是最理想的治国者。然而,后世往往有德者无位,在位者缺德。虽然圣王在现实中可遇不可求,但儒者还是在遵循帝王乃天下之主的大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其施行德治仁政。这种忠君思想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相悖的。但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如果加以正确的改造,即使在现代民主政治语境中也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忠”反映了对权威的维护与服从、对共同价值目标的坚守,“忠”的对象不能是君主而应是人民,应该忠诚于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党员而言则还要对党忠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奉献自己的力量。另外,儒家道统中一直保持着“从道不从君”的信条,古人受时代所限,难以确立民主政治之道,但当今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现代语境中的“从道不从君”的内涵应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担当和精神,这种精神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
(四)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借鉴
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儒家文化的人文性更浓,更强调敬天保民、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方面,高度重视民心向背,对百姓保持一种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比如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每遇灾荒在知情的情况下通常也能有效组织赈济,这体现了对民本理念的认同。在当代社会,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两点需要摒弃,一是不能将“民”看作家长制下的“臣民”“子民”,而应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树立人民主权理念。二是要去除保民是为了“邦宁”的思想,保民利民不是执政者的施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受政府的保护是人民的权利,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习近平强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对民本思想的扬弃和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将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党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还应树立文化自信,乐于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因素,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张荣明.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41.
[3]王平川,刘淑霞.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唐都学刊,2006(4).
[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9.
[5][意]尼科洛·马基亚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3—74.
[6][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7.
[7]葛荃,鲁锦寰.论王权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解读 [J].山东大学学报,2006(4).
[8]秦晖.传统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0.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01.
[10]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6.
责任编辑:杨绪强
10.3969/j.issn.1009-0339.2016.05.018
B222
A
1009-0339(2016)05-0085-06
2016-10-02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16ZZD036)。
章再彬,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干部,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