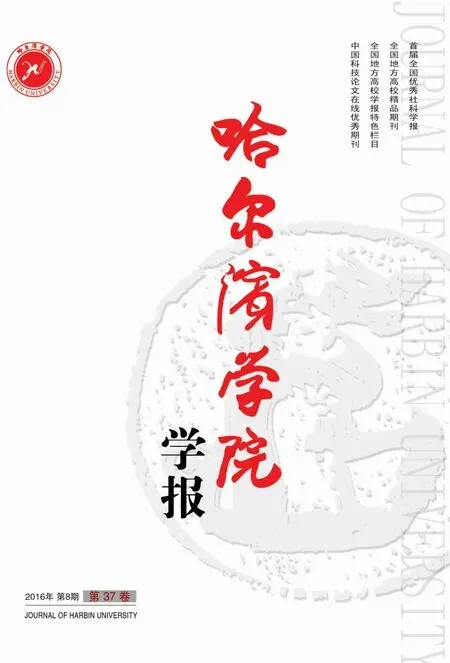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本真状态”的张力
王丽圆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本真状态”的张力
王丽圆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确定为“在世界中”,同时他把“此在”的生存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本真状态,一种是本真状态。笔者认为,两种生存状态的差别在于“此在”和世界之间以及和他人之间是否有张力。文章试图通过分析非本真状态的无张力和本真状态的张力特征来证明这种观点,并总结本真状态的张力特性,指出这种出现在人(“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可以看成是从近代哲学的主客对立的张力到后期海德格尔所研究的天、地、人、神之间更高层次的张力之间的一个过渡。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本真状态;非本真状态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方式做了现象学的分析,把人称为“此在”,之所以将人称为“此在”,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活在一个敞开的领域中,“此在”即存在在此的意思,这里的“此”就是这个敞开的领域,就是世界。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研究,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是主客对立,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看法是把二者当作是相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即人和世界相对立,而海德格尔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人生活在世界之中,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这种张力并不是对立。研究这种张力对理解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本真状态中的张力做详细的考察,以便更好的理解“此在”的本真状态。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存在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即“此在”以一种随波逐流的方式混同于常人当中 ;一种是“本真”的生存方式,即“此在”不再在常人当中随波逐流,而是把自己的存在把握为本己的存在,真正作为自己存在。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明示一点,即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同样都只是初始状态下可能发生的两种存在方式,仅此而已,不存在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含义,并不是说非本真存在状态就是坏的,不重要的,相反,非本真存在状态是理解本真状态所必不可少的。
那么非本真存在状态与本真存在状态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张力特征上:在非本真状态下,人与他人混在一起,都只是常人中无差别的一员,我们就是生存在这种平均状态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和世界、和他人之间几乎是没有间隙,没有个体空间,没有张力的,完全的裹在一起,缺乏对自我的正确反思,缺乏对自己独特存在的意识,在公众中浑浑噩噩,这不是“此在”本己的、真实的存在;在本真状态下,没有了常人的遮蔽,“此在”不得不重新的审视自身和世界的关系,这时“此在”与世界、与他人不再裹在一起,而是有了一定的空间,“此在”不再是与他人无差别的存在,而是个别化为最本真的自身,通过“先行到死”和“愿有良知”,“此在”把握到了自身和世界之间的张力,把存在把握为我的存在,此时的存在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存在。
一、非本真状态的无张力特征
“此在”的存在应该是我的存在,但是“此在”在日常的状态中往往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即我而出现于世界,而总是容身于与世界和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此在”的这种日常的状态是一种非本真状态,在此种状态之下,“此在”与世界之间是没有张力的。
1.常人中的无张力状态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之中’是此在存在的本质特征。‘在之中’是此在存在形式上的生存论术语,而这个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建构。”[1]即“此在”总是在世界之中的,在世界之中就不可避免的与各种具体事物打交道,同时也与形形色色的他人打交道。就与他人关系而言,他认为世界是共在的世界,是他人和“此在”共在的世界,而“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是在其中的那些人”,[1]因此,“共在”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是一种把自己与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正是通过“共在”,这个世界才形成一个共同拥有的世界。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以常人的方式生活的。常人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常人是个中性的东西——他人,是“大家伙儿”。“此在”和他人永远是一开始就裹在一起了,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在这个“大家伙儿”里了,没有不在其中的人,除了像“狼孩”一样的情况,这是一种“此在”无法逃避的情况。
在这里,“此在”和他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空间,更没有明显的张力,“此在”就是他人,他人就是“此在”。他人,即常人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他把“此在”所有存在的可能性都拿走了,使“此在”泯然众人。“此在”的存在不再是在多种可能性中,积极的筹划和选择出一种可能性的自由的状态了,而是已经完全的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作为自己则消失不见了。“在这种不触目的情况下,常人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常人已然指定了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1]海德格尔把常人存在的方式叫做“平均状态”,在这里,常人规定了“此在”在生活方面的各种标准,“此在”不用为了把存在把握为“我”的存在而做任何决定,因为常人会帮他做出决定,而“此在”也习惯了躲避在常人之下。
当然,这里所说的“此在”和他人之间的张力,并不等于让“此在”和他人对立,不是在“此在”与他人之间建立完全敌对关系。首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在”处在与他人的各种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社会和共同体生活。其次,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说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此在”首先能够把握到自己真实的存在,能够自由的为本己的存在筹划,在自身独立的基础上,与他人之间实现真正和谐的共处,而不是放弃自身的责任,泯然众人,任由常人决定一切。虽然看起来也是一幅很和谐的景象,其实这是一种假象的自由,当他真正需要为本己的存在做出决定时,常人都偷偷溜走了,没有任何人会帮他作出决定,因为实际上“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是己经听任这个无此人的摆布了”。[1]
2.闲言、好奇、两可中的无张力状态
海德格尔把“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从属于常人这种状态叫做“沉沦”,有三个具体的基本样式:闲言、好奇、两可。
第一,闲言,重点是“言谈了一番”,并不是为了交流信息或者获得什么确切的东西,也并不触及任何所聊内容的本质性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聊得高兴,只是为之操劳了一番。语言本应该是在说出的时候包含着一种领会,这种领会应涉及到对存在的当下领会以及“为了重新解释或从概念上加以分环勾连所需用的可能性和视野”。[1]可是,在交谈的过程中,人们对语言中间包含的领会不了了之,弃之不理,只是关注了语言本身,语言变成了无根的闲谈,变成了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是被海德格尔称作“平均领悟”过的言谈。
第二,好奇,即仅是为了看,仅是为了从一个新奇跳入另一个新奇,好奇被世界的外观所攫获,它不是为了领会所见之事的存在,而是仅止于看,它到处都在而又无一处在。人在世界中,原本通过寻视与世界打交道,这种寻视是什么都注意,却并不局限、并不停留在某一物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直在寻视着,存在的领域也因此不断地打开着,可是当这种寻视停下来时,寻视就从操劳中脱离,变成了为了看而看,为了知道而知道。
第三,两可,介于闲言和好奇之间,“对在日常共处中来照面的那类东西,人人都可以随便说出什么,因而人们很快就无法断定什么东西在真实的领会中展开了,什么东西却不曾展开。”即一件事情的展开是由好奇和闲言来推动的,而其真正的行动和实施显得无足轻重。
那么,人为什么会有闲言、好奇和两可呢?这些就是人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就是人原本混世方式,人和世界之间在这种原始状态下就是混在一起,并不是人可以从世界中跳出来,把世界当做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的对象,把自己当主体这样的,我们都处在大众平均日常状态下。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你在和世界打交道时,你们之间几乎是没有间隙的,几乎是没有明显张力的。正如你使用一件工具时,你不会是把它拿在手上不用,反而对着它苦思冥想它的长度、宽度、高度、颜色、形状、质料啊什么的,而是直接拿起来就用。闲言和好奇就是我们的日常状态,人从根儿上就喜欢闲言和好奇,例如对于一个八卦信息,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表示浓厚的兴趣,口耳相传,并且添油加醋,带上主观的色彩去谈论这件事,可是大家就是这样聊聊,不会真正的关注事实本身。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把这种“此在”和世界融为一体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还挺合理的景象称作非本真状态呢?只是因为就“此在”自身而言,非本离真,没有把自身的存在把握起来,没有把存在把握为我的存在,没有把握到本己的存在,所以称它是非本真状态。在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作沉沦的状态下,“此在”和世界之间几乎是没有张力的,因为张力首先得有两个不同东西在,但这两者就是一个东西,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语言,也不再造就“此在”的展开状态了,“此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无根的东西了;同时“此在”也不再用寻视和世界打交道了,寻视停下来变成了好奇的看,“此在”的各种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被固化了,两可更是将可能性模棱两可化,就这样,“此在”自身的展开几乎被封锁,“此在”和世界之间的张力一定程度上被切断,“此在”和世界就这样几乎混为一体。
3.怕和畏张力特征对比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日常生活中,“此在”总是处在与世界和与他人之间毫无张力的关系中,在这里“此在”与众人混在一起,随波逐流,同时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熟悉的用具和事物,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作在家的状态。
在这种在家的状态中,当出现一个我不熟悉或者是具有威胁性的事物时,就会有一种逃避的情绪产生,即怕。怕是一种情绪状态,情绪总是已经发生了的,当你感觉到怕的时候,怕已经发生了。当“此在”转而去注意这个使自己产生怕的对象时,怕这种情绪就立刻被对象化了,因此怕一旦被注意就一定有具体的对象。既然是对象,那一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就这样,因为怕,“此在”和世界之间稍稍拉开了一点距离,开始审视这个使他怕的东西来了。“此在”不再完全是和其他“共同此在”混在一起了,但又不是完全的离开他们,因此“此在”和世界之间稍稍建立了一点张力,至少是和怕的对象之间建立了一个张力。
畏与怕不同,虽然二者同属于情绪状态,但是畏没有什么具体的对象。畏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对存在本身的焦虑和惶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周围众人追求的东西对我是个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周围熟悉的事物都被拿掉,我处在不在家的状态,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惶恐油然而生,周围世界和他人从我的身上渐渐剥落,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原始的本真的自己,我和周围的大众不再是混为一谈了,我真正认识到我的存在,而不是和他人无差别的存在。我的生命完全变成了个别化、个体化,我可以自由的把握本真的自己,就这样我和世界、和他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但又不是完全的对立。由此,我和世界、和他人之间有了一定的张力,正是这个张力所在,让我从非本真状态进入到本真状态做好准备。
怕和畏之间张力特征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怕中的张力只是“此在”和具体怕的对象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有着完全的境域化,即当这个怕的对象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个张力就可能会消失。而畏中的张力是“此在”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张力,不再是和具体的某个对象之间,这个张力是随着畏的情绪一直存在的,不再是一个境域化的东西。怕中的张力不足以使“此在”真正的认识到本真的自己,畏中的张力却使“此在”个别化为自身,为回归本真状态做好了准备。
因此,在非本真状态中,“此在”和世界之间、和他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张力的,虽然怕这种情绪状态暂时让张力的产生有了可能性,但是这个张力不足以让“此在”真正回归本真状态。
二、本真状态的张力
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虽然同样起始,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在本真状态中“此在”和世界、和他人不再是裹在一起了,“此在”个别化了,不仅如此,本真状态中有着非本真状态没有的张力特征。
1.向死而生中的张力
前文已经说过,“畏”中的张力把人引到了能够把握住本真的存在的自由这一点上,把人个别化为自己的存在,为“此在”从非本真状态进入本真状态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地揭示了“此在”最本己的、无关涉的、不可超越的、不确定的可能性“死”。
他认为,死亡作为唯一的、必然的可能性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同时死亡也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当死亡这种可能性实现时就会取消掉其他人生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可能性都在死亡的笼罩之下,可以说,死亡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整体性。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死经常是忌讳的,讳莫如深的,因为“此在”已经习惯躲避在常人之下,对自己“真正切身的存在状态”完全不顾。可是当“此在”意识到自己始终是有死的时候,他会从常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从被闲言和好奇的掩盖之中清醒过来,进入到一个真态的生存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里的死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肉体的死亡,而是对死亡的一种领会。死亡这件事是确定的,可是他什么时候到来并不确定,这里“先行到死”的状态,是海德格尔用“前”的视域来理解存在的体现,就是说人就是这么一种存在者,他不是现成的,他的存在意志都是未完成的敞开状态。所以,他能够在没死的时候就活在他的死里边,能够经历他的死,只有包括了对死的体验的生活,才是这个非现成的“此在”的实际的生活。
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就可以理解了,这其中就包括了生和死之间的张力,生和死肯定是两个东西,但并不是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是不搭边的,相反二者是可以相容的,是有个张力的东西在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有个前提就是这里的死并不是真正的肉体的消亡,而是先行的。其次,就是在我生的过程中就一直包含着对这个死的期待,期待并不是盼望的等着他到来,而是一直都在领悟着死亡的终极性。我知道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即在生的过程中有着对死亡本真的领悟,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更加积极的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都把握为自身的可能性,反而把握到了生命的整体性。同时凭借这个先行的死,我摆脱“大家伙儿”对我的包围,获得了人生某种真正切身的意义,领会到了生活中什么是虚妄的,什么是值得我活的,为生命展开了更多的积极的领域,不再是常人中封锁的状态,这又是一种积极的活。
先行到死是为了更积极的生,积极的生更加加深了对死的深刻领会,生死之间的张力就是这样。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喜欢过年,每年腊八刚过过年的气氛已经来了,就已经是在过节了,而且比真正过年那几天还更加能体会到过节的快乐,向死而生也是这样的,正是在这个生和死的张力之中,你才会更加切身的体会到真正的存在。
海德格尔也讲“向死而生本质上就是畏”。[1]“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为“此在”进入本真状态做准备,其中包含了“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张力,这里我们也讲了向死而生包含着生和死之间的张力?这两种张力有什么关系吗,这样讲是自相矛盾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提到过情绪是已经发生的,是给定的,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时你会意识到自己被抛的境地,而畏是“此在”特殊的现身情态,“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之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的现身情态就是畏,畏是为如此确定了存在者之能在而畏,而且就这样开展出最极端的可能性来。”[1]即“此在”先行的过程中一直涌现的威胁就是极端的可能性——死亡,而“此在”在向死而生中的自我领会就是畏。即对“向死而生”中生和死之间的张力中,“此在”一直有着畏这种现身情态。因此,这两种张力的关系如下:首先,畏中包含的“此在”与世界中的张力,把“此在”个别化为自身,这为“此在”向死而生,真正领悟到生和死之间的张力,从而进入真正切身的本真状态做准备。其次,在生和死之间的张力,即“此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包含着畏这种现身情态,即时时刻刻把自己个别化为自身的这样“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张力,畏死就是向死而生中“此在”的现身情态。
2.良知中的张力
当畏来袭时,“此在”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焦虑状态,这时的“此在”已经不再处在常人之中,这时它需要找到自己。“此在需要某种能自身存在的见证,即见证此在按照可能性想来已经是这种能自身存在”,[1]海德格尔把这种见证称作良知。
良知一直以一种呼唤的方式在指引我们回归本己的自身,这种呼唤一直都存在,可是在日常状态下我们一般听不到这个良知呼唤的声音,因为当我们消融于“人们”之中时,我们只听到无休无止的闲言、好奇和两可中,良知的呼唤是一种沉默的说,不同于闲言的肤浅、两可的模糊和好奇的猎新。这种沉默的说只有在“此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才能听到。毫无疑问,良知呼唤的正是我们自己——“此在”,“此在”作为被呼唤者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呼唤者是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良知是作为“此在”本身能在的见证,那么良知呼唤的目的就是使“此在”回归本真能在的自身。海德格尔讲到,“良知即呼唤,是在其自身中召唤常人自身;作为这种召唤,它就是唤起这个自身到它的能自身存在上去,因而也就是把此在唤上前来,唤到它的诸种可能性上去”,[1]可以看出,呼唤者也是“此在”自身,这是本真能在的自身在呼唤身陷常人中的自身,呼唤的内容是让“此在”回归。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本真能在的自身,这是矛盾的吗?不是,我们一直强调海德格尔“前”的视域,在被抛之前,在未沉沦在常人中的那个本真状态下的自身在呼唤。当“此在”听到这个呼唤时,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不是我生命的根基,还有一个高于我的东西才是我生命的根基,可是我和这个高于我的东西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因为这个高于我的东西是来自我的自身,因此,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是有个张力存在的。呼唤者和被呼唤者都是我自身,二者相互不同,却又是不可分开的。意识到这个张力的“此在”,所以就不会在我的外部去找一个现成的东西当做我的生命的根基,而是自己积极的去存在,积极的去创造我的根基,因为良知告诉你,你不是自己的根基,你的生命还是不完美的,所以你一直是对你的存在有所亏欠的,你需要为你的存在负责,而且也只有你能为你的存在负责。
当“此在”听到这个来自自身良知呼唤的时候,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种可以放任不管,依然沉溺于常人的遮蔽中寻求自由和平静;一种是积极的响应这个良知的呼唤。“此在”选择了后者,因为它无家可归的状态在“畏”的基本情态中本真的暴露了出来。通过对先行到死的领会,“此在”下定决心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弥补自己对存在的亏欠,接受自己不是自身存在的根基,完全的接受自身被抛的状况,这是一种“愿有良知”,被呼唤者积极的响应呼唤者的呼唤,这下决心的响应需要“此在”本身坚强的意志。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常人状态下,“此在”所有的决定都不需要自己来做,自有常人会帮“此在”做出决定。而真正当“此在”需要为自己本真的存在做出决定时,为自己亏欠的存在做出弥补时,为自己无家可归的状态作出交代时,常人却偷偷溜走了。因此,当“此在”终于下定决心挑起自己人生的担子时,“此在”才真正的进入到本己的存在状态。
在“此在”下定决心去回应良知呼唤的时候,前面我们讲的呼唤者和被呼唤者的张力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当良知在呼唤“此在”时,这个张力的方向更倾向于呼唤者把被呼唤者拉回到本真的自身。而当“此在”下定决心去响应这个良知呼唤的时候,这个张力的力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是被呼唤者积极主动的愿有良知,不断地向本真的自己回溯的过程,“此在”不再只是单纯的被呼唤者,而是主动的接受这个呼唤显示自身是有罪的这个境况,当张力的双方共同努力时,这个张力才更加完整和不可或缺。
良知中的张力就存在于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当“此在”体会到良知的呼唤时,张力对“此在”本身来说是被动降临的,当“此在”下定决心去回应这个呼唤时,这个张力是“此在”主动把握到的,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张力的全部内容。
3.先行的决断中的张力
先行是“此在”对死亡这种极端可能性的本己的领会,决心(决断)是“此在”决定响应良知的呼唤。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决心只有作为先行的决心才是向着“此在”最本己的能在的原始存在,只有当决心有资格作为向死存在,决心才开始领会能有罪责的这个“能”。所以他把二者合称为“先行的决断”。先行的决断中的张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先行到死中的生与死之间的张力和良知中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的合作而产生的张力,二是先行的决断本身蕴含的张力。
我们知道,在“此在”领会到自己的生命是随时都可能失去,死亡随时可能发生的时候,当畏死这种现身情态把“此在”无家可归的真实状况摆在“此在”面前的时候,“此在”会正视自己的这种生存状况,更加积极的筹划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更加积极的活,这就是“此在”领会的生和死之间的张力。当“此在”认识到自己无家可归时,一种平时被“此在”忽略的声音——良知的呼唤被放大了,呼唤沉沦的“此在”回归自身。在听到这个呼唤时,“此在”认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是有亏欠的,因为自己不是自己生命的根基,正是这个内疚感让“此在”更加坚决的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更加努力的创造自己人生的根基,这就是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
那么,以上这两种关乎本真存在的张力是什么关系呢?这两种张力在先行的决断中结合了,先行到死是一种领会,决断是一种行动,那么先行的决断就是从领会到行动的过程,把领会付诸实践的过程,对死亡的深刻认识使我认识到生命的随时消亡性,这更加让我清楚我不是我自己生命的根基,我的负罪感更加重,我的罪责是我的“不完善性”,我就会更没办法拒绝不去回应良知的呼唤,我就会更加下定决心。体会到生和死之间的张力让我从常人的遮蔽中清醒过来,把种种可能性把握为自己的可能性,把握为生命的本身。而当我决心去响应良知的呼唤,挑起创造自己存在的根基的重担,而不是把这个重担推给别人时,我真正把握了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在先行的决断那里,这两种张力结合,是生命的个别化和意志的个别化相结合的过程,这个“个别化”就是“此在”本真的存在。可见,在先行的决断这里,生和死之间的张力和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此在”和世界之间真正拉开了距离,可又不是完全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此在”得以进入到一种真态的存在方式中。
这是先行的决断中张力的一个表现,先行的决断充分体现了海德格尔对“此在”原始生存状态的分析。这里引出了两个重要的“将来”和“曾经是”的维度,因为先行到死是将来的,而决断是“此在”接受自己曾经“被抛”的命运。这里的两个时间维度和物理时间不一样,在这里,“将来”不是对现在完全没有影响的尚未到来,而是早已经到来,“将来”和“已经”总是裹在一起的,“曾经是”也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与“此在”的将来和现在毫无关系的维度,“将来”和“曾经是”构成了我的现在,对我的存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我的存在中,我时时刻刻的向死而生中,时时刻刻的不断做出决断承担自身被抛的命运,“将来”和“曾经是”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我现在的存在,造就了我的心情,造就了我诸多感受。可以说,先行的决断表现的这个“将来”和“曾经是”,是包含张力的,这个张力是“曾经”“当下”“将来”相互缠绕、相互造就的张力。
因此,向死而生中生和死之间的张力,良知中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被结合在了先行的决断中的张力。[2]后者和其中所暗示的“将来”及“曾经是”的维度中包含的张力构成了“此在”本真状态的张力。
三、结语
非本真状态和本真状态这两种“此在”初始的存在状态的不同之处在于:非本真状态下“此在”和世界之间、“此在”和他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空间,更没有任何张力,“此在”躲避在常人之下浑浑噩噩;在本真状态下,通过对先行到死的领会和响应良知呼唤的决断,“此在”和世界、和他人拉开了距离,并且把握到了生与死之间的张力,呼唤者和被呼唤者之间的张力,这两种张力合作共同构成了“此在”的先行的决断。
笔者认为,“张力”这个思想似乎一直潜伏在海德格尔思想内部,其不同于近代哲学,受主客体对立思想的引导,近代哲学的张力一直表现为主客体对立,这就掩盖了我们生活中人和世界之间的张力,因为生活中不会人人都像哲学家一样把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分析,彰显了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张力。在海德格尔后期,他进一步探讨了天、地、人、神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张力。由此看来,《存在与时间》中所彰显的人与世界的张力,我们可以看作是近代哲学主客体对立的张力到海德格尔后期天、地、人、神之间的更高层次的张力的过渡。
当然,深入地探讨近代哲学主客体对立的张力和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天、地、人、神之间的张力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主要是探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本真状态的张力,但这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对立的张力和更高层次的天、地、人、神之间的张力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陈嘉映,等.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王琦.庄子幸福观的现代性反思[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4).
责任编辑:谷晓红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8—0001—07
[收稿日期]2015-11-05
[作者简介]王丽圆(1990-),女,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8.001
On the Tension of Authenticity i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WANG Li-yuan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In “Being and Time”,Heidegger defines the “Being of Dasein” as “Being-in-the- world”,and,at the same time,he divides the existential state of “Dasein” into two types,namely authenticity and inauthenticity. It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lies in whether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Dasein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others). It attempts to show the tension of authentic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ensionless state of inauthenticity in order to support this ide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Desein and world is a transition from the modern idea of tens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o the higher tension that Heidegger’s study of (heaven,earth,God and man).
Key words:Heidegger;“Being and Time”;authenticity;inauthent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