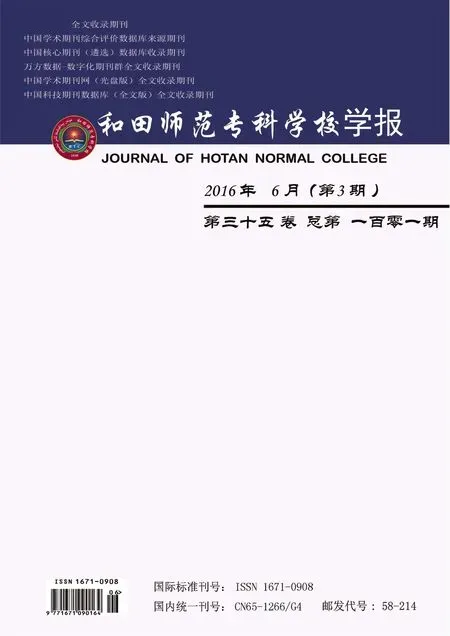维吾尔族食文化及其当代交融与嬗变——以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社区为例
张少云 娄利杰
维吾尔族食文化及其当代交融与嬗变——以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社区为例
张少云 娄利杰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新疆 和田 848000)
维吾尔族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方式上经历了从草原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型,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园林业的三重生产、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以烧烤熟食法为主的食文化。烧烤的独特性、食料结构的奇异性和使用方式的散慢性等构成维吾尔族食文化的主要特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民族间不断深入交流,维吾尔族食文化与内地食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外地食文化本土化;本土食文化外地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导致和田地区维吾尔食文化的嬗变与转型,催生出新的民族食文化特色。
维吾尔族食文化;交融与嬗变;新的特点
食文化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重点探讨“食”的文化意义。毫无疑问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或者一个民族的食品构成、获取方式、加工方法和享用仪式等,从而折射出的一个地域或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禁忌、价值观念、审美思想。也可以说食文化反映一个地域或者一个民族的多层次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各种文化形式的总和,它是文明尺度和民族特质的体现,标志着一个地域或者一个民族文明进程和审美情趣。
人类食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生食、熟食、烹饪三个时期。在生食阶段:人类的饮食是“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1]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人类开始了熟食阶段,其代表性的熟食法就是烧、烤。由于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主食与副食区分,烹饪经验不断积累,形成了熟食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前,维吾尔族食文化并没有充分发育,处在熟食文化后期与烹饪文化初期阶段。由于食文化原生态性,在现代人眼中,便是独特的食文化。
一、维吾尔族传统食文化的特点
维吾尔族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方式上经历了从草原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型,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创造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园林业的三重生产、生活方式,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先民利用南疆地区大小不等的绿洲从事农业生产,根据昆仑山脉的山川谷地的草场发展畜牧业,同时又开发出具有很高水平的园林业,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极其独特的食文化。
(一)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烧烤食文化的独特性
维吾尔族熟食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烧烤方式完成生食向熟食的过度,并一直影响至今,在今天的田野调查中仍能普遍看到和田地区农村虽然使用了锅,但是灶台非常简陋,甚至部分家庭仅用三个石块支起锅做饭,从不讲究是否浪费柴草与烹饪食物的效果。而制造维吾尔族主要食物的馕的“馕炕”,一家或者几家必备“灶具”,却非常讲究,从制造的“灶具”的用土配方到外部的平台都有严格的比例和尺寸限制。上世纪50年代写成的《南疆农村社会》一书中曾统计过南疆地区农村家庭情况,几乎每个村都有几户甚至十几户贫苦农民家中无锅现象。在内地人看来,锅是家庭必备器皿,有家必有锅,没有锅家庭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南疆地区熟食法以烧烤为主。用锅烹饪的食物在解放前只有贵族享用的奢侈品。现今南疆地区婚丧嫁娶待客最高食品仍然是“颇罗”(抓饭),就是用锅烹制的食品。
维吾尔族的烧烤食物的技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传统意义上的烤肉、烤鱼、烤馕、到烤鸡蛋、烤蔬菜瓜果,无不展示维吾尔族群众的聪明才智。
以田野调查中的烤馕为例,和田地区烤馕分为两大类型;家用烤馕和商业烤馕;家用烤馕讲究实用性、节俭性,一般一个家庭在自己的馕炕打馕,一次要用去一袋面粉(20-25公斤),烤馕20-30个,5口之家可使用10-15天。讲究口感好、耐饿、不变质。不讲究外表美感;商业烤馕主要对象是出售,讲究外在的烤馕颜色金黄。造型美观。《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馕的种类达18种[2],而今和田地区的馕的品种在20种以上。最为神奇烤馕当属于田县的“库麦其”一种是直接在烧热的沙中烤熟的大饼。
(二)和田地区维吾尔族食材结构的奇异性
由于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生活在200多块大小不等的绿洲之上,农业、畜牧、园林三维立体的生活、生产方式,造就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食料结构奇异性。原则上讲和田地区食文化,没有明显的主食与副食之分,可以概括为面食、肉类、水果,三者融合一体的食文化,较少使用蔬菜。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维吾尔族农民的早餐就是一张(块)馕、一撮葡萄干,富裕人家再加进一些核桃仁、杏干之类,吃完喝一碗冷水,便是一顿早餐。至今维吾尔族食文化中,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饮食习惯,食品中可以没有面粉,吃肉或者吃干鲜水果可以连续使用十几天,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反应。这是内地社区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
在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社区所有的烧烤食物或者新型的烹饪食物中,蔬菜很少出现,多数食物均为面、肉、果的结合体。如“颇罗”(抓饭),主要食料是大米和大块羊肉、加上适当的胡萝卜和洋葱烹煮食物,体现出来的是“咸味”食品,但是优质的“颇罗”,一定加入一定比例的葡萄干等干果,才是上乘“颇罗”,
维语中的“乌马什”就是玉米面糊糊,是玉米面、肉丁和青杏混合煮制而成;吃起来别有风味。类似的例子很多,米肠:羊大肠中填实米和羊肉等煮成;面肺:羊肺中挤入调好味的淀粉浆煮成;更有意思的是有一种馕竟然是羊尾巴脂肪、核桃仁、葡萄干等烤成。据说最好吃的“糖包子”是羊脂肪和白糖混合制成。
综上所述,维吾尔族食文化中缺少蔬菜的搭配和使用。面、肉、果的搭配形成奇特食文化类型。
(三)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用餐方式的散慢性
维吾尔族用餐方式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所谓的早、中、晚餐,也是根据用餐顺序排列的叫法。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的早餐,安排在乃麻孜之后,家中老小从“苏帕”上睡醒、穿好衣服,就在刚才睡过的地方铺上一张彩色印花布即饭单(餐单)。由家庭主妇提一个水壶(铜制品或者塑料制品)从长者开始给每位手中倒水,洗手,限洗三下,可以用干布擦干,一些农村的农民洗过手后在腋下夹干,但是不能洗过手之后甩干。长者把馕掰开放在餐单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用餐,餐单上有馕、葡萄干、杏干、核桃仁、时令水果等,如果馕太干,可以在自己喝水的碗中蘸水吃。餐毕,长者布置一下家庭事务,全家人领悟后,长者喊一句“阿米乃”,全家人停止一切活动,双手捧在面前,由长者领作“都阿”(祈祷)结束。当然家庭富裕人家在早餐还会有各种果酱、甜酱,喝奶茶、油茶等。
中餐一般吃拉条子,如果没有客人,大部分家庭不动火,干活回来,吃点馕喝点水,就是一顿饭;田野调查中发现有时一家人几天不动火,就是干馕、冷水;有些人家没有用餐时间限制,饿了,打开餐单,坐下吃馕,吃饱了就到外面的水桶里舀瓢冷水喝下去。中午如果能吃上一顿“颇罗”或烤羊肉,只能是喜庆的日子。
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的“漂馕”吃法,一天上午,在玉龙喀什河边,一位挖玉石的维吾尔族老人唱着歌走向河边,从“袷袢”内口袋里拿出一个馕直接抛到玉龙喀什河上游,自己开始洗手、脸、做祈祷,这是干馕漂到跟前,老人拿起干馕,蘸着河水用餐。后来得知这种吃法叫“漂馕”。维吾尔族对玉龙喀什河的崇拜以后详加论述。
二、维吾尔族当代食文化的交融与嬗变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特点,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在饮食文化方面也互相学习和吸收、在融合中求发展,形成丰富多彩的食文化。
(一)维吾尔族食文化的交融
随着和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不断深化,每年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和田,这种快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给和田地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以和田地区民族食文化与内地食文化交流为例,不难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食文化现象,这种食文化现象大致分为:本土食文化外来化;外来“食文化”本土化;
1、本土食文化外来化
和田地区烧烤食文化闻名于世,并被各族人民接受与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的本土食文化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以新疆烤羊肉串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新疆维吾尔族的商贩,扛着烤羊肉串的铁架子,烤变了内地每一个大中城市,成为家喻户晓的食品,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提到新疆,就想到烤羊肉串,其商品效应不言而喻。现今烤羊肉串从内地风光30多年之后,重返新疆时,发现烤羊肉串家族又有一个新品种,并独领风骚。在和田市小吃夜市除传统的烤羊肉串之外,还有维吾尔族从内地城市学习的“煮串”。 “煮串”摒弃了用火烤制方法,使用火锅料汤煮制方法;在食材选择上,从单一的羊肉到各类的肉制品、豆制品、蔬菜等应有尽有,极大地丰富羊肉串系列。让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尝到另类的“烤羊肉串”。
馕是维吾尔族传统的食品,过去馕的都是“咸”味食品,当外来的面包、蛋糕等现代化烤炉食品进入和田地区之后,也引发了当地烤馕业变革,如今和田地区市面上出现了一种“甜馕”,糅面的方法与面包方式类似,烤制的方法不同。烤出的馕,既有面包香味,又有馕的劲道,深受和田地区各族群众的喜爱。
这类本土食品外来化的现象美不胜收,已经成为和田地区维吾尔族食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2、外来食文化本土化
当外来食物不断涌进和田地区维吾尔社区时,当地人表现的最多的是让这些外来食品本土化。以粽子为例,内地的粽子有两种类型,一种甜食型;另一种肉食型。因为肉食型粽子与“颇罗”(抓饭)有类似的味道尚不如抓饭,所以不被重视;而甜食的粽子却深受喜爱。内地粽子大都是撕开竹叶即可使用。和田地区的粽子撕开竹叶放进小碟子内,上面浇上酸奶、蜂蜜等民族食料成分,其风味更独特更美味。
据调查,外地食文化到和田之后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过程,适应当地人生活习惯才能被接受。凉粉在内地是一种最普通的小吃,在和田地区却有专门的凉粉店。就是因为维吾尔族的凉粉表现出最多的民族风味。虽然也叫凉粉。但是绝不是内地凉粉的内涵。
(二)维吾尔族当代食文化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社区随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趋同性不断增大,也引起当地食文化的嬗变。
1、烹饪方法的多样性
当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社区民众认识到外来的烹饪方法更节约燃料、食品味道更浓、食品消化更容易时,单一的烧烤方式就受到冲击与考验。现今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特别是城市人口不再单一食用烧烤食品,追求不同烹饪方法的食品。以火锅为例,过去和田地区没有火锅店,当清真火锅烹饪方式出现在和田地区时,引起维吾尔族群众对火锅食品独有情钟,食客不断膨胀,常常饭店爆满,在热气腾腾中一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享受美食。
炒菜的出现应该说也是维吾尔族食文化的重要变化之一。过去维吾尔族没有炒菜的烹饪方法,更不要说炒菜技术。当炒菜技术传入和田地区之后,维吾尔族饭店特别是上档次的饭店出现了炒菜。虽然与内地炒菜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却受到本民族的欢迎,以在饭店吃上炒菜为荣,成为一种时尚。
目前,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经营的饭店,如果是炒菜、火锅等内地烹饪方式的饭店,就是高档饭店。如果以传统烧烤为主的饭店大都是普通饭店。
2、食材选择的多样性
过去维吾尔族的食材,仅有清真肉类:包括牛羊肉、骆驼肉、马肉(部分人使用)等,面类:包括小麦面、玉米面、青稞面等,蔬菜仅限于胡萝卜、大白菜等,食材选择非常有限。如今和田地区蔬菜面积不断扩大,蔬菜品种不断增多,豆制品、菌类引进,让和田地区食材选择上有更多的可能。食材的丰富性,打破了过去单一的食品结构,丰富了食文化;以豆制品为例,过去维吾尔族不食用豆制品,源于对豆制品的不理解。认为豆制品不符合清真食品要求(现今和田地区部分农村村民仍不敢使用豆制品),当了解到豆制品加工制作过程之后,开始食用豆制品,多用于火锅食料选材。菌类的食用也大致经历这一过程。蔬菜食用由过去仅食用胡萝卜大白菜到今天食用各类蔬菜,变化之大,就是维吾尔族成员都始料不及。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内地市场只要有的蔬菜,在和田地区都能找到,并且蔬菜质量超过内地。
3、用餐方式的多变性
维吾尔族现今的用餐流程没有大的变化,流程中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三餐已经有明显的区别,在农村至少要有一顿是开火做饭。完全革除了过去一天或者几日不生火的生活方式。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开始用餐具食用食品,逐渐消除用手直接食用,虽然餐单还大量存在。但是餐桌开始出现在大众生活中。并呈现出中亚或者欧式风格,部分维吾尔族精英阶层,开始讲究餐具的精美,食品的多样,以甜、酸、辣等味为主,追求食物的形式美。这种变化在和田地区食文化中绝无仅有的变化。
三、结论
民族学视野下,探讨当代维吾尔族食文化的交融与嬗变过程,就是从侧面了解维吾尔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与冲突问题。从上述论证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维吾尔族食文化与内地食文化趋同性不断增大
对和田地区维吾尔族食文化的田野考察过程中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深入发展,让世代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状态的维吾尔族群众感受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绚丽多彩的世界。食物、食材的多样性改变维吾尔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结构,原来烧烤的熟食法正逐渐被烹饪熟食法所代替。虽然烧烤熟食法在和田地区某些农村仍然存在,甚至还是主要方式,但是,丰富多样的食材出现,烹饪熟食法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烹饪熟食法制造的食物正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传播,原有烧烤食物的特色渐渐退去独特性,与内地食文化差异性逐渐缩小,趋同性增大。形成食文化互补现象,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食文化宝库。
(二)维吾尔族当代食文化出现新特色
维吾尔族食文化的趋同性增大,并不意味着维吾尔族食文化的消失,而是呈现出新的民族食文化特色。不管是外来食文化本土化或是本土食文化外来化,都不是原有食文化特色,而是新的食文化。这将丰富发展了维吾尔族食文化的内涵,形成新的民族食文化特色。这种新特色是在原食文化的基础上,融进了内地食文化工艺流程或者食材搭配方式而产生。新的食文化追求甜、酸、辣,现今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三)维吾尔族餐具的变迁正逐步向中亚与欧式风格发展
对和田地区食文化田野调查中发现,食品的制造与内地互动较大,与周边的国家的互动较小。
但是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维吾尔族餐具的使用却讲究中亚或者欧式风格。目前在维吾尔族精英阶层家庭出现餐具玻璃器皿化、餐盘色彩绚丽化、用餐方式欧式化等现象。虽然有时也有中式用餐方式,但仅限于拉面、面条等使用筷子,多数情况下使用勺子,而勺子也多为欧式造型。这种现象代表着维吾尔族食文化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食物的内地化,餐具的中亚或者欧式化。
(四)维吾尔族食文化的宗教性是不动的底线
和田地区是高度信仰伊斯兰教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对食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田野调查中了解到,食文化创新与变革都没有触动宗教戒律底线,都在宗教戒律允许的前提下交融与嬗变,不管熟食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食材如何丰富,所有食品仍然追求“清真”的特性,这说明宗教的意识形态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服从于内心信念的追求。用改变饮食文化的方式,无法改变人宗教信仰的信念。
[1]《四书五经·礼记》[M](中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22页。
[2]《突厥语大词典》[M](汉译本,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版,第478页。
201-11-12
本论文系校级课题:《新疆南疆地区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以和田地区为例》,(批准号:10765131124)阶段性成果。
张少云(1968-),男,回族,和田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