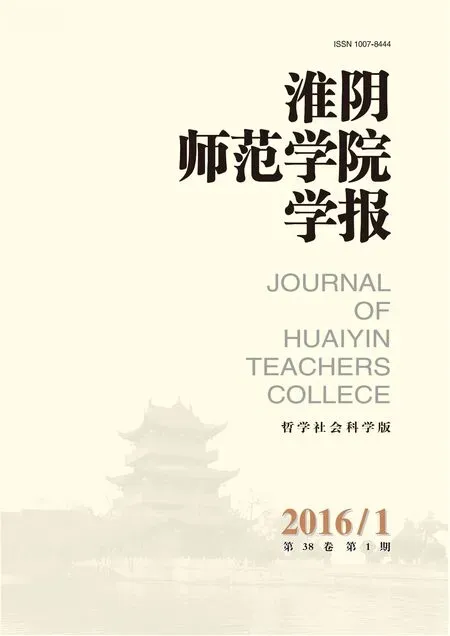政治发展三题
魏明康, 万高潮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政治发展三题
魏明康1,万高潮2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要在当代中国“创造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关键是要逐步建立、健全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即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普选制,以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以保证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
关键词:邓小平; 当代中国; 政治发展
自“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的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以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100年为期,建设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而以高度民主为制度核心。本文拟就此讨论三个相关问题。
一、政治发展与高度民主
如何理解高度民主呢?所谓“高度”当然是比较而言的。比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纵向的,即自己跟自己比。应该承认,这种历时态的比较意义不大。因为只要不发生大的历史倒退,现在总会比过去好,将来总会比现在强。自己跟自己比,难以显现出某一事物特有的优越性。还有一种比较是横向的,即拿自己与别人比,在共时态的比较中检验孰优孰劣。实际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所设定的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高度”,就是以这种比较为旨归的,即所谓“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是否已经具备了这个“高度”呢?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的态度是肯定的。然而十年“文革”使人们清醒了。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邓小平曾强调:“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333也就是说,倘若撇开意识形态偏见看问题,则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水平上尚远不及西方国家。但是,何以人们又多称社会主义民主要高于资本主义民主呢?这里有两个方法论上的原因。一是人们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2]21,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686,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就理所当然地高于资本主义民主。这种政治思维方式的缺陷,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不是从“实践理性”出发而是从“玄想理性”[4]388出发,因而不区分“只有在理想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可能实现的理想”[4]43,甚至还以前者来否定后者。而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之所以可能用“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来否定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把既存的具有其一切不公正与缺陷的制度和在设想中可能存在的制度加以比较而完成的。进行比较的是实际的情况和理想的情况。”[5]189所以另一位美国学者萨托利说:“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去比较现实中的民主是不行的,这是作弊行为。在指的是民主的现实时,也要求指社会主义的现实。反之,如果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提到民主时也必须是指它的理想。”[6]14尤其法国著名思想家阿隆,他在批评萨特等极左派知识分子时曾一针见血地说:“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如指“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大屠杀,如果为通向无阶级社会扫平了道路,那么这些大屠杀也就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如把今天的法国与他们理想中的法国相比较,而不是与过去的法国相比较。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丝毫无损地经受住这一试验。”[7]200-219
人们之所以多称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本主义民主,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因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国体”“政体”[3]677两分说,即指西方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国家,新中国则是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所以后者就先天地具有比前者更高的民主。然而若究本穷源,政治学说史上原是无国体一说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是政治统治的内容还是政治统治的形式,就统统内涵于政体这个概念中。关于此,在世界上第一本《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本人曾有细致分析:“政体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同于‘公务团体’,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则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相应于上述各类型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8]132-134此后到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的理论家洛克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人们最初联合成为社会的时候,既然大多数人自然拥有属于共同体的全部权力,他们就可以随时运用全部权力来为社会制定法律,通过他们自己委派的官吏来执行那些法律,因此这种政府形式就是纯粹的民主政制;或者,如果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那么这就是寡头政制;或者,如果把这权力交给一个人,那么这就是君主政制;如果交给他和他的嗣子,这就是世袭君主制;如果只是交给他终身,在他死后,推定后继者的权力仍归于大多数人,这就是选任君主制。”[9]80-81当然,人们可以承认,服膺于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式的阶级分析方法,而非源自英国光荣革命的阶级合作式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国体这个概念,未必不算是一种理论创新,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国体可以撇开政体独立地显现自己的优越性。按结构功能方法,国体是一个功能概念,政体是一个结构概念,倘若没有民主政体这样一个结构,就不可能拥有人民当家做主这样一种功能,后者只能从前者生发出来。唯其如此,英国科学家波普尔曾提出:“把重点放在‘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一问题上是错误的。应该由人民还是由少数精英,由善良的工人还是由邪恶的资本家,由左翼党还是由右翼党来进行统治,所有这些问题的提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民主与否并不取决于由谁来统治。每个政府都能解散,这就促使它努力使其行为令人满意。如果一个政府知道人民不那么容易摆脱它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动力。”[10]何况不仅理论分析的逻辑是如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更是无可辩驳地证明,国体、政体不可分割,只要没有切实的民主政体作保证,所谓“高度”的民主国体就终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要在当代中国“创造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关键就是要建立、健全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具体的政治体制。
二、政治发展与普选制度
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如何在党政各级“搞民主”,邓小平曾言简意赅地说:“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11]所谓改革和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就是要逐步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普选制,以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对人民负责。什么是民主?从词源学意义和发生学意义来看,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其意为人民(demos)的统治(kratia),其制度核心是以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所以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政治文化多强调:“对民主为害最大的莫过于一位好皇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12]201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民主一词的含义有所不同。《尚书》载周公旦曰:“天惟时求民主。”《汉书》载“鲁穆叔告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三国志》载“夏侯惇谓王曰:‘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凡此种种,就表明“民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指的是为民作主,所谓民主即“民之主”,于是便有了以明君贤相青天大老爷相标榜的君主专制。不仅古时如此,就是在今天,这样一种颠倒的民主观仍大有市场:把民主理解为“群众路线”这种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理解为恩赐性地“让”群众讲话,理解为居高临下地“调动”群众积极性,就是典型一例。毫无疑问,要建立、健全民主政体,最重要的就是要将这种被颠倒的“民主”再颠倒过来。当然,所谓颠倒并非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建立古希腊式的民主政体。据历史记载,古希腊最大的城邦雅典也不过拥有十万人口。除去妇女和奴隶,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者仅数千人,所以“希腊人很难想象出类似代议制政府的任何东西”[13]1,建立以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直接民主制对他们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当代中国是一个远非古希腊窄小城邦可以比拟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至少从操作层面上来讲,中国人民不可能通过公民大会这类直接的民主形式来当家做主。何况从高效行政的角度看,“在一个从事复杂的政策制定活动的庞大机构中,要长期不断维持一个直接的、平等的民主制,无论它是谈判型的还是市场型的交换,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14]68更何况从政治价值的角度看,还存在着“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仅仅要求由全体会议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6]402的选择。唯其如此,现代民主政体的要义,并不在于由人民直接实施统治,而在于通过行之有效的普选制,来切实保障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对人民负责。这也就是发展政治学之所谓:“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政治“就是由未来领导人自由竞争选民的选票”,“竞争的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本质”。[15]410-415
所谓行之有效的普选制,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全体公民均有被选举权。这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同等的可能性。考虑到现代政治为政党政治,这亦意味着,从一党制到强党制的政治发展,每一合法政党均有成为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同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体公民均有选举权。这意味着,任何公民要使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可能成为现实,就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选票。考虑到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这亦意味着,任何合法政党要想成为参政党与执政党,均必须使自己赢得多数公民的选票。这样,人民就不仅能够通过投票产生政府,而且“无须流血就能通过投票解散政府”,从而能够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同时,由于“每个政府都能被解散,这就促使它努力使其行为令人满意”,从而能够保障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行之有效的普选制的建立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于此,邓小平曾为当代中国制定了一个以“半个世纪”为期、以“这一代”与“下一代、下下一代”作代际交替的政治发展路线图。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他曾明确表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16]220-221同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及1989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又曾表示:“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16]242那么现在就改变这个制度,像美国那样在中国搞多党竞选,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原因在于,欧美“处于民主化时代达一个半世纪,处于福利时代达一个世纪”[14]422,时至今日,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之间才形成所谓“自由模式的良性系统”,三者同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故此“自由模式由于主张一切值得追求的价值都应该尽力地追求而回避了选择问题。但是对大多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现实的或切实可行的选择”[17]21-28。之所以“不是”,邓小平强调,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能不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否则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6]285在邓小平心目中,为稳定政治以发展经济计,中国“现在”确实还不能推行高层直选与多党竞选。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因此排斥“半个世纪”以后中国政治空间的向民主开放。无论是依发展政治学的理论逻辑,还是依同为炎黄子孙创造的台湾经验,倘若“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的高层直选成为现实,则各政党势将成为选举机器;又只要执政者经普选产生,则不仅政府制度的民主化,就是政党制度的民主化,也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至于代际交替,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提出,因为科学范式不可通约,科学革命多是经科学家之间的代际交替而实现的,“在其中,一套陈旧的范式被一套新的范式所取代”[18]71。而由于在政治范式背后不仅有意识形态,更有实际利益,发展政治学则注意到:“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19]319关于此,邓小平的观点亦明晰而坚定。1986年12月他曾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 “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20]1157
三、政治发展与分权制衡
改革和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其次是要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以保证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众所周知,“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要与人的本性相适应,这些问题已被政治哲学家讨论了无数次。”[21]15在西方,因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长期熏染,其政治学说就多以“人性恶”为自己的人性论基础并据以设计政治制度。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表示:“即使承认君主政体为城邦最优良的政体,王室的子嗣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对于这种情况,主张君主政体的人将起而辩护说:老王虽有传位于子嗣的法权,他可以不让庸儿继承。但很难保证王室真会这样行事;传贤而不私其子的善德是不易做到的,我就不敢对人类的本性提出过奢的要求。”[8]165-166到17世纪,洛克强调:“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9]89唯其如此,所以在“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家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就都必须将“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属于不同人”[9]98。受洛克的见解尤其是英国君主立宪经验的影响,法国古典思想家孟德斯鸠即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时才休止”,这是人性使然;因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22]154-156。而将以上学说付诸实践,则两百年前,美国国父之一的麦迪逊曾强调:“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3]264问题是任何政府都是由人而不是由天使来建立和统治的,而人是自私的政治动物,热衷于以公权力谋私,所以美国政府的制度设计就只能是“三大权力部门各自分立”[23]246。时至今日,“民意测验表明,三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人对政界人士的诚实程度和道德水准评价低或甚低”[24]443。尤其是美国知识精英,就如同他们的英国同行休谟称:“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和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根本没有什么保障”[25]272,他们直言:“对处在代表国家行事地位上的人,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那些权力范围中的行为的法律宪法条款,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以他们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在追逐纯财富的人。”[26]38然而在中国,由于“国”之为“国”是为“家”的放大,即所谓“家天下”,故依家族治理的原则在“国/家”(state/family)一体化的政治结构中以“修齐治平”的公式来进行国家治理。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核心的儒家学说就从来主张“人性善”。这种人性论反映为政治理论,便是孔夫子提倡的“为政以德”,即将政治活动道德化与家庭伦理国家化。其情形当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与时任总书记张闻天在讨论孔子哲学时所作的分析:“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27]161问题是两千年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至少离开孔夫子所设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推行“为政以德”,推行“移孝作忠”,不仅容易产生伪善,容易混淆私德与公德,而且极容易助长家长制式的政治专制主义。这就是康德所批判的:“一个政权可以建立在对人民仁爱的原则上,像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这就是父权政治。因此臣民在这里就像是不成熟的孩子,他们不能区别什么对自己真正有利或有害,从而他们应该怎样才会幸福便仅仅有待国家领袖的判断,并且国家领袖之愿意这样做仅仅有待自己的善心。这样一种政权乃是可能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28]182尤其严重的是,一旦执政者推行这种“仁爱的独裁”[5]180,由于这种政治体制的主旨本来就在“移孝作忠”,同时相应的政治文化亦大肆鼓吹“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故只要假以时日,人民终将失去抵制这种政治独裁在制度上的合法性与权利上的正当性。例如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虽然事后公开承认错误,但依然要求运动的受害者:“如果你的母亲错打了你,你肯定不会因此怨恨和责怪自己的母亲。”[29]1尤有甚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竟有中共高级干部暗通满清遗老之旧道德,所谓“二姓尚可耻,况万姓乎?譬之妇人事二姓为更二夫,是改适也;归民主则人尽夫矣,是野合也”[30]21,居然也以“三从四德”为政治伦理,批评敢于向毛泽东提不同意见的彭德怀:“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洁’之妇。”[31]257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任何先天人性的存在,不论其为善抑或为恶。不过既然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并且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又不能不强调:“关于人性本善……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32]而达成此种“联系”的手段,即“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的新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33]那么由这种“新人”所带来的政治效应如何呢?若征诸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些非常无私和非常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的一般行为中,因为他们毫不考虑他们自己,他们也根本不考虑别人;他们确信,他们有权把任何人变成他们为之而牺牲自己的那个理想的牺牲品。”[34]268至于这种“新人”是否果然“非常无私”,列宁曾信心十足地肯定:“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35]作为一位活跃于帝俄时代的职业革命家,他还曾表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36]132-133“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36]134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从来表明,即使并不存在先天的人性,经几千年私有制熏染,“自私”这个东西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经深深积淀在人们心中并挥之不去。尤其生物科学已经证明,“自私”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在制度,亦不在思想,而是在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性“基因”[37]1。更何况即使如列宁所言,残酷的地下政治环境有可能吓阻潜在的腐败分子,一个成功的地下政党终有公开掌握政治权力的那一天。唯其如此,19世纪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才会有如此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38]342用当代中国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深圳特区开拓者之一的袁庚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没有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人从树上爬下来,为了生存甚至要互相厮杀,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要受外界影响,而权力这种东西就像鸦片,越吸越上瘾,因此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腐化。”[39]1
如何防止权力腐败的必然发生呢?1945年7月在延安,当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问毛泽东,目下生机勃勃的中共是否有办法跳出中国政治史上司空见惯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0]16关键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民主”并不是指的价值层面的自由民主和操作层面的制度民主,而是指群众运动。他一方面建立了一个“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掌权者的腐败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这种腐败产生的事实,于是又定期使用“大民主”方法去冲击这种腐败,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41]265-266,所谓“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2]254,所谓“过七八年又来一次”[42]71,如此等等,其结果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制约政治腐败,反而又造成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正是通过总结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包括“总结我们过去十年”,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16]307所谓“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当是指英法等国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早在1848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曾提出:“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治理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于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一切共和国都应当具有的,而且可以预言:不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很快就将不复存在。”[43]3显而易见,与托克维尔当年的思路相一致,邓小平在以上讲话中所不赞成在当代中国实行的,亦不过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这种具体制度形式,而非它的制度原则,亦即中共“十六大”报告之所谓:对权力作适度划分,以便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1980年,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时就已经明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1]339这也就是2014年9月,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毫无疑问,若细心体会邓小平、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以上讲话,不难明了,为了卓有成效地制约权力、防止腐败,执政党已不再打算走群众运动的老路,而是要在制度上实行分权制衡,即国家不仅要设立专门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且各国家机关均将在同一平面作政治互动,并无不受制约的所谓“最高权力”的优先存在。
除了“人性善”的预期外,反对分权制衡者通常还持有两条理由。一是分权制衡是阶级对抗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对立,不存在分权制衡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二是分权制衡使政府各机构相互牵制,不如议行合一效率高。其实这里第一条理由并不能成立。现代分权制衡当然是起源于第三等级与专制王权的对抗,即马克思之所谓:“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44]同时马克思称,自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所谓“永恒的规律”就只配叫做“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45]了。大概为马克思所不曾料到的是,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专制王权在西方社会早已不复存在,欧美各国依然坚持分权制衡。之所以如此,一个当然的原因就是西方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平衡利害关系的需要。具体到当代中国,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确实已经高度一致,即都在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但是人民内部还存在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具体利益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相互区别,这也是活生生的事实。仅此一条,就足以表明在当代中国实行分权制衡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至于说分权制衡不如议行合一效率高,其实这也是不少西欧人的观点,不过他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议行合一应该排斥分权制衡——“西欧人认为美国的体制是无效率的,而他们的议会制有一种权力的融合,并不一定要求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对抗。经常发生在美国体制中的行政/立法僵局不会在议会制中发生,这是因为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都由同一政党控制。如果英国的保守党在下院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其政党领袖就自动成为行政首脑。当保守党内阁提出一项新法律,它就会被送往下院通过。如果在特殊情况下,执政党成员与其内阁中的党领袖意见不一致,他们可以撤回他们的支持并投不信任票。然后政府倒台而由一个能获得下院多数支持的新领导群体代替。如果新的选举使反对党在国会中获得数量上的优势,那么内阁辞职而代之以新获胜政党的领袖。”[46]286当然,认为分权制衡不如议行合一效率高的国人未必欣赏英国议会制,他们的本意多是指分权制衡不如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效率高。然而这种观点亦是一种缺乏历史感乃至缺乏政治学常识的见解。一方面,这种观点看不到马克思当年所盛赞的巴黎公社仅是一个窄小的城市共和国并处于兵临城下的境地,看不到马克思当年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要在幅员辽阔的当代中国实施在操作上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认定分权制衡必然效率低下,实际上是错误地把政治过程与行政过程混为一谈了。毫无疑问,政府行政必须富于效率,这一点完全无可非议。然而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制约,并非意味着对于具体的行政过程的掣肘,而是要确保行政机关执行且只执行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法令与决议而不致越权和专权。在这里,决议的执行过程依然是不受干扰、富于效率的,反复的讨论只发生在法律、法令与决议的形成过程中。毫无疑问,制定法律、法令与决议过程中的反复讨论同样是无可非议的。难道可以以行政效率为理由,否定政治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民主讨论吗?想想几句“最高指示”便轻而易举地将一个民族引向“空前浩劫”而人民完全束手无策,想想某些领导人在“拍脑袋决策”过程中的一念之差使国家交了多少“学费”,答案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相形之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实在明智。为了确保政治效能,他们甚至宁愿牺牲政治效率,也要让总统与国会相互掣肘:“制宪者们既不信任杰出人物,也不相信群众,他们有意地将低效率掺入政治体制。”[24]42
【周恩来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7]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波普尔.民主理论[N].明镜周刊,1987-08-03(1).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1.
[12]科恩.论民主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3]布利策尔.西方民主观[J].国外政治学,1989(1).
[1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1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亨廷顿.难以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8]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1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1]威廉·斯通.政治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3]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4]伯恩斯.美国式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5]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6]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2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9]武际良.风雨难摧“中国心”[J].百年潮,1999(8).
[30]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J].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66(1).
[3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6.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223.
[34]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35]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8.
[36]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7]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8]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9]袁庚.共产党人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气一样[N].世界经济导报,1986-08-17(1).
[40]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3.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4.
[46]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超
Study on Three Problem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EI Ming-kang1, WAN Gao-chao2
(1.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Institute of Govern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reate more effective democracy tha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key i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an effective democratic regime.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eded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an effective system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eople’s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eded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etup of government apparatu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for ensuring that all government apparatus far away from going beyond their authority or being authoritarian.
Key words:Deng Xiaoping; contemporary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魏明康(1958-),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28-07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