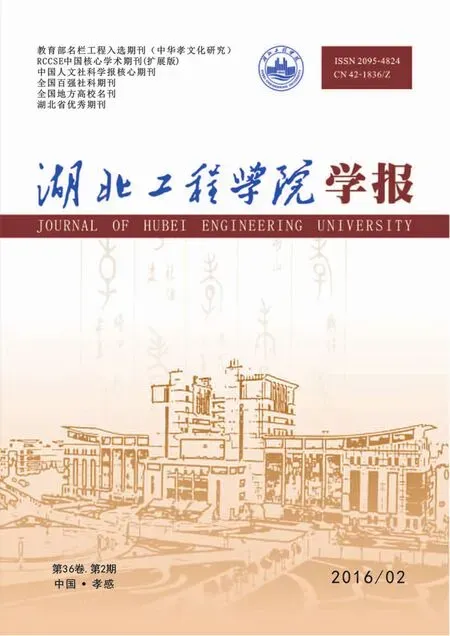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系统性安顿
——从身体人类学和生命主体论的视角看“孝道”
张 灵,魏 昕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主持人语:
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系统性安顿
——从身体人类学和生命主体论的视角看“孝道”
张灵,魏昕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孝文化或“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有云: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传统社会当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维系传统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和基础。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安排,“孝道”充满着丰富深刻的现实性、超越性和先贤生命安排的智慧,它聚焦物质的奉养,但又超越物质的奉养。“孝道”在今天看来,也充满了“身体人类学”和“生命主体论”的精神内涵,内蕴着对交往主体的双向关怀。虽然在命名和践行的策略上它强调了“长上”,但它深层指向的是意义普遍的“仁道”、“人道”,在它的“潜台词”里有着对“长上”的更严格、崇高的要求与期待。它把每个个体的生命安置在了一个与时推移而不断上升,受到的尊重也不断增加的理解、想象与规划上,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大智大慧、大爱大勇和崇高境界与追求。这也是中国文化“崇古”“尚古”的一个原因所在。“孝道”可以说是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的一种具有理性、现实、明朗特性而又有超越精神的准“宗教”,因为它是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全面的,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现世的有意义的安顿。
关键词:孝道;身体人类学;生命主体论;仁学;人道;奉养;终极关怀;崇古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或者说构成了一种现实、理性、明朗的宇宙、天地,而“孝”是支撑这个宇宙天地的核心纲维,自然也集中表征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性。“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如有的学者指出“‘孝’在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被称为首德”。[1]某种意义上,“孝”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孝道”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生活实践范式,其智慧精华值得我们在今天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孝”的深刻、丰富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智慧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阐发。
一、“孝乎惟孝”,“人之行莫大于孝”
《论语·为政》一章记载:有弟子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将这种“孝悌”的为人方式和态度传递、影响到包括卿相大臣在内的从政为官者,让他们也以如是态度和方式治理国家,这也是在参与、从事政治事务,除了这,什么才是从事政事呢!?特别值得吟味的是孔子所引《尚书》中的“孝乎惟孝”这句话,将之翻译成现代白话其实就是:“孝啊,只有孝啊”。它表面上只是一个感叹句,只是一个空洞的反复,它没有具体地指出“孝”的伟大、崇高、智慧,“孝”的思虑的深远,等等,但正是在这个近似“空转”的吟诵里,充满孔子对“孝”的肯定、赞美、咏叹。当然,这也是《尚书》的作者、《尚书》中这句话的述说者对“孝”的认识与态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创新者的孔子,对“孝”的意义、价值的阐发记载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中。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孝”的论述很多,如在《学而》篇中他还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里,孔子用的同样是感叹句式。足见孔子对“孝”的认同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怀有强烈的感情的,以至于一想到、一提及“孝”,一种赞美之情油然而生。《孝经·三才章》中有一段孔子的话也很能说明他对“孝”的重要性的自觉:“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孔子看来,“孝”的正当性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民之行也”,即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遵行的方式、规则。那么“孝”何以如此之重要,它具有怎样精微深远的思想或精神意义?
二、“孝”:聚焦物质的奉养,但又超越物质的奉养
“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白发飘拂,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而孝字的下部是个孩子,两手朝上伸出,托着老人,作服侍状。[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孝”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其中的“善事”包含养和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奉养;敬,敬爱,二者相辅相成,都为“孝”的本质内涵,缺一不可。“养”为基础,“敬”则根本,“养”为浅,“敬”则深远。
《论语·为政》有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人类之“孝”的精神诉求。“孝”作为一种生活之道,一种人生社会实践之道,一种特殊的主体间交往原则,意味着的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层面“反哺”式的奉养行为,一种衣食的供给关系,它有着更深刻、高远的精神动机与态度。它远远超出了动物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的物质反哺行为,完全是一种人类超越一般动物的相似行为的富有人性光辉的生命行为和态度。
因此,“孝”不仅仅是父母的衣食供养等物质层面的问题,而且是对主体间的具体“孝道”关系的评判,不仅无法以单纯的物质条件的优劣、多寡来衡量,也不应该如此衡量,而是要将之放在主体的具体现实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中来衡量。
“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为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3]《礼记·檀弓下》中的这段话鲜明生动地展示了在孝道践行问题上物质之养与精神之敬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汉代桓宽著作中的两段话也有深刻的阐发:“善养者不必刍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贵其礼,不贪其养,礼顺心和,养虽不备,可也。……富贵而无礼,不如贫贱之孝弟。……事亲孝者,非谓鲜肴也,亦和颜色、承意尽礼义而已矣。”“君子重其礼,小人贪其养。夫嗟来而招之,投而与之,乞者不取也。君子苟无其礼,虽美不食焉。”[4]
其实,这些论述固然是在强调子女后代对父母先辈的物质奉养一方面关键在于必须出之以礼、行之以诚、伴之以敬、动之以情、示之以悦,另一方面量力而行、尽心足慰,不以物质的多寡优劣为忧,但也绝不可以反过来逆推出一种忽视物质奉养之重要性的结论。无论如何,“孝道”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的主体间交往伦理,它所忧心、关怀的关键点,毋庸讳言,恰在于物质的奉养一点。
这里就包含着一个关于“孝道”的貌似某种悖论,有些矫情,但其实是充满着丰富深刻的现实性、超越性和先贤智慧的生命安排:聚焦物质的奉养,但又超越物质的奉养。
如何理解这种生命伦理设计,我们不妨引入一些现代西方思想的理论命题。
三、孝:一种身体人类学的现实关怀
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变革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宣称:“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发现了现象学的统一性和它的真正含义。”该书一反昔日的哲学仅仅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传统,而把形而下的身体作为哲学分析的起点。后来福柯又用他独特的思想史研究的形而下视角,出色地发展了身体研究的文化思路。[5]这股思潮进一步在西方思想众多领域扩展开来,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身心二元分离的现象开始改变,身体美学、身体政治学、文学身体学等等应运而生,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学界的几股显潮。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思想自其源远流长的早期开始就有一种身心一体的良好意识,“孝道”这种重要人伦法则的设计正是这一意识的最典型的体现。但是,随着西学东渐日益深入,我们多少遗忘或忽略了我们自己固有的传统,因而我们在研究包括孝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问题时也不免多少忽略它原本内含的思想构成。而身体哲学、身体人类学、文学身体学的意识、方法、观念无疑可以借鉴过来更好地激活我们在“孝道”理解、阐发上原本隐藏的思想资源,从而深化、提升、扩展我们对“孝道”的理解、领会。
在西方的身体人类学看来:“长期以来理性至上的启蒙观念得到过分的强调,使头脑和身体形成某种潜在的对立,最终导致理性反过来压制身体的情况。”[5]可以说正是因为西方近现代文明在思维层面日益的理性化导致了在文化层面对身体、感性的忽略,因此现象学等带来的思想变革就具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故此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对于肉体重要性的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6]深受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呼唤感性,“身体”的突围成了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7]。肉身似乎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可靠证据,而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即生活的问题。
身体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命运当然是与西方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密不可分的,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现世、理性,崇尚知行合一的特性一致,恰恰身体始终是中华文化关注的焦点,而“孝道”正是这种文化中知行合一的关节点。所以“孝道”之在中国文化中根深叶茂,是有着深刻的生命与思想根源的。
身体存在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中不管以正面还是反面的方式都没有被忽略过。在《论语·为政》中,当孟武伯问什么是“孝”的时候,孔子即言:“父母唯其疾之忧”。一个孝子,所做一切都会令父母无所担心,而父母所要担心的唯有他的健康,因为健康除了与个人的行为有关以外,还受到包括环境在内的其他非个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子女的健康是父母最牵心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身体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本钱。《孟子·告子上》中告子所言“食色,性也”更为中国文化普遍认同。而在《礼记》中孔子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对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而孟子则回答:“……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在孔子孟子看来身体及其欲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存在的,并没有什么异常。身体的存在及其欲望的正当性在中国文化中是被坦然、理性而又现实地对待。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具体的生命无一幸免地会衰老、丧失生存能力,这是自然规律。因此,物质层面的奉养就成了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就物质奉养来说,“孝道”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同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西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针对的不仅仅是老年普遍面临的问题,西方的保险完全建立在泛社会的、普遍理性考量的基础上。而“孝道”采取的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以情感和伦理为基础、为出发点的方式,西方采取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排除情感与伦理考量的方式。当然这也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构成方式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8],而西方在“家”和总体性的“国”之间存在一个“市民社会”或者说狭义的“社会”这样一个巨大构成空间,而这个空间,完全是建立在客观、理性、不关家庭情感的交往原则之上。正是“家国同构”这种意识和国家治理想象与理念决定了“孝道”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家庭维系方式,而且成为了一种国家治理方式。
换言之,身体在西方文化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渐为形而上学和工具理性覆盖与压制的过程的话,中国文化从很早就有一种对于身体的清醒、现实、理性的意识,而“孝道”首先就有对身体面临问题的一种实用而富有策略但同时又富有终极精神关怀的解决之道。
四、“孝道”背后潜在的生命主体精神与生命主体间的“对话”意识
要充分理解“孝道”背后的深刻意义,我们还需要引入生命主体、生命主体意识、生命主体精神和“对话”这几个人文科学的重要概念。因为,“孝道”其实是建立在生命的双向对话意识、双向关怀精神基础上的,而双向关怀、对话意识的产生又是建立在生命主体意识的基础之上。
“生命主体”作为一个现代哲学概念首先为哲学家T. 里根所采纳:“一个生命主体,有一系列的特征,包括有信念、有欲望、记忆、感觉、自我意识、一种情感生活、对自己未来的感知,能够开始行动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及在逻辑上独立于其他人的利益和功利的存在。这样一个人有着内在的价值,即他所具有的价值独立于其他人的效用性。因为这个内在价值,一个生命主体有保护这个价值的权利和不受伤害的权利。其他的主体有责任来尊重这些权利……‘那些满足了生命主体标准的人和动物本身,有一种与他物不同的价值——内在价值——他们不应被看作是或仅仅是作为物件来对待。’”[9]正是因为一个真正的生命主体,他是以肉体的存在为基础的,他有着自己的欲望、感觉、情感、对未来的感知等等,同时他意识到自己独立于其他人的效用性,他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即是说他不能只是一个对其他主体有用的客体,而且其他主体有责任尊重自己的这些权利和价值。显然,正是生命主体的意识和精神诉求,将生命存活的物质基础——肉体和生命存在的精神诉求紧密地扭结在一起。生命主体的这些特征不仅意味着生命个体对自身身体存在、身体欲望和精神需要的正当性的要求,而且也意味着对“他者”(即“他人”)同样的存在与诉求的理解、承认与尊重。正是这种对自己以及他者的相互理解、承认与尊重的必然诉求,决定了生命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是一种“仁学”意味的“兼爱”、“爱人”、“互爱”关系。
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对“身体”的界说也具有相似的思想旨趣:“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阈亦非博爱之阈,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相互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一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以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10]——“身体”既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也是一个将人们“相互唤入生活”的中介,一个“政治的器官”,在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也正是因此,“孝道”也超越着物质的奉养。所谓“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贵其礼,不贪其养,礼顺心和,养虽不备,可也”。相反,“富贵而无礼,不如贫贱之孝弟”。“孝道”不仅仅是一个对“衰老”和“丧失自我奉养”的生命自然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基于生命主体精神和生命主体间的双向“对话”而生成的一种包含着物质诉求的精神交往之道或策略。这也印证了黑格尔对人的一个深刻的阐述:“只有当个人欲望不再指向一种物质,而是针对同样心情的另一人时,他才能从双方交往中得到承认,获得自己是人而非物的认识。”[11]
五、“孝道”之名的背后指向一个体系性的“仁学”
“孝道”超越了基本的物质奉养,它变成了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的全方位的一种精神交往原则,一系列的“事亲”礼仪,这涉及父母长辈的生活起居的每一个方面。如:“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2](《孝经·纪孝行章》)另一方面,涉及父母长辈在世乃至去世以后的更长久时间的终极关怀。如《论语》中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孝道”虽然从名称上看,是对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如何“事亲”做了全方位、超越现世的规范,但事实上,它是相互的,它同样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包括父母长辈如何对待子女晚辈的规范,由于“家国同构”的国家想象,以“孝道”为名的这套行为规范成为了对从家庭到朝廷的整个国家各种人际关系进行引导规范的系统性伦理体系或制度。如《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敬,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义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孝经序注疏》谓:“慈爱之心曰亲”。“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爱敬之心,是常道也。”(《孝经注疏·圣治章》)因此,这种安排在每种关系主体之间,也即每个生命主体与另一个生命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等的关怀、责任和义务。
《郭店楚简·语丛三》云:“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亲,乃生于爱,而爱之生,源于人的本性。因此,“孝道”实际上是一种“仁道”、人道,如同汤一介先生所指出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道始于情’(从《性自命出》全篇看,此处‘道’是指‘人道’,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意思是说‘人道’是从人先天所固有的情感始有的,我认为这正是孔子‘仁学’理论的根基所在。”[13]朱熹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语类》卷67)。儒家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朱熹“集注”云:“孝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中庸》亦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朱熹还进一步申言:“论性,则仁是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14]
正是“孝道”蕴含着这种深刻博大的“仁学”精神,它才超越了单纯的“老年关怀”命题,而指向了每个生命乃至万物。如《孟子·尽心上》所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郭店楚简》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以爱人,仁也。”因此,推广“孝道”,实乃推广、弘扬“仁学”、人道。
“孝”之名,旨在暗示、强调做人的起点,即从身边基本的事情做起,但其背后的精神所指又极其宽广。
六、“孝道”的“潜台词”与其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终身安顿
“孝道”是一种“仁学”及人道主义的人际伦理安排,因此在“孝道”言说中,充满了平等对话、换位思考的精神。既有《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不同家庭之间的换位思考,其实也充满着家庭内部乃至从家庭到朝廷之间所有人之间的换位思考的平等的理性意识。
《礼记·礼运》所谓“十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言“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均表明:“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双方相对应的义务基础上的,如‘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等等。”[13]臣、子、弟、妻、妇与君、父、兄、夫、姑之间互有约束,互有权利义务,而不是单方面的。或者说,在“孝道”之名下的一整套伦理规范里有一个巨大的“潜台词”,这套“潜台词”是约束、要求在上、长者的,有一个“上率下行”的价值与实践理性的逻辑前提的。
“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12](《孝经·纪孝行章》)这句话是从反面强调了无论长上还是幼下,均须遵行规范,约束自己,长上并非无条件地领受奉养和尊重。《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把君臣之间的对等要求做了尖锐、鲜明的阐述。
《孝经·三才章》:“(君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君王首先要做仁君,使臣以义以礼。同样,为老要尊。老百姓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为老不尊”——这都是从负面强调了以“孝道”为名的社会伦理规范、价值体系对长上、尊者的严格要求。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这是中国文化对老年人的精神品质的一种描绘,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对老年人或“长上”约束、要求或期待的“潜台词”。
应该说,“孝道”不仅充分体察到了生命自然衰老这一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趋势给人的生命存活与尊严带来的挑战,同时,它还从精神尊严的角度,把人安置在了一个人道的、“仁学”的、无边的、充满正面价值诉求的伦理与礼仪安排体系中,显示了对生命的超越性关怀。
这套价值体系、礼仪规范,其实是将每个个体的生命,特别是精神生命安排在了一个不断上升、不断进步、日益令人爱戴、尊奉的轨道上,从而使个体生命不是随着肉体衰败而走下坡路,相反,在这样一个人生与社会的生命安排中,人的尊严只会越来越受到尊崇,生命只会接受、体验到越来越多的光荣。
所以,虽然“孝道”的设计表面上是把长上安排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其实,这只是基于抵抗生命衰老的需要,基于父母慈祥呵护儿女往往天经地义般,而儿女常有不能在父母年老体衰时一如他们对待子女那样对待他们的现实——年老体衰的父母常常处于被动、劣势,当然也基于要把人生安排在一个让生命越来越感到尊严和体面的光荣的人生想象、人生蓝图上,因此,“孝道”基于实践理性和现实生活经验,将这套伦理安排、价值体系命名并强调在一个“孝”字上,只是一种策略。
中国人也常有“养儿防老”之说。其实普通老百姓,固然基于生存的现实,有这种功利主义色彩的考虑,但他们又往往是“话说得丑,但事做得俊”。他们对待儿女,其实充满了慈爱和无私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也说过:“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的‘纲’。倘如旧说,抹掉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情,否则变成了买卖行为。”[15]
当然“孝道”的精神实质在封建时代被逐渐转化为一种更加单方面强制性的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即所谓“三纲五常”的时候,它多少偏离了“孝道”设计的初衷,它忽略或者说遗忘了“孝道”原初设计中包含的主体间换位思考、双向平等互动的意识和对长上的“潜台词”式的要求。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了封建主义的国家理解与想象对“孝道”的扭曲及其危害:“我认为阻碍新现代化的陈旧传统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专制主义、封建主义遗风、特权思想和家长制。有一种风气,我起个名词叫做‘尊官敬长’。……毛泽东同志再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他自己又鼓励个人崇拜。有同志说,什么时候把群众和首长放在同等地位上,中国就有希望了。”[16]这种单向度的“尊官敬长”的确是一种“孝道”扭曲后的文化流毒。但也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那种强调单方面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权力结构的‘三纲’是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相悖的。其实先秦儒学并不讲‘三纲’,只是在汉朝特别是到东汉《白虎通义》中才把‘三纲’法典化,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工具。”[13]
七、小结
哲学家张世英先生通过深入考察得出一个看法:“从孔子的‘孝悌——为仁之本’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一大进步。”[17]笔者觉得,这应该说是儒家道德理论或者说关于道德的理论阐释的一种深化,一个进步。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是同步的,是同样深刻而具有精神超越性的,孔子的“孝悌——为仁之本”,强调的是这套伦理规范的践行落实问题,在这个角度,“孝悌”自是“为仁”之本,“为仁”的出发点;而从更深层的精神之源而论,何以要“为仁”,何以要行“孝悌之道”,仍在于每个生命个体,每个生命主体,都有天然的、内在的“恻隐之心”,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孝道”即“仁道”,亦即“人道”。它不仅仅是要求“孝”与“忠”,它的要求是双向的,它只是基于生命的自然特点以及现实的社会经验而将“孝”置于了首先考虑的位置,甚至由于封建社会国家社会理解与想象的局限,而将“孝道”这套价值伦理体系在主体之间做了倾斜性的、单方面强制性的安排,而忽视了“孝道”体系背后的“潜台词”,但“孝道”的实质和深远的用意,对生命的尊重和超越性关怀等是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弘扬。
“孝道”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个体生命的一个既立足现实及物质生存需要,又超越了现实、现世和物质需求而具有了高贵的精神诉求,充分关怀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人生意义,具有了生命终极关怀、宗教意味的价值伦理体系,包括了生命在世何以为、何所为的设计与安顿。特别是它把每个个体的生命安置在了一个不断上升,受到的尊重也不断增加的理解、想象与规划之上,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大智大慧、大爱大勇与崇高境界和追求。
“孝道”可以说是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的一种具有理性、现实、明朗的特性而又有超越精神的“准宗教”,因为它是对生命的一种全面的、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现世的有意义的安顿。
[参考文献]
[1]余志平.一个栏目与一份期刊、一本书[M]//多维视野中的中华孝文化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代序.
[2]陈晓明.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论[J].求索,2008(3):73.
[3]陈澔.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293.
[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308.
[5]叶舒宪.身体人类学随想[J].民族艺术,2002(2):9.
[6]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8.
[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23.
[8]盛泽宇.“家国同构”问题与中国的法治国家建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6):93-103.
[9]尼古拉斯·布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61-962.
[10]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476.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0.
[12]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99.
[13]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1.
[1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1994:460-471.
[15]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8.
[16]张岱年.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J].群言,1986(11):4.
[17]张世英.儒家与道德[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1):21.
(责任编辑:祝春娥)
A Study on Filial P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Life-Subject
Zhang Ling,Wei Xin
(SchoolofLiberalArts,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Filial p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filial piety is of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all the virtues. It is well known that filial pie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Filial piety is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urns out to be the link and support that has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As an ethical value, filial piety includes profound reality, transcendence and the sages’ wisdom. It focuses on the supporting and waiting upon one’ s parents in material, but it is not restricted to material. Nowadays filial piety includes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life-subject, which means the two-way cares for the communicative subjects. Although filial piety emphasiz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lders in some aspects, as what its name implies, it always aims at the universal humanity. If one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implied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he will find that it has strict demands and lofty expectation for the elders. Filial piety can be viewed as a quasi “religion” existing in the mainstream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r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has many features, including rationality, reality, open and forthright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cendent spirit, etc. since filial piety has the wide, realistic and significant understanding of life.
Key Words:filial piety; the body anthropology; the concept of life-subject; Ren; humanity; supporting and waiting upon one’ s parents in material; ultimate care; antiquity-worship
收稿日期:2016-01-04
作者简介:张灵(1965-),男,陕西洋县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82-0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2-0005-07
本期“中华孝文化研究”专栏刊登了五篇文章。《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系统性安顿——从身体人类学和生命主体论的视角看“孝道”》一文很有新意,文献支持和论证也很好,具有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可以说是一篇体现孝道研究深化的优秀论文。《“父慈子孝”——儒家亲子间对等伦理原则与当代代际关系的梳理》,以儒家父慈子孝伦理关系的平等性作为立论基点,返本开新,针对当下亲子关系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并提出重建新孝道和新型平等亲子关系的一些建议,也是一篇有现实性和独到见解的论文。《孝廉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价值》《论当代家庭结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两文虽有自己独特的选题角度和问题意识,但在论证的深入程度上仍然需要加强。《华裔美国文学中“孝文化”与“美国梦”的冲突与融合——以李健孙的〈荣誉与责任〉为例》一文,选题有新视角,跨度大,但在分析中似乎与孝文化的关连性尚待加强。
(主持人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昕(1992-),女,山东蓬莱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