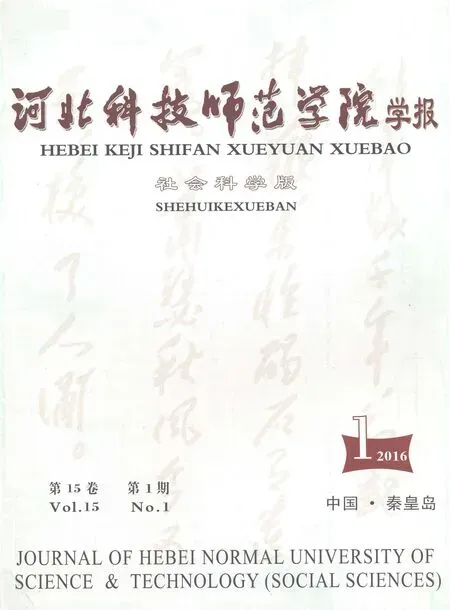复杂的“平衡”与“新颖”
——论师陀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
杨凯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复杂的“平衡”与“新颖”
——论师陀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
杨凯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时代思潮的对话。师陀30年代的创作既是一种文学实践,又是展现其复杂内心世界的方式。通过剖析他的创作历程,力图还原一个徘徊于革命浪潮中的师陀形象。新的创作人格的建立有助于理解潜藏于师陀小说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为认识师陀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契机。
时代对话;复杂的内心;创作风格;张力
一、被忽视的时代对话
如果要用两个词语简约而又准确地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艺界的真实情状,那就是“众声喧哗、同异混溶”。这其中所含蕴的巨大的、不平衡的张力,依然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种时代喧嚣的根源在于民族矛盾加剧、亡国危机逐步逼近时,启发民智的启蒙传统让位于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要务,这种严酷的现实使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融入集体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不过其独立的批判精神又时刻跳出来拖住他们汇入主流的脚步。在现行的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人们都把革命文学思潮当成20世纪30年代文学主潮——这当然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因为无论从其强大的号召力还是对40年代乃至建国后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哪个社团流派能有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但是也必须看到,革命文学并没有垄断30年代的中国文坛。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创作方法的文学作品与主流文学如何构成30年代文学大环境?要想认清问题的复杂性,就要关注30年代的上海。各种类型、风格的作家凭借着强大的现代出版、报刊业获取了一部分受众。尽管文学论争如此繁多,但自由、包容的大环境给文化人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师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文坛。可以从个性言说的角度来考察师陀始终独立的姿态及其复杂的创作,然而不应该忽视他与整个时代的对话关系。
就以往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对师陀创作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对师陀作品整体性的关照、系统性的考察还未真正开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者对师陀的解读属于共时性的,因此研究成果多为感悟式的[1]。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很多批评者,诸如刘西渭,往往能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从而影响此后的师陀研究。建国后对师陀的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复苏。但受刘西渭、朱光潜、王任叔观点的影响,当代批评者往往不能跳出已有研究的窠臼,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师陀40年代的作品《果园城记》上,并将他放在传统乡土文学的体系内加以分析。因此,师陀30年代的创作一直是被忽略的。要想全面地认识师陀的思想及艺术风格必须从起点开始关注师陀创作发展演变的脉络。其二,当下对师陀的研究确实是多方位的,所采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多样的,然而对他的内心情怀及激烈的思想交锋依然鲜有独到的发现与精微的深探。人们往往用独立或边缘化来形容师陀的一生。例如,截至目前唯一一部全面研究师陀的专著——王欣的《师陀论》,就相当细致地讨论了师陀受“五四”影响的个性言说。她看到了师陀的独特性,以及“五四”传统、京沪两地文化对师陀的影响,但有意把师陀的特立独行放在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位置上看,并着重探讨师陀性格因素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然而,作家创作与时代的对话关系远比顺应潮流要复杂得多,且师陀独立于任何文学团体这一现象本身就不仅仅是个性使然,更是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选择。因此,所谓个性使然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另外,贾瑞华等把师陀及其创作有意置于边缘化的方位进行研究[2]。虽然这一研究不乏深刻之处——比如可以有效地撇开左翼与京派的思维限制,也能够指出师陀创作相较于传统乡土文学所独有的“异质性”等,但是,也没有看到师陀与时代的对话关系。边缘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越是选择外围的人其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往往不输于任何有团体归属的个体。因此,只有看到师陀的内心冲突才能真正准确地解读其思想与创作。其三,目前的师陀研究缺乏对其艺术风格变化的认识。这一问题往往与对师陀整体认识缺乏有关。
综上所述,笔者重点探讨师陀思想、创作与时代的对话关系,试图发掘更为生动、深刻的师陀形象,在此基础之上分析20世纪30年代师陀创作所蕴含的有意味的张力和审美景观。
二、复杂的内心与小说创作
革命文学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主潮,认清它对文坛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师陀。实际上,“左翼文学”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从其内部来看,对于“第三种人”的不同态度、“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冲突、有关“民族形式”的争论等等体现了“左翼文学”界内部的分歧,更不用说一些“中间阶层”作家在政治承担与艺术自律上持不同的态度[3]。从其外部来看,“左翼文学”并不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团体,那种激进的情绪始终弥散其中。凡是不用阶级、革命斗争的视角进行文学实践的作家都被排除在外。在他们看来,体现阶级的文学才是“真实”的文学,因为这能体现生活的“本质”。然而社会生活与一般物质是不同的,物质有固定的属性,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因素,该用哪一因素来确定生活的性质,或者说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用来确定生活的属性吗?因此,用相对封闭的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反映生活的“本质”与“真实”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而对这种评判方式的执着必定不能容纳对生活与艺术持不同观点的作家。李欧梵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为了激进的代言人且他们那种批判观念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性[4]481。这虽然不是专指左翼知识分子,但揭示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实质。另外,即使在努力践行革命号召的青年心中也不可避免地有裂隙存在。尽管这一时期的文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左联”、“普罗文学”的感召,积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从而创作出适应革命需要的作品,但启蒙精神仍然深刻影响着这群文人,造成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矛盾冲突。这种焦灼感集中体现在由精英走向大众的艰难改造上。因为需要更广泛的群体参与革命,大众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工农神圣、崇高的形象反逼知识分子放弃启蒙,进行艰难的思想改造。以革命的、大众的视角进行创作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升华、加入主流话语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刘忠所言:“大众本身的庞杂和模糊也使它在把握上存在很大的虚幻性。”[5]总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文学作品中出现有趣的“沉默”现象,尤其是小说创作,其中包含了一个庞大的“不说”系统[6]——被人代言的体系,那就是底层群众的声音。只要读一读鲁迅的《示众》,这一体系就被暴露无遗。在大人们身体的缝隙间钻来钻去的孩子、像死鲈鱼一样张着嘴看的人、浑身汗渍的壮汉、抱着孩子看热闹的老妇构成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些人毫无目的地聚拢来,尽兴后又匆匆散去。鲁迅极其生动地描写这这群人的神态、动作及嘈杂的声音,但他们的语言乃至思想就完全被遮蔽在“不说”的体系内。知识分子只能用冷漠、麻木来总结这群人,他们是如何被影响,思想又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这对于启蒙者来说始终是一片空白。因此,即使知识分子到底层去又有什么来证明他们的创作体现的就是大众呢?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少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既向往着革命同时又产生了暧昧不清的态度。从现实来讲,革命话语也未必就是铁板一块。郁达夫在《鸡肋集·题辞》中说:“在那里(作者:五卅运动后的革命策源地广州)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到革命中去,谁知鬼魅弄旌旗,在那儿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着玩儿的肥皂球儿,不到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7]可见,团结统一并不是革命的真实状态。
种种精神与现实的复杂状况使革命的内外部都产生激烈的论争。而对于1931年来到北京、1932年出现在文坛的师陀来说,他并不是这一境况的局外人。从他记录自己创作历程的文章中,可以窥见师陀不平坦的内心体验。《两次去北平》和《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师陀在写于1987年11月30日的《两次去北平》中说:“我是到北平找‘出路’的。”[8]364这“出路”指的是什么?在1986年11月27、28日及12月4日的采访中,师陀明确地表达了“不愿呆在河南,想到北平去谋出路,参加共产党”[8]389的意愿。可见师陀的人生方向是十分明确的。不仅如此,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这一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写宣传标语,与工人交朋友。可以说师陀参与革命活动的意识可能要比许多此后的左联青年都明确得多。但是当他在丁玲主编的《北斗》上发表《请愿正篇》后,丁玲邀请他与“左莲女士”交朋友时,他又提出另外一套说辞:“都做一样的工作,那就不一定参加一个组织。”这一说法看似顺理成章,但我们不应忘记师陀是抱着极其明确的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来到北平的。王欣也看到了诸多矛盾之处,如王欣主要从师陀产生政治理想的原因来分析他政治思想的变化[9],而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恰恰不是为什么师陀有政治理想,而是为什么他在有明确理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居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两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微小差异并未止足于此。师陀仍然在走向革命中心的途中徘徊。他说:“一九三四年‘反帝大同盟’解散了……我自己呢,还是从事革命,并争取入党。”[8]392如果说1932年的师陀还怀着只要能革命并不在意是否参加组织的想法,到了1934年他又想积极入党,这其中的思想波澜远不像字面描述的那样平静。在访谈中他还提到:“时至今日,我仍是无党无派,那主要是因为我心目中把党神秘化了,总认为自己不够标准,所以也不敢提出此要求。”[8]389从正面理解“把党神秘化”,可以认为革命在师陀的理想中有着十分光辉、崇高的形象,而从反面理解,师陀这句话的逻辑就是革命理想与现实生活是有差距的,现实中的巨大裂痕阻止了师陀走进革命中心的脚步。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师陀谦逊的表达,但“神秘化”的含义是如此模糊,使人不得不考虑这番话中没有说出来的信息。关于这个问题的猜想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得到了证实。这两个口号的论争鲜明地显示了左翼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斗争。作为这一论争的经历者,师陀在代表两个阵营的倡议书《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中国文艺家协会》上都签了名。是否可以把这一举动解读为师陀犹豫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据师陀的好友卞之琳和夫人陈婉莹的回忆,师陀是个极其认真、耿直、倔强的人,但他有时却做着模棱两可的事,说着不怎么清晰的话。也许正是这其中的种种差异反映了他内心极其激烈的斗争,边缘化确实是师陀建国前人生取向的特点。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京派又不曾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坚持蜗居在“饿夫墓”中。这一边缘化的位置是他选择的结果,这里确实有一些性格的因素,而更多是受现实矛盾冲突的影响。
反观师陀的政治叙事,其中包含了太多“不说”的因素,他用创作诠释了情感态度上的复杂性。在师陀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的七篇短篇小说里,以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和革命活动为背景的就有四篇,但这些作品总是与主流话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想以此证明师陀的左翼情结恐怕难以成立。《头》以长工孙三被本村权贵庞老爷和军阀联合势力斩首为基本情节框架。而核心人物孙三并未正面出现,甚至连是不是孙三偷了庞老爷的那五头驴都不甚清楚。弥漫在小说中的恐怖气氛是由一些“次要”人物的活动造成的,如方天化戟与鬼魅对话,木匠的儿子勤勤因撞见孙三的头而吓得发烧,等等。小说确实表现了以庞老爷为代表的封建权力体系的压迫,而这并不是村民恐惧的源头。庞老爷的强大势力与被压抑的死亡气氛及骤然消失的飘忽感相比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表现革命志士的《雨落篇》却偏偏用一个看守宪兵对革命志士的家庭、孩子的联想弱化了阶级话语,强化了人类情感的共性。表现工人暴动的《谷》叙述了主人公黄国俊依靠特务白贯三帮助被逮捕的朋友——共产党员洪匡成的故事。而洪匡成被捕又与革命无关,恰恰是白对洪的妻子的欲望构成了事件的起因。黄国俊不是暴动的领导者,他因煽动工人起义却未受伤而陷入自责。阶级话语是故事的外表,内在情感线索多少又与阶级无关。在表现日本侵略者对百姓欺凌与压榨的《哑歌》中,喊着沙哑口号的日本儿郎是整个故事的背景,而穿黑军装的汉奸才是一场场闹剧的根源。整个小说中弥散的气氛则是刑大叔两口子对儿子的期盼。这并不是说师陀的这几篇小说不表现政治话语,而是要关注足以与政治话语相抗衡的情感和氛围。贴近政治却看重复杂的心理与情感是师陀区别于京派与左翼的根本特征。
在此,有必要理清师陀与京派及“左联”的关系。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当代的研究中,对师陀派别划分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尽管师陀没有加入“左联”,但因为他的经历、创作与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使得许多研究者看重他的左翼情结。而师陀在建国前不用阶级的视角进行文学创作,他对乡土、自然风光的独特情感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京派”风格。为了能够更系统地处理文学史,很多研究者就倾向于把师陀划为京派。“沈从文先生的手臂,长在作者的身上了”[10]195成为对师陀的经典评价,这也使得当代的研究者企图拉近师陀与京派的距离。这其中存在的误区在于,许多研究者按照对流派特征的认识和自己的理论资源来肢解作者的创作。尤其对于京派来说,它本就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团体,京派作家的个性特征往往被“美”、“人性”等笼统的概念所遮蔽。师陀作品中有30年代主流话语的同时也存在着对抗性的力量,而田园风光也不像沈从文那样表现理想与人性美,更不应该把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当做一种范式。因此,笔者认为师陀是在两种风格中探索一种平衡。左翼文学创作往往以政治话语压抑自我,而京派文人常常制造与现实的隔膜。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两种取向都有过犹不及之嫌。师陀对审美的选择恰好位于两者之间,尽管“他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10]176,这种尝试中存在着风光与人事并不怎么和谐的缺陷。
三、景色与人物的平衡和张力
之所以有研究者把师陀划入京派原因有二:其一,自《里门拾记》起,师陀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乡风乡土的小说及散文。其二,作品中的田园风光使人不自觉地把他和废名、沈从文相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师陀作品中的风光与人事有着极大的不协调。其中确实有技巧尚不成熟的因素,但作者有时却执着地诅咒着乡土又沉溺于旷野与暮色之中。在《里门拾记》和《落日光》这两个小说集中,这种近乎偏执的倾斜尤为明显。小说《毒咒》几乎是一边以轻松的笔触描绘着荒凉的旷野,一边借毕四奶奶“这块地上有毒:断子绝孙,灭门绝户。有毒”[8]98的毒咒表达着愤怒。尽管作者声称:“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8]127,但作为研究者却要关注这种不平衡带来的现实意义和独特的风格。解志熙认为师陀创作的起点是《里门拾记》,因为他在不自觉地进行系列小说的创作[11],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一方面是因为他臆断地割裂了作者的创作。另一方面,《里门拾记》中的那片乡土并不具备中原小城的特点。这虽是师陀返乡奔丧的产物,其中所表现的重点是一种对现实的焦虑,这与其说是中原的破败不如说是整个现实价值体系的崩塌。
杨刚认为《毒咒》表达了作者对乡土的憎恨[10]180,这种判断存在偏颇。《毒咒》作为小说集《里门拾记》中的一个分子,不应该将它与其他篇目剥离开进行单独的解读。虽然《里门拾记》的结构并不是有意为之,但师陀短篇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同一小说集中各篇目间的开放性、兼容性。它们虽然不存在情节上的直接联系,却有着语言风格、小说环境气氛、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性。如果单从景色与情节的调和程度来看,可以把《毒咒》中的不平衡看作是缺陷甚至一种怪异的手法。虽然旷野是荒凉的,可是也不乏秀丽、宁静的情调,甚至坍圮的宅院、荒芜的土地、农夫们关于毕四老爷辉煌过去的只言片语的回忆都构成了一种神秘的美。从师陀对景物的执着描写可以判断,这种不和谐是一种常态,作者甚至有意制造这种倾斜之感。上文论述过师陀小说中“不说”的因素。这种“不说”往往以情节的形式呈现,其作用是消解“说”出来的内容中包含的权威性。而在这里,风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不说”的形式,其作用是包容各种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如此,简单断定作者要借《毒咒》表达对乡土的憎恨之情就未免太简单了。另外,之所以说《里门拾记》展现的不单单是中原小城的衰败,更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崩溃,是因为小说集中各篇目间有强烈的互文性。《毒咒》中的毕四爷是村中的权贵但他没有男丁。这种现象破坏了旧有价值体系的完整性。毕四爷企图通过讨“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源。男继承人是延续封建价值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讨“小”绝对合理。然而,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女主人——毕四奶奶的地位就受到极大的冲击。“母凭子贵”的价值观念在完善男权体系的同时也挑起了实际掌权者的不满情绪。因此,处在旧体系中的毕四奶奶以疯狂的诅咒使已怀有身孕的、延续旧观念的 “小”落得一尸两命的结局。最终,完整的价值体系崩塌了。毕四爷遵守着旧价值,反过来却被这种价值诅咒,最终象征着权威的庭院破败了。值得注意的是,讨“小”这种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是被怎样定义的,或者说诸如毕四奶奶这样的人物到底有没有可能破坏旧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还需要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研究。然而作为文学作品,作者探讨的核心问题不是讨“小”是否有据可依,而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瓦解。可以肯定的是讨“小”这种现象古时已有,可是千百年来的文学并没有质疑它的合理性。只有到了现代,随着整个封建价值观的衰败,作为这个体系中一分子的讨“小”才有可能失去合法性。因此,这就是《里门拾记》与《果园城记》的差别。作者用他的返乡偶得建构了一个价值观念的王国,而并不一定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原小城。另外,外界怎样影响乡村在这篇小说中并未表现,但反观如同一个大农村的中国,在30年代不正面临着价值瓦解的残局吗?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破败是一个一直被历史关注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冲击着农村?不少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正是横跨城乡的华资企业瓦解着农村的经济基础与上层价值[4]214。在《过客》《秋原》《受难者》《路上》《倦谈集》中,外部力量或左右或消解内部的乡土。村中的“会首”、混过营盘的大爷、投机战争的发财梦、不伦不类的丁祭等等决定了村民的来去、造成了村中的悲剧。可见,《里门拾记》中的乡土并不是封闭的小环境,各种外来的力量使原有的价值体系最终成为七零八碎的残片。而师陀执着的风光描绘并不诗意,而是导致王任叔所谓的“模糊”与杨刚所说的“晦涩”的根源。师陀小说中的田园风光有一种吞噬的力量,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这种风格一致延续到师陀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师陀写于1983年9月25日病榻上的《杂记我的童年》将这种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小时候我常常挨打。”[8]345之后师陀便开始描写那日的落日美景。笔触轻松自然,全然没有刚挨过打的悲痛。在这段有所排斥的回忆中丝毫不见作者的仇恨。不难发现,被毒打后年幼师陀眼中的景色自然不可考,而此时的风景多半是病榻上的老人的冥想。只要回到旷野,仇恨、悲伤、怨气都被吞没,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30年代作品中的旷野也具有这样的力量。一方面,它造成了巨大的不和谐,另一方面,本应爆发出来的忿恨被清新自然的旷野吞没。旷野的张力使得情感被压制,造成师陀30年代小说中弥散不去的压抑甚至恐怖气氛,表达着讽刺、揶揄的态度。同时旷野往往打断情节的发展,尤其是《谷》和《受难者》,读者只能从描写旷野的文字中间捕捉破碎的情节,使得“模糊”与“晦涩”充斥在小说中。然而这种不和谐在《果园城记》中得到改变。
纵观师陀一生的创作,他并不执着于描绘乡土社会,也不唾弃都市生活,更多的是表现人的精神状态。《果园城记》中景与人的融合象征着师陀创作的成熟,但30年代在景色与人物间寻找平衡的尝试也表现了一种张力与弹性。
[1]王欣.师陀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2]贾瑞华.在边缘处的生命探寻——从边缘人形象看师陀独特的艺术追求[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
[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章建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忠.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0.
[6]曹清华.“说”与“不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个维度[J].学术月刊,2010,42(5):113-120.
[7]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380.
[8]师陀.师陀全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9]王欣.论师陀作品的政治叙事[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6):83-87.
[10]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3):5-19.
(责任编辑:母华敏)
The Complicated Balance and Novelty——The Novels of Shi Tuo in 1930s
Yang Kai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000,China)
A writer’s cre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ialogue with the times.Shi Tuo’s creation in 1930s was both a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a way which showed his complicated inner world.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creation process,it tried to restore a hovering image in revolutionary era.Establishing new personality was a chance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which was hidden in Shi Tuo’s novels, and it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literary style.
dialogue with the times;complicated inner world;style;tention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1.013
2015-11-10;
2015-12-13
杨凯芯(1991-),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I206.2
A
1672-7991(2016)01-00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