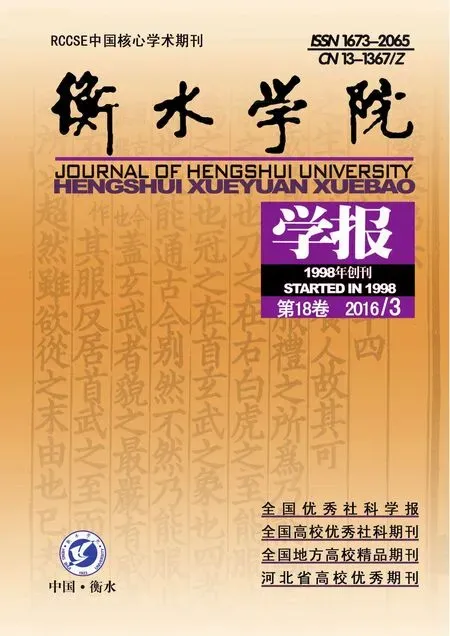中国人的良善生活:财富、公正与责任
俞 丽 霞(1.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2. 上海社会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上海 200235)
中国人的良善生活:财富、公正与责任
俞 丽 霞1,2
(1.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2. 上海社会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 要:普通中国人追求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高成本的生活。德沃金对选择的运气和无情的运气、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个人和环境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人的良善生活的线索。不公正的制度以及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阻碍了人们对良善生活的追求。政府应承担应尽的责任,改革不公正的制度并改变资源分配非常不平等的状况,为人们创造平等的选择环境,同时根据资源条件设计众多普通人可以承受的生活模式。人们只有在能够承受生活的成本和风险以后,才可能过上体现自身抱负的生活。
关键词:良善生活;中国;公正;责任;德沃金
在摆脱了生存(subsistence)贫困之后,普通中国人如何过上良善生活?当前,他们追求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高成本的生活,但金钱只是过上良善生活的必要条件。笔者不探讨良善生活的具体内容。借助德沃金对选择的运气和无情的运气、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个人和环境的区分,我们将看到,在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以及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不公正的背景下,很多中国人还远离良善生活。原因在于:他们必须自己设法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抵御生活中的种种无情的坏运气,由于物质资源的限制,他们的选择无法体现自身的抱负。在哪里划分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决定了中国人能否过上良善生活。
一、 良善生活与金钱
在当前中国,金钱的地位至高无上,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官员,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在追逐它。尽管绝大部分中国人已摆脱了生存贫困,但很多普通中国人“挣钱”还是在应付生活,因为不断上涨的物价、奇高的住房价格、教育收费、医疗费用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承受力。为数众多的普通中国人生活在重压下。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通过金钱来解决,不然就可能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服务以及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普通中国人要在满足生存需要之上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很多的钱。企业、商业等行业时常唯利是图,以至造成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曾一度只追求 GDP。普通民众、企业和政府其实都知道这些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不断进入公众视野的部分官员的腐败似乎是这种不平等的一个典型。良善生活与金钱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拥有多少金钱才可能保证良善生活?金钱就应该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吗?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对创造财富的能力(wealth-talent)的剖析让我们看到金钱至上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即某些人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是其他人愿意花钱购买的这种天生的能力,是一种人格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常被视为一种资质(merit),利用这种才能的人似乎理所当然地拥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另外,创造财富的能力常被视为有助于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因此拥有这种才能的人应得到更多财富。德沃金指出,这种论断其实预设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即市场经济结构。在一些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生产别人所需的东西的才能往往得不到发挥,因而几乎不能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他提出了驳斥这两种关于创造财富能力的观点的三种理由。首先,赞赏某种品质并不一定要以物质的形式。一个只对伟大科学家和艺术家颁发并不值钱的奖杯的社会并不比另一个对他们进行巨额物质奖励的社会低等。其次,他认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应该得到赞赏的品质是不合理的。什么算作一种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许多方面是偶然的,有些才能能够创造财富具有历史偶然性。德沃金承认,像智力、勇气、判断力等这些品质长期以来受到赞赏,它们对于创造财富的确很重要,但这些品质本身也是多维的,究竟哪个维度能创造财富是偶然的。因而,他认为,运气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我们都赞赏运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这么做。最后,德沃金认为,即使这种才能是一种应受到金钱奖励的优点,商业市场成为奖励的标准和媒介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市场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须受政府的管制[1]322-323,325-327。但当前膜拜金钱的中国社会离这种反思很远,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为了它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的中国人才远离良善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现状与德沃金的观察不谋而合:成功生活的标志就是财富的积累,一个追求这种成功的人的生活依然是受人妒忌的合理目标,而不是备受同情或引起关切[1]107。在当前的中国,人们似乎不会对利用创造财富的才能而致富存有多大的异议,哪怕由于某种能发财的运气而一夜暴富。或许,令人们无法接受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是利用制度本身、利用权力来获取不正当的财富而造成的。
金钱确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比重要,但这恰好说明了社会存在问题。很多事情(上学、看病、找工作、很多冲突和纠纷)有时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按照规范(规章制度、法律法令)解决,很多时候要靠支付金钱、“找关系”来解决。似乎人们在摆脱了生存贫困之后还是在重压之下生活,离期盼的美好生活还比较远。这种情况是否说明很多中国人仍未真正摆脱贫困?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还在为满足更美好的生活的需要而努力,美好生活的需要确实高于生存的基本需要。这种较高的生活需要显然是良善生活的一部分,如接受好的教育、看得起病、住上较舒适的房子。当然,对于部分家庭出生背景特别优越或挣钱能力特别突出的人而言,无论生活成本多高对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普通中国人,这一切都是沉重的负担。即使一些人可以积攒起令他们自己欣慰的金钱,可这笔金钱未必一定能保证他们过上美好生活:他们可能会因病致贫,可能买不起一套住房……在运气好的情况下,挣很多的钱确实可以保证良善生活。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一种结果是挣不到多少钱,这自然无法保证过上良善生活;另一种结果是即使挣了很多钱也无法应付高成本和缺少保障的生活,因而还是远离良善生活。由于生活的很多方面无保障,由于太多东西得依靠很多金钱来解决,人们不得不努力挣钱。这一切说明金钱是良善生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二、良善生活与公正
既然金钱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么为追求它,就不惜一切手段。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感受到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冷漠、自私、势利的社会氛围中,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等公共规范的事件经常发生,但过错者是否依法得到处理是因人而异的。在这种局面下,良善生活如何可能?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不惜一切手段追求金钱是有关系的,但一小部分人之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地积累财富的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公正的缺失。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不遵守维系人们合作和共存的道德、法律等规范的程度令人吃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遵守规范,而且所违反的经常是基本规范,但这类行为得不到根本性纠正且日益变得司空见惯,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存在道德危机。中国的道德危机不是在于,人们的善观念尽管不违背道德和法律,但却不应被赞赏,而是在于很多人违反或多或少公正的、关于人们合作和共存的规范。这样的道德危机首先是正义的危机(也是社会秩序危机),因为不断遭侵犯的是底线伦理,并且人们不愿遵守自己认为基本上公正的规范。在一些情况下,对于某些人,规范是可以随意突破而不受处罚的,遵守规范的人反而蒙受损失。正义的危机源于善的危机。在中国,善与正当不可分,道德与政治不可分。政府不仅制定法律也规定道德,政府是道德的授权者,并树立道德榜样来规劝人们做什么样的人。但在目前,众所周知的部分政府官员严重的腐败表明,他们违反了自己规定的道德和颁布的法律,这样的后果是人们日益不认同原先的道德权威和榜样。最终的结果是人们不愿遵守道德和法律。因而,中国的“道德危机是道德自我的危机,是道德意愿或道德能动性的危机”[2]。
柏拉图认为,公正与良善生活不冲突,公正不损害一个人过良善生活的能力,而是成功的生活的前提[1]240-241。在他看来,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拥有的资源超过正义所允许的限度的人都决不可能过上更良善的生活。德沃金提出,如果将良善生活视为“以正当的方式应对正确挑战的生活”,那么损人利已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不好。在不公正的社会中,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的生活都会变得更不好,都不可能应对正确的挑战,因为他们的资源要么比公正允许得多,要么比公正允许得少,尽管不公正不是某一个个人造成的。“这说明为什么根据挑战模式,不公正对人们是有害的”。在德沃金看来,如果将柏拉图的上述观点理解为意在表明公正是良善生活的硬参数,那么,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这个看法显得太严格,但基本上是正确的[1]265-267。
当下中国的情形表明,不公正严重影响人们能否过上良善生活,这恰好诠释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之后,良善生活似乎离不开以下内容:让自己或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从事能使自身得到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职业、安全的食物、清洁的水和空气、住房等等。但在中国,众多普通人的这部分需要满足起来比较困难,面对高物价、高房价、不安全的食品、严重的环境污染,收费高昂的医疗等一系列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有时无力应付。由于政府、专家、各行各业有时都不可信任,所以很多中国人有时不得不自己充当很多的角色, 要对生活负全部“责任”①。但是对于一小部分人,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制度可以为他们抵御所有可能的坏运气,他们可以利用制度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这是否印证了德沃金的观点:当环境很不公正时,人们难以过上正当的生活,甚至难以想象一种完全良善的生活[1]265?
这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可以借助德沃金对两种运气和两种责任的区分来分析。首先看一下德沃金的运气区分。他将运气区分为选择的运气(option luck)和无情的运气(brute luck)。“选择的运气是一个慎重、成败参半的赌博结果如何的问题——某人是否由于接受一种孤立的风险而获益或受损,他或她本来可以预见并可能不接受这种风险。无情的运气是非此意义上的慎重赌博的风险结果如何的问题”。比如说,买入了价格上涨的股票是交上了好的选择运气,被坠落的流星击中是遇到了无情的坏运气[1]73。德沃金用假想的保险市场来解决无情的运气之一的残障问题,即人们可以购买保险的方式来抵御残障使其掌控的资源变少的风险。人们应对选择的运气负责,因为选择体现了人格差异以及不同的人想过不同的生活②[1]74-75。而集体应对无情的运气负责,对遭遇这种运气的人们进行补偿[1]79。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社会为人们提供平等的选择环境,如人们可以为某种无情的坏运气投保,那么无情的坏运气可以转变为选择的运气③[1]77。这里,平等的选择环境对于区分选择的运气和无情的运气起着关键性作用。不管在实际中两种运气的界线应划在哪里,两种运气的区分总是存在,因此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划分也总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讨论。
在中国,平等的选择环境在一些情况下不存在。中国的很多制度建立在运气之上,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出生在怎样的家庭等等这些偶然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境遇和前景。很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受无情运气的摆布。社会没有把一些无情的运气变成选择的运气,甚至让普通民众承担不公正的制度的严重后果。在阿瑟·里普斯坦(Arthur Ripstein)看来,责任含有承担损失之意。如何划分责任即确定“坏运气是谁的”是个政治问题,而划分应在公平对待相关各方的平等背景下进行[3]。这与德沃金的强调平等的选择环境是一致的。
三、良善生活与责任
对于中国这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摆脱贫困一直是中国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显而易见,良善生活一定不是受贫困威胁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轻消除贫困的成就举世瞩目,绝大部分中国人摆脱了生存贫困。这里不讨论还有一部分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们的生活。那么当前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又对其他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相对不平等是否是我们过上良善生活的一个障碍呢?德沃金指出,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可能会使社会付出道德代价,尤其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之后,如果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的话,有时这种道德代价甚至还可能加剧[1]106-107。那么中国社会为这种不平等要付出怎样的道德代价?其实,尽管大部分中国人摆脱了生存贫困,但生活并未变得有保障,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压力,离良善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有些人反而感觉以前物质匮乏时代的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他们并未完全摆脱贫困,他们又陷入了地位(status)贫困和能动性(agency)贫困[4]。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为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付出的道德成本。
有学者指出,在财富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低收入者虽然生存有保证,但他们遭受着地位贫困,低收入使他们不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是获得尊重的基础。特别是在一个以金钱作为社会地位标志的社会,地位与凭借金钱才能获得的东西紧密关联,低收入者可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从而得不到尊重④[4]126。目前,奇高的房价、高昂的教育费用(如果要选择好的学校)以及医疗费用远超出一大部分中国人的承受能力。
在德沃金看来,“人们的命运由他们的选择和他们的环境所决定”[1]322。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个人不应对所处环境的不幸方面即无情的坏运气产生的结果负责[1]287。选择体现人格,而人格由抱负(ambition)和性格组成。他的抱负是广义的,包括一个人“所有的爱好、偏好、信念以及他的总体生活计划”。一个人的环境由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组成。人格资源包括体力和智力,创造财富的能力属于这类资源。非人格资源指的是“那些可以从一个人再分配给另一个人的资源——他的财富、拥有的其他财产,以及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提供给他的利用这些财产的机会”[1]322-323。显然,集体责任即政府或社会的责任体现在对个人的环境负责,对资源分配负责。他认为,资源分配应对抱负敏感、而不应对天赋(endowment)敏感。资源分配对抱负敏感指的是使人们的资源多少反映他们受不同爱好、偏好、信念和不同的生活计划而导致的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等个人选择方面的差异。资源分配不对天赋敏感是使人们的资源免受在自由放任经济下使相同抱负的人的收入产生差距的那类能力的影响[1]89。德沃金这种资源分配的主张与他对两种运气、两种责任的区分是一致的,这启发了我们思考中国人怎样才能过上良善生活。
德沃金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人的能动性(agency)。作为道德和伦理行动者(agent),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渗透着他自己的信念、爱好、价值观、判断,并且必须考虑自己可能拥有多少资源。一个人在形成自己的抱负和偏好时,至少要将公正作为幸福的软参数,即不仅考虑到能获得多少资源,而且考虑到应该获得多少资源。因而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管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而不能将它们归为好运气和坏运气。否则他的人格就是分裂的。在此基础上,他拒绝将个人的昂贵爱好视为坏运气或残障,认为社会不应补偿昂贵爱好[1]287-291,296。在德沃金看来,政府应该努力确保人们之间的生活幸福或其他成就形成差异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选择和人格上的差异,而不是他们拥有的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上的差异[1]303。如果坚持每个人过上成功的生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政府就应尽可能使公民的命运不受其“经济背景、性别、种族或特殊技能和残障”的影响[1]5-6。
在中国,由于制度不公正造成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人们拥有的资源特别是非人格资源差异巨大。很多人必须自己确保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必须把挣钱放在核心位置,但即使这样还未必能抵消糟糕的环境的负面影响,使自己过上良善生活。如果良善生活所必需的资源无保障,人们可以做出的体现抱负的选择范围是受限制的。其实,抱负的形成也深受环境的影响,受资源的限制。“人穷志短”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这说明很多中国人的能动性的实现非常困难,这使他们无法过上良善生活。
地位贫困与生存贫困并无必然联系,但地位贫困可能转变为能动性贫困。实现能动性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但物质上的富足不是能动性的必要条件。糟糕的是,地位贫困将一部分人置于正常能动性标准之下,从而使这部分人遭受能动性贫困,得不到尊重,并失去自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物质条件很差,但由于几乎没有东西是实现能动性所不可或缺的,所以人们并未遭受能动性贫困。社会必须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确定每一位成员的“正常能动性范围”(normal agency range)。对于中国社会,保证实现能动性的物质资源应该包含哪些东西?个人必须拥有多少面积的住房、什么档次的汽车、在什么层次上消费等等。或者简单地说,该有多少收入?由于物质资源的限制,每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只能在一定限度以内。这个能动性范围只能由社会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确定,即确定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参与的社会活动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一般能动性标准不能只让少数人才能参与这些社会活动。但中国社会似乎没有关注这个正常能动性范围。住房价格、医疗费用以及教育费用等都超出很多人的承受能力,很多消费品的价格、一些垄断性行业生产的产品价格也居高不下。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很难做出体现其抱负的选择,或者说在应付生活后没多少选择的机会,因而他们的生活远离良善生活。
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已成巨富,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热衷于积累更多的财富,迷恋于奢侈生活。在德沃金看来,这种生活的重要吸引力在于它只为非常富裕的人所保留,但现在却被视为有价值的生活。这就说明,在一些社会中财富被赋予了异常突出的重要性[1]107[4]148。众所周知,一部分过上这种奢侈生活的人的财富的获得是利用了权力、不正当的优势的结果。官员腐败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另一方面,这部分人的奢侈生活以及获取财富的手段也为一些人树立了糟糕的榜样,或许其他一些人会羡慕这种生活,如果无法过上这种生活,可能不会认真对待生活。这种情况可能是无法实现能动性的另一种情形。
四、结语
德沃金对选择的运气和无情的运气、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区分为思考中国人的生活现状提供了线索。确定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能否过上良善生活。
尽管绝大部分中国人摆脱了生存贫困,但离良善生活还有距离。普通中国人追求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高成本、缺少保障的生活。不公正的制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物质上的高成本,也使社会付出了很高的道德代价。政府应承担应尽的责任,改革不公正的制度并改变资源分配非常不平等的状况。在物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为人们创造平等的选择环境,使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无情的坏运气转变为选择的运气,降低这些坏运气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人们只有在能够承受生活的成本和风险以后,才可能依据自己的抱负选择过怎样的生活。同时,形成什么样的抱负受到资源拥有量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当前,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阻碍人们过上由自己选择的生活。在当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应该设计一种人们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良善生活,这种生活能使他们受人尊重并享有自尊。
注 释:
① 这里用“责任”一词并不太准确,参见下文的相关讨论。
② 德沃金注意到,这两种运气间的差异可以是程度上的,有时会不知如何描述一种特定的坏运气。我们会看到,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是否该对坏的选择运气补偿的争论。
③ 在可以为失明投保的情况下,不购买这种险种而失明就属于这种情形。
④ 慈继伟指出,地位贫困对于遭受生存贫困的人们而言是雪上加霜,允许生存贫困和地位贫困同时存在的社会是不道德的。低收入者不能参与的社会活动包括不能接受教育、就业以及消费。
参考文献:
[1] DWORKIN R.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CI J. The Moral Crisis in Post-Mao China: Prolegomenon to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J].Diogenes, 2009,56(1):19-25.
[3] RIPSTEIN A. Equality, Luck and Responsibility[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4,23(1)3-23.
[4] CI J. Agency and Other Stakes of Pover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3,21(2):125-150.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The Good Life of Chinese People: Wealth,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YU Lixia1,2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To a great extent, the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make money to lead a costly life. The distinctions made by Dworkin between option luck and brute luck,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people and their situations can throw light on how to judge the good life of Chinese people. Some unjust institutions and pretty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wealth impede their pursuit of 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ar its due responsibilities to reform the unjust institutions and change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to create situations for people to choose equally.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design life patterns available for common people. The ordinary people can live a life after their own ambition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can bear the high living cost and risks.
Key words:the good life; China; justice; responsibility; Dworkin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85-05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16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俞丽霞(1977-),女,江苏张家港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