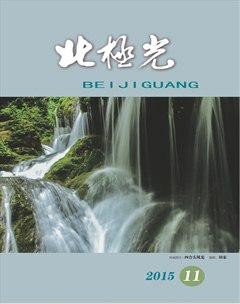试论《夏洛特少女》纺织母题的意义
李婷
摘要:少女中了咒语,与世隔绝地编织纱罗。这个文学母题从希腊神话到近代小说,绵延不绝。本文以丁尼生的《夏洛特少女》为纲,西方十九世纪几部小说为目,旨在揭示这一传统,发掘该母题背后的心理意义及哲学意味。
关键词:母题;《夏洛特少女》;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幽闭情结
不弄明白《夏洛特少女》(The Lady of Shalott)中“罗纱”的象征意义,恐怕无法彻底理解丁尼生这首长诗。夏女遭了诅咒,困坐愁城,整日纺织不辍。手底下的罗纱好似罗网(web的双关含义),将她围个结实,没法回到俗世,只能透过一面宝鉴偷觑红尘。可日子一久,她又有点迷上这份差役,乐得把鉴上的情态,编织到纱匹里去。罗纱就是她所沉醉的化外世界,跳脱在世相外头反映着大千生灵。
这个一体双层的象征意义,并非全是丁尼生的发明。我们在神话和童话里,都能找到夏女的祖宗。安徒生《野天鹅》讲艾丽莎的继母把她十一位哥哥都变成天鹅。小艾丽莎只有拿荆棘编做衣裳,给哥哥们穿上,才能破解咒语。而在她成功前,不准和世人说片言只字,否则所有努力都成虚话。这故事昭示了夏女“纺织母题”的第一义:纺娘被罗纱丝丝缕缕地缠住,无法和世间接触。而古希腊的命运三女神则代表了另一层意义。这三个老婆子纺织操纵着芸芸大众的生命线,自己则超越神人,游离于命运之外,恰似与织机长相厮守的夏女。
飘然出尘,不被世情困扰,才能长生,因为无情者不老。故而命运女神亘古长存。童话《睡美人》里公主被纺锤刺中,能历百年而容貌如生,也是“纺织母题”的一个变体。夏女为了兰斯洛丢弃罗纱,破了罗网,却也失去了世外的长生法诀,最后落得个香消玉殒。这便是诗中谶语的真实含义。好比睡美人被王子吻醒,虽然爱情和美,但从此就驻颜无方了。
英方小说家中,颇有几个对“纺织母题”感兴趣的。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第148页的一段话:
“人们的命运错综交织,仿佛一张奇特的罗网,要把它解开,已经要运用我所有的心力。而那罗网之外的宇宙虽然诱人,我也不能浪费智慧的光芒,让它平白消散在无垠的空间中。”
在艾略特看来,不仅命运如同夏女手中的纱罗,就是人的思绪,也仿佛经纬丝线,交错繁复。她笔下的女主角,往往沉浸于幻想的迷宫中,编织着绮丽的纱线,渐渐迷失,不能自拔。比如在《丹尼尔的半生缘》(Daniel Derondo)第26页描述道:
“关德林(Gwendolyn Harleth)在沉思的迷宫中终于快走到尽头了。过去的九、十个小时里,她脑中一次次地浮现未来的憧憬,一次次地拒绝荒谬的发泄,一次次地在走各条道路所付出的代价前退缩。”
这几句话赋予了夏女“纺织母题”一层新义。夏女将宝鉴中的形象编入纱罗,如果换个角度看,就是关德林用自己对周遭的印象建一个思维的迷宫,或者套用佩特(Walter Pater)的话,织一张“微妙心绪的罗网”(the network nf otlr subtlest nerves)(佩特221)。如此看来,夏女的纱罗图案也不全然是照搬所见,她会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编入心血之作中。在这点上,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说得最明白:
“对我而言,意识无疑是真实世界忠实的喉舌。但对真实世界而言,意识并非一面忠实的明镜。谁真以为那样,谁就错和比喻较了真。”(培根234)
读罢艾略特的作品,我们对“夏女母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其实是未涉世事的少女自我幽闭心理的体现。她们对闺阁外的人事一面惧怕,一面向往,偷觑着世俗的只鳞片爪,却又不敢一步踏出去。而此类微妙的心境,又都在纺纱织线这项日常琐事上沉淀下来,具现为一个神话,一个童话,一个骑士故事,或者一本小说。
当然,小说失去了神话童话那种隐喻象征的传统,少女情怀又被打回了原形。亨利·詹姆斯后期作品中多有夏女的姐妹,他称她们为“沉思者”(reflector)。在《贵妇人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v)的序言中,他解释了伊莎贝尔·亚契(Isabel Archer)在房中的寂寞守夜,认为这是整本小说的文心所在:
“论其实质,不过是场平常的守夜,可比二十个‘事件更能推动情节。设计这个场景,是为了让它既像事件般灵活,又如画面般简约。”(亨利·詹姆斯《贵妇人画像》46)
詹姆斯的短篇小说《笼中》(Inthe Cage)与“夏女母题”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女主人公是个穷电报员,二十出头,每天在电报局里干着枯燥乏味的活。外面的花花世界常向她搔首弄姿,可她却被贫穷诅咒着,只能被禁闭在小小的“牢笼”中。而社交来往更与她无缘。这对爱慕虚荣的女孩来说,是最要命的灾难。但自卑而艳羡,屈辱而孤愤的情绪并不长久,她常常会因为偷窥到发报者的隐私而得意起来。
詹姆斯把夏女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满腔惆怅却也能从偷窥人间的快感中得到发泄。所以这位女发报员也颇织了一阵子纱罗。“她常想:自己能随心操纵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亨利·詹姆斯小说集》,143)“她从电报里读出他们的交往,他们的故事,没完没了地猜测着各种意思。”(同上,155)“她真正能留下的信息很有限:她把它们割裂组合,翻来覆去,穿插编织。”(同上,143)
故事继续,女电报员逐渐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开始,她还没觉察到这危险,她仔细斟酌,耐心品评,终于选择埃弗拉上校做她的心上人。小说到了高潮,女电报员再也耐不住寂寞,跑出了笼子,去和她的“兰斯洛”幽会。哪知道梦想破灭,斯人心有所属。原来镜子里的终究是幻象。詹姆斯的夏女只得再缩回笼中继续编织纱罗。“突然之间,笼子成了她安全的保障。对那等在外面的另一个自我,她的的确确害怕了。”(同上,213)
詹姆斯的结局与丁尼生略有小异,但无论返回笼中长守寂寞,抑或逃出笼外憔悴老去,夏女们都没有逃脱那个诅咒。芳华与爱情不可兼得,这便是命运的诅咒。endprint
詹姆斯与丁尼生各执命运的一端,而狄更斯更胜一筹。他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里包揽了夏女主题的两种结局。小杜丽给麦琪(Maggy)讲故事,说有个公主非常漂亮睿智。在公主的宫殿旁边,有所小茅屋,里面住着位可怜的妇人,独自过活。公主几乎每天路过茅屋,都看到那小妇人在纺纱。直到有一次,公主停下了马车,她才发现在那茅屋里,小妇人独自看守着“大大的宝藏”——某个路过行人的影子。公主似乎早已知道妇人自我幽闭的缘由,因为她只淡淡地说:“提醒我为什么。”妇人回答:“打一开始是因为再也没有像他这么好的人路过了。……没人记挂这影子,失去它也没人不快活。而影子的主人早就上路,去和等待他的人相会……”(狄更斯342)故事的结尾,妇人死了,把她的宝藏也带进了坟墓。
表面上看,妇人和公主间有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们分别象征了小说第一卷“贫穷”和第二卷“富有”。但探究根本,两人其实同病相怜。公主也是被困锁宫中,无法逍遥于人世。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解释为何公主和妇人间仿佛有种莫名的渊源。公主对小妇人的秘密洞若观火,而小妇人也能向公主展示自己最珍惜的“宝藏”。甚至我们可以说,她们二人其实是小杜丽意识的两面。小妇人就好比詹姆斯的女电报员,是小杜丽避世的港湾,而公主就如同丁尼生的夏女,是小杜丽想象中的自我。可无论是公主还是小妇人,她从来没有想过逃出纺织纱罗的命运,小杜丽也脱不去那个永久的诅咒。
夏女母题是自我幽闭,沉思冥想不能自拔的悲剧。可是广而言之,不独少女如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幻想中驰骋,却也同时被自己的幻想囚禁。佩特论述这点最为详尽:
“假如我们继续沉溺于对于世界的想象中(……),那意识与现实的差距会更大——对世界的观察尺度将被自我的狭隘意识牢牢限死……那些印象都是孤独孑立的产物,所有意识都是它自己梦中世界的囚徒。”(佩特221)
佩特帮我们找到了夏女母题的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哲学意义: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自己意识的囚牢,我们困坐在这个笼子里,只能将自己对世界的印象编织成梦想的纱罗。没有人能真正客观地考察世界,所以纱罗的花纹永远是镜中幻象,似真非真。而这个幻象迷离的天地更进一步让人失去了直面人生的勇气。躲在里面仿佛能够长生不老,即使对外面富丽堂皇的坎摩罗宫,也不愿再望一眼。对于此类体会,沉思沉郁的文学家恐怕最有心得,所以小说里多见夏女的影子。
如此看来,夏女最终抛却纱罗,冲了出去,虽然香魂入了尘土,比起永久沉沦于幻觉的芸芸众生,倒是得了大自在了。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