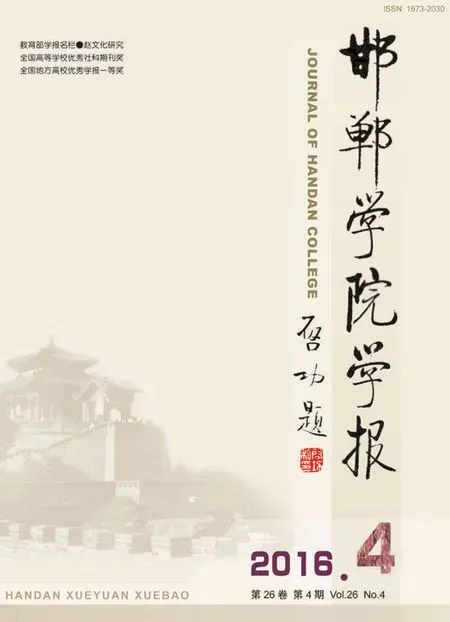论荀子“名分”说之政治伦理意蕴
陈光连
(金陵科技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1169)
论荀子“名分”说之政治伦理意蕴
陈光连
(金陵科技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1169)
荀子提出正名即重新制名之理想,基本上和孔子正名及制名以使权分礼分得以正确的实施以重建礼乐政治伦理秩序相一致。“明贵贱”与“别同异”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是具有伦理道德意义,一是具有逻辑认识功能,前者属于应然领域,后者属于实然领域。荀子制名之目的在于指实,即名与实相符,故“明贵贱”之名与“应然之实”相应,而“辨同异”之名则与实然之名相应。和“等贵贱”在伦理领域侧重追求社会至善相应的是,在道德领域,其分的意旨在于明辨荣辱;“辨同异”则是为了成就正确的知识。西方之逻辑仅着重辨同异,即知识方面的问题;而荀子之名学则汇通了知识以辨同异,且重伦理政治以明贵贱,兼具知识和价值两方面,就文化心灵而言,荀子实较西方逻辑学者为弘深。
荀子;名分;贵贱;荣辱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本性集中体现和表达为一个“伦”字。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伦或人伦正是从实体性出发考察伦理的观点。无论在道德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生活世界中,伦或人伦的内涵却指向由个体之间的诸多关联所形成的实体,其意义并不是指个别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个别性的人与他所处的那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伦理关系,不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伦之间的关系,所谓人伦其现实性是个体与他所处的伦理分位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安伦尽分才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而按照伦理实体要求而行动的正名,自孔子以来就是应对伦理失序的基本对策。宋代思想家司马光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曾提出:“名份虽小,其事关重大。”名份关系到人伦和谐、社会有序,名份内涵规定着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方面是说:君是君,臣是臣,各尽其责,各守本分。另一方面是说,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名份和地位。长幼有序、尊卑贵贱不可逾越。传统名份论要求人伦关系双方都能在其位,负其责,才能维持社会人伦纲常,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在孔子看来,只有从正名做起,如果人人都能各尽其责、各安其分,使社会的每个成员与其名分相符合,才能恢复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
一
而相较荀子的思想而言,在荀子的“所为有名”即正名的必要性提出了名的认知功能:制名指实、辨同异、喻情志,这是制名和正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不过,他更为重视的是名的社会伦理及政治教化功能。①关于名的功能,陈汉生写道,荀子“同意把语言的作用主要评估为道德作用,有助于管理人民和提供国家秩序。不过,荀子也承认指正这些功能。明贵贱,设计词的分类功能和规范功能。辨同异显然是一种指正功能。”见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周云之等译,李先琨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8页。在荀子看来,制名和正名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具有重要的社会伦理功能:明贵贱。而明贵贱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易于社会管理;二是维持伦理秩序。因为荀子生当礼乐制度崩坏之时,周文之盛,不可复在。而此时名辩之风大为盛行,异端邪说蜂起并作,以致是非无定,而礼乐制度之义亦不为世人所重视,并得到正确认识。故《正名》篇有感而发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这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荀子不满于此思想状况,尤其不满于礼乐制度之义在这一状况下被曲解而加速其没落,于是他起而呼吁:“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从而使乱归于正、言归于顺,改变此一思想分歧的状况,使是非得定,贵贱得明,而礼乐制度之义也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社会伦理秩序亦得以正常的维系。劳思光先生在谈及孔子正名观念时,曾指出:“此类理论可看作‘礼’观念之延伸”。并云:“为政以‘正名’为本,即是说以划定‘权分’为本,盖一切秩序制度,基本上皆以决定权力义务为目的,在一社群中,权分之分划既明,即可建立一生活秩序;专就政治秩序说,一切政治秩序之主要作用亦只是权分之划定”。[1]91虽然此处“权分”二字改作理分较为恰当,但大体而言,此段文字转向来分析荀子正名之目的亦无不可。由于荀子在人禽之辨上强调“义以定分”(《王制》),又以分莫大于“理之不可易”(《乐论》)之礼,可见,他的分不专限于权分之义,而可兼具理(礼)分之意。
而荀子提出正名即重新制名之理想,基本上和孔子正名及制名以使权分礼分得以正确的实施以重建礼乐伦理秩序相一致。概而言之,孔子尚名是从反面说明正名之作用,而荀子则从正面去说正名及制名的教化功能。《正名》篇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尤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词以乱正名,故其民慤。慤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守名约之功也。”此谨守名约之功相信孔子也是意许的,荀子的正名及正言的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孔子发展而来。然而,“谨于守名约”是否就是真的达至“迹长功成,治之极也”的效果?如果所制之名的标准在于其是否与实然之实相应,则“谨于守名约”也至多只能够是语言忠实地反映或描述客观事物或事实,而不一定达到治之极的理想。“名实相应”或“制名指实”等词都是当时的通语,诸家所说不同,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名”、“实”之义及其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规定。对荀子来说,名与实然之实相应,只是制名的必要条件,名与应然之实(即礼分)相应,才是正名的充分条件。言由名致,所以正言的标准除了一方面要视乎言之意是否合乎礼之标准外,另一方面也要言中之名须与诸种应然之实相应。孔子强调在人伦关系中的个人理应名实相符,这是落在伦理意义上之正名,而非逻辑上的意义。故冯友兰尝谓:“孔子之正名,仅从道德上立论,故其正名思想,仅有伦理之兴趣,而无逻辑之兴趣。”[2]373
荀子既以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自居,当然继承孔子正名的伦理政治旨趣,故其名学思想也当以伦理秩序为其最高秩序所在。“荀子身处当时之学术环境,目睹名实相乱之现象足以危害社会之安定,思有以解决此一难题,而提出其名学之主张。而荀子名学之缘起,除了继承孔子之正名义外,则是批判名家及墨辩之诡论而来,且由此而使荀子之名学思想具有强烈之伦理政治意味及逻辑本色。”[3]73而荀子制名之目的在于指实,而指实之作用有二,一是辨同异,二是明贵贱。故荀子说:“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正名》)荀子以为人心接触各种不同形状的事物,若不分别制名以指实,且名实关系必会相互混淆,纠结不清,而贵贱之分际不明,同异之界限无法分辨,以致人的思想无法沟通,而行事也必滞碍难行,故知者或圣王之所以制名,其目的则在于除此弊害。引文中的“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并以为两件事,陈大齐先生则认为是一件事,并指出:“名是用以指实的,但荀子于‘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句后,又说到‘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然则,指实与明贵贱辨同异,究竟有没有分别?依荀子所论看来,两者似乎是一件事,并没有什么分别。荀子论无名的害处,举了贵贱不明,同异不别。而智者之所以制名,无非是驱除此种害处。其言‘制名……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前后正相呼应。至于插在中间的指实,上文未有伏笔,不免突如其来。唯有把指实解释为与明贵贱辨同异是一件事,方可以免突兀之嫌,而思察荀子原文,确亦应作如是解释。”[4]141-142而此论亦为周群振[5]216-217、周云之[6]198-199等学者所赞同。故冯耀明对陈氏之说评论:“荀子言制名之目的,在喻志与行事。喻志即‘道行志通’,行事在‘率民一焉’。然而,为何‘贵贱明,别同异’就可以使‘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呢?原因是‘别同异’可使实然的分位得以界定,‘贵贱明’可使应然的分位得以分清,则喻志与行事之目标自可达至。然若‘制名以指实’只限于‘别同异’说,则可以使志喻而必可以使事行,要使事行,必无明贵贱。虽然用名而不能别同异,该名自不能立,但名已立而不能所指之价值分位,则此尚非名之正,而由之而成之说,亦非正言、正论。”[7]34
依冯氏所言,陈氏依上下文之脉络点出指实与明贵贱别同异的关系,并以之为一本,其说前后不一,且细究荀子原文的脉络,陈氏的说法暧昧不明,其实,指实与明贵贱、别同异实为二事。也即,制名之目的在于指实,指实之作用在于明贵贱、别同异。至于明贵贱、别同异二者之不同,冯友兰先生明确指出:“指事物之名之功用,在于别同异。指社会上人与人各种关系之名,其功用在于别贵贱,如君臣父子等名,即专正此等名,使为君者必合于为君之名,为臣者必合于为臣之名,荀子承儒家之传统的精神。故其所谓正名,除逻辑的意义外,当有伦理的意义。故曰‘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2]377以此言之,“辨同异”其作用在于区别事物或认识对象之同异,进而分辨认识事物之是非,属于“知”或“智”的范畴,“明贵贱”乃伦理政治上的正名,其名指人伦之间的关系之名,目的在于分别贵贱,使亲疏有别、贵贱有等,属于“伦”或“德”的范畴。
可见,“明贵贱”与“别同异”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是具有伦理道德意义,一是具有逻辑认识功能,前者属于应然领域,后者属于实然领域。荀子制名之目的在于指实,即名与实相符,故“明贵贱”之名与“应然之实”相应,而“辨同异”之名则与实然之名相应。徐复观先生指出:“名与礼是不可分的,作为名的正与不正的标准之类,不是政治伦理上的所居之位,而是对所居之位的价值要求。亦即是对所居之位要求所应尽到的责任”。[8]326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借用过来说明荀子的正名思想并无不妥。此所以说“制名以指实”时,一方面要“辨同异”,而另一方面要“明贵贱”,其要旨在于一方面能辨别诸名所指之实的实然状态的同异,另一方面又能明示诸名所指之实的应然分位的要求,即正名的价值要求是对名所指之实的分位、礼分而言的。如果说,孟子明确提出了五伦说,建立了人伦关系的范型,借此建立诸多的人伦关系,荀子则对五伦说作出详细的职分规定。伦的哲学真谛,一是强调秩序,二是强调区分。不同的伦对应不同的分。“伦不同,分也不同;人伦地位不同,个体的伦理权利与伦理义务也不同。……分由伦决定,分的伦理目的和最高取向是要维护这种伦,但同时分又构成伦的实质性内涵。”[9]149在等差性的人伦关系中,可以说在自我之上有君、父、夫,在自我之下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推衍下来则有亲、民等。如果我是夫的话,则在我之上有君、父,如果我是父的话,则在我之上只有君,如果我是君父的话,则我是人伦的终极点。自我的地位不同,职分不同,其中所蕴含的自我德性的分殊不同,不同的德性对应着不同的伦,不同的伦又蕴含着不同的理,而理是德性修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伦是德性修养所面对的人伦生态,分是德性修养所恪守的道德义务,因此道德主体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人伦坐标中都应恪尽自己的伦理本务,安于自己的伦理本位。“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荀子·王霸》)因为人不能兼任多种职位,兼通多种技能,农民、商人、士大夫、社会百工根据自己所长而固定于某一职业,使“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而不能上下僭越,名分相离,否则,不仅社会制度遭到破坏,人伦秩序也不能良性互动。可以说,区分自我本位的职分在于稳定人伦秩序,实现社会至善。
二
和“等贵贱”在伦理领域侧重追求社会至善相应的是,在道德领域,其分的意旨在于明辨荣辱。荀子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可见,荀子作为儒家大师,其荣辱思想有继承孔子、孟子的重义倾向,把荣辱和“仁义”联系起来,来反映人的道德价值。“先义”表明荀子荣辱思想是对孟子“耻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把“耻”与仁联系起来,认为“耻”是的四端之一,有耻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耻感表现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道德价值判断在人内心中的情感积淀,当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相比,是正确的,在人的内心产生愉悦感,是错误的,则在人的内心产生羞恶感,并进而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从而回到人之正路符合礼仪的轨道上来,言行适宜,举止适中, “义者,宜也”,这就是“义”。但孟子的“义”是仁义,人之先验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通过“求放心”的存养而致其不失,仁是肯定的情感,义是否定的情感,“求放心”的过程也是义对仁的爱人之心发用的纠偏,义告诉人们在道德行为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使道德行为归于道德的本性和能力,并使义沉浸于主体德性的修为中,因而,孟子的义是从心的存养处去说的。
而荀子的义是礼义,“礼者,伦也”,礼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秩序的和谐,重视社会的名分等级,惟齐非齐,和而不同,而义是对道德主体具体道德行为的纠偏,并且是在礼的规范的制约下进行的,使道德行为适中而符合礼仪,因而,荀子经常礼义连用,对荣辱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从心性上去说,而是从道德行为的结果、危害中来阐发的。得到荣誉的人永远都会通达,得到耻辱的人永远都会穷困,通达的人永远制服别人,穷困的人永远被别人制服,只就是荀子所说的荣辱的分别,而造成这种分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好“勇”。这里的“勇”非《中庸》载“子曰:‘知耻近乎勇’”的“勇”,孔子所说的勇是人的德性,是人之为人的美德,知道耻辱、克服过错是需要道德践履的勇气,强调人应勇于改过迁善,人可以立下成圣成贤的志向,然而按照道义的标准反求诸己,悔悟、自责于已然的过错,羞恶、自律于未然的不善,则需要勇毅的品格,宋代哲学家张载也说:“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可坚勇。”(《张载集·张子语录中》)而荀子的勇是“分”勇,即主体在道德境遇中面对不同对象作出不同行为而分出不同的勇的等级: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荀子特别推崇“士君子之勇”,即“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很显然,不畏权贵,不谋其利,为坚持仁义面对死亡威胁也坚强不屈,这才是义的表现和本质意义所在,道德主体在面对不同的伦理境遇,面临着不同的道德选择,个体人格的沉淀、提升的关键在于能够持义,而通过这样的勇敢所获得的荣耀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义荣”,而强调 “义荣”是荀子道德世界观在义与利关系上的折射。
要想了解荀子荣辱观的真切含义,必须从人的行为的善恶出发,方能对其本性及根源进行透彻地理解。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的“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按他的说法,荣有“义荣”,“势荣”之分,辱有“义辱”、“势辱”之别。“义荣”是因为“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 等人格的内在价值而获得的荣誉。“势荣”是因为“爵列尊,贡禄厚,形势隆”等外在因素而获得的荣誉。“义辱”是因为“流淫污,犯分乱理,骄暴贪利”等恶劣行径而招致的耻辱;“势辱”是因为受到诬陷,强暴和欺凌而外受刑罚所招致的耻辱。荀子的荣辱之分,是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在社会道德领域的反映、运用和表现。他的这种观点明显受到稷下学派的影响。荀子在此明确荣辱之界限及缘起,为君子、小人的道德修行,为人为事指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和度量。同时,他的荣辱之分也折射出荀子重视等级名分的特质。高正在谈到荀子的道德起源时说:“这种以‘分’求‘一’,即以等级差别求得整体和谐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要求确立新的等级制度,并据此建立统一新政权的愿望。”[10]103荀子述“正名”,论等级,驳十二子,旨在为封建大一统扫清思想上的障碍,纠正意识上的混乱,区分荣辱,其意也概如此。
而荣与辱不是一成不变的,荣可致辱,辱可致荣,其间包含相互转化的机理。荀子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荀子·荣辱》)在荀子看来,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一律都是凡人,只有靠后天的积蓄,然后才有圣人君子,才有贵贱、荣辱的等级出现。圣人是“人之所积”,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都可以成为圣人,但不一定都成为圣人,那就是所积的不同,因此他很注重学习,注重后天环境的培养,用他的话说就是“注错习俗”,圣人、君子、小人并无定性,关键在于积,只有切实持久的积累,才能够学有所得,“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化性关键在于起伪,在于后天的努力创造。小人可以获得后天的荣誉、高贵,圣人也可以获得小人的卑贱、耻辱,他们之间所起的变化,均在于后天环境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化性起伪是一切荣辱之分、贵贱之别的根本动力因素,而“等贵贱”、“分荣辱”其伦理归旨在于定人伦。荀子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谓别?”(《荣辱》)所谓别,就是分:区分贵贱、长幼、贫富、尊卑等名分等级秩序,这与礼的原则是一致的。荀子认为,只有通过等级名分,才能使农民精心种田,商人精于理财,各行各业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各自承担自己的义务而各得其所。荀子主张给人以养、给人以求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放任之,则产生争斗,争斗则致危辱,“忘其身,忘其亲,忘其君”,甚至是该受刑辟的“狂惑疾病”,人其形体的“鸟鼠禽兽”(《荣辱》)。
因而,荀子提出等级名分说,上至君子,下至小人,在生产上实行工商农贾的职业分工,在产品上实行多少厚薄的分配数额,在伦理上区分长幼贵贱的不同等级,这样,人们的荣辱思想就披上名分的合法外衣,少了利害冲突,少了利欲之争。势辱并不算什么,但如果“犯分乱理,骄暴贪利”,那样的义辱才是真正的耻辱,势荣也不算什么,他有权势地位,富贵利禄,而我有道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光荣。人人这样有心,自然就没有斗志,社会自然也就伦理有序。柯雄文指出:“道德经验的范例确实是道德知识的例证,但是在伦理生活中,它们并没有如‘推理许可证’一般的作用,不能指示我们如何以道持身,如何从事由个例到个例的推理吾人应如何推理的理论概念并不能决定个例推理的信服力。反之,是反省的当事者在思考道德具体意义。成就而生的洞识,对荀子来说,是储蓄德性与卓越之灵的宝库。最后,此种积逐渐由合乎类的片段反思及行为构成模式。”[11]122荀子荣辱之分在其形成中蕴育着变的精神,而变的动因在于“化性起伪”。对此,康有为评说:“荀子治气而心之术,言变化气质,古今论变化最精。”[12]378化性起伪,即在后天学习的过程中须循师法,遵礼义,重名分,方为荀子荣辱之分的中节、中理、中行。
三
荀子正名之言“明贵贱”是为了贞定价值的地位,并进而要求人们明辨荣辱,以义为上。“辨同异”则是为了成就正确的知识。“西方之逻辑仅着重‘辨同异’,即知识方面的问题;而荀子之名学则汇通了知识以辨同异,且重伦理政治以明贵贱,兼具知识和价值两方面,就文化心灵而言,荀子实较西方逻辑学者为弘深。”[13]436其实,荀子在《正名》篇里导出了“别同异”和“明贵贱”即“知识”和“道德”的悖论。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借美诺之口对知识来源问题提出认识困境:一方面,认识的发生要以对所认识的对象有所知为前提,因为对该对象一无所知,则根本无法确定其为认识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所研究的对象是已经知道的东西,则认识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柏拉图由此论证了认识或学习的过程只能是回忆的过程。同样,荀子的思想也面临着如此的境地:一方面,追求德性意味着对善的向往,它在逻辑上以主体已经具有某种德性为前提,缺乏善的德性,显然难以将善确定为追求目标;另一方面,既然主体已经具有德性,那么,成就德性的努力就似乎是多余得了。那么,荀子如何实现“等贵贱”对“别同异”或者说“德性”对“知识”的超越?张载言:“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14]20张载把知分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两种,其德性之知是不萌于见闻的超验认识,亦是道德理性,就其具有诚明的属性而言,德性之知对于它所作用的对象,有着一种既超越感性的认识,又超越理性认识的直觉明鉴。就张载通过尽心已知德性而言,表明其认识的重点是认识德性,成就德性。
其实,在张载之前,荀子已对知作了明确的区别。荀子也把知分为两类:第一,关于对象的经验知识 ,《正名》言“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在此言论关于对象的经验知识,“征知”即心的证明、反思作用。五官各有分职,“耳目口鼻形各有所接而不相能”(《荀子·天论》),因此,必将心之统一综合才能形成对象的认识。但荀子的侧重点并非在于求证自然的经验知识,认为天体运转、昼夜更替、季节变换、风雨雷电等现象是自然界的功能所致,其自身有其运行规律,与人道兴衰治乱无关,因而,即使是圣人,虽然智虑精深也不要妄加揣度,“圣人不求知天”,而把着眼点在于“知道”。“道”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当否的准绳,需常悬于心中,否则,便会招致认识之祸,而认识了它,则可赞稽万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知道”才是荀子的主旨。“道”即是荀子所谓“至足”的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是以为天下之极也”(《荀子·解蔽》),圣人伦制即是礼仪之统,也是荀子所主张的“学有所止”而止于之“道”。“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荀子·解蔽》)。
由以上分析可知,荀子所探求的知识,①“智德”的探讨,在多玛斯文本方面,主要参见 St.Thomas Aquinas,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Summa Theologica(New York:Benziger Brothers,1946)之第二部的第一部分(QQ.57-61)和第二部分(QQ.47-56)拉丁文本则参见 S.Thomae Aquinatis,Summa Theologica.5 vlos.(Parisiis:Sumptibus P.Lethielleux,Bibliopllae Edidoris,1924)。其它尚见于他的《驳异大全》(S.C.G),第3部,《论德行》(De virtutibus)及一些杂论(Quodlibeta)。另外,亦可参考St.thomas Aquinas, Prudence(New York:McGraw-Hill Book,1974)。完全围绕着孔孟儒家的道德修养以臻于圣人的道德之极为目标,其诉求的“知”亦诚如张载所言是“德性之知”,相对于“闻见之知”或“经验之知”具有超越、直觉的一面,亚里士多德根据德性获得途径的不同而相应地划分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前者来自于后天的教导,后者产生于习惯,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认识德性,而是实践德性,因为任何德性都是非神赋天赐。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亚氏认为伦理德性是关于感性和行为的,故更接近于中庸,它是一种选择能力的品质。[15]36亚氏更强调理智德性对伦理德性的指导意义,着重论述理智德性的特点,理智犹如明亮的眼睛,指导着伦理德性的实现,但是,如果没有伦理德性,道德行为的选择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可见,亚氏所言理智德性犹如荀子所谓之知,即“别同异”之征知能力,而伦理德性即如荀子所谓之义,是经过后天的教化习俗所得,而其中贯通的是人的行为的道德实践,由此,荀子的“德性之知”不能理解为静态的道德知识,而是向善的价值信念与成德的道德践履的动态统一,师法之化、礼仪之教一方面以道所包含的行善趋向或行善定势;“还需进一步指出对于事理或行为对错的正确认识——一种伦理认识,正是知或智的恰当表现。在此意义上,知或智不仅作为为求知而求知的思辨理性,也作为为求善而求知的实践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为求行善(道德实践)而求知的道德理性。这个意义或界说基本上是在以朝向道德实践论为目的之道德知识论的范围内而言的。”[16]同时,在识“道”的过程中,也将对道的确认化为成德的行动,荀子的道也蕴涵着实践的意向。在荀子看来,成就德性必须经过“真积力久则入”的践履过程,最终即可达到神明自得、参天化地的境界。诚如魏元珪先生所言:“荀子虽倡性恶,但却不轻视化性以成善,察其忠心主旨所在,厥在强调借着实际的行动,以纠正人性之不足,故善乃由实践力行而来,并非天生以待成也”。[17]99人之性有向恶的趋向,必待道德实践的纠偏,化知识为德性,而实现德性之知向德性生成的超越,并且,道德与自然的欲望的冲突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因而,成人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的践履,在“性”的“感而自然”与“德”的“感而不自然”之间,须强力操持,坚持不懈,人虽有成人之限,仿佛有终,实其无终,须臾不可间歇,荀子曰:“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人与禽兽之别,贵其有义,而更贵其持义,德性的生成即在于“始则终,终则始”的对其价值无限信仰的道德践履中。
四、结语
因此,为政之要首先要定名分,在中国文化、中国伦理的发展中,就存在着伦与分相关联的两种状况:一是名分相联,有名必有分;反之,有分就必须有名。二是名分相异,有名未必有分,这便是徒有虚名,有分未必有名,这便是僭越。前一种情况显示的是伦理的有序状态,后一种情况则应称为伦理的失序,伦理的有序和无序,和名与分的关联有着直接的联系。经典儒家对伦理秩序的设计,就是首先确定人伦秩序与伦理关系,然后要求伦理关系中的每个个体都恪守本分,由此便建立了伦理的秩序,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强调人伦秩序的不变性和伦理权力、伦理义务的神圣性。而荀子之正名思想在政治伦理领域侧重于从“明贵贱”和“别同异”两个方面探求社会之价值,要求个人在正名之中能够明荣辱、成德性,从而实现社会至善和建立社会秩序。
[1]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李哲贤. 荀子之正名析论[M]. 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4]陈大齐. 荀子学说[M].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6.
[5]周群振. 荀子思想研究[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
[6]周云之,刘培育. 先秦逻辑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冯耀明. 荀子的正名思想[J]. 哲学与文化,1989(4).
[8]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9]樊浩. 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高正. 诸子百家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
[11]柯雄文. 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M]. 赖显邦,译.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12]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蔡仁厚. 孔孟荀哲学[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14]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8.
[15]亚里士多德. 可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6]潘小慧.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J]. 哲学与文化,2003(8).
[17]魏元珪. 荀子哲学思想研究[M]. 台中:东海大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贾建钢 校对:苏红霞)
B222.6
A
1673-2030(2016)04-0058-06
2016-08-15
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ZXB006)
陈光连(1974—),男,江苏灌云人,哲学博士、博士后,金陵科技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论庄子之“物无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