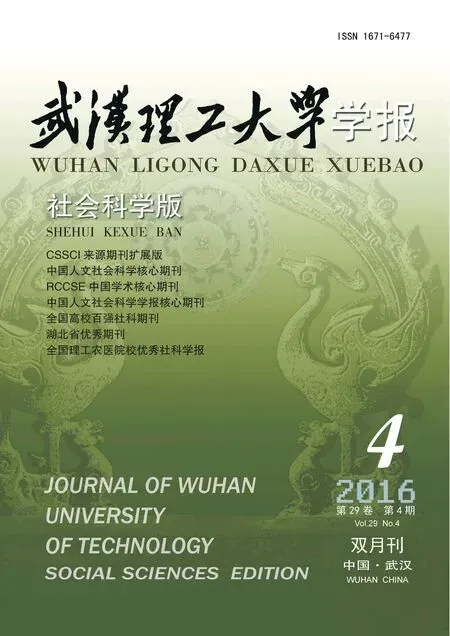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
——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
柳文文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
——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
柳文文1,2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相映成趣,布鲁姆的方法是诗歌的强力误读,而德勒兹的途径是返回混沌并从中再次现身,他们看似选择了不同路径,实则关注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同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前人成就的庇荫之下,在一个充满了具象和先定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家应该怎样实现自我突围。此外,布鲁姆批评的强烈主体性特征在德勒兹对培根创作分析中得到了拓展,影响的焦虑是创作中所必须面对的心理壁垒,它不仅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现实物质世界,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带有一种深刻的人类学关注,体现出作为一种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经验的特点。
影响的焦虑;布鲁姆;德勒兹;混沌;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这本著作包涵着吉尔·德勒兹哲学与培根的绘画理念之间的某种隐秘呼应,其中涉及到很多现代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德勒兹在书中不仅以一种游牧式开放自由的姿态探讨了在培根的艺术中感觉是如何呈现为形式,还看到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面对的影响的焦虑,且绘画由于其创作特点,画家所受到的影响也相对复杂,除了受到前辈画家的影响,外界具象也会给画家的形象创作带来压力,绘画就是与俗套作斗争的过程,是超越影响焦虑的意志表现。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构诗歌传统,以一种逆向式的诗歌批评理论为后来的强力诗人开辟出一条创新和自我实现的道路。在这个层面上,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相映成趣,布鲁姆的方法是诗歌的强力误读,而德勒兹的途径是返回混沌并能够从中再次现身,他认为这是培根完成形象差异化的一条必经之路,德勒兹和布鲁姆看似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实质上他们都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关注着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同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前人成就的庇荫之下,在一个充满了具象和先定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家应该怎样实现自我的突围。
一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把强力诗人的创作描绘成摆脱前代巨擘影响的种种尝试,他将迟来的诗人看作是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他们必须面对诗歌传统这一父亲的形象,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抗意识和超越前人的焦虑。在布鲁姆看来,新人和前驱的关系就好像某种强迫型的神经官能症,它的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双重情感,从这种情感中派生出的是一种救赎的模式。布鲁姆提出了这种新的“逆反式”诗学批评,其实质上看来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批评,他要求人们回到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想象的自主性,通过一种深刻的内在力量来实现艺术上的超越和创新。“我们——不管你是不是诗人——都深受‘影响的焦虑’之害。我们一定要在它的根源里找到我们自身的位置,在弗洛伊德以其辉煌而技穷的智慧称之为‘家庭罗曼史’的致命泥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57在布鲁姆看来,影响的焦虑不仅是诗人所面临的问题,对于其他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艺术家们必须面对前辈大师的成就而又试图有所突破,在这种内心争斗中的过程中探索一个本真的自我,以获得想象力的彻底自由与解放。布鲁姆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去寻找诗人焦虑的根源,其目的是为了确认诗人自身的位置,他“关注的只是诗人身上的诗人,亦即地地道道的诗人的自我。”[1]10他把焦点始终放在弗洛伊德内在意识的框架中,这种逆向式诗学批评充分体现出人类自我呈现这一根深蒂固的冲动和一种极强的生命意识,人的自我一旦被某种东西遮蔽,就会产生焦虑的情感。对于布鲁姆来说,这种遮蔽来自于前辈诗人缔造的诗歌传统,强力诗人必须依靠六种修正比来完成对前人的超越和自我实现。他虽然承认诗人也会受到诗歌领域之外因素的影响,但他显然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地道的诗人自我之外。
德勒兹在这一点上与布鲁姆形成了某种呼应,他认为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与“俗套”(Clichés)做斗争,“俗套”遮蔽了画家的自我,它包括物质世界里已经存在的具象以及画家心理上的感知、记忆和幻像。为了避免落入摹仿的俗套,艺术家必须作为一个逆反式的人物来改变艺术史上所谓的“经典”的图像或再现的套路,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之变形或是毁灭它,探寻新的形式,改变其中的“俗套”,构建属于自己的形象。任何伟大的艺术家只有逐渐摆脱影响,才能赢得自己,在艺术的范畴,突破不意味着替代,意味着扩大“疆域”。德勒兹在书中讨论了画家培根与委拉斯凯兹、塞尚、高更和梵高之间的艺术继承关系,前辈画家的作品既是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具象,也是画家对此的记忆和感知。他寻求与前辈画家之间的类比,通过确认自身的对立面来探索新的“自我”。培根承认前辈画家已经构建了形象之间所有可能性关系,想要寻找新的途径是十分困难的[2]3-4。他的《教皇》系列是对委拉斯凯兹《教皇英若森十世》的变形和扭曲,培根甚至沮丧地说:“我尝试着去扭曲委拉斯凯兹的教皇,却是非常失败的...”[2]90“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作品之一。我想,作为一个画家对它深深痴迷,一点也不奇怪。我想有许多艺术家都会承认,在某些方面这幅画非常杰出。”[3]在培根看来,委拉斯凯兹的教皇已经画出了某种绝对的不可替代的东西,就像一个巨大的屏障挡在培根面前,尽管如此,培根的《教皇》在艺术史上应该是成功的,委氏画中的教皇是个贪婪的活生生的当权者形象,到了培根的绘画中却发出凄厉绝望的呼号。培根按照“苔瑟拉”的方法将前驱画作中的形象接续下来,表达了形象心理上的某种逻辑联系,但他最终用流动的笔触和色彩所表现出的事件性和触感消解了与委拉斯凯兹的教皇形象连续性,他画出了教皇的尖叫,表达出喊叫背后的一种更原始的力量,培根在“克诺西斯”之后,用画作中独有的节奏和韵律实现了自我的逆崇高和对前驱的超越。此外,培根利用照片来抓住现实中的具象以及转瞬即逝的感受,培根一方面通过照片来学习和作画,一方面又否认照片的任何美学价值,他既放任自己沉浸在这些陈腐的形象之中,又极其厌恶并拒绝它们。照片作为真实的剽窃物,强加给我们一种难以置信的真实,这是一种经过篡改或伪造过的真实,相比实物具象而言,照片是对实物观看的连续视觉之流的瞬间截取。无论是照片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具象,培根对待这些陈腐形象的分裂态度实际上是艺术“双重化”的表现。艺术既要表现现实的存在,又要表现其不存在,既要表现出它的限定性,限定性在绘画创作中以图解的形式体现出来,又要表现出它的无限性,既要表现出过去,也要表现出未来。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看,这是艺术创作者对一种可能性世界的探索和追寻,是一种来自内在体验的超越事实的认同。艺术家周围的具象是碎片化难以看清的,这些碎片建构起来一种对真实整体性的遮蔽,成为艺术家看清世界和自身的迷障,因此也就成为其焦虑之所在。这种焦虑源于一种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追求,向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表现出了欲望的生成性和主动性。
艺术家的这种自我寻找和超越的欲望既是收缩的,也是扩张的,德勒兹一方面肯定了画家在心理上受到来自对前驱画作中形象的感知的影响,这些修正行为就是一种向内收缩的过程,艺术家在这种心理内溯式的误读、接续、倒空、逆崇高修正行为之后,最终在死者的回归中找到一种神性的力量,其中既没有前驱者,也没有艺术家自身,而是一种近乎于诺斯替式的神秘存在。从布鲁姆的这种逆向式批评中,可以隐约窥见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影子,一种回归浪漫主义的秘密梦想。另一方面德勒兹指出了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自我与外部真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出了其深刻的人类学根源,影响的焦虑也来自于想象与现实间的冲突,由于现实限制想象,画家对现实具象的应对和处理包涵画家超越现实和自我扩展的需要,使其在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可能性世界。为了突破现实的界限,这台欲望机器带着巨大的能量向外扩张奔突,为人类个体和集体现实的绝对广度和深度提供无意识扫描的空间。
二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中的六个修正比虽以语言修辞为方法,但他真正关注的是诗人的主体意志,“作家通过修辞完成创新、超越焦虑心理才是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侧重点。”[4]如果说“克里纳门”和“苔瑟拉”阶段是焦虑的蓄积期,那么从“克诺西斯”经历“魔鬼化”再到“阿斯克西斯”就是返回混沌超越焦虑心理的必经之路,在这个阶段诗人必须经历主体性的毁灭和再生,毁灭就是使诗人或艺术家重新进入一种原始的混沌状态。在德勒兹看来,混沌也是绘画及一切艺术形式用来对抗影响焦虑的最有力武器,是超越前的涅槃,绘画必然要将它自己的灾难整合进来:画家必须自己穿越混沌和灾难,拥抱它,然后从中重新现身,现代绘画从混沌中创造力量并获得力量,从而将“智性的悲观主义”转变为一种“神经的乐观主义”[2]61。这里的混沌不是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而是一种感觉的语言,它破除定见,建造一座以感受和感觉的聚块构成的感知物纪念碑,以此来对抗影响的焦虑,并从中催生出新的形象。德勒兹在他与迦塔利合作的《什么是哲学》中指出,“艺术跟混沌对抗,目的恰恰在于借混沌之石攻定见之玉。”[5]
当前驱的存在和现实中的具象像洪水一样扑来,艺术家的想象力就会被淹没,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样一场原始灾难中重返自身。培根画作的感觉表达方式在之前的艺术家那里是不常见的,在现代主义的艺术史逻辑中也罕有与之类似的作品,培根是如何战胜影响的焦虑并最终实现了对前驱的超越?“用布莱克的话说,诗的影响乃是个人在状态中的穿越。”[1]46我们可以说画家在创作时也必须经历个人在混沌中的穿越,这是一种放弃意图的意志,在混沌中将自我从前驱的影响中分离出来,实现意志的绝对自由,从而找到真正的主体和自我。在培根访谈录中,他提到在创作“基督受难”三联画的时候,经常沉溺于醉酒的糟糕情绪中,常常是在惊人的宿醉与晕沉的笼罩下画画,有时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酗酒使他多了一点自由。后期创作中他耗费着巨大的精力来使自己变得更加自由。这种自由既不借助于吸毒,也不借助于酗酒,而是通过一种“无意志的意志”,正是这种“无意志的意志”使一个人完全自由。[3]这实际上是一种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酒神精神”,人类在消解自我与世界合一的混沌中以获得重生的极大快意。为了实现这种“无意志的意志”,在面对画布上已经存在的各种“俗套”时,“画家要做的并不是去覆盖一个空白的表面,而是要把画布倾空,将其清除、除净”[2]86,为自己廓清一块思想空间,这是一种退回混沌状态的“克诺西斯”修正性行为,在这一修正性行动中,发生了一种与前驱相关的“倒空”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重返虚空,而是从现实经验世界中的解放,从而进入一个非静态非固化的不断生成的混沌空间。“萨满巫师们在他们那可怕的整个入教仪式里返回到原始的混沌状态。他们的目的是最求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在非原始社会状态下,这种返回混沌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1]60混沌中存在着文明人难以想象出的异常强大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在混沌中自我被悬置起来,“自我”变成了“非我”,或者说是诞生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自我”,只有返回混沌,真正的创造才能发生。混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深度空间,事物彼此渗透侵越,成为一个没有限制的潜在性和诱发性存在。这种“混沌互渗”的状态处于混沌与复杂性之间,是一个虚拟的、无限的起源性水平面,是主体性生产的能量和物质水平面,体现了主体性的自我创生性和机器过程,创造了主体性生产的“存在之域”,具有时空上的延展性和异质的跨越联接性[6]。返回混沌不是清空日常现实中主观截取的部分,而是在取消界限和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将这些碎片还原成整体,还原成其原本所是的样子,在混沌里只有世界的发生和涌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混沌中的超越其实是一种现象学“朝向事物本身”[7]75的态度,一种现象学式的本质直观:直接领会事物所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不添加也不取消,在物我交融中让事物本身显现出来。哲学家亨利·马尔德尼认为塞尚的油画是从一种未经过理性处理的“混沌”中直接涌出来的,这是一种“最原始的眩晕经验”。[8]340同样,培根的画也来自于内心最原始深处涌现出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召唤”[2]68,充满无限的力量。他的画面是一种感觉的聚块,他通过一种本能的方式将这种感情意识形式化了,让他自身在画作中显现出来。培根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感觉化的描绘,用德勒兹的说法就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将手和眼调整到一种互不从属且相对独立的“触觉的视觉”状态下,“什么都看不见,就好像是处在一场灾难,一片混沌之中”[2]101,由此,才能赢得画布上与俗套之间的战役,创作出一个新的形象,所以,就作品本身来说,培根的画作是一种本能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形式的本能——如德勒兹所说的“触觉的视觉”状态,也是感情的本能。他的作品之所以在感觉的呈现这一方面被认为是独特而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从感觉到形式的转化本身,而更在于其所呈现出的那种感觉不是一种“俗套的”感觉,而是一种打破了“语汇表”的另类而刺激的感觉,它暴力、压抑、扭曲、是欲望的爆发,也是迷狂的疯癫,这是培根所采取的一种危险的“魔鬼化”的自卫机制,在一种情感的迷狂境界中实现了“灾难性平衡”[1]118。在这种情感混沌中,一切激情都成为模棱两可的存在,艺术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削弱的努力,他们放弃自身意志回到心理组织的先期阶段来探索一个更加丰富和陌生的本我,以便能够在伦理和本能的逼仄之中突围。
德勒兹将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定义为一种图解式(diagram)的,并认为这是对行动绘画的超越,而“图解就是一种混沌,一个灾难,但它也是秩序或节奏的萌芽。它是与既定形象相关的狂暴的混沌,与此同时,它也是与绘画中新秩序产生相关联的节奏的萌芽。”[2]102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图解是要引入“事实的各种可能性”[2]101,它打开感性的各种领域。塞尚说的“深渊”,克利说的“混沌”,消失的“灰点”,都指的是这个。图解的功能不在于表达连续的时空或是再现某种现实,而是为了构建一种将要到来的现实。它始终“先于”历史,在每个时刻它都构成着创造或可能性之点。[9]197图解是一个起点,是节奏和秩序的萌芽,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拓扑性,是反复和震荡的;这是一种不断并联和串联的根茎状态思维,总在越界,这样的异质联接总在产生新东西,具有极强的创造性,这种并置多样性,由不停跳跃引发“创造性混沌”的思想,与同时期的非线性科学发展具有某种隐秘的联系,与现代艺术思想也不谋而合,“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时讲几个故事,不同的观点保持分歧,各自指向完全不同的领域。分歧是连续的混沌,而混沌正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它肯定所有不同种类,将自己变得复杂,在几个基本系列之间,产生内在回响。”[10]51培根绘画时用上了木条、刷子、扫帚、破布甚至是点心袋,他既要获得一种原始的混沌感觉,又要用图解来限制它,在画面上留下操作感,显示艺术家的把控。“在培根的画作中存在一种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却隶属于一个精确的系统,它不是通过模糊来获得的,而是一个用清晰来毁掉清晰的过程。”[2]6这里面暗含着双重张力:一方面,它是一种解构性混沌与灾变,这意味着非确定性和解辖域,这股力量消解着任何再现与具象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解构的同时,这股力量又在重构一种秩序或节奏的萌芽,在绘画中表现为其建构性、生成性的可操作力量。前者是一种灾变与深渊,迷陷于终极混沌,走入极端则表现为波洛克的“行动绘画”,画面完全被凌乱、毫无意义的线条所攻占,这种毁灭性的力量过于泛滥以至于歇斯底里。而后者,抽象艺术在混沌世界之外,显得过于节制而冷静。培根在感觉式的描绘和引入图解之间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三条绘画道路,在混沌中一边解除确定性断言,消解焦虑带来的歇斯底里,打破创作中的定见和陈腐的形象,一边不停地生成新的秩序与节奏,完成艺术创作的超越。
三
布鲁姆在六个修正比中时常借用弗洛伊德的思想,但最后却背了离弗洛伊德,让诗人走上了义无反顾的弑父之途。在这一点上德勒兹与布鲁姆之间产生了某种默契,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将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在《感觉的逻辑》中却无意中呼应了布鲁姆的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批评,其中可以窥视到德勒兹与弗洛伊德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在强烈反叛中存在着不经意的认同。事实上,弗洛伊德仍然是德勒兹理论道路上不可绕开的存在,德勒兹对弗洛伊德的强力反叛正好证明了德勒兹与弗洛伊德之间的竞争关系,德勒兹也难逃影响的焦虑这个圈套,无法摆脱自己的俄狄浦斯式的困扰,我们甚至可以说弗洛伊德就是德勒兹要反抗的那个俄狄浦斯的父亲。
此外,布鲁姆批评的强烈主体性特征在德勒兹对培根创作分析中得到了拓展。影响的焦虑是创作中所必须面对的心理壁垒,焦虑的产生是因为自我的被遮蔽,这种遮蔽不仅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现实物质世界。艺术创作的意义就在于探索可能性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和扩展自我的需要,其中带有一种深刻的人类学关注,体现出作为一种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经验的特点。培根充满狂暴形式的绘画是一种以艺术形式表现出的哲学思考,面对影响的焦虑,他选择返回混沌,在混沌中消解了前驱、自我和现实,用一种现象学式的不断逼近事物本质的方法寻求到了独特的绘画节律,通过对“纯形象”的追求和对图解的把握运用实现了视觉的触觉化,完成了自我和艺术上的超越。
[1]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2.
[2]Deleuze, Gilles.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M]. Daniel W. Smith,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3]培根访谈录[EB/OL]. (2014-05-10) [2015-05-10].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517263.
[4]王敏.“影响的焦虑”背后的权利意志: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主体性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28-32.
[5]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501.
[6]Guattari,Felix.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M].Paul Bains and Julian Pefanis, (trans). 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82-83.
[7]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 [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5.
[8]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340.
[9]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97.
[10]Deleuz,Gilles. Plato and the Simulacrum[J]. Rosalind Krauss, (trans). 1983,27(Winter):45-56.
(责任编辑王婷婷)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nd the Transcendence in Chaos:On Deleuze’s Interpretation of Bacon’s Art
LIU Wen-wen1,2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WUT,Wuhan430070,Hubei,China)
Deleuze’s interpretation of Bacon’s painting contrasts finely with Harold Bloom’s poetic “Anxiety of Influence”. Bloom’s way is the powerful misprision to poems while Deleuze’s approach is returning to chaos and reappear from it. Superficially, they chose different ways. In fact, both of them put emphasis on the sam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how can artists get a breakthrough of themselves in the shadow of their forefather’s achievements and in a world filled with representations and predetermined experience. 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trong subjectivity in Bloom’s poetry can be expanded in Deleuze’s analysis of Bacon’s creation.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is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that must be fac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which not only comes from the tradition, but also from the real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carries a profound anthropological concern, which reflects the art experiences as a kind of spiritual universality.
anxiety of influence; Bloom; Deleuze; chaos; Bacon
2015-09-14
柳文文(1980-),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生,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比较文学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混沌美学与美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Ib-107)
J05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