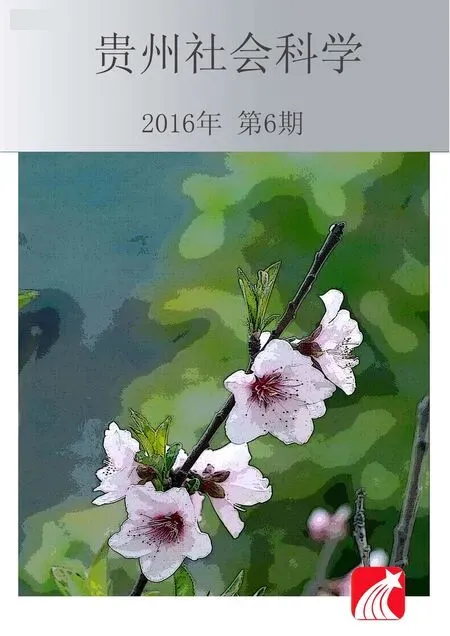包买制路径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贵州丹寨苗族蜡染为例
许江红
( 1.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2.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包买制路径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以贵州丹寨苗族蜡染为例
许江红1,2
( 1.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2.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贵州苗族乡村中蜡染的生产与流通中的包买现象比较常见。包买制下的的蜡染生产流通模式,以及该生产流通在地方苗族乡村文化脉络的“嵌入”机制,对蜡染的生产性保护与传承有重要意义。包买现象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潜在的风险性影响,有必要探索包买制路径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可持续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买制;蜡染;苗族
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以及相关政策与实施是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理论的探讨也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常见的议题。相关研究不仅梳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由来、特点、性质,也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的文化空间、族群的文化认同、文化意识、文化自觉等概念的联系,相关研究也涉及讨论国内文化遗产运动的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使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成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1,2,3]有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保护的操作规程、作业方法等提出建议[4],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的对策建议。[5]总的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视野开阔,议题丰富,但既有的一些研究还注重于类型学的描述,从工艺美学、民俗学的视角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其理论视角还有待拓宽,关于生产性保护的分析以及相关政策建议也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从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乡村中蜡染生产与流通中常见的包买现象入手,试图探讨包买制下的蜡染生产流通模式,以及该生产流通是怎么“嵌入”到地方苗族乡村文化脉络中来的,是怎么实现生产性保护与传承的,而其潜在的风险又如何。
二、传统的苗族蜡染与传承
贵州苗族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间工艺美术技艺,蜡染是其中的代表。苗族使用蜡染制品十分普遍,在祭祖、婚丧、节日等重大场合以蜡染为饰,生活中蜡染衣、裙、围腰以及其他棉织生活用品也随处可见。民族学家很早就仔细描述了苗族蜡染的工艺流程和美学价值:(蜡染)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图样色彩可以独出心裁,自由设计,……绘时神妙意匠,真令人感叹不已![6]该套工艺在苗族民间流传久远,历代传承。*2006年,贵州省丹寨县的苗族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类别为传统手工技艺,遗产编号Ⅷ-25。
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所有的文化因素,在根本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为满足社会中的个体之“生理上的基本需求”,然后满足“制度上的需求”(如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整合上的需求”(如宗教艺术等)[7]。在苗族传统社区,制作蜡染的用途既在于祭祖、婚丧、节日等重大场合,也为供应自己与家庭的日常使用,如与异性的情感交往、婚嫁以及后辈子女使用,也有用作于社区里、亲友间的馈赠或交换。苗族妇女手工制作的蜡染品大多是社区内部自给自足的生活用品,基于其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目的,以此视角看待苗族蜡染,可以发现苗族蜡染除了满足社区成员穿衣、审美等普通的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外,此外还具有文化认同、族群识别、社会关系维持等方面的作用。民族传统手工艺及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以身体示范、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手上的技艺,使其成为民族的文化遗产,呈现文化、表达价值,构成一种整全的文化象征。[8]苗族蜡染制作正是这样,由一代又一代年轻女性向长辈女性学习,蜡染制作技艺因而通过一代代女性的双手持续传承下来。
三、新时期的包买制
(一)从自产自消费用品到商品的蜡染
现代性是当代世界的根本性原因所在,任何民族概莫能外。台湾学者叶启政说过:自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尤其是亚非社会所经历的最显著的问题莫过于“创新迭现”,原有的文化传统一再受到挑战,其文化丛不时被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因新旧交加,使得既有的维系社群关系的基础产生动摇,生活方式也因而一再发生改变。波兰尼因而称此变迁为“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9]无疑,贵州苗族社区在过去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最近三四十年尤显剧烈)也毫不例外地处于生产生活巨变、传统面临推陈出新的大转型中。外面世界的文化走进来,苗族人走出去,苗族社区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苗族蜡染商品化的重大的驱动力。具体而言,这驱动力与两大类的苗族蜡染消费群体密切相关。第一类消费者是苗族本族群的消费者。他们多是年轻人,由于自小进入国民教育系列接受现代教育,缺失了传统乡土服饰制作的生活条件、闲暇、技艺习得的机会,很多人因而缺失制作蜡染的技能,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民族认同具有使用本民族蜡染制品的文化需求,其消费特点为民族文化的“文化消费”与“实用消费”或“生活消费”的统一。第二类的消费者是“外来消费者”。在苗族社区面临“现代化”的“早期”,很多艺术工作者,也有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境外人士,深入偏远乡村社区收购充满传统美学色彩的珍稀苗族蜡染;近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兴起,消费者多为对苗族文化有兴趣的外来观光客,购买的则多是带有苗族文化符号的当代手工艺品。他们的消费特点都在于基于“异邦”文化想象的“文化消费”、“符号消费”与“审美消费”。
(二)新时期的包买制
新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方式导致了苗族蜡染新的制作方式与流通方式的变化。苗族服饰(主要是刺绣的工艺的服饰)的市场化影响到了苗族蜡染融入市场的速度,在早期,将苗族蜡染变为商品的是以中介身份出现的贩运者(掮客),她们最早的收购是以“代销”方式进行的。以丹寨的掮客Y为例,村民们把“老衣”(老的蜡染制品)交给Y,她再把“老衣”带到凯里或省城贵阳转卖给上一级收购商。提取了自己的利润后,Y把余款支付给村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购的人越来越多,苗族蜡染制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古老的苗族蜡染制品越来越少。在宏观层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的变化,国家大力推动民族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包买商在这时应运而生。
包买制作为蜡染生产制作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在很多苗族社区涌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买制也称为“包买主制”,是以非正式契约、分散生产等为特点,在资本、原材料供给与成品销售等几方面,乡村手工艺者与包买主形成合作的一种手工生产模式。农户从包买商那里领取原材料,带回家中做成产品,然后交换给包买商,并从包买商处领取工资。在贵州一些苗族社区,目前有一些文化企业或商贩进来,采取“企业或商贩+农户”的包买制模式,给村民下订单、提供材料、按期收取产品、进行转销。包买制可以看做是小型手工劳作者与包买商之间自发的交易模式,是特定的乡村文化产业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包买制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换的方式,促进了家庭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增强了农户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使得手工生产能相对稳定并可续进行,是手工产品顺利加入市场竞争的根本。
丹寨的包买商YF,在村里成立了蜡染合作社,组织生产。她是个地方能人,20世纪80年代就因为手艺精湛,为国家领导人所接见,并经常出国参展,在此过程中,她销售自己的手工艺品,但是,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不可能满足庞大的社会需求。随着逐渐摸索出市场的需求脉搏,她在村里将村民组织起来,利用自己外部市场的渠道与信息优势,根据订单安排生产,给村民提供原材料,主要是蜂蜡和白布,村民制作好后交给YF,然后再组织销售,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另一个案例的N公司,老板不是当地人,早先是做布匹批发生意的,由于考察农村白布市场,发现苗族村民在白布上用蜡画出美丽的图案,发现到了商机,于是她与地方能人合作,开办公司,公司采用两种组织形式,一是招纳当地的妇女到县里的工厂集中生产,按件计酬;二是给村民提供蜡和白布,村民在家生产,赶集时拿到县里的公司,公司再给予报酬。在乡村熟人社会里,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寻找有蜡染技艺的人较难,她与本地蜡染高手YL合作,利用其人脉关系,克服信息阻塞,进而大大节约了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
包买制的出现,还可以从作为手工艺品的直接生产人——乡村妇女的生活世界来考察。尽管现代性对乡村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乡村的妇女们还未从传统的文化脉络里完全脱离出来,她们没有习得可以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和市场的能力。田野调查中,丹寨的一位乡村老年妇女说:“人家给我布和蜡我就画,不给我就不画……我是没有钱买布和蜡(来画蜡花)”。为什么会有甘于将自己的劳动力转让给包买商的现象?其实前述老年妇女所使用蜡画的原料钱并不贵。其一,她们的地方性知识里,一直不把蜡画(制品)当作“正当的”商品。她们不理解,单纯的蜡画制品有什么用处,至少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什么用处。一位妇女说,蜡染的布,做床单的,有个尺寸,做衣服的布,也是根据衣服的样式,但是对一块蜡画(制品),又不染,不知道城里人买去做什么。“好看、美观、值钱”这些概念是被外来者植入的。其二,她们对画蜡画获得收入的理解,就是认为得的钱是拿来贴补家用的,用于生活开支即可,比如给娃结婚盖房、买种子、买生活用品等,小富即安,至于“投资、钱生钱”这种理念,是没有的。其三,她们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乡村,没有地方能人那些通往外部世界和外部市场的渠道,因而也没有机会和勇气直接面对外部的未知的风险,只能依托乡村能人或包买商所营造的以乡村信任联系起来的合作社等初级组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包买制是适应城乡不同文化碰撞的连接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新模式,可以说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而这也是包买制能够兴起的原因。
四、包买制与生产性保护
(一)包买制与生产性保护的关系
苗族社区的包买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生产性保护在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原则下如何组织生产和销售的问题,使蜡染制品得以藉其文化符号走向市场,从而实现了蜡染这项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2012年2月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参见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官方网站《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http://www.mcprc.gov.cn/sjzz/fwzwhycs_sjzz/fwzwhycs_flfg/201202/t20120214_356522.htm国家主管部门界定的生产性保护主要针对传统工艺品、传统医药、传统美术等制作、炮制、创作工艺与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的保护性手段,旨在“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其原则为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以及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丹寨的蜡染技艺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传统技艺成为生产性保护的对象。如何实施生产性保护,贵州丹寨县出现的包买制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苗族社区在经历现代化的历程中,一方面,受到市场化的冲击,社区内部需求的萎缩,蜡染技艺传承动力衰弱,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外部市场需求又在扩大,而这个外部市场需求不同于社区内部的互惠需求。在新形势下,技艺传承者需要经历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制度来实现生产和销售。包买商向乡村妇女提供原材料——蜂蜡和白布,组织她们利用闲暇时间按传统的蜡染技艺进行生产。在此过程中,蜡染制品以商品的形式出售,从小习得的蜡染技艺得以传承,乡村妇女们的文化自觉和自我的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运转此一生产与流通过程的核心人物——包买商大多是本乡本土的地方能人*包买商里也有一些是与地方能人密切合作的外地人,他们对民族手工艺品与苗族文化非常熟悉。,许多是国家级、省级或县级非遗传承人,还有些虽然没有传承人的名号但也技艺精湛,善于创作蜡画制品。她们手上的技艺给了其与外面世界交往的平台,通过对外文化交流与市场交易的行动影响了乡村邻里,形成了示范效应。地方能人们不仅熟悉技艺,也往往充分利用其社会资本,对内整合社区资源,对外搭建销售平台。传统的蜡染制品原本是苗族社区自产自用的产品,面对外部的市场,地方能人会做产品形式上以及生产工艺上的改变。地方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村民的观念也受到影响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地方能人充当的包买商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村寨里普通妇女的市场接入问题。在熟人社会里的包买制有效地规避了市场中可能的道德风险以品质与熟人社区为基础建立的流通渠道,促进了销售的可持续发展。
大体来说,包买制的案例印证了:只有融进社会、融进民众、融进当下的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有真正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只有为民、惠民、利民,才会得到社区民众的支持和主动参与[10]。包买制作为一种特别的生产性保护手段,在蜡染原有的需求环境改变,蜡染消费市场的萎缩乃至消失,造成蜡染技艺传承动力衰弱,技艺传承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蜡染消费的外部市场,使技艺拥有者解除了面对市场的疑虑与风险,获得相应的酬报作为其家庭生计的重要替代或补充。技艺人在参与生产中为了高酬报与可持续酬报,自觉提升生产技艺并自觉传承技艺(给子女、亲戚等)。
(二) 包买制的意义
以往学者[11,12]对包买制的论述主要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论述,或者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证包买制在乡村手工业发挥的作用,从而论述乡村手工业在明清历史中的地位。以上的这些论述都很少谈论包买制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与当代地方社会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家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及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背景下,新的文化消费市场的出现,民族文化产业的兴起,包买制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将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首先,民族地区乡村手工艺与民族文化产业结合,民族文化中珍贵的传统技艺成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其传承也获得了很大的可能性。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手工技艺面临着困境,于是生产性保护提供的这种可能性使得传承得以有保障。因为较为有效的组织生产与销售,包买制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场、与生产两头对接的问题。包买商有效地掌控着产品质量,他们知道市场需要的是苗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这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工艺持有者画的内容很重要,她们生产的原料的环保性很重要,她们拥有的传统技艺很重要,这些是她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也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内核。包买制这种嵌入苗族社会的制度形式,没有脱离苗族社区文化,而是一种对苗族社区文化的适应,这种适应在生产中既保证了蜡染技艺的整体性、原真性,也在销售的过程中有效地降低了生产者面对市场的风险。在市场需求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包买商可以通过扩大或减少包买工人来灵活地适应市场。生产有了连续性,才能做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可持续性。
其次,通过包买制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方面的问题。所谓活态传承,主要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的环境中进行有效保护和传承,在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开展传承。活态传承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活态传承是区别于以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在当下市场化大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切实通过自身的重构满足市场的需求、为经济发展服务。蜡染既是苗族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制作技艺,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体现。把村民们耳熟能详的制作技艺、日常生活方式发展成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在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植入对其发展有利的成分,这是可能的,也会有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市场与社会的需求,就须不断加以调整和重构,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活态”传承与发展,否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极可能固化为博物馆里缺乏社会内容的藏品[13]。包买制作为苗族社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制度,有效地激活了蜡染技艺主体创作的积极性,将民族文化元素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赢得了市场,这种调整和重构,在唤起了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同时,做到了活态的传承。
其三,苗族社区兴起的包买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制度,对苗族社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到传承方式的变化,使传承方式更加多元化。过去主要是社区内部以家庭为中心长辈传给小辈(主要是母传女)方式,邻里之间相互学习。包买商往往借助社区内部熟人关系本身所附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展生产活动,围绕包买商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传统社区内部家庭、邻里之间的互动,甚至形成跨村落跨社区之间的一种雇佣关系。种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出现,使得技艺的传承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
(三)可能的风险
包买制在一方面确实在现实层面落实了生产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包买制的出现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形成了一定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期可持续传承产生了一定的非预期后果,进而产生一些可能的风险。
其一,社区的传统传承模式趋向瓦解与传承人消失。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苗族社区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苗族民众的生计以传统的农耕为主,苗族文化的传承也表现为高度的稳定性、保守性与整合性。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认为的,传统社会都立足于较低水平的相互依赖性和较高水平的地方自给自足性基础上。[14]包买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区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目前,市场对苗族蜡染制品的需求与以往相比有很多变化。在过去,苗族传统社区的蜡染制品主要是自产自用,供自己、亲人使用或馈赠社区内的其他成员。而现在,苗族蜡染制品已经走出本社区,在更大的市场里流动。这种市场需求形成了新的类似“大生产”的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中,往往出现资本宰制手工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被边缘化,蜡染制品所承载的社区内部原有的人与人的关系被改变和扭曲了。从微观层面来看,在过去,一位母亲历经数月劳作,生产了包含着辛劳、爱意与光阴记忆的,具有唯一性的、难于简单复制的蜡染制品;而现在,由于市场的驱动,蜡染制品成为换取货币的、包含无差别劳动的载体——商品。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低端市场的一般需求,原本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图案、工艺,往往被通俗的、迎合异文化想象的流水线图案、工艺所代替,进而逐渐消失。大量简单复制的图案或服饰,冰冷地反映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传统艺术“光韵”(Aura)消失的命运[15]。苗族蜡染制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由于传承人身份的扭曲、主体性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
其二,传承人的劳动异化。由于市场需求的驱使,手工制作已经和传统时代的制作有很大差异。包买制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资本、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等几方面将乡村手工艺者强加于对包买主的依附之中。[16]一般而言,包买制下的依附性经营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资本依附、原料依附、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双重依附。其中,在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双重依附的状况里,生产者往往变成为包买主加工产品的工资劳动者,他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也仅是为获取工资收入,丧失了生产的独立性。在贵州的一些苗族社区,目前就有企业与商贩采取“包买者+农户”模式向村民下手工生产订单,安排计划、组织材料、回收产品、进行转销。包买制下的手工艺人,其生产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非农化,为获取工资收入,围绕包买主的订单任务,陷于重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手工产品)的关系功利化、冷漠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趋势。包买制下的劳动异化,使得社区里以传承人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风险和黯淡的前景。
五、结语
文化产品的包买制通过其生产流通实践,较为有效地实践了生产性保护。在苗族社区,由于有效地借用了包买制这种方式实现了蜡染制品的生产、流通、销售,使得苗族社区蜡染文化得到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在生产中既保证了蜡染技艺的整体性、原真性,也有效地降低了生产者面对市场的风险,通过对技艺拥有者的酬报实现了可持续性。作为新的组织与制度形式,包买制是“嵌入”到转型期的苗族社会文化脉络中的。非遗的生产不仅仅只是物质的生产,也包括精神与文化的生产和传承,以及组织与制度的再创造。在苗族蜡染的生产性保护中,核心是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关键是包买制在苗族社区建立起来新的社会关系、组织方式与制度安排,在生产中实现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这是有别于传统的新传承方式。 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注意到,包买制背后过度商业化、雇佣劳动的异化对社区关系、文化传承带来的非预期后果与风险,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不容回避的议题。
[1]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15.
[2]彭兆荣,等.遗产的解释[J].贵州社会科学,2008(2):13-18.
[3]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5.
[4]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10.
[5]田艳.试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14(1):13-17.
[6]陈国钧.苗夷族的工艺——纺织与绣花.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北京市:民族出版社,2004:137-138.
[7]容观.关于结构功能分析——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之六[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4-16.
[8]刘红婴.世界遗产精神[M].北京市:华夏出版社,2006:177.
[9]叶启政.“传统”概念的社会学分析[M]//姜义华,等,编.港台与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
[10]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途径[J].文化学刊,2012(5):117-122.
[11]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9.
[12]傅春晖.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J] .社会学研究,2014(2):189-217.
[13]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J] .学术研究,2011(05):35-41.
[14]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83.
[15]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15.
[16]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32.
[责任编辑:明秀丽]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13BMZ047);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文化、市场与权力”(2016-xwd-b0304)。
许江红,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C957]
A
1002-6924(2016)06-088-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