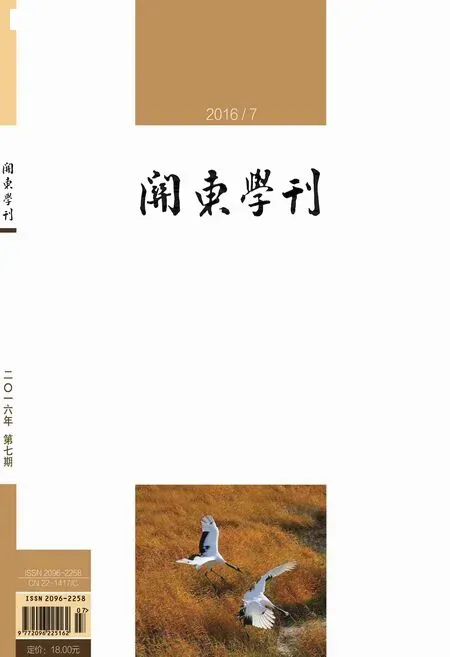刍议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解构运作
汪韶军
刍议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解构运作
汪韶军
《论文字学》是解构哲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德里达从“文字学”入手,提出分延、痕迹、替补等一系列概念,从内部瓦解了言语中心主义,消解了单一意义的神话,并进而欲击垮传统形而上学。解构哲学体现出一种无中心、无深度的削平特色,从而为后现代文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论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
《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是德里达的一部成名作,也是整个解构哲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本书中译者汪堂家先生称:“《论文字学》是德里达哲学的真正秘密。这里不仅隐含着德里达几十年来不断为之奋斗的哲学理想,而且展示了后来被他自由运用的写作风格和解读方略。”*汪堂家:《“解构”策略的可能性》,《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以树立自己解构的靶子,并提出一些关键概念,勾勒自己的解构理论;第二部分是其解构策略的运用和解构理论的展示。
德里达的写作风格艰涩难懂。为了理清他的解构哲学,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些问题:德里达的解构对象是什么?对象X为什么会成为他的眼中钉?他为什么要从“文字学”这一角度切入?他的解构策略是什么?解构之后是怎样一幅景观?亦即,这种解构哲学对哲学史和现实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德里达的解构工作是否成功?它自身有多大的合理性?
一、解构什么?
笼统地说,德里达的最终解构对象是西方几千年以来一直延续着的在场形而上学,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他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德里达认为,不仅是自柏拉图至黑格尔,“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页。海德格尔曾说,尼采尽管尖锐地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但尼采也未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因为他只是用强力意志置换了传统的相、是者、实体、上帝、物自身、理念等本体概念。而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其实也适用于他本人,原因在于他的存在哲学虽然解构了传统的本体论,却又建构了基本本体论,提出存在问题、真理问题和意义问题,要求思想听从存在的召唤,存在被当成符号的第一源泉和最终源泉,而这就是存在的逻各斯。因此,他的思想也不是否定,“而是重新要求将逻各斯和存在的真理作为第一所指。”*[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6页。德里达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接过接力棒,彻底打垮在场形而上学。
在场形而上学是一种本质论哲学,在它的视野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即经验的现象世界和超经验的本质世界或形而上学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地位上不是并列平行的,本质世界超越现象世界而又制约现象世界,它是现象世界的根据和意义之源。在场形而上学总是追求经验界背后的最高的本质性的东西,这被尼采指斥为一种异世思维方式。德里达也要破除人们的这种妄求。他有句名言: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我们也可以说,他把解构的矛头对准了这个“深度”。
二、寻找突破口
德里达选择了传统语言学中言语与文字的对立作为突破口。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他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最初意义是言谈,后来又被引申,用以指称原则、规律、道理、理性、上帝等。比如,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逻各斯”即指一种支配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则。由于逻各斯可以表示言说与思想两个领域,因此德里达用“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时指称言语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与在场形而上学。章启群先生指出过:“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哲学传统中以‘显现物’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章启群:《哲人与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在具体运用时,此概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对前面说到的两者不作区分,狭义的则专指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对哲学史的解构与对文字的反思不可分割,因为言语中心主义是产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源头,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体现(这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狭义用法)。“与表音——拼音文字相联系的语言系统是产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而这种形而上学将存在的意义确定为在场。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充分言说的时代,始终给对文字的起源与地位的所有自由思考,给整个文字学加上括号,对它们存而不论,并因为一些根本原因对它们进行抑制。”*[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59页。(着重号原书即有,下同)因此,德里达就从这个源头处开始,从被传统“存而不论”的文字学入手,来消解言语中心主义乃至传统形而上学。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的时代确立了能指(signans)与所指(signatum)之间、表达式与内容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它持一种工具主义,能指只是指向所指的一个指针,而且是一个不称职的指针;在拥有所指的情况下,能指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因此,逻各斯时代是一个完全抹去能指的时代。就言语与文字两种能指的关系而言,逻各斯时代又推崇言语而贬低文字。德里达回顾了文字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不幸遭遇。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文字一直是一个遭到贬抑和边缘化的角色。为意义和语言行为提供基础的只是通过语音将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统一体;而“文字、字母、可感知的铭文始终被西方传统视为外在于精神、呼吸、言语和逻各斯的形体与物质材料。”*[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47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也认为,言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文字只是第一能指(言语)的能指,只有言语才是语言学的对象(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仅限于表音系统,文字则被排斥在外)。不仅如此,索绪尔还谴责文字掩盖了语言的外观,认为与其说文字是一种外衣,不如说是一种伪装。总之,逻各斯的时代看重面对面的说——听系统,而文本退居到一种次要地位。言语被认为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而文字只起着次要的工具作用。
三、如何解构?
(一)从内部瓦解
德里达的策略是从旧结构中借取用于破坏工作的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人认为解构主义有一种寄生性,它反对从外部直接对抗传统,而主张从内部迂回曲折地加以瓦解,使它产生偏离,直至不知不觉中动摇其根基。具体运作是发现本文蕴含的自我瓦解的因素,然而通过能指游戏开启阅读的多种可能性,从而消解单一意义的神话。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的确如此,他说:“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能有的放矢。”*[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32页。
以索绪尔为例,德里达就是要将索绪尔与索绪尔本人对立起来,用索绪尔的语言来说出索绪尔没有说出的东西(这里的“索绪尔”可随意替换成他人或他物)。他接过索绪尔自己确立的两大原则——任意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但又抓住它们反过来批评索绪尔。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只是一片树叶的两面,能指是由所指派生出来的,二者之间有一种图画式的相似性。德里达则认为,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恰好可以用来反驳他自己:“我们应该以符号的任意性的名义不接受索绪尔将文字定义为言语的‘图画’……事实上,甚至在所谓的表音文字中,‘书写’能指可以通过一种多维网络来指称音素。”*[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62页。这里是说,一个能指可以对应多个所指,而一个所指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能指来加以表达,能指与所指并没有自然的依附关系,能指对所指并非是描绘式的直线反映,从而斩断了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针对言语中心主义对文字的偏见,德里达反驳道,文字不是符号的符号、能指的能指(替补的替补、中介的中介)。索绪尔将文字排除在语言学研究对象之外,是没有理由的。言语与文字谁也没有优先于谁的优越性,要说有什么先在的东西,那也只能是“分延”(la diffé rance)。这个概念是德里达组合区分(differ)与推延(defer)两个词而自造出来的,是德里达文字学理论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德里达曾说这是一个经济性的概念,因为它能同时包含两种近乎相反的意义:“分延产生它禁止的东西,使它导致其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09页。我们要结合他的“痕迹”(trace)概念来理解“分延”。德里达说,差别是语言学价值的根源,但是如果没有痕迹,就不能设想差别,痕迹可以说是起源的起源。“没有将对立作为对方而保留在同一物中的痕迹,差别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意义就不可能产生……纯粹的痕迹就是分延。……痕迹是感性丰富性的条件。虽然它并不存在,虽然它不是在所有丰富性之外的此在,但它的可能性先于我们称之为符号的一切。”*[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89页。“我们应该将痕迹的无目的的生成过程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理解为一种状态,理解为能动的运动,理解为动机的排除,而不是理解为既定的结构。”*[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70页。综合这些言论来看,分延可以说是痕迹的分延,痕迹是分延着的痕迹;分延与痕迹不是确定的内容,而是一个无目的的、无限的流动生成过程,是先于一切差别、丰富性、确定内容之前并使它们得以可能的纯粹运动。这样一来,传统语境中的言语与文字都是既成的差别,它们就没有先后、优劣之别。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先在并使其成为其所是的话,那就只能是分延(痕迹),分延才是其根据、其“本原”,是意义的生发机制。
当然,德里达是不会承认有所谓本原的,他要破的正是本原问题。德里达在强调痕迹相对于语言与文字的起源性意义之后,着力防范人们把痕迹当成起源,表现出一种“随说随扫”的特性。德里达说,既然痕迹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也不是所有感性丰富性之外的此在,它就不是什么起源。不存在所谓的起源,寻求起源本身就是在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痕迹是虚无,它不是在者(étant),它超越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时常使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107页。这就是说,痕迹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我们不能追问它是什么;痕迹只是一个自身无目的的无限生成过程,由于这种能动运动,一系列确定的内容和差别才被构造出来。“分延才是更‘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32页。“存在——神学”是德里达给传统形而上学安的别名。可见,他在破他之后又开始破我。这一步棋是他必须要走的,没有这一步,他就将重新堕入在场形而上学,哲学史上就会又多出一种新的以分延为本原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在前一步中,他说分延才是绝对的起源,这只是为驳斥言语中心主义而采取的权宜说法,并不表示他接受本原观念,相反,本原观念正是他所要破斥的。
(二)替补的逻辑
在全书的第二部分,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悲惨的热带》,特别是卢梭的有关著作进行了解构性阅读。他的策略是:“在不脱离卢梭原著的情况下……发现各种可能性,发现属于卢梭的原著,但不是由于他创造或发掘的意义资源,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动机,他宁可有意无意地中止这些东西。”*[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448页。即通过文字的差异游戏来开启阅读的多种可能性,发掘被作者所忽视、所压抑的不在场因素(文本自身的解构因素)。这种差异游戏是通过替补逻辑来实现的。“替补”(supplément)同样是一个经济性的概念,它的逻辑不是同一性的逻辑,因而能使我们提出相反的概念而又不至于自相矛盾。“这种替补能力成了语言的真正‘起源’或非起源。”*[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353页。“这种逻辑确保‘替补’一词或概念具有十分惊人的灵活性,以致句子的假定主词始终可以通过使用‘替补’说出多于、少于或不同于他想说的东西。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卢梭的作品,而且涉及我们的阅读。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周密考虑这种进占活动(prise)或意外事件:作者以某种语言和某种逻辑写作,他的话语本质上无法完全支配这种逻辑的体系、规律和生命……阅读始终必须关注在作者使用的语言模式中他能够支配的东西与他不能支配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作者尚不了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明暗强弱的量的分配,而是批判性阅读应该创造的指称结构。”“创造这种指称结构显然不在于……重新确立作者在与历史交流中确立的自觉自愿的意向关系。”*[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31页。在德里达看来,每个词的含义并不像一棵树那样,栽在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无限的替补过程宣告了所谓的确定意义只是一个神话。就这样,替补逻辑通过正在阅读的文字来摧毁文字。
四、解构之后的景观
我们看到,德里达已经颠覆了言语与文字的等级关系,解构了言语中心主义。进此一步,没有所谓的确定意义,有的只是分延、痕迹、替补等无尽的意义撒播过程(la dissemination)。由此,德里达完成了聚合到发散、单数到复数、封闭到开放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他否认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绝对权威,在他看来,作者所赋予的意义充其量只是众多意义中的一种。就这样,文字的现有词义被淘空开始隐退,新的意义不断被补充进来进行替代,文本变成了一个繁衍着多样性、可变性的意义之网,向着未来的阅读而常新。德里达认为,文本不过是痕迹的织体(tissu)而已,是包含差别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可以打上×,打×意味着在场只是个虚幻的影子,也意味着原义的偏离和消失。因此,文字是一种先验所指缺席的语言游戏。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差异游戏:“严格地讲,没有一种文本的作者或主体是让·雅克·卢梭。”*[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360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书本死了,作者死了,但书本与作者的死亡宣告的是言语的死亡,另一面则是文字史的崭新变革。
在传统视野中,文本就像一个漩涡,把读者卷着做向心运动。而在解构理论的透视下,文本则成了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深度的平面,它自身处在不断的裂变过程中;语言似乎不受人的控制,它自身就有无穷的能量和创造力。结构中各要素本来被看成是静止的、确定的东西,现在开始流动起来,变得那么飘忽不定;原本静止、封闭的整个结构也随之开始松动,转向无限的流动生成过程和开放过程。
德里达认为,既然文本不存在先在的确定的意义,那么任何寻求确定性的企图都将碰壁。对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来,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暗中作祟。以把握确定意义为特征的阅读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式阅读。
五、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德里达由论证一个词意义的不确定性,推导出一个句子乃至整个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个结论的得出看似水到渠成,但笔者认为,这个推导过程并不怎么严密,因为一个词的意义固然是不确定的,但与其它词结合使用时,意义恰恰就被限定了(当然不是限定得死死的);词与词之间相互掣肘,使得文本意义不至于过于飘忽、悬空。语词在上下文中获得一个相对确定的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语言现象的存在,显然会降低德里达解构工作的有效性。
德里达否认文本有所谓的确定意义,是否就意味着他否认文本具有作者所赋予的原初意义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文本诠释乃至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问题。笔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在“作者的原初意义”与“文本的确定意义”之间做出区分。事实上,德里达并不否定前者,他否定的只是后者,否定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绝对权威。“这种重复注释的阶段在批判性阅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这种承认和尊重,批判性创造就会盲目进行并且几乎会随意提出各种主张。”*[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231页。由此可见,德里达也认为作者的原初意义还是存在的,只是在解构式阅读下,文本的意义才开始像种子一样撒播开来。如果德里达否认作者的原初意义,那么从逻辑上说,他就不能说他的批判对象就是像他所指斥的那样,他的所有批判就会因此而失去对象,成为无的放矢。
德里达以“文字学”为突破口,最终是要摧毁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言语中心主义在他眼里只是“小刺”,他是要借此拔除隐藏在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根“大刺”。然而我们可以置疑,单在“文字学”的层面上是否就能彻底批倒传统形而上学?对话语、哲学陈述的语义学分析和批判性阅读,是否就能批倒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为,言语中心主义虽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批倒言语中心主义并不等于批倒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而这一工作德里达主要是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完成的。
有人比喻说,黑格尔之后,传统形而上学就像一只待宰的老羊,一直在被质疑、被批判。这里将尼采与德里达做一简要比较,以便进一步认清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他们两人分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头一尾,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抨击在众人之中都是最为激烈的,都造成了一次“地震”,使人们面临一个无底的深渊。但他们的批判又有各自的特色: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他的策略似乎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把整个传统颠倒翻转过来,德里达则是消解一元中心论,不再制造任何新的中心;尼采处处强调不平等的合理性,尤其反对以高就低,德里达则力图否认有所谓高低差别,他要通过一提一按将两方拉平。赵敦华先生就此分析道:“‘解构’不是颠覆,不是颠倒双方的位置。否则的话,那将导致文字中心主义或非理性中心主义,引起新一轮的哲学对立。解构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认任何名目的优先地位,消解一切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页。,“‘补充’的逻辑并不肯定补充物具有压倒原初存在的优越性,它只是对‘原初’的中心地位和‘补充’的边缘地位的解构;解构之后,中心和边缘的区分和对立不复存在。”*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306-307页。德里达与尼采的解构风格也很不一样,尼采就像一团火,几乎不用理性的推理论证,就从外部直接断言传统形而上学的非法,而德里达则是冷静的,他深入到传统的内部,在暗中将传统的根基蛀空,就是说,他揪住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一些观念将其贯彻到底,使其走向反面,从而自行坍塌。
解构主义批评的还不仅仅是传统西方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批判。它要向社会、向制度、向顽固传统宣战。解构哲学把一切夷平在一个平面上。正是由于这种无中心、无深度的削平特色,引发了价值观领域的革命,使它成了后现代思潮的哲学基础。解构哲学蕴涵着巨大的颠覆力量。章启群先生形象地将德里达比喻为西方文化中的“孙悟空”:“他把西方传统的价值、理念都颠覆了,把西方传统的世界秩序砸了个稀巴烂。”*章启群:《今天是什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解构哲学是与多元、开放社会相适应的。如今,“解构”和“消解”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但有人往往有意无意地滥用解构精神,借解构的名义来自壮,为感性冲动张目。后现代文化中充斥着太多滥俗的东西,更多的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便是明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解构是否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客观地讲,解构不是简单地毁坏和颠覆,而是清淤。就言语中心主义而言,德里达明确说过,他不是要抛弃音位学,而是要抛弃音位主义:“解构这一传统并不在于颠倒它,也不在于宣告文字无罪,而在于表明文字的暴力为什么没有降临到无辜语言的头上。”*[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第50页。可见,他是要超越价值判断来看待文字。解构不等于一往不复的破坏,不能等同于历史虚无主义,其批判并没有上升到对整个西哲传统、整个西方文化的彻底否定,德里达回答卡昂(Didier Cahen)提问时所说的一段话亦可为证:“我当然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者破坏。”*[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子项目“海南文化软实力科研创新团队”(01J1N10005003)。
汪韶军(1973—),男,哲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口 57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