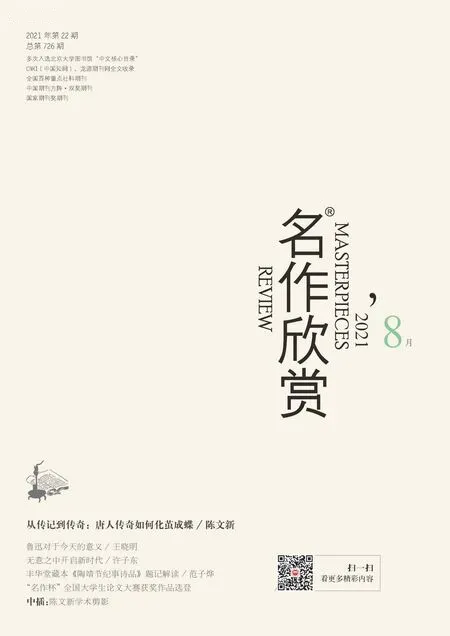探寻情爱秘径的“异域”旅程
——评鲍贝长篇小说《观我生》
河北 李浩
探寻情爱秘径的“异域”旅程
——评鲍贝长篇小说《观我生》
河北李浩
《观我生》写下的是一次行旅。在这个充满着神秘、陌生、冒险、故事、爱欲和轰轰烈烈的牺牲的旅程中,作家鲍贝更赋予它柔性却开阔的波澜,在道来的娓娓中时见惊心。它让人不由自主地跟随,甚至有些急于发问:下面会发生什么?迎接他和她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她和他,会寻到真正的安妥么?……我用两天的时间将它读完,然后,重读。
单身的富家女,年夜的个人旅行,神秘之地不丹,机场的邂逅和搭讪,恋和爱的故事……《观我生》具有流行小说的一切质地,没错儿,它具备强烈的流行性,它更会成为某个年龄段少女少男们获取经验和滋养的必读书。在许多的点上,它都会让他和她们踏入到一场陌生而惊异的“经历”之中,并会将自己对应地在故事中放置——这是一个陌生人的陌生故事,同时也是他们和她们的。他们在故事中照见自己以及自己的可能,就像许多人在阅读《红楼梦》时的经历一样。我指认《观我生》的流行性并无半点轻视之意,而是确认:它流畅好读,时时有惊奇,并具有某种适度的华美之感。还有一点,它在故事上的吸引力不容忽视。鲍贝在故事上明显是走心的,但文字中,却不显得用力。
“不够顺利”的旅程让“我”和那个化名Frank的藏族男子开始了共同的冒险,这时,另一个故事插入了进来:僧人哈姆的情感经历。他如何入寺,如何开始了情爱,如何被这份情爱带入到都市的世俗红尘中,又如何自处,如何得知真相,如何成为……“我”和Frank一边在异域找寻这个“哈姆”,一边体味和见证着不丹这一异域中的风情与宗教意韵,共同经历、经验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历险”。它们吸纳,敞开,抗拒,沉痛,虚无,故事在波澜中渐上高潮。而此时,并行的那条故事线也起伏得更加激越,只会诵经的哈姆没有融入世俗社会的能力,而哈姆深爱的女人原是被人包养的“情人”,此时,这个女人已经怀上了哈姆的孩子……用“套盒”的方式将另一故事插入并共同前行在以往的小说中已有前例,鲍贝在使用这一方式叙述的时候却让它再次生花,并有了自己的样式:在小说的第284页,Frank(此时他用另一个名字,贡布)向“我”承认:哈姆是我。那么Frank讲述的哈姆的故事也就是Frank的经历——平行的故事在后半段合成一个,但它并不结束。旅程还在,故事还在,你们发现在故事的合流处波澜更加壮阔,而新的支流又从中生出。更有意趣和精妙感的是,当Frank与哈姆的故事合流之后,我和我父亲的故事又一次与之合流,哈姆深爱着的女人也一样……这个Frank(或者贡布,或者哈姆)带着酒意再一次说出:“哈姆是哈姆,我是我,哈姆是我,我亦是哈姆。就如你是你,我是我,你亦是我,我亦可以是你。”这段带有酒意的话里面包含深意,抛却其中更为复杂的禅意,我以为它也是说给它的读者听的:这,既是一个他者的故事,同时也是你和我的故事。它,需要我们细细思考。
从杭州至不丹。书中,鲍贝用散文式的笔触描述着不丹的风物、人情、异域感——它有足够的魅力,甚至,让“我”产生了去不丹旅行的冲动。然而鲍贝的着力并不在此,她“创造”一个具有流行童话式的故事的目的并不在此,在这篇故事精彩、富有魅力感的小说中,鲍贝更倾心于和我们探讨情感的可能和“救赎之路”。不丹,在小说中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异域,多少也是精神上和宗教上的,因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旅程也就有了更多的复杂意味和精神指向。她设置,哈姆是一个曾经的僧人,这就给他的身上直接打下宗教的烙印,让他在其中,出其中,再入其中。她设置,“我”有一个重复又不停前行的梦,在这个梦里,“我”有一个心心相依却又有距离的“他”,“他”有一匹马。她设置,哈姆的女人死在前往加噶多加寺的路上,连同她肚子里的另一条生命,在偶然和有意之间。她设置,那个哈姆,或者Frank或者贡布,和他的伙伴们选择在虎穴寺的悬崖上了结一生,带着罪恶或眷恋。“为什么贡布已经不会再爱,他把他的爱都施予了谁?”
对了,“我”应当说出,小说中哈姆的女人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塞壬。它是情和欲,是水做的诱惑,是由在爱情中受伤自溺的女性化身而来,因此,爱和欲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原罪”性质。在轰轰烈烈之后,当他和她面对“现实”,就有了厌与弃,于是就有了别和离……它有着不得不面对的宿命,这份宿命,针对所有的人。在小说中,鲍贝近乎不懈地赋予情爱以火焰和炫目的美感,又在之后让它沉入更大的孤独和虚空之中。“我仿佛在听一曲爱欲狂喜与死亡呻吟的乐章与佛教曲的二重奏。”
“就如走在这条赎罪的道路上,没有什么罪是不可以被原谅的。生与死,爱与恨,俱在一念之间。”“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一个个都是无比虔诚的佛教徒。但我又觉得,他们却都做了佛教的叛徒。也许,这么多年的经历,已让他们明白,宗教似乎无法自救,亦难以解救任何人。只有死亡,方可以让他们确信他们活着。当他们纵身一跃跳下悬崖的瞬间,也许体验到了一种永远存在的牢固。”“或许,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看得见死亡有张漂亮的脸。而现实中的生命,却常常丑陋卑贱、不堪入目。”鲍贝在《观我生》中如是说。她说得真切,漂亮。然而,救赎仅有这一条通向往生的道路吗?它是道路么?永远存在的牢固又是什么?鲍贝对此或有答案,她将自己的清晰和疑惑,将自己的忐忑和叹息都贮含在她的文字中。
小说中,“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女子,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参与和经历着其中的轰烈感,这个“我”,还要回到旧生活中,按某种的部就某种的班,有了这样一番经历之后这个“我”也许不再是原来的“我”。当这个“我”,将贡布留下的储蓄卡塞入自动取款器时,又将经历的是……
作 者: 李浩,现为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长篇小说《如归旅店》,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