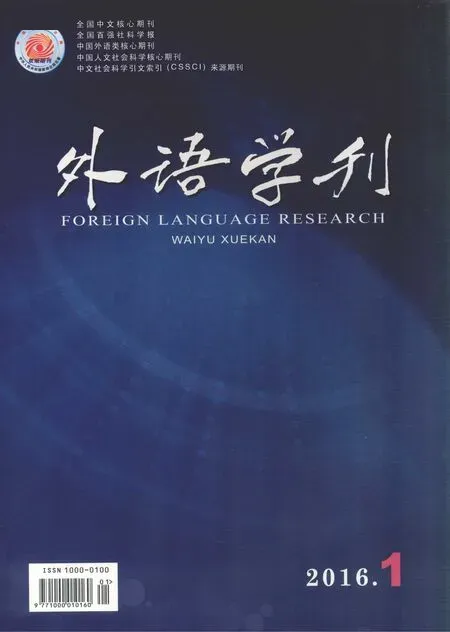近现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汉语词汇借用*
张天宇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117)
近现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汉语词汇借用*
张天宇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117)
词汇借用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类型之一。本文以《牛津英语词典》为标准,探讨近现代中英语言接触如何触发并影响英语对汉语词汇的借用。分析发现,近现代中英语言的接触总体属于“偶然接触”和“强度不高的接触”,因此英语中汉语借词多为非基本词汇,同化程度不高,借用形式多样;其主要借用机制是语码转换、语码选择和“协商”;借用动机是填补语言系统的语义缺项和强调借词背后的中国文化身份。
语言接触;词汇借用;借用动因;借用机制
英语的全球传播使其与很多语言都产生不同程度接触,从中借用大量外来词汇。这种“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贯穿着英语发展的整个历程。奥托·叶斯柏森曾说,“整个英语语言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借词组成的链条”(Jespersen 1982:67)。中英语言的直接接触有近380年的历史,早期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接触的制约,英语中汉语词汇的借用并不多见。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世界最大的两门语言的持续界面逐步展开。本文以《牛津英语词典》为标准,探讨近现代中英语言接触对英语中汉语词汇借用的影响及其借用机理。
1 中英语言接触引发的词汇借用
词汇的借用伴随着文化交流。由于早期中国与外界没有直接接触,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词汇silk,China,sino,tea等都是随着贸易的辗转间接进入英语的。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最早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silk是在公元888年经丝绸之路由拉丁语sericus和希腊语seres进入英语。China这个词源于印度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指华夏,原义为“智巧”。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称中国为Cathay. 秦朝的“秦”字进入拉丁语变成Sinae,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古希腊、罗马等把中国称为Serice,即“丝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古罗马人称为Serice和Sinae的人是同一个民族,马可波罗称为Cathay的国家和Cina所在地理位置相同。后来China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统一称呼,Sino则成为英语的一个构词成分,表示中华民族或汉民族,如sinological(汉学的)、Sino-Tibetan(汉藏的)、Sino-Soviet(中苏的)等。 Tea最早出现在1601年,是厦门方言,由葡萄牙人从爪哇带到欧洲。明朝中叶以后,贸易往来使中英语言直接接触,表示中国食品、度量单位、货币等与贸易相关的汉语词汇开始进入英语,如 ginseng(人参,1691)、samshu(烧酒,1697)、longan(龙眼,1732)、ginkgo (银杏,1733)、ketchup(番茄酱,1711)、sycee(银锭,1711)等。马礼逊的到来开辟中英语言交流的新纪元,中西交流从物质文化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表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汉语词汇被带到英语中,如 kuan(官,1814)、Confucian(儒家的、孔子的,1837)、Taoism(道教,1838)、 cumshaw(感谢(闽南语),1839)、kylin(麒麟,1857)、yamen(衙门,1858)、yin & yang(阴阳,1893)等。鸦片战争使得 yen(瘾、渴望,1908)、yen-shee(烟屎,1912)等词语进入英语。近代国外的华人劳工生活艰辛,他们为了消磨时间经常会参与赌博游戏,fantan(赌博游戏的一种,1878)进入英语。辛亥革命将 SunYat-senism(三民主义)等词带入英语。新文化运动使得 Pai-hua(白话文,1923)、mahjong(麻将,1920)等进入英语。民国时期的中西方交流空前深入,使得汉语借用词汇的数量和语义场迅速增长。
词汇的借用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所关注的“借词”。萨拉·托马森和特伦斯·考夫曼将“借用”定义为外来成分被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并入该语言社团的母语:这个语言社团的母语被保持,但由于增加外来成分而发生变化(Thomason, Kaufman 1988:37)。唐纳德·温福德将“词汇的借用”定义为一个语言社区世代保持其母语,但借用外来语言的词汇和结构特征引发语言接触性演变(Winford 2003:11)。可见,词汇借用后将受到受语系统的同化和使用频率的筛选,最后才能进入权威的英语词典,我们称之为“词典借词”。换言之,词汇的借用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结果是“词典借词”。因此从“词典借词”入手能更准确地看到语言接触对词汇借用的影响。
根据爱娜·豪根基于语言层面对于借词范畴的归类(Haugen 1950:220),以《牛津英语词典》为标准,按照借用过程中对汉语语素替换程度递减的顺序,英语中汉语借词类型可概括如下:
1840-1949年间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共有200个,其中名词193个,占96.5%;动词5个;形容词2个。这与托马森的等级理论(Thomason 2001:70-71)完全吻合,即“偶然接触”的词汇借用只有非基本词汇;“强度不高的接触”的词汇借用多为功能词(如连词及英语then这类副词性小品词)和实义词,但仍属于非基本词汇。从同化程度来看,早期借入英语的词汇已经高度同化,读音和书写都更接近英语,并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比如tea传入英国后很受欢迎,tea既指“茶叶”又指“茶树”,还指喝的“茶水”、“茶点”、“茶会”;作动词指“喝茶”、“吃茶点”;派生出复合词teaer“喝茶的人”、teaette“沏茶勺”、teaey“浓茶的、像茶的”等多达190余个。Silk借入英语后派生、复合、功能转换组成的词有65个:silk作名词表示“丝”,作形容词指“丝的”,作动词表示“玉米抽穗丝”,派生 silked(穿似的、蒙丝的)、silken(丝制的)、silkly(有光泽的)、silkiness(柔软光洁)、silk+nouns(41个)、silky+nouns(15个)。China在英语中的派生词更多,Chinese(汉语、中国人)、China+nouns(61个)、Chinese+nouns(128个),如果再加上China和Chinese作为第二成分的复合词,China的派生词可达到200多个。近代传入的 yen(渴望)和现代的 Maoist等词同化程度也较高,但多数汉语借词属于必要借入,其屈折变化和派生现象很少,呈现的同化程度不高。(Jiang 2009:90-106)
借词的语义场分布与语言接触领域相关。按照加兰德·卡农提出的19个语义场的分类标准(Cannon 1988:3-33),其中艺术50个,饮食与炊具27个,语言及书写18个,政府与政治17个,娱乐11个,人种11个,宗教和哲学10个,度量衡10个,动植物9个,朝代7个,社团组织4个,服饰4个,社会地位及职业3个,武术2个,地理2个,医药1个,其他14个。从语源角度来讲,作为源语言的汉语,可以分为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用语,它的前身叫“官话”,是汉语诸方言中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除此之外,汉语还包含北方方言、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语等10种方言,其中以闽南语和粤语使用较广泛,方言作为汉语的变体在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都与普通话有相应的差别。近现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词音译借词34个,其中包括乐器如 erhu(二胡,1908)、paiban(拍板,1884)、se(瑟,1874);青铜器如 lei(罍,1929)、ting(鼎,1904);瓷器如 Ko(哥窑瓷,1882)、meiping(梅瓶,1915)等,全部来源于“官话”。1637年英国舰队登陆中国开始贸易是在澳门和广州一带粤语使用区,加之由于早期移民到英语国家的中国人多来自广东和香港等粤语使用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海外以开餐馆为生。近现代时期英语中有关食物的汉语音译借词有16个,其中源自粤语12个,疑似粤语1个,占81.25%。
从借用形式来看,由于早期没有将汉语转化成罗马字母的标准体系,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西学奇迹》、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以及后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麦杜思(Medhurst)的《汉英字典》等都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1859年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制定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又称威式拼音,并于1867年开始推广使用,现代时期成为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直到1958年我国统一汉语拼音方法。分析中发现,近现代时期威式拼音形式借入的词汇比例很高。近现代时期英语中汉语音译借词有122个,其中可确认的拉丁拼法词汇占30个,威式拼音占67个,疑似9个,占54.9%。
2 英语中汉语词汇借用机制及动机
借词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些特殊的程序让外部语言的成分进入一种语言”(Thomason 2001:129)。针对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托马森提出7个主要机制: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被动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协商(negotiation)、第二语言习得策略(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trategies)、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bilingual first-language acquisition)及蓄意决定(change by deliberate decision)(Thomason 2001:129-156)。其中,语码转换、语码交替和协商是中英语言接触过程中的汉语词汇借入的主要机制。
语码转换指的是同样的说话人在同样的会话里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成分。在发生语码转换的会话中,发话人和受话人往往都是双语者。语码交替指同样说话人跟不同的交谈对象(通常是单语人)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吴福祥 2007:3-22) 语码交替也发生在双语者身上,但双语者往往在一类环境里使用一种语言,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环境里使用另一种语言。李楚成的研究表明,在香港社区的交流中粤语与英语之间存在语码转换,在形式上以粤语/中文为主,当中插入英语单词或词组,这种语码转换已经成为大部分香港人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楚成 2003:13-19)。语码转换与借用之间是一个连续统,当一个语码转换的词汇使用越来越频繁,直至成为受语系统内部的一个稳定成分,并被新的学习者学习,那么它就成为借用成分。
协商指的是母语为语言A的说话人改变语言模式以接近另一语言B的模式。在协商导致语言演变的情形里,发起这种变化的语言A的说话人可以是完全的双语者(语言B流利使用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的双语者(不是语言B流利使用者)。在最极端的双语者的接触情形里,如果语言A的使用者和语言B的使用者均参与“协商”过程,那么结果将是两种情形:或是语言A和语言B都发生改变,或是产生一种全新的语言C(吴福祥 2007:3-22)。 “洋泾浜英语”作为中英语码混合的产物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形下产生的。在勃姆(Bohem)的《来自贵族的军队》(OftheNobelArmy)中记载了女主人公——一位中国妇女使用的一段“洋泾浜英语”:You no go outside!(You can’t go outside! / 你不可以出去);You go outside, you quick die(If you go outside, you will be killed at once. / 如果你敢外出,你就会被打死。)(马伟林 2005:191-193)。可见,“洋泾浜英语”没有标准的语法体系,常常将汉语语法、粤语方言的发音等因素带入英语。但这种“破英语”在中国近现代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汉语词汇融入英语的主要渠道之一。如当代英语中的习惯用语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明显留有洋泾浜英语的痕迹。美国人列文森评价“洋泾浜英语”的作用时指出,“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它的词汇”(Levenson 1965:134)。
这些演变机制发生的原因,也正是英语中汉语词汇借用的动因。尤里埃尔·怀恩莱希将其概括为“需要论”(need)和“声望论”(prestige)(Weinreich 1953:57)。即从语言内部的因素来讲,借用是语言系统需要一些特定的词语来指称新事物,而从语言外部因素来讲,如果一种语言被公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那么使用者很可能从中借用,以彰显自己的学识和社会地位。豪根将其进一步阐述为:由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的借用是一种带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的借用,反之则往往是一种必须的借用(Haugen 1956:210-31)。在近现代中英语言的接触中,汉语相对于英语一直属于弱势语言,“必须借用”占据借用的主要动因——即填补语言系统的语义缺项。语言系统内部存在借用的潜在机制,即不同民族的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出现“词汇空缺”。在食品、传统艺术等语义场的借用中,这个动机表现比较明显。对于中国特色的食物或传统艺术如 chowmein(炒面)、towcok(豆角)、so-na(唢呐)、wu ts’ai(五彩)等,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表达,甚至很难简洁地形容,直接借入则最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此外,强调词语隐含的中国文化身份是汉语词汇借用的社会和心理动因。“文化身份”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即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它包括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英语中汉语借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是母语语言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受语对源语文化认同的体现。由于不同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差异,借用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也有所不同,如早期移民英语国家的华人多靠苦力生活,他们语言不通、技能缺乏、找工作很难,Chinaman’s chance被译为“微乎其微的希望”或“毫无希望”;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嘲讽,koutou(叩头)隐含有“自己毫无主见地服从别人的意见”的意思。近年来,英语中汉语词汇的借入出现音译回流现象,即直接以汉语拼音形式借入,如guanxi(关系)、hongbao(红包)、ganbu(干部)等直接取代relationship, red pocket, leader频频出现在英文媒体中,其原因在于强调词语背后所指的“中国特色”。近年来英文报道中提到中国的高考,都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aokao(高考)。与西方国家不同,“高考”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概念,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在符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保护公民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使得高考在中国的人才选拔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上个世纪高校招生数量相对较小的情况下,高考甚至成为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机会。因此,中国的高考用“gaokao”更能够准确地表达其涵义。
3 结束语
中英语言的接触历经“间接接触”(接触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语言接触,常表现为通过其他语言或翻译实现)和“直接接触”(接触双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分离的语言接触)。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中英语言接触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近期美国的专门跟踪世界语言的权威机构“全球语言检测中心”统计,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数量领先,以5%-20%的比例超过任何其他语言来源。世界最大的两个语言的持续界面正进一步展开,而借词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丁思志. 香港-语言接触的实验室[J]. 青海民族研究, 2013(24).
李楚成. 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35).
马伟林. 中国皮钦英语的历史地位[J]. 学术界, 2005(2).
吴福祥.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 民族语文, 2007(2).
袁 咏. 社会变化与语言接触类型及变异探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14(5).
Cannon, G. Chinese Borrowing in English[J].AmericanSpeech, 1988(63).
Haugen, E.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J].Language, 1950(26).
Haugen, E.BilingualismintheAmericas:ABibliographyandResearchGuide[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56.
Jesperson, O.TheGrowthandStructureoftheEnglishLanguage[M]. Oxford: Oxford Press, 1982.
Jiang, Y. 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J].WorldEnglishes, 2009(28).
Levenson, J.R.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Thomason, S.G., Kaufman, T.LanguageContact,Creolization,andGeneticLinguitistic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Thomason, S.LanguageContact:An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Weinreich, U.LanguagesinContact:FindingsandProblems[M]. The Hague:Mouton, 1953.
Winford, D.AnIntroductiontoContactLinguistics[M]. Oxford: Blackwell, 2003.
LexicalBorrowingfromChineseinEnglishinModernTimesfromtheLinguisticContactPerspective
Zhang Tian-yu Zhou Gui-j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Lexical borrowing is one of the contact-induced linguistic changes. Taking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as a corpu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ntac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has resulted in and influenced the lexical borrowing from Chinese in English language in modern times.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eral level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ntact is accidental contact and low-frequent contact, which leads to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xical borrowing: non-basic vocabulary, part assimilation, different source languages. The main possible mechanisms via which borrowings occur are code-switching, code-alternation and negotiation. To fill in the lexical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o mark the Chinese identity are the motivations for lexical borrowing.
language contact; lexical borrowing; borrowing motivation; borrowing mechanism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社科重点培育项目“英美语言政策与英语全球化历史进程研究——我国语言文化推广的借鉴与反思”(15ZD012)的阶段性成果。
H039
A
1000-0100(2016)01-0054-4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1.010
定稿日期:2015-08-29
【责任编辑孙 颖】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