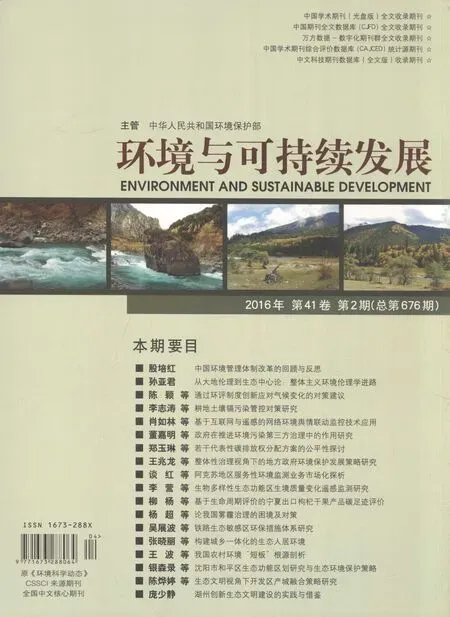从大地伦理到生态中心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进路
孙亚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从大地伦理到生态中心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进路
孙亚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作为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克里考特在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基础上,从价值层面、情感基础及实践原则方面夯实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以“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关注的生态中心论对于现实的环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在上述三方面的进路,并考察了其理论的内部张力及实践可能。
【关键词】利奥波德;克里考特;生态系统健康;截缩内在价值;实践可能
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被视作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1]在当代的继承。在克里考特[2](p8)看来,大地伦理的革命性在于伦理关注的两个转移:即从个体向整体、从社会内部向总体环境的转移。然而,国内以往的研究大都笼统地把克里考特的工作视作利奥波德思想的细化,这不免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既需要价值层面的阐明,也需要情感基础的支持与实践原则的建构。以上三方面的阐发(利奥波德是基本空白的)体现了克里考特的思想的重要性,而他的生态中心论也标志着整体主义环境伦理的真正确立。基于此,本文从价值层面,情感基础以及实践原则三个方面对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做了考察,并讨论了其理论张力与实践可能。
1价值可能:描述与规范的统一
1.1截缩内在价值
在克里考特看来,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上体现了笛卡尔之主客二分[3](p307),而存在之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区分在于其是否依附意识[3](p358)。在价值论上,现代哲学体现了休谟的事实-价值之分野[3](p80-81),而作为第三类性质的价值乃是第一类性质之于意识(consciousness)的效应。以此,价值需由主观赋予而不能客观地存在[3](p16)。
某物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是属于其“本质上天然或构成”的价值[3](p247),又意味着它可被内在地赋予价值,即为其自身(以自身为目的)而赋值。基于此,克里考特[3](p224)提出了“截缩内在价值(truncated intrinsic value)”的概念:即我们赋予某物的“为其自身”的价值,即使它不具价值于自身之中。因此,这种价值是非人类中心的(nonanthropocentric),但不是非人类源生的(nonanthropogenic)或者至少不是非脊椎动物源生的(nonvertebragenic)[3](p224)。这里的“不具价值于自身之中”,显然是针对基以意识的赋值过程而言的;例如:一个无意识的生命体具有自身的善恶(如新陈代谢的正常与否),却无法为自身赋值,它的为其自身的善成为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经由(其他)具有意识者赋值。
可见,克里考特[2](p151)认为,在现代主义框架下的内在价值(或广义上的价值)包含两层意义:其一,价值的激发过程须由主体的意识赋予[3](p248)。关于“意识”的内涵,克里考特虽未精确地界定,但他指出“由于非人动物,至少所有的脊椎动物,是有意识的,因此在宽泛意义上可以被认为具有赋予价值的能力”[3](p224)。因此,克里考特所谓“意识”的最底层面大体可与感觉(sentience)互通,而并不为人类或具有自我意识的高级哺乳动物所独有。其二,价值的终端载体可以是非人类的自然实体(包括物种、群落与生态系统等),后者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即内在地蕴含自身的“善”。在克里考特看来,这种“善”指向的是“健康(health)”[3](p295)。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1)健康是什么?(2)为何健康本身是好的?
1.2生态系统健康的价值意味
对于“健康是什么”,克里考特引入了生态科学之于伦理学的启示:健康,已从“无病症检出”的状态转向生物体与环境互动中的一种理想生存方式,即康乐(wellness or well-being),后者是“人类健康的一种生态学理解”[3](p290;297-298)。进而,克里考特[3](p362)认为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是“一种生态系统中互相联系的过程与功能的正常状态”。特别地,克里考特[3](p296)总结了五项生态学健康的客观标准:即生物生产率(biological productivity)、本地物种多样性(local species diversity)、全球物种多样性(global species diversity)、种群内部的基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populations)及生态功能(ecological functionality)[3](p296)。虽然具体指标的精确性有待完善,克里考特的整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进路是明确的。
“为何健康本身是好的”的问题面临着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困境。为此,克里考特[3](p355-356)借鉴了纳尔逊(Nelson)[5]的分析,后者认为一些道德概念,如背叛、智慧、健康等,是蕴含着价值意味的“重”描述符(“thick” descriptors),即它们既是描述符,同时又是规范符。作为描述符,在本体上它们是客观的对象;作为规范符,又带有“善”的伦理负荷从而与主体的道德实践指向相涉。以此,纳尔逊[5]认为重描述符是“不可分割的完形(indivisible gestalts)”,从而消弭了事实与价值的界限。与纳尔逊一致,在克里考特[3](p335)看来,健康本身内在地具有价值意味。与纳尔逊不同的是,克里考特[3](p354;364)不认为健康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虽然健康具有客观性),而是如同其它任何价值一样是主观赋予的。这与现代主义价值论的主流基调是一致的。通过健康的概念,克里考特把内在价值的所有者由人推及生态系统:“就像身体健康的医学标准一样,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将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普遍性,工具价值性与内在价值性。”[3](p335);“如果我们可以内在地赋予价值于我们自身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则我们也可以内在地赋值于生态系统的健康。此即,我们可为生态系统的健康自身而赋予(及物动词)其价值 …”[3](p355)。
以此,以生态系统健康为指向的环境伦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我们为何要接受它呢?即,如何解释传统伦理学的视域以及生态中心论在当代的必要性?对此,克里考特的策略是,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衔接入休谟-达尔文的情感社群主义(sentimental communitarianism)之伦理演化模式中。
2情感基础:伦理演化模式
2.1休谟的利他情感
有别于功利论与道义论(两者皆基于理性),休谟的伦理体系建立在“利他情感(publick affection)”[8](p47)之上:“我们必须放弃基于自爱原则以解释每一种道德情操的理论。我们必须采纳一种更为利他的情感,并使得我们对于社会的利益,即使基于它们自身的考量,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因此,休谟的伦理学蕴含着整体主义倾向的实践原则:“每一促进社会利益的事物必然传播愉悦,而致害的事物则产生不安。”[8](p58)不过,休谟的伦理学体系面临两个问题:(1)利他情感如何而来?(2)利他情感又如何获得作为伦理基石所必需的普遍必然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休谟的回答是“机械”式的[8](p93-94):“既然人心是由相同的诸元素合成的 … 它将永远不会对公众之善完全无动于衷 … 这种人性的情感 … 为所有人所共有,它可独自地作为道德的基础 … 一个人的人性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且此同一个对象触动着这一存于所有人中的热情。”这里的“相同的诸元素”的预设只是把第二个问题转移到了第一个问题,对此,休谟的表态是“超验而封闭的”[8](p112):“此标准 … 终极地源于最高意志,后者授予每一种存在各自独特的本性 …”然而,这种将道德的起源归因于最高意志(神)的思路并不能解释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伦理的历史性。就像克里考特[3](p109)所指出的:如果诸道德情操源于最高意志,那么它们合当是永恒不变的。
2.2达尔文的情感起源
规避了休谟的超验预设,达尔文从人类演化的机制阐述了伦理情感的起源。相对于休谟的利他情感,达尔文使用内涵更丰富的“社交情感(social sentiments)” 或更原始层面的“社交本能(social instincts)”。对此,达尔文在承认种际竞争的同时,也指出种内协作的普遍性,即在生存竞争中,群体中的个体比孤立的个体获益更多[3](p61)。这种族群成员相对于孤立个体的生存优势迫使个体为融入族群而生成一种自我让步的本能,从而产生了伦理行为[2](p54)。因此,达尔文把道德起源与普遍性的伦理学问题消解为(人类)社群演化的实证确认[9](p93):“如果谋杀,抢劫,背叛等等是寻常的,部落不可能集聚起来 … 此类罪行 …. ‘被打上了永久丑恶的烙印’”。以“社群(community)”为演化的核心单位,社交本能孕育出整体主义的道德感[9](p96-97):“行为被认为是 … 好的或坏的,仅当它们明显地影响部落的福利,而不是该物种的福利,也不是该部落某一个体成员的福利 … 道德感源生于社交本能,因两者首先都排他地相关于社群。”同时,演化的过程性决定了伦理形式的非封闭性:“当人在文明层面进步时,小的部落融合为大的社群,最基本的理性将告诉每一个个体他应该将他的社交本能与同情心扩展至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 ”[9](p100-101)。因此,伦理对象随着社群的发展也是不断扩展的:“我们的同情心变得越来越敏感与发散直到它们扩展至所有的有感知众生”[9](p101)。
2.3伦理的文化负荷
伴随达尔文的伦理演化的一个问题是,伦理形式的多样性,与物种(社群)演化的单向性(社群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呈现出“一” (部落社群之形成机制)与“多”(伦理形式的多样性)之间的张力。为此,克里考特[3](p111)引入了文化的作用:虽然伦理本源于因自然选择而生成的本能情感,文化规定了道德情操的具体内容:“伦理学当然地植根于自然选择的诸感情,但道德中亦具有很大的文化成分,后者给予我们的诸无私情操以形式与方向。我们可概括地说,文化塑造了诸道德情操。”基于此,克里考特[3](p182)虽然接受了达尔文关于伦理起源的演化机理,却并不认为我们的情感内涵仅仅停留在原始社群中的同情心(sympathy)的层面,单单后者(除了有感知动物以外)很难使得众多对象(如植物,种群,生态系统等)成为可能的环境伦理受体。在克里考特[3](p183)看来,人类社会层面的文化意义上的“演化”赋予了我们更广泛的道德情操的内涵,如群体自豪感与忠诚等,后者使得具体伦理在人类社会中的继续演化及分化成为可能:
“所有的正常人都被给予,一些比另一些更丰富地,诸道德情操,不过后者适用于谁以及怎样地应在行为上被表达则受到我们文化环境的塑造。诸道德情操自身是未确定的及可塑的。以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而言,它们自身是潜能,后者只在某一文化情景中成为现实。”[3](p111-112)。
不过,道德情操在个体层面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伦理的相对性,如某一身体特征(如身高)总是分布于一常态范围内一样,道德情操也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定性,后者保障了伦理实践原则的普遍性[3](p108)。不难理解,演化机制的约束性保障了道德情操在统计意义上的稳定性[3](p87)。
以此,克里考特的文化演化机制较为自洽地解析了伦理的“一”与“多”之间的张力。这里,整体主义环境伦理面临着一个实践性问题:如何平衡社会(人际)伦理原则与环境(人-非人)伦理原则之间的张力?对此,克里考特阐述了基于伦理演化的伦理累积(accretions)效应。
3实践原则:伦理累积效应
3.1大地伦理
与达尔文一致,在利奥波德[1](p203)看来,伦理是演化性的且其动力单位是统摄互相关联之个体的社群:“所有的演化迄今的伦理立足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即个体是一个由互相依赖的诸部分组成的社群的成员。” 进一步地,伦理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社群之合作[1](p202):“此事物[即伦理]起源于互相依赖的诸个体与诸团体的合作模式的演化的趋向。”在此基础上,利奥波德引入了生态学之于环境伦理的启示意义,“这一迄今只被哲学家们所研究的伦理的扩展实际上是一个生态演化中的过程”[10](p634),而生态学“扩展了社群的边界从而将土壤,水,植物,与动物,或统称之为大地,包含在内”[1](p204)。可见,利奥波德倾向于将伦理对象推广至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元素。这种社群扩展蕴含着伦理主体与伦理受体的不断分离。虽然利奥波德大大拓展了伦理对象,他提出的大地伦理也成为生态中心论的雏形,但他的社群(community)概念模糊了人与非人的界限,也没能解决社会伦理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张力。对此,克里考特给出了自己的进路。
3.2实践优先级
面对社群扩展中的不同伦理原则之间的张力,克里考特强调了伦理演化的累积效应:“利奥波德把伦理发展的不同阶段――从部落习俗到普世人权,以及最终到大地伦理——称作‘累积’。累积意味着‘外部的增加或积累’。大地伦理是一种累积,即,它是一种在我们所积累的若干社会伦理上的增加,而非后者的取代品。”[3](p71)在克里考特看来,伦理累积模式既体现在道德情操上[3](p168),也体现在伦理义务上[3](p71-72):“附随于[作为]生物社群中的公民身份的诸责任(保护其[即生物社群]完整,稳定与美丽)并不取消或取代附随于[作为]人类地球村中的成员身份的诸责任(尊重人权)”。伦理累积模式,犹如树木年轮之增广[3](p168),它使得诸义务生成时间的先后作为义务间优先级的参照标准成为可能[2](p58):
“进一步地,作为一条通则,在冲突中,相关于我们所从属的内层社会圈的诸义务盖过那些相关于更为远离树心木的年轮 … 若一狂热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以生物社群的完整、美丽与稳定的名义而鼓吹施加战争、饥荒与瘟疫于人类族群 … 将是同样地不正当的。一般而言,对家庭的诸义务位于对国家的诸责任之前,而诸人道义务位于对环境的诸责任之前。因此,大地伦理不是严苛的,也不是法西斯式的。它不抵消人类道德。”[2](p93-94)
可见,这种伦理进路既是自然主义的(诸义务的优先级参照诸义务在伦理演化中生成的先后),同时也是人本主义的(最先生成也是最优先的义务是基本人权的满足)。以此,克里考特回应了张力问题:社会伦理照旧,环境伦理只是在保障前者的基础上的额外补充。
4理论张力与讨论
4.1关于价值
借用纳尔逊的“不可分割的完形”的重描述符,克里考特在语义层面消解了事实-价值二分的难题。这里,“不可分割的完形”的论断不免有些武断。我们或许可以说,事实意义上的重描述符为人敞开了价值层面的实践维度,同时价值意义上的重描述符也不能脱离事实层面的认识。以上进路表明的是事实与价值的互融,而主观性从广义的实践维度中获得了超越个体的相对一致性,后者体现了一种客观性。
这一进路不是简单地以主体间性取代客观性。例如,在贾米森(Jamieson)[11]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解中,主观性被视为个体的独特的偏好,客观性则被视为(这种偏好在)主体间的一致性;因此,价值既可以是主观的(如果是个体独有的看法),也可以是客观的(如果是被共同接受的)。对于贾米森[11]的观点,克里考特[3](p358-359)是明确反对的,因这一进路容易导致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见对异见个体的打压。区别于一般的主体间性,克里考特[3](p359)强调了理性之于主体间的价值观的仲裁作用。这一思路本质上是休谟式的[4](p469):如果我们承认一种“好”,那么实证认知将告诉我们发现“好”以及达到“好”的途径,这是理性之于伦理实践的意义。因此,在克里考特看来,伦理学是不可能完结于自身的,而实证认知是实践的必要条件或手段。
虽然克里考特的关注中心在于“健康”,后者似乎并没有成为价值的终极载体。特别地,健康的价值是条件性的[3](p356):例如兔子的健康在其族群造成生态失衡时成了一种恶,而它们的不健康在生态系统的层面上是更大的善。可见,善的大小在于其辐射的广狭,生态系统的善(健康)大于具体族群的善(健康)。进而,克里考特[3](p358)认为至广大的生态系统之善(健康)也不具有终极性:“亦如人或兔子的健康,生态系统的健康仍是一种可撤销的善。它可被损害或被牺牲以达到我们赋予更高价值的目的。”以“我们”作为价值的唯一评判者,伦理主体似乎有着最终解释权。那么,什么是“我们”更看重的目的呢?克里考特没有解释,这暗示了其理论的不彻底性。或许,以实证认知作为实践条件的立场而言,这一不彻底性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实证经验的历史性使得伦理实践不可避免地呈现阶段性与开放性,即伦理演化的非封闭性。
4.2关于实践
应该说,克里考特[3](p296;356)的诸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如本地物种多样性、生态功能等)间存在着张力。例如,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可以增加本地物种的多样性,却常常损害本地生态系统的功能。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不同的指标呢?对此,虽然克里考特没有直接讨论,我们可以从他关于价值的论述中了解一些头绪。在克里考特[3](p88-89)看来,价值可分为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s)与趋近价值(proximate values):前者作为终极目的为所有主体所承认,后者作为服务于此目的的手段而包含了多样性的可能;进而,价值的争论只囿于趋近价值,即作为手段的合理性的问题,而后者的调解须求诸理性(而非情感)。可见,这种“理性”只是工具理性,即关于经验的综合命题的判断,而作为普遍必然的终极价值具有超验性。这里,存在着手段的经验性与目的的超验性之间的逻辑距离。或许,我们可以把终极价值的对象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健康本身,而趋近价值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标准。由此,不同健康标准之间的张力只是实证科学的问题,而后者无法游离于经验之外,并且无法否定随着实证认知的深入而消弭张力的可能。作为经验总结的诸健康标准在超验的指向上,至少在主观期望上,具有一致的方向性。换言之,健康本身是目的,具体的健康标准仅是手段,后者的合理性,在广义的实践之维中,是可以被期望的。在克里考特[3](p96)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集体的利益与生物社群的完整性将趋于一致。这预设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总体环境健康的存在性与唯一性。以这样的抽象思辨为个人信仰,我们似乎在形上层面消解了张力问题,但在经验层面,并没有摆脱具体实践的困惑。我们可以寄理想于明天,但当下该如何作为呢?
在社会伦理与环境伦理的实践优先级上,克里考特的设定也过于生硬简单了。如果社会伦理的诸规范一切照旧,按照趋近价值服务于终极价值的思路,人类都可以社会伦理的必要性为任何群体的私利行为辩护。因此,这样的环境“伦理学”只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管理策略,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伦理色彩,后者以主体利益的自我让步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种让步,如同在社会伦理层面,逻辑上并不以主体生命的终结为唯一形式。“环境法西斯主义(environmental fascism)”[6][7](p262)之推论的荒谬在于将让步形式作了最狭隘与极端的理解:即牺牲一方的根本,如个体生命的终结、族群的灭绝或系统不可逆的崩溃。对于环境伦理而言,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平衡甚至共荣,本是它的题中之义,后者指向的是环境问题的非极端性解决方案,即人与自然的共存甚至共荣,是否可能的问题。对此,克里考特的答案是肯定的[3](p14);而对于如何达到共存或共荣的具体实践,克里考特的理论是有待完善的。
参考文献:
[1]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2]J. Baird Callicott.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3]J. Baird Callicott. 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4]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Reprint,Oxford:Clarendon Press,[1739]1960.
[5]James Lindemann Nelson. Health and disease as “thick” concepts in ecosystemic contexts,Environmental Values,1995,4:311-322.
[6]Frederick Ferré. Persons in nature:toward an applicable and united environmental ethics,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1996,1:15-25.
[7]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8]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Reprint,New York:Library of Liberal Arts,[1751]1957.
[9]Charles R.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London:J. Murray,1871.
[10]Aldo Leopold. The conservation ethic,Journal of Forestry,1933,31:634-643.
[11]Dale Jamieson. Ecosystem health:some preventive medicine,Environmental Values,1995,4:331-334.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简介
环境保护部主管和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原《环境科学动态》,CC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于1976年创刊,现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2011年6月第三期本刊改版并定位为“国家级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依据从环境保护的视角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办刊宗旨,创新设置“理论战略探索”、“政策专题研究”、“法律法规研讨”、“典型案例解析”、“研究动态瞭望”、“研究成果报道”、“生态文明之窗”等栏目。本刊底蕴深厚尤其自2011年改版以来一直发挥集中选题的宣传优势,提前发布选题,开展征稿组稿,期刊学术质量显著提高。据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评估,我刊学术影响因子显著大幅度提高,多年来一直位于全国收录环境科学类66种期刊中的前列。
同时知网《2015年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显示:我刊机构用户总计近5000个,分布于11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代顿ITS公司、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法国国防部、牛津大学、韩国最高法院、韩国最高检察院、日本国会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伊士曼化学公司、陶氏化学、NSD生物技术咨询、南澳大利亚大学等国外机构,我刊业已成为对外宣传我国环境保护成就和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从201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主办的《2015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获悉,全国242种全文被转载的理论经济学学科期刊中,我刊全文被转载12篇,转载数量位列第五名,综合指数排名第七名。仅次于《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动态》。
2016年本刊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统领,重点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绿色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为议题,策划选题,以期为“十三五”绿色环保新蓝图建言献策。
2016年拟重点选题: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气环境质量管理、机动车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与修复、环境外交、环境与健康、农村环境保护、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固体废弃物环境管理、环境产业、污染减排重点以及环境与贫困等。请各界人士能予以关注并不吝赐稿,同时欢迎相关单位及课题组协办专栏或者专刊。
From the Land Ethic to Ecocentrism:the Approach of Holistic Environmental Ethic
SUN Yajun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ecocentrism,J. Baird Callicott,based upon the land ethic of Aldo Leopold,has materialized the holistic environmental ethic,with respect to its axiological foundation,sentimental bedrock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Ecocentrism,focused on “ecosystem heath”,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rategies of re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I trace the approach of the holistic environmental ethic in the above three aspects,and investigate potential tensions within this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possibility.
Keywords:Leopold,Callicott;ecosystem heath;truncated intrinsic value;practical possibility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88X(2016)02-0012-05
作者简介:孙亚君,哲学博士(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环境哲学与生态学研究
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应对生物入侵的环境伦理研究”(15CZX0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2015M570332)
引用文献格式:孙亚君.从大地伦理到生态中心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进路[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41(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