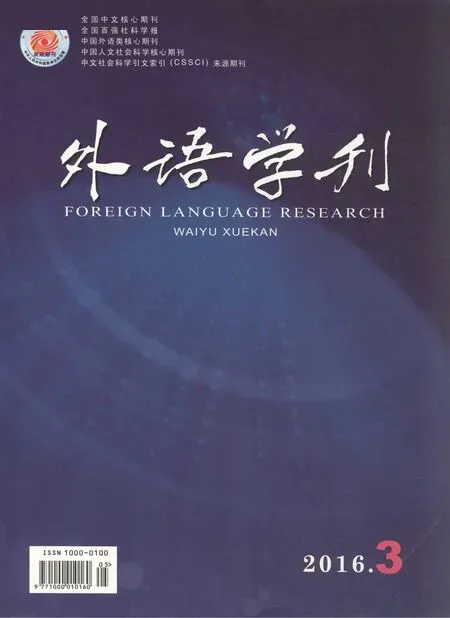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命题与西方哲学传统*
聂大海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命题与西方哲学传统*
聂大海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克里普克否认一切先验知识都是必然的传统主张,认为先验、后验是认识论概念,必然和偶然是形而上学概念,因此存在先验偶然命题。本文主要在批判与继承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讨论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命题,以期深化对其的理解。
先验偶然命题;形而上学;严格指示词;分析命题;综合命题
康德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一切先验知识,也就是分析命题都是必然命题,一切后验知识也就是综合命题都是偶然命题。克里普克否定这种传统区分,认为必然和偶然是形而上学概念,先验和后验是认识论概念,而分析和综合属于语言哲学概念。它们明显属于3个不同领域或范围。克里普克指出,“我们问某种东西是否可能是真的或可能是假的。如果它是假的,它就明显不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它还可能是假的吗?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世界是否有可能不同于它现在这个样子呢?如果答案是‘否’,那么关于世界的这个事实就是必然事实。而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关于世界的这个事实就是偶然事实。这一点本身与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无关”(克里普克 2005:16)。因此,必然性不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克里普克说,“当我们把一个陈述称为必然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只不过说,第一,该陈述是真的,第二,它不可能不是真的。当我们说,某种情况偶然是真的,我们是说,虽然它事实上是真的,但有可能情况不是如此。假如我们要把这个区别归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应该把它归之于形而上学”(涂纪亮 1988:378)。据此,克里普克认为“水=H2O”是后验必然命题,而“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是先验偶然命题。
1 先验偶然命题与巴黎的标准米尺之争
存在先验偶然命题是克里普克的一个重要结论。克里普克引述并反驳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一样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那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但是,这当然不是赋予它任何特别的属性,而只是标示它在用一把米尺进行测量的语言游戏中的特殊作用”(克里普克 2005:35)。克里普克认为使维特根斯坦困惑的问题是:由于这根棍子被用作长度标准,所以人们就不能把长度归属于这根棍子本身。维特根斯坦似乎遵循描述规定的如下原则:(1)在一定规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描述不能用于这一规定本身,更不能超出这一规定;(2)同一描述涉及的规定之间、描述和作为其前提的规定之间不能相冲突。如果按照以上原则,维特根斯坦一定认为描述似乎另有条件,对于存放在巴黎的国际米原器,我们无疑可以用其他方式描述其长度,但我们的确不能说它是一米长或是不是一米长。一米长是我们描述长度的一种规定,而一旦遇到这个规定本身,我们描述长度的米制方式似乎就走到某种边界。一般认为规定是主体为描述对象所做的关于量和质、方式和方法等的规范性设定。按照这种说法,巴黎的国际米原器就是意义的公设或预设,也就是前提性的规定。我们不仅不能说国际米原器是一米长或不是一米长,也不能说零是正数还是负数。这意味着,所有游戏都必须有规则,规则赋予游戏意义,而所有游戏规则都必须建立在一定规定的基础上。其实在克里普克引述维特根斯坦这席话的后面还有几句关于颜色的类似情形:“让我们想象像标准米尺那样存放在巴黎的色样。我们把‘棕褐’定义为密封保存在那儿的标准棕褐色的颜色。这样一来,无论说这个色样是或不是这种颜色都将是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 2002:50)。可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标准米”和“标准色”不过是语言游戏中的角色。它们是表现手段或概念框架,是在语言游戏中作为样品或范型来使用,用来度量、划分和谈论世界。
可是,克里普克反驳说:“维特根斯坦一定错了,这根棍子就是一米长”(Kripke 1980:54)。
克里普克将上述命题陈述为:棍子S长度在某确定时间t时是一米。根据克里普克,在这个同一命题中“一米”与“在某确定时间t时S的长度”不同,“一米”是严格指示词,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指称一米;而“在某确定时间t时S的长度”是非严格指示词,在一些非真实的情景下,如果对棍子施加各种压力和张力,它就可能变长或变短。事实上,在某些情景下,S并不是一米长。那么“S是一米长”的形而上学状态就是偶然陈述的状态。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说,这个同一命题是偶然为真的;在认识论意义上说,这个同一命题是先验的,因为根据定义,人们是未经过进一步研究而自动地知道S是一米长。因此,“棍子S长度在某确定时间t时是一米”是一个先验偶然真理。
对于“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是先验偶然命题,黄敏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以及两种可能的回答(黄敏 2009:292)。
第一,“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不是先验命题,因为“在某确定时间t时S的长度”的指称需要实指来决定,因此含有经验的成分,“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是经验命题。对于“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的先验性,克里普克指出,“那么,对于通过提到棍子S来确定米制的人来说,‘S在t时间棍子是一米’这个陈述的认识论状态是什么呢?情况似乎是:他先验地知道它。因为,如果他用棍子S去固定‘一米’这个术语的指称,那么作为这种定义的结果(该定义不是一个缩写的或同义的定义),他就是未经进一步研究而自动地知道S是一米长”(克里普克 2005:37)。显然,在这里先验性的根据是定义,更确切地讲是纯粹人为约定。在克里普克看来,他理解的“一米”定义是:某个人看着他面前的一根棍子S说,“一米”就指称这根棍子S在那个时间的长度。
一种可能的辩护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因为,一个命题是否是先验命题取决于其真值条件得到满足这一事实,而不仅仅取决于真值条件包含什么,真值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不需要参照任何经验内容。关于什么是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先验性,陈波(2010)将其概括为:一个命题是先验地可知为真的,如果:(1)可以独立于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知道它为真;或者(2)可以仅仅凭借定义或者规定知道它为真。陈波认为(2)有很大问题,因为定义和规定不是任意的。它们需要某种经验的根据,也需要某种认可,许多定义不过是先前认识成果的浓缩和总结。因此,根据定义和规定为真并不就是先验地为真。针对这一批评,我们认为在这里所谓的定义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而是纯粹的、任意的约定。因此克里普克说的“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就包含“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无论这个长度是多少”的意思。因为在克里普克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先验性是逻辑在先的。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一旦先验地确定一米的长度,一米作为严格指示词来指称一米是不会变的,而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可能会因为冷热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不是偶然命题,而是必然命题。因为,无论“在某确定时间t时S的长度”有何变化,它都是一米。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在确定什么是一米时,“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当然必然为真,但是一旦按这种方式确定什么是一米,“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就可以有意义地为假。黄敏认为这些辩护不适合克里普克,这里的关键是克里普克认为先验是认识论概念,而偶然是形而上学概念。这一点可以从最近国际计量局打算重新定义“千克”得到验证:科学家发现存放在巴黎附近塞夫尔的国际计量局的圆柱体钵铱合金的重量比好几十个复制品的平均重量轻50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的重量)。为此科学家正在寻找非物质的方式定义千克,其实,除千克外,国际单位制中其它6个单位如米、秒、安培、开尔文、摩尔和坎德拉如今都不以实物参考物为依据。这说明物质的定义方式或约定是先验偶然的,须要修正“圆柱体钵铱合金的重量”而不是“一千克”。同理,在“一米=棍子S在t时间的长度”中,如果须要修正,那一定是“在某规定时间t时S的长度”,而不是“一米”。
2 先验偶然命题与康德传统
无论人们对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与后验必然思想如何评价,这一思想都会在西方哲学传统的讨论中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其中,一个来自于康德对分析命题、综合命题以及先验综合命题的区分,另一个则来自于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消解。
康德区分(a)先验分析命题:命题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不借助任何经验,逻辑的必然为真,如“一切物体都是有广延的”;(b)后验综合命题:命题的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之中,是经验的判断,经验的偶然为真,如“牡丹花是红的”;(c)先验综合命题:命题的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之中,是先验的判断,经验的必然为真,如“5+7=12”。在康德看来,先验分析与逻辑的必然性有关,能独立于经验而得到证实;后验综合与偶然性有关,依赖于经验而得到证实;先验综合既有先验性又有经验的必然性。
康德不同意莱布尼兹关于“5+7=12”是分析命题的看法,而认为“5+7=12”是先验综合命题。因为我们不能从五的概念与七的概念相加中逻辑地推出十二,用大的数字更能明显地说明这类命题不是分析命题。如果借用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康德可能认为“5+7”与“12”没有相同的涵义,因此“5+7=12”不是分析的,但两个词项有相同的指称,因此“5+7=12”是先验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解释为,只有命题才是知识,一方面,先验综合命题与先验分析命题具有同样的先验性,它不依赖于经验,经验反而依赖于它,它是概念的,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先验综合命题又与后天综合命题相同,它是经验的。知识虽然开始于经验但并非都来自于经验,因此感性里包含着先验的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包含康德的信条: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无直观则空。由此可见,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超越莱布尼兹的唯理论与休谟的经验论而归为先验论。如果我们把康德的经验理解为意义,那么我们对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遭到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质疑。弗雷格认为分析命题能传达逻辑和意义的知识,也就是说,存在着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的知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数学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是不同的,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是重言式,不能表达知识。看来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路下,先验综合命题要么不存在,要么是无意义的。但对于分析命题不能表达知识这一点,卡尔纳普给出约定论的解释,即分析命题不具有认知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语言外部问题,它参照实用性、方便性和经济性标准,这一标准是约定出来的,没有确实的依据,是任意的,因此分析命题完全不同于综合命题,综合命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有认知意义。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是从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路出发,只承认逻辑真理和经验真理二分,逻辑真理由分析命题表述,经验真理由综合命题表述。
艾耶尔指出,康德论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时使用不同的标准。“5+7=12”之所以是综合的,因为“5+7”的主观内涵不包括“12”的主观内涵,依靠的是心理标准。而“一切物体是广延的”是分析命题之依据矛盾律,是逻辑标准。心理标准会使某些命题陷入困难,因为对于无穷大的数这样的概念,康德式的直观是难于把握的,这也是弗雷格放弃康德直观标准的原因。
如果命题或是先验的或是后验的,那么命题可组合成4类:先验分析命题、先验综合命题、后验分析命题和后验综合命题。由于康德断定所有后验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因此后验分析命题被排除。而克里普克一方面捡起康德遗弃的后验分析命题,认为存在后验必然命题,一方面又受到康德先验综合命题思想的启发。那么康德启发克里普克什么呢?那就是分析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使人们不得不做出如下选择:如果你的命题得到证明,那么它对存在的东西毫无所言;如果它是关于存在物的,它就不可能得到证明。如果它是由逻辑论证得到证明,那么它就代表一种主观约定;如果它断定一个事实,逻辑就无法确立它。如果你是求助于概念意义而证实它,那么它就远离实在;如果你是求助于知觉而证实它,那么它就是无法肯定的。康德使克里普克看到经验中有先验主体的建构,但克里普克没有把康德的经验理解为弗雷格认识论意义上的公共涵义,而是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实在的偶然性。克里普克暗示,其实康德在先验综合命题中已将先验的与必然的相分离,只是康德以来的传统把这一思想抛弃或遗忘。(克里普克 2005:14)
3 先验偶然命题与奎因对分析/综合命题区分的消解
康德以来的分析与综合命题区分的传统遭到怀特和奎因的反驳。怀特认为有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只是这种区分不是一种鲜明的区分,而是一种程度的区分。但奎因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分析命题。在以下3个命题“(1)No unmarried men are married//未婚男子不是已婚的;(2)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单身汉不是已婚的;(3)No bachelors are married//单身汉是未婚男子”中,奎因假设(1)和(2)同为分析命题,那么(1)是逻辑真理,(2)不是逻辑真理,但(2)可以通过(3)中的“单身汉”与“未婚男子”的同义性替换而使(2)还原为(1)。如果这一论证成立,那么问题是我们依据什么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男子”?
这可能有3种依据。依据1:如果一个命题按照语义规则为真,那么它就是分析的。可以表述为S在语言L中是分析的,当且仅当S仅根据L的语义规则便是真的。这个根据来自卡尔纳普的如下约定:在一个语义系统E中一个句子S是L真的,当且仅当E中S是真的,且只要根据E的语义规则就可以确立其真值,而不须要参考任何(语言之外)事实。对于此种分析定义,奎因反驳:如果语义规则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它们被假定为分析的,那么便导致一种循环。
依据2:词典定义赋予“单身汉”与“未婚男子”这两个表达式以同义性。这相当于说,S是分析的,当且仅当S通过定义可以归结为逻辑真理。即“单身汉是未婚男子”是逻辑真理。奎因反驳:词典定义赋予“单身汉”与“未婚男子”同义性是词典编撰人以先在同义性为根据的。
依据3:如果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那么这些表达式就是同义的。用莱布尼兹的说法就是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性。奎因反驳:如果要保证以上替换顺利进行,就要知道这样的相互替换是不是认识的同义性的充分条件,说“单身汉”与“未婚男子”是同义的就等于说“必然地单身汉是未婚男子”可理解为“单身汉是未婚男子”是分析的。如果“必然地”是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性前提,那么这也不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因为“必然地”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概念。也就是说,S是分析的,当且仅当S是必然的,也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
通过以上分析,奎因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论证不是直截了当的循环论证,但类似于循环论证,即类似于空间里的一个闭合曲线。在其中,我们能根据同义性阐述分析性,又根据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性阐述同义性,包括在由“必然”辖制的语境下,根据分析性来阐述必然性。因此,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分界线一直没有划分出来。认为有这样一条分界线可划,这是经验论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奎因 2007:22-38)
对于奎因的结论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解读:(1)强版本:我们没有确切的标准来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划界,分析性不是一个有效概念,不存在分析命题。(2)弱版本:我们难以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划界,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是相对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奎因的“可修正性”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的,即S是分析的,当且仅当S是真的,且不因经验而需要修正。但这与奎因的意义整体论相冲突,奎因的意义整体论认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不是单个的陈述,因为没有任何陈述是可以免于修正的。这样奎因也同时反驳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S是分析的,当且仅当S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确证。对于这种一方面认为意义的单位可以是单个的陈述,另一方面认为每个陈述可以孤立地得到确证或否证的还原论教条。奎因主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因此,如果承认所有语句的真值都不能免于修正,那么就不存在分析命题,如果承认数学语句的真值能免于修正,那么就仍然存在分析命题,只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是相对的。
如果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是相对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有“单身汉”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未婚或离异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我们修改概念框架,不再以未婚或离异作为必要条件,如已婚但已独居几十年的男子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单身汉。所以分析真理是相对于某个时刻的概念框架而言。随着概念框架的变化,“单身汉”这一概念发生变化,“单身汉是男子”可能仍然表达分析真理,但“单身汉是未婚的”只是偶然真理。这似乎与克里普克相符合,但与康德以来的传统相矛盾。
4 结束语
克里普克批评康德以来的传统把必然性与先验性联系在一起,而坚持认为必然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这可以被视为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某种恢复。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必然和偶然。事物的本质属性与该事物的关系是必然的,而事物的偶然与该事物的关系不是必然的,因为事物的偶然属性也可能不属于该事物。由此可见,一方面,克里普克关于必然和偶然的思想充满对康德、奎因的批判与继承;另一方面,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
陈 波. 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吗(上)[J].学术月刊, 2010(8).
陈 波. 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吗(下)[J].学术月刊, 2010(9).
黄 敏. 分析哲学导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奎 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涂纪亮.语言名著选集(英美部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Kripke, S.A.NamingandNecessity[M].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0.
Kripke’sContingentaPrioriPropositionsandtheWesternPhilosophyTradition
Nie Da-hai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ccording to Kripke, the notion of a priority and a posterity are not the notion of metaphysics, but of epistemology. And the notion of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are not the notion of epistemology, but of metaphysics. It means that Kripke denies all prior knowledge are necessary and believes contingent a priori truth do exis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ruth of Kripke’s contingent a priori propositio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tradition,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Kripke’s view on it.
contingent a priori proposition;metaphysics; rigid designator; analytic proposition; synthetic proposition
*本文系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项目“克里普克语言指称理论研究”(2015ZZ022)的阶段性成果。
B089
A
1000-0100(2016)03-0020-4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05
定稿日期:2015-10-09
【责任编辑谢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