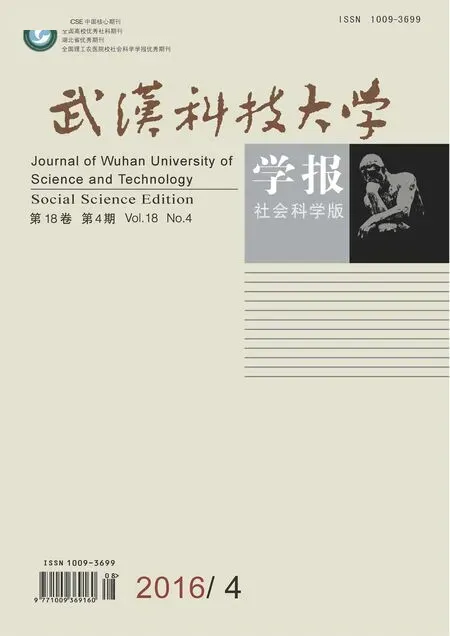枭首与死刑制度
柏 桦 金 潇
(1.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2.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枭首与死刑制度
柏桦1,2金潇2
(1.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2.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枭首是古代一种死刑方式,在最初阶段仅是一种牺牲祭祀的方式,随着国家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纪功与威吓的手段,进而成为法律规定的刑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残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律上予以清除,但在传统的“明刑弼教”方针下,也经常以“非常法”的形式出现。为了限制统治者的任意,通过条例规定部分罪名可以枭首。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枭首已经成为历史,但在法律清除或限制枭首酷刑的同时,律外用刑、法外用刑还非常普遍,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枭首;明刑弼教;死刑制度;法外用刑
死刑,在古代被称为“极刑”“大辟”。在“明刑弼教”的指导原则下,死刑执行乃是在公开场合执行。“杀人于市”,通过残忍的方式将人犯处死,以使人们知道儆戒,“刑期于无刑”是以刑罚来警告人们,使之畏法而不犯法,达到刑罚悬而不用的目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是没有犯罪、没有诉讼,使人们遵循朝廷倡导的道德,遵守朝廷制定的法律。德主刑辅,在以严刑峻法维护道德的理念下,曾经出现过许多残忍的处死方式,诸如凌迟、车裂、炮烙、刳胎、镬烹、抽肋、锯颈、醢脯等,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枭示”,也称为“枭首”。从墨、劓、剕、宫、辟“五刑”,到隋唐以后笞、杖、徒、流、死“五刑”,最终确定死刑有斩、绞二等,但枭首与凌迟并没有从法律上完全予以废除。枭首能够在中国存在五千年,即便是清末法律变革以后,法律上明文废除枭首后,枭首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人头高悬于城门之上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现在也能够看到许多历史照片。因此探讨枭首的历史渊源,反思这种死刑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为构建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一些借鉴,就十分必要了。
一
枭是一种鸟的名称,因为此鸟鸣叫声音凄厉,古人视之为恶鸟,如果听到该鸟的鸣叫,就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因为枭是恶鸟,古人将之比喻为奸佞之人。“懿厥哲妇,为枭为鸱”,也就是说“可叹此妇太逞能,她是恶鸟猫头鹰”。“枭,相传长大后食母的恶鸟。鸱,猫头鹰,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不祥之鸟”[1]611,614。“鸱枭鸱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乃是“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抓走我娃娃,不要再毁我的家”[1]272-274。
人们通过对这种恶鸟的痛恨,引申到对奸恶之人的痛恨。汉武帝时,有人提议:“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孟康注云:“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镜”。如淳注云:“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2]456-457,这种提议被采纳,汉代“祠黄帝用一枭破镜”[3],也成为制度。张晏认为:“枭,恶逆之鸟。方士虚诞,云以岁始袚除凶灾,令神仙之帝食恶逆之物,使天下为逆者破灭讫竟,无有遗育也”[4]1218-1219。师古云:“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4]1219,将这种恶鸟“牺牲”,祭祀黄帝,寓意将奸恶之人斩尽杀绝,也直接影响到枭首的定义。“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段玉裁注:“不入鸟部而入木部者,重磔之于木也。仓颉在黄帝时,见黄帝磔此鸟,故制字如此”[5]。磔枭鸟以悬于木,历史久远,而将奸恶之人首级悬挂于木,也是枭示的主要表现方式。
所谓的枭首,就是将犯人的头颅砍下来,悬挂于木杆之上而展示,故此也称为枭示。随着社会发展,枭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悬于杆首,也可以装在木笼之中张挂在各种建筑物及树木上,还可以让人拿着到各处去展示,称为“传首”,更有将人犯头颅用油漆涂抹,以铁线、绳索或木棍等物穿起来展示,甚至多个头颅穿在一起。
枭首不仅仅是一种死刑执行方式,也是一种祭祀礼仪。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每逢大祭祀,都要以人为牺牲,将一些俘虏或奴隶的首级砍下来,或摆在祭台,或悬挂在旗杆之上,特别是古代军礼要祭旗纛,不是杀俘虏,就是杀罪犯以祭祀,称为“禡祭”。“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礼记·王制》)。郑玄注:“禡,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孔颖达疏:“为师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蚘,或曰黄帝”。“谓出师征伐,执此有罪之人。还反而归,释菜奠币在于学,以可言问之讯,截左耳之馘,告先圣先师也”,“讯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这里实际上是讲禡祭要用有罪之人祭旗,直到明清,尚有这种祭礼,如努尔哈赤的使臣出使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已斩(使者)之祭旗矣”[6],努尔哈赤便将林丹汗的使者也杀了。注和疏都认为“馘”是截耳,而古字有“馘”、“聝”、“酋或”、“月或”等,都具有砍下某部分的意思,“馘”是砍首,“聝”是截耳,“酋或”杀敌酋,“月或”是割肉(即割生殖器)。先秦之时杀死敌人多以首级记功,故用“馘”字,后来因为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首级携带不方便,才截耳以记功,便以“聝”而代之。
这种杀人祭祀,现代考古发掘已经可以证明,在夏、商、周三代乃是常见现象。由祭祀转变为刑罚,并且带有羞辱性质的,一般始于传说时期黄帝杀死蚩尤,将蚩尤头颅砍下并悬挂于辕门前。“蚩尤个人既被杀,他的族人总有不少为黄帝所虏,蚩尤族人仍可称蚩尤,所以能使‘居前’。因为蚩尤战败,所以部落联盟的首领,风伯、雨师等全在战胜者前后奔走,所以能使他们或进扫,或洒道”[7]。神话传说中能够有一些真实的历史存在,正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讲:“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8]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论述,是解读古代神话传说的一把钥匙,且不管传说多么神奇,但传说中的某些内容,确实是在以后的制度与风俗习惯中体现出来。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都是五刑之属三千,如“墨、劓皆千,刖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吕刑》,具体内容现在已经难以得知,但从商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之心”“炮烙之法”等及其残酷的处死方式来看,当时的刑罚是很残酷的,枭首应该也是经常使用的处死方式。如周武王伐纣,“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杀妲己”[9]108,妲己也被武王斩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10],这种枭首以示功、枭示以惩恶的做法,也被后世所因袭。如“竖牛之祸”的竖牛,是鲁叔孙穆子与庚宗妇所生之子,名牛。古人13岁以下的男孩称为“竖”,因为与庚宗妇一起杀嫡立庶,最终被“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左传·昭公五年》),宁风乃是齐国地名,也就是将竖牛之头悬挂在荆棘之上。荆轲刺秦王,为了取得秦王信任,欲借樊於期之首,樊自刎,“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战国策·燕三》)。在战国时期,七雄征战,斩首万级以上的记录就有10余次,这些首级除了报功,也向秦国人展示功绩,更威吓战败国人。悬挂首级则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还采取“京观”的方法威吓于国之民,如晋楚邲之战,楚臣潘党提出:“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左传·宣公十二年》),这种京观是将尸体堆积成山,既可以向国人展示武功,又可以威吓敌国。楚庄王认为:“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拒绝将晋兵尸体立为京观,却讲到古明王用京观“以惩淫慝”,则可见这种展示由来已久,枭首示众则更不在话下了。
二
枭首之刑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处死方式,至少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了。“枭首在秦、汉时惟用诸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诸律,始於斩之外别立枭名。自隋迄元,复弃而不用。今之斩枭,仍明制也”[11]4199。“夷族之诛”,乃是指秦始皇时嫪毐作乱之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9]327。刘邦以彭越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雒阳下”[12]2733。所谓:“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4]1104。这种“具五刑”的杀人方式,在吕太后主政时予以废除,但实际上也还存在。
秦汉时期枭首并不仅限于“夷族”,如楚汉战争时,刘邦“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2]377。汉武帝时,梁平王刘襄的大母李太后有淫行,“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12]2088。“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丞相屈氂下狱要斩,妻枭首”(《汉书·武帝纪》)。汉哀帝时,有人诬告丞相薛宣妻敬武长公主与薛宣子薛况淫乱,王太后“使者迫守主,遂饮药死。况枭首于市”(《汉书·薛宣传》),曹魏在参酌汉律的基础上,制定《魏律》18篇,“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晋泰始律》增为20篇,“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但还有“王者立此五刑”的原则,即“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晋书·刑法志》)。
由上可见,枭首乃是秦、汉“夷族之诛”的一种形式,似乎不能够成立。至于枭首入刑始于六朝,则据北魏孝文帝时定律,“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魏书·刑罚志》)。南朝梁“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北齐律》12篇,其五刑,“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北周《大律》25篇,规定的死刑,“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磬是敲击致死,而枭首为死刑第四等,仅次于车裂。隋文帝杨坚“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不过,在隋炀帝时,杨玄感反叛,也“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啖其肉”(《隋书·刑法志》)。枭首在非常时期也经常使用,但已经不是常刑了。
沈家本认为:“自隋除枭首之法,唐、宋二代,此事遂希”,并且列举宋代几个事例,认为宋代“亦偶行之,非常法也”[13]。唐宋是没有将枭首列入常法,但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又为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解之刑。归于重法,闲民使不为变耳”(《辽史·刑法志》)。这里将枭首列入死刑中的一种,而辽穆宗应历十三年(963年),“杀鹿人弥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辽史·穆宗纪上》)。这是针对普通人,并不是谋反大逆之罪中的“非常法”可比。
隋至元除了辽代以外,枭首作为非常刑存在,特别是针对谋反、大逆案件,还有比枭首更残酷的处死方式,都属于律外用刑。朱元璋勒定《大明律》,虽然也没有将枭首列入常刑,但后世在条例中则明确规定有8种行为是可以枭示(首)的①。清代乾隆年间增加到12种行为要枭示(首)的②,以后不断修例,枭首适用范围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乾隆以后,授权督抚大员以恭请王命即行正法的权力,枭首之刑往往不受律例的约束。特别是咸丰三年(1853年)《就地正法章程》颁布,枭首之刑更不是朝廷所能够控制了。如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期间,处决了30 808名人犯。当时“广州城内的刑场上‘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坐赭色’,‘空气恶劣如毒雾’,‘令人欲作三日呕’,真是惨不忍睹。不难想象,外地府县刑场上当然也是同样的景象”[14]。即便是有律例规定的罪名可以枭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够约束地方官,乃至团练、民团以及土豪劣绅滥杀无辜了。
三
清末法律变革,沈家本延请东西各国学者及律师人等,开始进行修律。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言:“请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得到圣旨恩准,即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1908年的《大清现行律例》则仅有斩决,但“时虽有死刑唯一之议,以旧制显分等差,且凌迟、枭首等项甫经议减,不敢径行废斩也”。更何况自《就地正法章程》实行以来,“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11]4200-4203,可以说终清之世,一直没有废除枭首之刑。
北洋政府沿用清末法律,仅仅把“帝国”改为“民国”,把“臣民”改为“人民”,把“覆奏”改为“覆准”,删除有关皇帝特权的条文而已。南京政府的刑法,历经修订,1935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有2编47章357条。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死刑唯一的执行方式就是枪决,这种法律的出台,从法理上取消了枭首制度,但在军阀混战、剿共清匪、抗日战争、三年内战的情况下,不但军人经常杀戮,地方官也经常不走什么司法程序就将犯人处死,就连会党、土匪、民团、土豪劣绅以及保甲长也可以随便杀人。
军阀混战时期,“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 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 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暴力行为成了常事”[15]。“各地红会与各会派之间互相仇杀之例甚多,会与会间,界线分明,严若鸿沟,稍有侵犯,冲突遂起,杀人盈野,习以为常”[16]。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以抗税抗捐的形式发起运动,则被称为动乱,“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如果不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17]325,这种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宣布是领导者,致使许多无辜者被杀。为了以儆效尤,这些被杀了的所谓“领导者”的头颅往往被悬挂起来。残酷的行为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被无情镇压的人们满怀仇恨实施报复,“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雅克·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有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17]355。非常处死与残忍报复往往是相得益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国民党政府没有了理智,人民也失去了理智,亦可见一个国家必须因循法治的轨道,任何破坏法律的人和事,如果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就会使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有市场,最终会破坏社会秩序并导致社会的无序,受害的只有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北伐军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他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18]。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蒋介石崇尚法西斯统治的情况下,试图在中国也实行法西斯主义,再与传统制度联系在一起,就具有独裁性质,而“国民党县以下行政官吏有90%以上是地主富农,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可以通过转嫁的方式把一切负担压到农民身上,这就是中国农村为什么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不断起来革命的根本原因”[19]。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农民革命,国民党将专制时代的保甲制度改造加工,让他们“搜捕革命者,镇压革命人民”[20]。从那个时期文献记载以及一些人的回忆录中,都可以见到保甲长随便杀人,而且经常将被杀的头颅悬挂起来,当时刑法已废除枭首等酷刑,但城乡到处都能够见到悬挂的头颅。
四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既要为生活在今天和平安定的时期感觉到幸福和荣耀,也感觉到肩负重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法治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构成。从古代枭首作为祭祀,转变到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再到法律予以废除,作为一种非常法的形式存在,又回归到在法律中对某些罪名可以枭首,这是古代枭首制度演变的大概。进入民国后,枭首在立法上完全废除,而在动荡时期,不但立法不能够规范社会,却出现更残忍的屠杀,也就不得不引起一些思考。
首先,观念上的转变。古代枭首从祭祀转变为杀戮,最初主要是纪功、惩奸慝,当法律规定为死刑是一种形式,惩奸慝则成为主要目的。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钦定的儒家政治模式一直被历代王朝所遵循。“钦定的儒家思想认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道德、社会和文化秩序,最终达到天下和谐、天下太平”[21]。法律支撑道德的原则,使“明刑弼教”“辟以止辟”“刑期于无刑”“以儆效尤”等理念融入司法,这样即便是法律没有枭首之刑,统治者也可以任意使用。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正象球戏中一个球体向另外一个球发出时就应该发生它的效力一样”[22]27。如朱元璋认为“明刑弼教”就是天理,给自己大搞律外用刑找到依据。朱元璋能用人而不信其人,能断案而不信其案,每每先入为主,对人对事逞其纵横捭阖之能,恩威并济,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表,如他将“审出诬告情节得实,将好词讼刁民凌迟于市,枭首于住所,家下人口移于化外”[23]510。一些人因为穿的靴子像官靴,便“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23]512。军官私役军人,科敛屯军,“将他凌迟处死,传首沿途号令”[23]514;“斩首,前去本卫枭令”[23]515。京城有“做贼的、掏摸的、骗人的,不问得赃多少,俱各枭令”。富民强迫良民为奴,“除将本人凌迟示众,并一家人俱刺面入官为奴”[23]516。因此,明代《问刑条例》出台,将8种罪名纳入枭首,实际上是限制统治者的任意胡为。乾隆帝认为:“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24],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授权督抚以先行正法之权,因为“观此情形,是奸顽之民,不容朕行宽大之政也”[25]。将稍微对王朝统治不利的人,都视为“奸顽”,这是古代律外用刑的重要理由。视人民如仇讎,不但是专制君主所为,也是独裁者所为,也就不难理解在民国时期还存在法外用刑了。要改变这种看法,必须关注人民,在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下,多为人民着想,法外用刑自然也就成为历史了。
其次,立法与司法的协调。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22]129。古代曾经把枭首之刑清除出法律之外,但统治者还是以“非常法”的形式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残酷的处死方式,即便是明清律例将枭首限定在一些罪名之内,也没有束缚统治者的手脚。如《大清律例》清清楚楚地写明可以枭首示众的罪名,乾隆帝却允许督抚根据情况,“即一面具奏,一面正法枭示,并将犯由及该犯姓名,遍贴城乡,使愚民咸知儆惕”[26]。嘉庆帝在督抚已经将抢劫犯正法枭示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其办理宽纵之咎,实所难辞。嗣后须留心随时查察,如有抢劫逞凶匪犯,即行严拿加重办理,不必拘泥常例请旨”[27]。连皇帝都让臣下不必按照常例办理,督抚们也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法律成为具文,不但不能够约束君主,连官员都不能够约束,也就使立法与司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法律不能够约束统治者及官吏,当然也不能够约束人民。当时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前后出台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结构也堪称严谨,但军阀与独裁者们,又何尝遵照法律呢!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中美合作所内骇人听闻的刑具,城市和农村到处悬挂的人头,酒馆饭店张贴的“莫谈国事”警语,至今也不陌生。司法不能够忽略法律,立法也不能够不考虑到司法,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次,制度变迁要跟上社会发展。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2]427,因为缇萦上书,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而广为人知。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存在于野蛮时代的各种没有人道却已成为风俗习惯乃至制度的做法,也逐渐在文明时代予以改变,“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28]。文明社会不断进步,残酷的刑法也因此不断有所弱化,古代从墨、劓、剕、宫、辟“五刑”,转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在君主专制政体的条件下,这种进步也太慢了。当西方已经工业革命,废除了以前残酷的肉刑,清王朝还顽固地坚持“辟以止辟”的原则,不但不肯废除笞杖刑罚,在保留明代凌迟、枭首、枷号、充军、发遣等条例内的刑罚之外,还增加锁系铁杆、锁系巨石、发遣为奴等刑罚。在西方人眼里,“由于某个谋反者,整个村庄被烧毁,整个行政区遭受惩罚,整个省责令戴孝,有勋位的人剥夺某些勋章。天子就这样下达了波及广泛的处罚”[29]。不能够跟上世界的变化,也不认可社会进步,必然会受到惩罚。在刑罚的落后及列强的威逼下,不但导致对自己的法律失去信任,还强行使中华法系中断,这都是不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缘故。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法治是有安全感的,要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制,不但要遏制人情关系、权大于法,而且要纳入制度规范之中,在构造全新法治文化的同时,使法治深入人心。
最后,顺应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至今已经发展了五个阶段,即“文明一,始于原始的或表意文字;文明二,始于字母文字;文明三,始于欧洲的印刷术;文明四,始于电子通信技术;文明五,始于计算机技术”[30]。每一文明的发展,都是人类的进步。从中国枭首的发展历史轨迹来看,进入文明二之后,原来祭祀牺牲的重要性,已经被彰显功绩而惩罚奸恶所取代。在文明三,国家多元化使国与国之间战争更加频繁,因为国家的对外侵略与防御、对内安抚与镇压的职能存在,虽然枭首在法律上取消,但在特殊时期,还是以“非常法”的形式体现。文明四在血腥的世界战争及世界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极端与文明相互博弈,枭首在法律上予以取消,如用“非常法”的形式处置则会遭到大多数人的谴责。文明五,虽然计算机互联网使世界距离拉进了,但也不能够消除邪恶。文明的发展导致残酷的死刑方式已经被逐渐废弃,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将证明,死刑最终会在世界范围内取消,代之以自由和财产刑。枭首酷刑已经成为历史,但依然可以用之警示,人类高度文明的发展来之不易。
注释:
①可以处以枭示的8种情形分别为:1、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为首,监故者,仍剉碎死尸,枭示。2、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撑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三人以上者,比照强盗已行得财律,皆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其虽拒敌,不曾杀伤人,为首者,依律处斩。若止十人以下,原无兵仗响器,遇有追捕拒敌,因而伤至二人以上者,为首坐以斩罪。3、若打造违式海船,卖与外国人图利者,比依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处斩,仍枭首示众。4、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及干系城池衙门,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伤人,俱随时奏请审决,枭首示众。5、响马强盗,执九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俱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于行劫处所,枭首示众。6、各处无藉之徒,引贼劫掠,以复私雠,探报消息,致贼逃窜,比照奸细律处斩,本犯枭首。7、各处无藉之徒,引贼劫掠复雠,探报消息,致贼逃窜者,本犯枭首。8、各边仓场,若有故烧系官钱粮、草束者,拿问明白,正犯枭首示众。参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75,1979年)。
②可以处以枭示的12种情形分别为:1、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为首,监故者,仍剉碎死尸。2、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撑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三人以上者(为首者枭示)。伤二人者为首之人。3、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乡道劫掠良民者。4、闽省不法棍徒在沿海地方引诱偷渡之人,包揽过台,中途谋害,死者,不分首从。5、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及干系城池衙门,并积至百人以上者。6、响马强盗,执九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俱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江洋行劫大盗。7、行劫罪囚,不论曾否得囚,有无伤人,为首之人。伤人者之伙犯。有杀人者,为首之人及伙犯。8、黔、楚红苗聚众抢夺,人数至五十名,杀人,为首者。聚众百人,虽不杀人,为首者。聚众至百人,杀人,为首者。9、出哨兵弁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不分首从。10、各处无藉之徒引贼劫掠以复私雠,探报消息,致贼逃窜者。11、故烧系官钱粮草束者。12、凶徒纠众谋财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公廨、仓库系积聚之物,并街市镇店,人居稠密之地,延烧抢夺财物者,不分首从。杀伤人者。有因焚压致死者,为首之人。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897-907页)。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司马迁.史记: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司马迁.史记: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86.
[4]班固.汉书: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71.
[6]清太祖实录:第1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96.
[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3.
[8]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02.
[9]司马迁.史记: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257.
[11]赵尔巽.清史稿:第1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司马迁.史记: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4.
[14]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M].区鉷,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43.
[1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M].杨品泉,张言,孙开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54.
[16]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463.
[17]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杨品泉,张言,孙开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8]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M].薛绚,译.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94:331.
[19]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1.
[20]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1919-1949)[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319.
[21]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
[2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3]杨一凡,田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3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4]清高宗实录:第15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948.
[25]清高宗实录:第9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547.
[26]清高宗实录:第13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152.
[27]清仁宗实录:第28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238.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29]老尼克.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M].钱林森,蔡宏宁,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8-19.
[30]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M].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
[责任编辑周莉]
收稿日期:2016-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0FFX001);司法部重点课题项目(编号:14SFB1002).
作者简介:柏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及法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4;D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6)04-04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