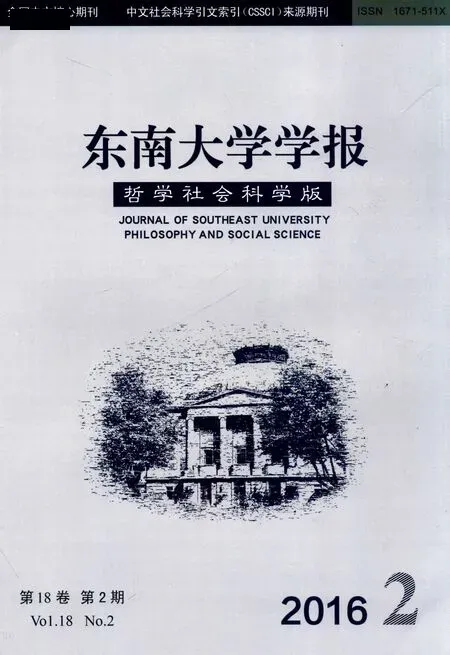“艺术
—社会”学与“艺术—社会学”——论两种艺术社会学范式之别
卢文超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艺术
—社会”学与“艺术—社会学”——论两种艺术社会学范式之别
卢文超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以卢卡奇、戈德曼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与以贝克尔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虽然都名为“艺术社会学”,但却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以探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为主旨,是“艺术—社会”学,是为了评判艺术价值之高低,重心落在艺术上;后者是用社会学研究艺术,是“艺术—社会学”,是为了发展社会学,重心落在社会学上。尽管目前“艺术—社会学”是大势所趋,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风险,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关键词]艺术;社会;社会学;贝克尔;艺术社会学
1982年,美国著名艺术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的代表作《艺术界》出版,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影响深远。在2008年出版的纪念版前言中,贝克尔回忆了自己在1970年代转向艺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缘由,即这个领域已做之事乏善可陈,尚待开垦。他剑锋所指的是以卢卡奇、戈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它当时在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贝克尔眼中,卢卡奇等人的著作“哲学气息浓厚,致力于探讨美学经典问题,专注于评判艺术价值”。[1]X这是他心存不满的。贝克尔后来投身于此,积十几年之功聚沙成塔,在美国发展出了另一种艺术社会学。
虽然卢卡奇和戈德曼等人的艺术社会学和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都号称“艺术社会学”,但在库恩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它们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并不相同,回答的方法和获得的结论也相距甚遥。
一、“艺术—社会”学的重心在艺术
以卢卡奇、戈德曼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艺术社会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它实际上是“艺术—社会”学,即以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为主旨的学说。他们对“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又基本是“反映论”或反映论的变体。在贝克尔看来,他们总是试图找出艺术如何“反映”了社会,而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又总是意味着“阶级结构”,“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理解的”[2]。在这里,贝克尔低估了卢卡奇和戈德曼等人艺术社会学的复杂程度。尽管卢卡奇和戈德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以往的阶级中心范式。卢卡奇就曾批评过狭隘地从阶级角度进行的文学研究,进而提出了一套以“整体性”为标准的反映论。方维规就指出,卢卡奇“以‘整体性’为其‘反映论’的标准和理想”[3]。尽管如此,贝克尔的基本判断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他们的理论基本还都是反映论。
实际上,尽管卢卡奇和戈德曼的艺术社会学号称“艺术社会学”,但它并没有多少经验色彩,相反,它却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方维规一针见血地指出,卢卡奇所秉持的“社会整体性”观念实际上排除了经验研究的可能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即把握现实整体(‘总现实’)的要求,使他陷入另一个抽象公式的陷阱,一开始就用社会整体性观念亦即纯粹的历史哲学视角,把社会经验的所有单独视角排除在外,以至不可能对特定社会事实的各种单独历史现象进行社会学的探讨,说到底也排除了各种实证研究”[3]。与之相似,尽管戈德曼声称自己想要做实证的科学家,但是,他的思想本身却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无怪乎德国社会学家西尔伯曼曾尖刻地讽刺说:“戈德曼的学说至多只能用来说明什么不是文学社会学”[3]。
卢卡奇、戈德曼等人的艺术社会学重心并不在社会学,而在艺术。他们的艺术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评判作品,而不是为了发展社会学。卢卡奇曾盛赞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正是因为他们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社会总体”。他说:“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家的目标就是对现实进行文学的复制。忠于现实,热烈追求着把现实全面和真实地重现——这对一切伟大作家来说是衡量其创作伟大程度的真正标准(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3]。对此,路茨就指出,卢卡奇“本人运用‘文学社会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几乎一直带着批判的口吻”[3]。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贝克尔看来,他们完全不是社会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在我看来,这些作者的早期一代——并不只是卢卡奇和戈德曼,但他们是我读过的——实际上完全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本质上是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评判”[2]。与此相似,在1960年代的“西尔伯曼—阿多诺”之争中,西尔伯曼也曾批驳阿多诺,认为他在进行所谓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时,身份并不是社会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4]。
总之,卢卡奇、戈德曼所关心的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社会学研究艺术。因此,他们基本上不假思索地保留了传统美学的预设,具有先验性;他们对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究也是为了对艺术品进行评判,具有批判性。可以说,他们的艺术社会学重心落在了艺术上。
二、从“艺术—社会”学到“艺术—社会学”
如前所述,卢卡奇、戈德曼等人的艺术社会学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社会”学,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反映论。在美国社会学家温迪·格里斯沃尔德对英美小说之差异的研究中,这种反映论已经经不起推敲了。在1891年之前,在美国流行的英国小说主要关注家庭和爱情,而美国小说则以探险等西部主题为主。人们将此归于英美国民性的差异,认为文学反映了社会。但是,格里斯沃尔德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并非来自国民性,而是来自版权法。1891年之前,美国引进英国的小说不需要支付版税,这使英国小说在美国很流行,因此,美国小说家有意避开了英国小说的主题,专门写英国小说很少涉及的探险等主题,只有这样他们的小说才能卖得出去。而在1891年,美国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以后引进英国小说需要支付版税,这使英国小说丧失了其价格上的优势,美国小说可以与之一竞高下了,于是英美小说的主题开始逐渐重合。因此,格里斯沃尔德认为:“只要美国小说家对于他们的小说的主题和主旨的选择与他们的外国同行所做的不一样,这就较少是因为美国性格或经历的差异,而更多是因为不同的市场限制”[5]。由此可见,传统的反映论在此问题上丧失了解释效力。
我们也看到,卢卡奇等人的艺术社会学实际上保留了传统美学的预设,他们更关注伟大的天才,更积极地对艺术进行价值评判。但是,在贝克尔看来,他们所秉持的这些价值观念本身并非是永恒的,而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能会因时因地而有差异。所以,贝克尔对这种路数的艺术社会学并不感兴趣。由此,贝克尔不再将目光仅仅放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上,而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他的“艺术社会学较少地对天才和稀有作品感兴趣,而更多地对工匠和日常工作感兴趣”[6]。他希望社会学家能恪守价值中立的立场,对艺术现实进行观察,而不仅仅是依据自己未经证实的理论预设对艺术进行介入,因为那毕竟是美学家的事业。在贝克尔看来,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贝克尔说:“美学的重大问题大多是‘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伟大的艺术?’以及其反面,什么根本不是艺术。这是一项典型的消极的事业,目的是阻止毫无价值的东西——它有它自己的(贬损的)名字,就像‘媚俗之物’或‘大众文化’——与真正的东西相混淆。我所喜欢的艺术社会学避免了这个问题,与之相反,它观察‘艺术’这个词如何在艺术界的组织生活中使用。谁分配了这个头衔,这种分配是如何保持和奉行的,结果如何——这些才是这样的经验研究中的标准问题”[7]。所以,贝克尔提出:“社会学家以这样的模式工作,他们对艺术作品的意义解码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探求艺术作品隐秘的、作为社会之反映的意义也没有太大兴趣,而更乐于把作品视为一群人协同工作的产品”[8]16-17。也就是说,在贝克尔看来,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这正是贝克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艺术所得出的结论,这也是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的要义所在。
由此可见,贝克尔在自己的艺术社会学与传统的艺术社会学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1982年,当传统的艺术社会学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时,贝克尔曾说,他的艺术社会学一点也不是“艺术社会学”,因为它“看上去和艺术社会学中的主流传统背道而驰。”[1]XXV而到了2012年底,当美国艺术社会学又发展了30多年,贝克尔式的艺术社会学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时,他又认为卢卡奇、戈德曼等人的艺术社会学根本不是艺术社会学,而只是文学批评而已。无论谁是真正的艺术社会学,我们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贝克尔就与卢卡奇、戈德曼等人的艺术社会学划清了界限。在贝克尔看来,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看待文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和我并不一样。他们观察艺术品的特征,并且表明这些特征是如何与他们所认为的艺术品在其中制作的社会的典型特征相联系的。我的观念是将艺术品看作一种协作活动的产物,将包含在它的制作过程之中的任何人都囊括在内”[2]。
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两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不同。正如贝克尔所言:“它们可能仅仅是对相同的经验材料提出的两种不同系列的问题”[1]XXV。对于卢卡奇和戈德曼而言,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而贝克尔感兴趣的则是艺术在社会中是如何制造的。说到底,我们可以将新旧艺术社会学之争看作社会学内部的新旧之争。马丁曾指出:“在社会学中,也有关于‘新’、‘旧’社会学的划分,所谓的‘新’社会学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占有优势,如贝克所言,‘旧’的社会学‘与美学十分相似’,它关注‘如何解读艺术作品,发现作品中潜在的、作为社会只反映的意义。’相反,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对文本译解投以很小的兴趣,而更关注诸如这样一些问题:‘职业化的组织,传统的发展与保持,实践者的训练,分配的机制,受众及其趣味。’”[8]37
三、“艺术—社会学”的重心在社会学
与卢卡奇、戈德曼等传统艺术社会学家不同,贝克尔提出了另一种思考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他说:“我对艺术界所说的,当将其一般化之时,也可以说是对任何类型的社会界所说的;一般而言,谈论艺术的方式,也是一般地谈论社会和社会进程的方式”[1]368-369。我们可以说,贝克尔关注的中心是“一起做事”。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这种集体活动和其他领域的集体活动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对他来说,谈论艺术就是谈论社会,因为两者都是在谈论“集体活动”。
可以说,贝克尔提出的这种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卢卡奇、戈德曼等人的旨趣截然有别了。贝克尔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超出了那种关于‘艺术是社会的’的主张,并且超出了那种在社会组织形式和艺术风格或主题之间进行的一致性论证。它表明,艺术是社会的,在于它是由人们合作的网络所创造的”[1]369。所以,说到底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关注的重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社会学,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集体活动。贝克尔说:“我们可以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寻找:负责制造具体事件的网络;这些合作网络中的重叠;参与者使用惯例协调他们活动的方式……”[1]370-371。
格里斯沃尔德对英美小说差异的研究,证明了传统的反映模式的破产。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一种更为开阔的“反映”论,她说:“我的发现表明,文学作为反映必须扩展,必须包括对生产环境,作者性格,形式问题以及任何具体社会的成见的反映”[5]。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这种“反映论”虽然还是在用“反映论”的名号,但其实质已经和卢卡奇等人的“反映论”距离很远,而更靠近贝克尔了。
比如,瓦格纳-帕茨菲茨和史华兹对美国越南战争纪念碑的研究就可以向我们展示艺术如何“反映”了社会进程。在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政府很不情愿修建纪念碑。那么对他们来说,越南战争也失败了,为什么要修纪念碑呢?研究表明,美国修建纪念碑是为了重新团结因为越战而分裂的国家。但由于越战以失败告终,所以在修建时必须淡化事件本身的失败色彩。由此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排除设计的政治内容,将牺牲者的名字加入,修建逝人墙。所以,在众多设计方案中,他们最终选择的是抽象的设计;尽管将其放在黄金地段,但却基本位于地下。这使逝人墙比雕像更吸引人,将参观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个体生命的苦难,而不是不受欢迎的战争的悲惨结局。瓦格纳-帕茨菲茨和史华兹通过对越战纪念碑的研究展示了美国的社会进程和政治文化。在这里,艺术是作为指示器而存在的:艺术品的建造过程折射了各种社会势力的角逐[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卢卡奇、戈德曼关注艺术,而不是社会学,正好是相反的。卢卡奇和戈德曼关注的只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而与之相反,贝克尔则提出了四类艺术家,即中规中矩的专业人士、特立独行者、民间艺术家和天真艺术家。中规中矩的专业人士是懂得并遵守艺术界惯例的人;特立独行者是懂得但违反部分惯例的人;民间艺术家是在其他组织的惯例下创作的人;天真艺术家是完全不懂艺术界的惯例、任意创作的人。在贝克尔看来,这四类艺术家不仅适用于艺术界,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的一切其他领域:“与一个艺术界的关系的四种模式——中规中矩的专业人士,特立独行者,民间艺术家或者天真艺术家——暗示了一种解释人们与任何一种社会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般化框架,无论它的关注点是什么,也无论它常规运作的集体活动是什么”[1]37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才宣称:“我们可以说(比它经常所说的有更多的正当理由),艺术界普遍地反映了社会”[1]371。格里斯沃尔德也说,她对反映论的扩展“与反映的隐喻紧密一致。因为,毕竟一个镜子不仅仅反映一个事物,而是反映放在它前面的所有事物。文学社会学家必须将多种多样的主题放在文学的镜子面前,以便实现反映论的全部潜能”[5]。但是,这种社会学家的反映论,已经与文学批评家的反映论大为不同了。
德国社会学家西尔伯曼的观点与贝克尔相似。实际上,19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著名的争论,焦点正是“用社会学研究艺术”还是“艺术—社会”学的问题[10]。在这个意义上,西尔伯曼堪称贝克尔的先驱。在他看来,“作为社会学,普通社会学和专门社会学一样,所涉及的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军事、工业、国家、宗教等方面,也存在于文学方面,它是人们努力探索的主要目的”[11]3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贝克尔所说的“集体活动”与西尔伯曼所说的“人的问题”尽管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相近的。那就是文学或艺术社会学只是一般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已。海涅克曾指出,艺术社会学的历史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学式的美学,即分析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即社会的历史,即分析社会中的艺术;第三个阶段即事实发现的社会学,即将艺术作为社会来进行分析[12]。在这里,我们借用海涅克的说法,但并不将此看作三个时间轴上的发展阶段,而是将其作为空间轴上的三种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这种划分,卢卡奇和戈德曼等人属于第一种模式,而贝克尔则属于第三种模式。在这点上,海涅克也与贝克尔有相似之处。她就曾宣称,她最近的工作就是发展一种“来自艺术的社会学,它将艺术视为一种揭示整个社会的典型的一般现象的手段”[12]。对于这种区分,方维规也敏锐地指出:“我们或许不得不对同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做出区分:一方面,‘文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建立在经验和实证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学社会学’是文学研究检视文学的一个视角,即‘社会—文学’视野”[13]。
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它也反映了社会之中的集体活动。贝克尔说:“我的思考方式总是去设想,你在一个地方找到的东西,同样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它们经常形式不同,但却或多或少相似”[2]。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公式,即“艺术=集体活动=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其他活动)”。这就无怪乎后来的学者施翁·鲍曼专门撰文从集体活动的角度比较艺术界是如何与政治运动相似了[14]。
四、结语:“艺术—社会学”的问题及来自埃斯卡皮的启示
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艺术—社会学”早已取代“艺术—社会”学成为艺术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在国内,虽然以往人们对艺术社会学的认知主要停留在“艺术—社会”学,但是,随着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艺术—社会学”相关著作的译介和研究,“艺术—社会学”逐渐兴起,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自身的问题。
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将重心落在了社会学上,这就存在着忽略艺术独特性的危险。比格尔曾指出,艺术史的分期不能照搬社会史的分期,因为“一旦历史被当作一个已知的参照系,并将之用于对社会诸个别领域进行历史研究,文化科学就会退化为建立相对应物的一个程序而已,这么做的认识价值就会变得很小”[15]99。或许与此同理的是,艺术社会学并不能仅仅被视作社会学在艺术领域的一个对应物。艺术有其特殊性,这会反制于社会学,影响其形态。贝克尔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的还原主义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赞格威尔指出“贝克尔的著作预设的观念是艺术生产是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所有类型的生产工作有同样的一种解释,这种一般原则是可疑的”[16]。布劳也指出,当艺术界被如此看待之时,艺术变成了一种研究所有类型的社会安排的工具,在此过程中,“艺术价值和产品变得基本不相关了”[17]。
那么,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如果说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并没有照顾到艺术的特殊性,那么,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埃斯卡皮在研究文学社会学时,则意识到了文学的特殊性。这是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应该汲取的优长。埃斯卡皮谨记着狄德罗在《关于书店商务的信》中的教导:“我看到那些让一般准则牵着鼻子走的人在不断地犯着一个错误,这就是把织布工厂的原则用于图书出版”[18]14,进而提出了“文学社会学应该尊重文学现象的特殊性”的观念。在他看来,“各种社会机制能够简化成为一些理性的模式,或者是一些可以确定的相互作用的游戏,然而当人们把这任何一种方案应用于文学现象时,文学现象总要留下一个不可约的余数”[19]135。比如在《文学的成功和寿命》一文中,埃斯卡皮就认为,不能把作家和原料供应者等同起来。这是因为他供应的是一种经过加工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只在某些方面符合确定的规格,这都与原料供应者相距甚远。也不能把出版商看作一位工业家,因为他每出版一本书都像是在创办一门新的工业。因此,“书籍工业并不是一种和其他工业相同的工业”[19]140。这显然更为可取,但显然也更为艰难。埃斯卡皮说:“如果我们想理解文学现象,我们就必须以一种纯属文学的特征性来观察它。这正是文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困难,因为它要求用社会学的方法论来作出文学的盖然判断”[19]170。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不避艰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把握艺术的社会性,又不失艺术的艺术性,才能对艺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才是艺术社会学真正的前景之所在。
[参考文献]
[1]Howard S.Becker.Art Worl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M].2008.
[2]卢文超.社会学和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访谈[J].中国学术.2015,34.
[3]方维规.卢卡奇,戈德曼与文学社会学[J].文化与诗学,2008(2).
[4]方维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Wendy Griswold.American Character and the American Novel:An Expansion of Reflection Theor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6,No. 4,1981.
[6]Howard S.Becker.Ethnomusicology and Sociology:A Letter to Charles Seeger[J].Ethnomusicology,Vol. 33,No. 2,1989.
[7]http://home.earthlink.net/~hsbecker/articles/mozart.html
[8]彼得·约翰·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M].柯扬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9]Vera Zolberg.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Ar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方维规.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兼论文学社会学的定位[J].社会科学研究,2014(2).
[11]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M].魏育青,于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12]Dagmar Danko.Nathalie Heinich’s Sociology of Art——and Sociology from Art[J].Cultural Sociology,2008,2:242.
[13]方维规.“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J].社会科学论坛,2010(13).
[14]Shyon Baumann.A general theory of artistic legitimation:How art worlds are like social movements[J].Poetics.2007,35:47–65.
[15]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6]Nick Zangwill.Against the Sociology of Art[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02,32:206.
[17]Judith R. Blau.Study of the Arts:A Reappraisal[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8.Vol. 14.
[18]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M].符锦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9]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卢文超(1985—),男,哲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艺术社会学研究”(15YSC008)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12-26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2-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