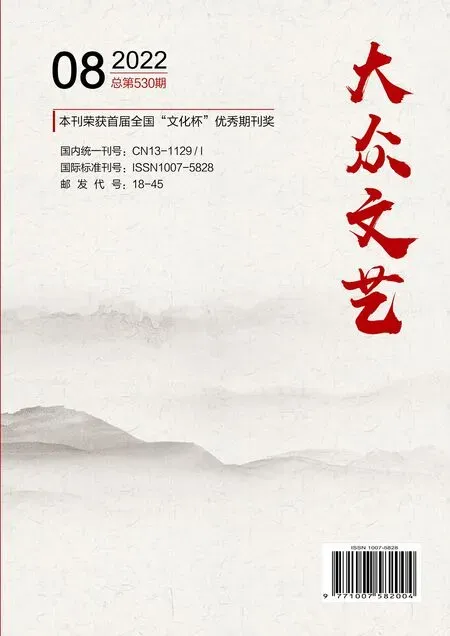从具象到抽象
——由云南黑白木刻发展引发的思索
郭 歌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650000)
从具象到抽象
——由云南黑白木刻发展引发的思索
郭 歌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650000)
云南版画艺术中,黑白木刻版画占有重要地位。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到“文革十年”,及至改革开放,再到八五美术新潮至今,云南黑白木刻版画的形式语言经历了一场由具象到半抽象再到抽象的变化发展过程,而引起云南黑白木刻这一外在变化的深层原因,除了其自身内在发展的动力及其兄弟艺术形式包围下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历史因素影响下其内在功能上的转变。
云南黑白木刻;具象;抽象;变化;思索
自新文化运动至今,不同时期云南黑白木刻的形式语言呈现出不同特点,这种变化不是一种跳跃式的前进,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况下循序渐进的演变发展。
一、云南黑白木刻在历史上的外在变化
战争年代,社会混乱、人民饱受战争摧残,木刻作为一种战斗武器,发挥了它“匕首和投枪”的作用。老一辈革命版画家王憨生的木刻漫画的形式语言就呈现出一种具象基础上夸张的艺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作品多为歌颂新中国建设时期美好生活等,瞿安钧的作品则开始摒除夸张的艺术气息,变得写实具象。
20世纪中期,从“双百方针”的提出至“文革十年”前夕。梅肖青的黑白木刻秉承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呈现一系列歌颂军人、反映人民生活的艺术题材,如《炉边夜话》《请大夫看病》等。《星光闪闪》描绘两战士在星空下长谈的情景,白色为底,黑色呈现人物故事情节,艺术造型潇洒,色调虚实相生。
改革开放后,木刻艺术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陈琦和万强麟根据傣族民间叙事长诗改编而成的《兰嘎西贺》插图,在写实具象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半抽象态势。画面黑白对比强烈,线条流畅,艺术家的幻想配合神秘的少数民族故事,使画面人物形象鲜明,场面气势恢弘,情节跌宕起伏。
彭晓的《十月景颇山》和《水果丰收•西双版纳的回忆》中,少数民族自然人文景观的题材以饱满的构图、流畅的线条表现出来,黑色为底,白色呈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在具象的基础上呈现一种变形后的装饰风格。
史一的《大江春秋》中,一位藏民站在江边粗大的砾石滩上、被支起的羊皮筏边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波澜壮阔的黑白对比下,动静结合,作品内蕴含着大气磅礴的人类精神。《石林•仙女湖》纯净永恒,仅是黑白之间就体现出“云岭高原”特有的日照充强以及山奇水秀的喀斯特地貌。
八五美术新潮后,艺术家们摆脱“高、大、全、红、光、亮”的形式语言,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本体的审美功能上。
李小明的《孤独》中,叶脉似的线条组成独特的构图,似门的黑色粗框里一个独自行走的人,被高大的建筑和热闹穿行的轻轨包围着。《山高水远•怒江》中,我们身处雄鹰之上的高度,俯瞰怒江在崇山峻岭间奔流到海。艺术家用深厚的概括内心视像和现实题材的功力,对造型回避。
2000年以来,马凯的《平衡的构成II》和《康苑路27号》,立足于传统与新意象结合,迸发出一种新语序。黄成春的《丛林深处》和《立昌景致》,凌乱随意却唯美富有诗意。
由此看出,云南黑白木刻的形式语言经历了一场由具象到抽象的变化过程。而这一演变的深层原因,除了其自身内在发展动力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历史因素影响下其内在功能的转变。也就是说云南黑白木刻在时过境迁的历史长河中功能的演变,必然会引起这一艺术形式的外在语言变化。
二、云南黑白木刻在历史上的功能转换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开拓者,革命时期曾提出“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我们去历史地看待理解,不可片面解读。战争年代,鲁迅是把木刻作为一种战斗武器,发挥其“匕首和投枪”的作用。王憨生的木刻漫画作品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创作出来的,起着战斗宣传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给版画家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氛围。这时期作品多为歌颂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美好生活,如瞿安钧的《假日里》《爱尼姑娘》和《月亮升起》。
梅肖青的黑白木刻呈现一系列歌颂军人、反映人民生活的艺术题材,如《人与狗》《炉边夜话》《星光闪闪》和《请大夫看病》,体现出作者浓浓的军旅情结。
还有再现文学题材的作品,陈琦和万强麟于1980年合作的《兰嘎西贺》插图是艺术家根据同名傣族民间叙事长诗改编而成的。画家用版画的形式语言直观再现史诗故事,呈现出古代云南地区印傣文化交流的结晶,体现了傣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消化的再创造能力。
彭晓于1987年完成的《十月景颇山》及《水果丰收•西双版纳的回忆》,画中景颇族和傣族的男女老少呈现出丰收时节的快乐忙碌,展现出云南沃土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热情积极的美好品质和生活状态。
80年代,史一的《金沙铁流》中人的高尚理想情怀跃然而出。《大江春秋》纯净永恒,让观者返璞归真,艺术家对生命的感悟在黑白木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80年代中,“后文革美术时期”和“星星美展”后出现了八五美术新潮运动。它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人们几十年来的习以为常的价值体系突然崩塌后引起的思想上的冲击变化在美术上的反映。艺术家们冲破思想上的政治意识形态禁锢,反叛艺术政治化、工具化和实用化,摆脱“高、大、全、红、光、亮”的形式语言,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本体的审美功能上。
这时云南黑白木刻的形式语言出现了新面貌,作品中的形式语言开始转向显露人的内心视像,追求视觉性,有些作品中更是体现出哲学思辨。在李小明的《孤独》和《山高水远怒江》中,艺术家面对观众敞开心扉,用哲学般的叙事方式诉说出人类丰富的思想生活。
2000年以来,新一代版画家马凯、黄成春等的作品受到世界艺术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新媒体新媒介等的出现,时刻引发着艺术形式的转向。
三、绝版木刻对黑白木刻产生影响
引起云南黑白木刻版画形式语言由具象到抽象的变化原因,还有其兄弟艺术形式如绝版木刻对其产生的影响。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云南版画异军突起,曾一度在全国美术界处于突出地位。而云南版画取得的喜人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版画家们对绝版木刻技艺的创造发明和出色运用。绝版木刻的一度夺人眼球导致黑白木刻有过一段消沉。但也有积极的影响,最突出的即在木刻艺术语言的色彩上:黑白木刻从原先的黑白时代进入到黑白灰时代,艺术家们开始对中间色调灰度产生思考和追求。
从以上云南黑白木刻版画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见,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云南黑白木刻的内在功能及外在形式语言与时俱进,经历了革命时期发挥战斗宣传作用的夸张,到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后赞颂美好新生活的具象,再到八五美术新潮后开始注重挖掘作为艺术本体人的抽象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外在表现一路呈现各有千秋的面貌,避免了千篇一律。但无论如何,版画家们将体现艺术真善美的美好愿望寄予版画作品中的志坚行苦的努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郭歌,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