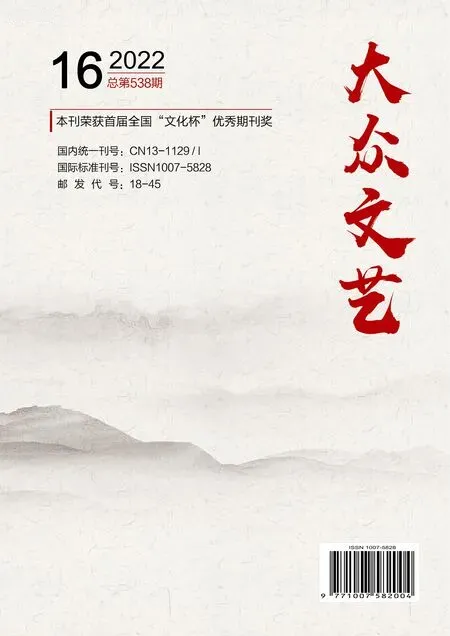湖北地区“摆手舞”的舞蹈形态与审美初探
周 仪 (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 430000)
湖北地区“摆手舞”的舞蹈形态与审美初探
周 仪 (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 430000)
摆手舞是土家族特有的一种传统祭祀舞蹈,流布在酉水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区,具体包括重庆秀山、酉阳;湖南湘西的龙山、永顺;湖北恩施的来凤、利川、宣恩等地。本文以“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为研究对象,着重从舞蹈流布与发展概况、舞蹈形态、舞蹈审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
摆手舞;湖北;舞蹈形态;舞蹈审美
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计划中青年人才项目《湖北地区舞蹈艺术形态与审美研究》(Q20152401)的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一、湖北地区“摆手舞”的流布与发展概况
(一)湖北地区“摆手舞”的流布概况
摆手舞是土家族特有的一种传统祭祀舞蹈,主要流布在湘、鄂、渝交界的酉水流域土家族聚居区。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上、下)》以及相关田野考察报告来看,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主要流布在恩施的来凤、利川和宣恩三地。现有研究成果中凡对湖北地区摆手舞的实地考察均以“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为对象。比如唐卫青、张瑞所在课题组成员曾于2014年4月对舍米湖村摆手舞进行实地调研,成文《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一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杨建平曾于2010年7至8月对舍米湖村民风民俗历史与现状进行过实地考察,成文《鄂西土家族民俗文化变迁研究》;此外还有李品林的《鄂西土家族舍米湖村摆手舞的田野调查》等。由此可见,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以“舍米湖村”保存最为完好也最为有名。
(二)湖北地区“摆手舞”的发展概况
湖北地区的摆手舞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古巴人狩猎舞、军前舞。此后历经土司王朝时期的祭祀舞、宴会舞,便一直保留在传统节庆(如过年、四月八节)活动中表演,土家人婚嫁习俗中亦有跳摆手现象。20世纪50年代,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以“来凤县”为源点,经官方支持得以发掘整理,并逐步走向舞台。虽然“破四旧”时期摆手舞的传承一度受到影响,但此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摆手舞不断得以恢复发展。2006年,来凤“土家摆手舞”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在传统的土家节庆活动中,在旅游文化表演的舞台上,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专业教学与创作中,都能看到摆手舞的传播与发展。其艺术价值、民俗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得到了充分肯定和体现。
二、湖北地区“摆手舞”的舞蹈形态分析
(一)舞蹈文化形态
从摆手舞的历史由来、本体积淀以及当代遗存来看,摆手舞在其流传与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三种典型的舞蹈文化形态:
其一,巫舞文化形态。摆手舞的“巫舞”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其表演时节、表演场地和表演目的方面。比如摆手舞是土家人在过年、祈年时节表演的一种民俗舞蹈活动。供奉土家先祖的“摆手堂”是其传统表演场地,“敬神祭祖”“祈年求丰”是其主要表演目的。其次,摆手舞在敬神祭祖、祈年求丰的目的和需求之下,严格遵照仪式程序表演,即摆手舞开始前先进行祭祖仪式,仪式结束后开始跳摆手(历史上有些地区的祭祖仪式中还含有道士做法仪式),舞蹈中众人按旧俗围成一个以摆手堂院坝杉树为核心的圆,伴随着锣鼓声点节奏,环绕大树摆手而舞。其仪式性、程式性均带有鲜明的“巫舞”色彩。
其二,纯舞文化形态。湖北地区的摆手舞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起,进入到舞蹈形态与舞蹈文化的挖掘与整理阶段。一方面以村落为基地的原生形态摆手舞得以复原和传承。原生形态的摆手舞虽仍带有祭祀色彩,但整个仪式包括舞蹈表演均以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为根本,其文化本质已与早期的“巫舞”有所不同,也正因如此,摆手舞的表演时节、表演场地更加自由,表演目的更趋向于娱人表演。另一方面摆手舞的纯舞形态以及舞蹈艺术本体特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舞蹈教学与舞台创作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创新发展,大大提高了摆手舞本体语言的艺术性价值。
其三,健身舞蹈文化形态。健身舞蹈文化形态是土家族“摆手舞”在当代生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时代变化、满足不同社会功能需求的结果。在全民健身的时代热潮中,在广场舞的广泛普及下,摆手舞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进入到体育文化视阈中,迎着全民健身的新时代风尚,成为当代广场舞园地的一朵奇葩。
(二)舞蹈表演形态
摆手舞作为土家族敬神祭祖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演形态有二:
其一,“礼乐兼备”。一方面,摆手舞祭祖仪式、敬祖之词及舞蹈动作等蕴含有“礼”的内涵,比如跳摆手前先进行祭祖仪式,供奉祭品,行叩拜之礼,唱敬祖感恩之词。唐卫青、张瑞的田野考察报告中就曾描述过舍米湖村摆手堂祭祀仪式时,众人在村内最有声望的老人的带领下“行叩拜之礼,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口中念词:土王土祖土王做主,有事才来奉请,无事不敢议论……仪式举行时,场面肃穆庄重”。1另一方面,摆手舞是祭祀仪式中以“乐(舞)”娱神的主要形式,也是整个仪式活动的核心内容。舞蹈表演时,人们依旧俗围成一个以摆手堂院坝杉树为中心的圆,环绕大树而舞,“舞者跟着锣鼓的节拍进退,期间没有交谈,没有嘈杂,每个仪式动作都有条不紊,显示了对祖先的崇敬之心。”2
其二,“鼓舞相和”。摆手舞早期以“歌、舞、乐”综合表演为特点,如今看到的摆手舞大多只舞不歌,但锣鼓作为伴奏,不可或缺。原生形态的摆手舞以一锣一鼓为伴奏,一到二人表演均可。锣鼓声既是摆手舞所依的节奏,又是摆手舞的号令。当然衍生形态的摆手舞,特别是用于娱乐、健身等的摆手舞,情况各异。但不管怎样,“鼓舞相和”的基本表演形式传承不变。
(三)舞蹈动作形态
摆手舞以模拟性为舞姿形象特征,以“颤膝、摆手、一顺边”为律动特点,其动作主要源自生产生活,是渔猎、狩猎、农耕生活中劳动动作及相关事物(动物)形象的模拟再现。比如舍米湖村摆手舞,20世纪50年代末重新发掘时恢复了四套基本动作,包括单摆、撒种、双摆、磨鹰展翅。其中“单摆”似赶鱼捕鱼;“撒种”是对土家人种苞谷场景的再现;“双摆”犹如土家人挖土;“磨鹰展翅”则是模仿老鹰自由翱翔的姿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摆手舞越来越多地亮相舞台,其动作内容不断扩充,增加了插秧、比脚、擦背、推磨、纺棉五套动作,形成了“新九式摆手舞”。而在网络资料中笔者发现,摆手舞的大众健身系列教材中共包括十五套动作,分别是单摆(分原地和行进两种)、磨鹰展翅、拉弓射箭、撒种、挖土、插秧、刮麻、挑水、纺棉花、推磨、拜年、双摆、比脚、擦背、抖灰尘。摆手舞动作套路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出舞蹈审美需求和本体发展的需要,也反映出与土家人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三、湖北地区“摆手舞”的审美特征
(一)以“朴实”见长
摆手舞是土家人古老的文化传承形态,尽管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摆手舞中所浸润的土家人“朴实”的民族特点从未改变。摆手舞以“朴实”见长,一方面是指“外在形式”上舞蹈服装、场地、动作等均以“质朴、真实”为特征,直观反映土家人的现实生活。比如土家人传统服装、包头、土家人日常生产生活类动作等。另一方面其“内在心理及情感”上尊神敬祖的虔诚心理以及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也体现出土家人“朴实”的民族性格特点。
(二)以“庄重”取胜
摆手舞作为土家人传统祭祀仪式中的主要表现手段,具有传统祭祀仪式的“庄重”之感。摆手舞的“庄重”,一方面体现在整个祭祀仪式的程序结构和环境氛围中,比如祭祀仪式有严格的程式,摆手舞的表演要在祭祖仪式完成之后,并且要求不准嬉笑逗趣,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规范表演。另一方面摆手舞动作中的重心下沉、整齐划一、平稳有序,其节奏、意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庄重”的特色,仪式感强。
(三)以“刚劲、粗犷”为本色
土家人作为古巴人后裔,自古以勇猛善战闻名。文献资料中也曾描述过早期摆手舞中包含有军前舞内容,遗憾的是如今这部分内容已经失传。但这并不影响今人对摆手舞的认知和理解。摆手舞以锣鼓为节,铿锵有力的节奏与“单摆”“双摆”“磨鹰展翅”“拉弓射箭”等动作,在表现土家先民战争、狩猎、渔猎等生活情景的同时,描绘出土家人刚劲、勇猛、豪放、粗犷的民族性格。
综上所述,本文以“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为研究对象,从舞蹈流布与发展概况、舞蹈形态、舞蹈审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首先,在舞蹈流布与发展概况中,本文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上、下)》以及相关田野考察报告为依据,指出湖北地区的摆手舞主要流布在恩施的来凤、利川和宣恩三地,且以“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保存最为完好。并在此基础上对湖北地区摆手舞的历史发展变迁进行了简要梳理。
其次,在舞蹈形态方面,本文从舞蹈文化形态、舞蹈表演形态、舞蹈动作形态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具体指出“湖北地区摆手舞”的舞蹈文化形态有三,即“巫舞、纯舞和健身舞蹈”;舞蹈表演形态有二,即“礼乐兼备”“鼓舞相和”;舞姿及律动形态以“模拟性”为特征,具有“颤膝、摆手、一顺边”的律动特点。
第三,在舞蹈审美方面,本文将其审美特征概括为“以朴实见长、以庄重取胜,以刚劲、粗犷为本色”三个方面,并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
注释:
1.参见:唐卫青,张瑞.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21-24.
2.参见:唐卫青,张瑞.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21-24.
[1]唐洪祥.河东摆手舞[J].中国民族,1993(7).
[2]李品林.鄂西土家族舍米湖村摆手舞的田野调查[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付静.土家族摆手舞文化的传承与保护[D].湖北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唐卫青,张瑞.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5]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上下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