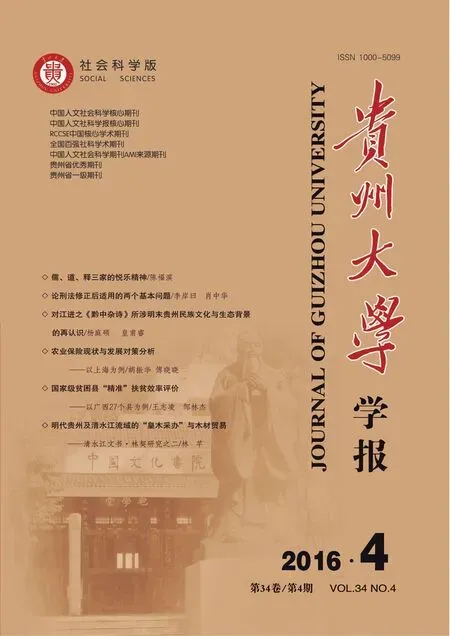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批判和回应*
王晓晖
(贵州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批判和回应*
王晓晖
(贵州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贵州贵阳550025)
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是考察工作场所层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劳动者的主体性、劳资关系的剥削性质和结构性对抗性质、劳动过程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理论面临的理论难题。本文梳理了核心理论面临的理论难题和核心理论支持者所作的回应,为建构更完善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结构性对抗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18
一、导言:劳动过程核心理论
劳动过程理论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及其代理人如何组织生产创造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在此过程中结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理论。时至今日,该理论经历了41个春秋和4个发展阶段,对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的劳工研究、工作社会学、组织研究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内学者呼吁应返回到生产中心性[1]的背景下,该理论无疑也是研究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然而,在其前两个发展阶段中,大量基于个案研究的争论,尤其是围绕创始人布雷弗曼提出的去技艺化和泰勒制控制系统两大主题的争论,让人觉得劳动过程理论缺乏公认的理论原则,几乎令该理论陷入绝境。为挽救劳动过程理论,保罗·汤普森在总结前两个发展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提炼出了劳动过程核心理论,简称核心理论。
核心理论由3个基本概念和4个理论原则构成。三个基本概念分别是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结构性对抗。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是指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是个变量,劳动力的发挥随工作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2]。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是指工作场所内的关系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的制约,但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事件不是完全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其他权变因素会导致工作场所的关系与社会层面结构性特征相对独立[3]130。结构性对抗,是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但根本利益冲突只是日常关系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它并未决定日常关系的具体形态,因此,日常关系会表现出冲突、顺从、适应、合作等多种形式[3]126。4个理论原则[4]48是:⑴劳动过程不仅创造剩余价值,而且是人类在世界上扮演角色和再生产经济的经验的核心部分,因此有必要去研究劳动的角色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⑵资本积累的逻辑推动资本不断改良技术和管理,变革产品和服务的生产;⑶为保证将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资本须利用管理系统来控制劳动;⑷由于存在剥削、控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结构性对抗”关系。四条原则中,第一条回答了劳动过程是否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对象的问题,另外三条原则刻画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性特征,也即是劳资双方在工作场所中的互动所面临的结构性环境。
核心理论为分析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框架,给后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工作指明了研究重点和方向,拯救了劳动过程理论。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间,核心理论启发学者们开展了大量关于控制与抗争、权力关系、主体性、技术等议题的个案研究,深入描绘了各种各样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结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劳动过程核心理论的批判
然而,核心理论也受到了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劳动过程理论阵营内部的学者的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劳资关系的剥削性质和结构性对抗性质、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过程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等三个问题上。核心理论不仅被认为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核心理论的批评是核心劳动过程理论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沦为经理主义的拥护者。核心理论是经理主义拥护者,是指在该理论框架中,资本的代理人被赋予了过多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控制策略和决定工作的性质的自由裁量权,他们较少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5]。核心理论有此缺陷,是由于它建立在“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观点之上。保罗·埃德沃兹提出了“劳动力的相对自主性”观点,是要将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防止劳动过程理论误入认为微观层面的工作场所内的斗争必然演变成宏观层面的阶级斗争的歧途。然而,受该观点启发的学者们更倾向于考察本地劳动市场和制度、性别、公民权、亲戚关系等权变因素对工作场所关系的影响,漠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制约,从而有意无意地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利润下降规律”抛之脑后。其结果是,研究者们热衷于并强于关注不同组织、不同产业的工作场所内的劳资关系的差别,提炼管理控制策略、工人抗争和工厂体制的不同类型,创造描绘各类工厂体制的如“关系霸权”“老乡专制体制”等新术语,无兴趣也无力去考察当今全球竞争资本主义的演变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主要涉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根据奥多尔蒂的观点,主体性是劳动过程的一个维度,即个人或集体行动者阐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历并基于该阐释来动员各类行动的维度[6]3。布雷弗曼对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引发了关于“缺失的主体”的争论。争论各方都认为,布雷弗曼遗留下的“主体性”缺口应被补上。汤普森虽然没有将对主体性的分析纳入核心理论之中,但他却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倡导要建构关于“缺失的主体”的完整理论。从研究实践来看,核心理论继承了劳动过程理论对待主体性的传统做法,即主要是从抗争、认同的角度来处理劳动者的主体性,认为劳动者的抗争、认同等对管理控制的反应形式,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体性,此即为汤普森和纽桑所谓的“控制、反抗、认同”模式[7]。受唯物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核心理论处理劳动者的主体性的方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缺口。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核心理论关于主体性的观点仍未跳出二元论的窠臼,即它将复杂的社会生活两极化,一极是客观结构的压制性力量,另一极是能动主体的自由的、创造性的行动,因而核心理论仍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劳动者的主体性。他们更期望从不安全感、脆弱性等“人类能动性的不确定性”角度出发去构建一个关于主体性的普遍理论。
劳动过程理论阵营内部的学者认为,如何处理特定工作场所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埃尔格认为,核心理论框架强于解释企业内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不擅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展开更广泛的批判,因此它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局部理论”[8]78。埃尔格给核心理论提出的难题是,工作场所里发生的事件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比如产品市场、国家、文化和广阔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联系的,此即为所谓的“联接纽带”问题。该问题的存在,首先源于汤普森放弃了工作场所内的斗争可能演变成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在理论上区分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阶级斗争,虽然有利于将核心理论从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失败预测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也使核心理论丧失了考察工作场所里发生的事件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产品市场、国家、文化和广阔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联系的理论旨趣。“联接纽带”问题的存在,更是由于核心理论放弃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利润下降规律”等思想。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正是分析特定工作场所内劳资关系与广阔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的“金钥匙”。丢弃了“金钥匙”,则更无望开启解决“联接纽带”问题之门。
三、劳动过程核心理论的回应
面对前述批判,核心理论该如何应对?核心理论未来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学者们尤其是汤普森、雅罗斯和埃德沃兹都就此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些探索预示着核心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剥削和结构性对抗
核心理论沦为经理主义的拥护者和它所遭遇的“联接纽带”问题,都与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问题相关。由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测尚未成真,汤普森便据此放弃马克思借以预测资本主义命运的理论基础,即劳动价值论。然而,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核心理论关于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质的观点则成问题。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剥削是指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而剩余部分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如果劳动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则我们难以判断劳动者所获报酬是否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因而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质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与此相应,以剥削特质为前提的“结构性对抗”观点也丧失了基础。
雅罗斯试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剥削性的观点,用“结构性不平衡”来拯救“结构性对抗”观点。他认为,回归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坚称劳动力具有创造“增值价值”的独特性质的观点无法在经验上被证实。所以,应该另辟蹊径为“结构性对抗”观点寻找根基,该路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不平衡”。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被视为是一种让劳动力处于劣势的制度,而劣势源于被迫性的劳动力市场交换。因为劳动者除拥有劳动力外一无所有,“饥饿之鞭”迫使劳动者去结成工作关系,被迫去接受不平等的“贡献—报酬”关系。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存在客观的“结构性不平衡”关系。然而,客观的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不平衡”并不必然导致劳资双方在生产场所中的“结构性对抗”。雅罗斯认为,只有劳动者体验到并认为“结构性不平衡”不完全合理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在工作场所中开展争取更多报酬、更高福利、更好工作条件等的斗争,劳资双方才会进入“结构性对抗”关系[5]。因此,特定工作场所中的劳动者的主体性是“结构性不平等”与“结构性对抗”之间的中介变量。
然而,雅罗斯的观点可能会为核心理论带来更多难题。他不仅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且放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使得核心理论丧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完全是自毁长城。相比之下,布洛维的观点更能为核心理论提供武器弹药:首先,布洛维对资本主义结构特征所作的论断,为确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关系提供了依据。如前所述,依据核心理论,剥削是“结构性对抗”关系的前提。雅罗斯放弃了剥削观点,布洛维则仍然坚持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的立场,并认为剥削源于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布洛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而且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还导致收入不平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生产工具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之间的持久矛盾;正因为生产工具的占有者能够凭借他们对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权力去占有劳动者努力创造出来的剩余,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剥削关系[9]158-159。其次,布洛维的观点还为微观上考察劳动过程和宏观上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都提供了想象力的源泉。比如布洛维指出,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直接形塑了工作场所的支配,而支配能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如专制体制、霸权体制等;剥削特征会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成为问题,从而要求资本主义为阶级再生产做出积极的制度安排,如微观层面的劳动过程中的压制和认同制造、宏观层面的教育、媒体等,都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制度性安排[9]166。布洛维的这些观点,都是从资本主义结构性特征出发去考察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宏观趋势的范例。
(二)劳动者的主体性
面对关于劳动者主体性的批判,核心理论的回应是应兼收并蓄各方观点。如前所说,核心理论继承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传统做法,以“劳动力商品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将劳动者的抗争、适应、服从和认同等视为主体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对待主体性的方法,是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性特征为前提,考察行动者在该结构下的反应。这与后现代主义从不安全感、脆弱性等“人类能动性的不确定性”出发去建构主体性理论的做法不同。核心理论的主体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互为竞争性理论。雅罗斯认为,要推动核心理论更好地处理主体性问题,应弥合核心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应该兼容并蓄两方的观点[5]。也就是说,我们需接受两方的假设:第一,如后现代主义所言,现代社会劳动者的主体性通常具有如此特征,即不安全、脆弱的个体为维持“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自认重要的、有能力的个体”的这种自我认同而产生的焦虑,瓦解了他们进行批判性、反思性分析和抗拒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能力;第二,劳动者的焦虑不仅是由维持稳定的自我认同的需要激发出来的,如核心理论所言,它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的客观实际的反映,即劳动者害怕被解雇,害怕被降低工资,害怕丧失福利等。
(三)与政治经济的联接
核心理论在解决“联接纽带”问题上花的心思可能是最多的,其方案可分为三类:坚守中层理论的范围,通过方法创新来解决问题,建构新的理论模型。
由于受埃尔格的影响,雅罗斯认为,核心理论应该漠视宏观政治经济问题,保持其中层理论的本色。埃尔格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有边界,理论边界可从范围和层次两个维度来确定。雅罗斯继而指出,核心理论是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动态关系的中层理论,它的边界应该被限制在工作场所(层次维度)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范围维度);社会科学内存在劳动分工,解释宏观的、社会层面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任务,而非核心理论的任务,我们也没必要去重构一个企图能解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等趋势的核心理论[8]80。雅罗斯还指出,理解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研究者的责任,而非核心理论的责任。
埃德沃兹和雅罗斯都提出了从方法上解决“联接纽带”问题的对策。埃德沃兹的方案是多层分析方法。他指出,要开展多层分析,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描述产品类型、竞争激烈程度、工作场所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等环境特征,这些信息能增加我们对工作场所内的关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了解[10]。雅罗斯虽然不赞同构建新的核心理论,但认为可用“元人种志”和定量研究方法解决“联接纽带”问题[5]。他认为,通过“元人种志”方法,可以整合众多考察工作场所的个案研究资料,寻找蕴含在个案中的共性和模式,从而揭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趋势;若采用调查问卷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内调查数百、数千甚至上万雇主和雇员,就能超越单个企业的围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揭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政治经济的特征。
汤普森借用批判实在论的思想建构了“作为分层实体系列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型”。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或实体构成的多层次的开放系统;所有实体,无论是自然的或社会的,都有因果力和敏感性,即它们以某种具体方式影响其他实体或被其他实体所影响。在批判实在论思想的指导下,汤普森从资本循环、调节理论、资本主义多样性、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的角度具体考察了劳动过程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建构出一个“作为分层实体系列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型”,用以激发学者们去理解劳动过程与其他社会层次之间的关联。此模型包含五个层次的实体:积累体制、价值链、工作场所、既得利益集团、多元主体。在该模型中,积累体制、价值链和工作场所社会关系等先在结构都是工作场所中的目标和策略、行动者行动的前提条件而对劳动过程产生影响,而在劳动过程之内,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等相互作用,会产生出适应、顺从、反抗、认同等的劳动者的反应模式,这些反应反过来将对工作场所社会关系结构、价值链和积累体制产生影响[4]63。汤普森指出,建构模型的目的不是要发展一个解释劳动过程的总体框架,而是要揭示出哪些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劳动过程有潜在的作用,且对各因素的作用需作具体分析。
四、结语
总体而言,核心理论构建了一个研究工作场所层次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理论框架,实现了拯救劳动过程理论的使命。它以劳动力商品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出发点,勾画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三个结构性特征,即持续的重组、劳动控制的必要性和结构性对抗。它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性特征的诊断,已经被证明是分析管理控制、抗争、主体性、技能等劳动过程重要维度的坚实理论基础。
有如人无完人,不存在完美理论,因而核心理论遭受竞争性理论的批判十分自然。劳动过程本身在不断演变,用以解释劳动过程演变的理论工具也应不断经受系统性的反思和拷问。本文理清了核心理论所受的挑战和核心理论创始人及支持者对挑战所做的回应,为建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借用拉卡托斯的话来讲,以挑战为激励,不断开展与其他理论资源的对话,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劳动过程核心理论必将赢得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持续进步。
[1]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2):13- 36.
[2]王晓晖.劳动过程理论:简史和核心理论[J].前沿,2010(10): 87- 89+117.
[3]〔USA〕Edwards,P K. Understanding Conflict in the Labour Process: The Logic and Autonomy of Struggle [C]//David Nights,Hugh Willmott . Labour Process Theory.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4]〔USA〕Paul Thompson,Steve Vincent.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Critical Realism [C]//Paul Thompson,Chris Smith.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5]〔USA〕Stephen,J Jaros. Marxian Critiques of Thompson’s (1990) ‘core’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 Evaluation and Extension [J]. Ephemera, 2005, 5(1): 5-25.
[6]〔USA〕Paul Thompson,Damian P. O’Doherty. Perspectives on Labor Process Theory [C]//Mats Alvesson, Todd Bridgman,Hugh Willmott.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9-122.
[7]王晓晖.生产政治——中小型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9.
[8]〔USA〕Stephen Jaros. The Core Theory: Critiques, Defenses and Advances [C]//Paul Thompson,Chris Smith.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9]〔USA〕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0]〔USA〕Paul Edwards. Developing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Themes from Industrial Sociology and Future Directions [C]//Paul Thompson,Chris Smith.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42.
(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5-23
2012年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项目“私营企业的工厂体制与员工技能形成的社会学研究”[黔省专合字(2012)70号]。
王晓晖(1973—),男,贵州石阡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劳工社会学。
C976.1
A
1000-5099(2016)04-01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