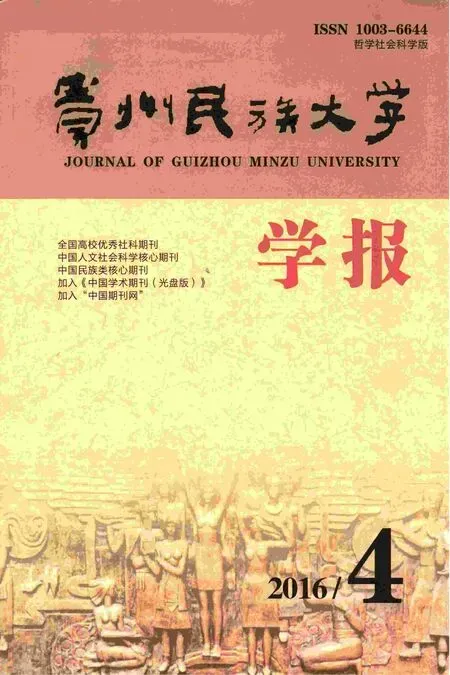文化遗产关键词:游戏
刘 谦,姚 曼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活动之一,游戏不仅见证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且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有着教化育人严肃的一面,也有着休闲娱乐轻松的一面;它可以是三五个毛孩在田间地头的玩耍嬉戏,也可以是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赛事;它不仅是儿童的专属,也成就着成人世界的互动与集体意识的表达。它不仅时时出现在远古祖先们的世界中,当代社会也随处可见它的身影。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这一日常现象,想要给它一个概念的边界和框架时,它却似乎总能够逃离束缚。现不妨从游戏一词的词源着手,关注其本源,探索其本质。
一、游戏的语词考古
(一)汉语“游戏”的词源学考察
“游”与“戏”两字在古代汉语里是分而有之的。《辞源》中,“游”的解释有:①在水中浮行;②河流的一段;③虚浮不实;④流动,流动的;⑤通“遊”,浮行为游,行走为遊,在古籍中两字多通用。[1]P2004《说文解字》又释“游”曰:“游,旌旗之流也,从□,汓聲。”[2]P563原是旌旗上垂下的飘带,可见其流动之感。因此,无论是与水相关的流动、漂浮,抑或是旌旗下垂的飘带的随风舞动,“游”字的本意给人以自由、无拘无束之感。《论语·述而》中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何晏注曰:“此六者,所以饰身耳,劣于道、德与仁,故不足依据,故但曰游。”[3]P85-86艺的地位虽不如正统的道德仁义,但对个人修养依然十分重要,因此需要游之。可见在古代中国“游”字即与正统、严肃的事物相分离,表达的是一种悠然自得、远离功利的态度。《庄子》首篇名为“逍遥游”,游于无穷而无所待,在绝对自由的境界中遨游,始得“逍遥”。“游”字所包含的自由、浪漫与无拘无束跃然纸上。
“戏”繁体为“戲”,《说文解字》释曰:“戲,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聲。”[4]P1108三军之偏,即三军之外附设的兵种,应当为非主力部队。可见“戲”字的本义与战争角逐有关,且表达正统、主流力量之外的含义。在《辞源》中“戲”的释义有:①角力,竞赛体力的强弱;《国语·晋》中曰:“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②开玩笑,嘲弄;《论语·阳货》曰:“前言戏之耳。”③游戏,娱乐;《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④歌舞,杂技;⑤姓氏;⑥通“羲”,“伏羲”也作“伏戲”;⑦险峻;⑧古地名;⑨大将之旗,通“麾”,引申为指挥。[5]P1306可见“戏”字包含的含义甚丰富,既有严肃的战争角逐,也指玩笑嘲弄之语;既可为孩童游戏、娱乐的总称,也可指向歌舞、杂技等具体娱乐形式。
“游戏”二字的连用最早出自于《韩非子·难三》中:“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6]P242此处的“游戏”直接与“大物”相对,在正规、严肃之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笑着对以重金招贤的楚国使者说道:“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7]P2145在这里,“游戏”意味着没有羁绊,没有束缚,即使处于污渎之中亦能享受自我的愉悦。《乐府诗集》中的《懊农歌》亦轻快地唱道:“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
由此可见,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中,“游戏”不仅指一般的嬉戏、玩耍,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超然物外、不追名逐利、逃离世俗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更体现着人们对自由、浪漫、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向往。
(二)西方语境中的“游戏”
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一书中曾对诸多语言中关于“游戏”、“玩”等含义的表达进行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语境中“游戏”概念所包含的特征至少有两层特性: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相比的超脱性以及暗含着的竞争与争斗。
首先是游戏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行为的超脱性。这一点暗合于汉语“游”、“系”、“游戏”的古义。赫伊津哈以英语“play a game”(玩游戏)的固定表达为例,“play”作为动词和“game”作为名词,两词中都包含着游戏的概念。“为了表达游戏活动的性质,名词里保留的游戏概念还是要在动词里重复。难道这不是意味着,游戏的性质特殊而独立,所以它必须脱离一般的行为范畴吗?游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做事情’,你玩游戏并不是像钓鱼和打猎那样‘做事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加莫里斯化妆舞会和从事木刻——你是在‘玩游戏’。”[8]P39
二是与军事、竞赛、斗争等联系在一起的含义。赫伊津哈提到古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里就充满这样的词汇,军事斗争或战斗常常叫做head-lzc或者hedu-lac,直译就是“战斗-游戏”。而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14节里,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接下来便是12个好汉的血腥搏斗。赫伊津哈评论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故事是否有历史依据,也不仅仅是解释那个地名的词源。唯一有意义的是,这一次搏斗叫做游戏,上下文并没有说他们不是游戏……显而易见,这里没有所谓诗歌的比喻,本来的事实就是,游戏可能致命,但它仍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游戏和竞赛在概念上是不分家的……既然在古人的心里,游戏和战斗是不可分的,狩猎纳入游戏的范畴就水到渠成了”。[9]P42-43游戏与竞赛、斗争的关联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西方语境中的“游戏”与汉语的“游戏”殊途同归。它们在本源上与竞争、军事活动等相关联,既有抽象的总称,在具体语境中也含义丰富。作为独立于一般人类活动的游戏,其特殊性值得深入探究。
(三)多义而动态中的游戏
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试图假借语言框住“游戏”。他思量着:
它们都是“娱乐性”吗?请你把象棋同井字棋比较一下。或者它们总是有输赢,或者在游戏者之间有竞争吗?想一想单人纸牌游戏吧。球类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球拋在墙上然后接住,那这个特点就消失了。看一看技巧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再看看下棋的技巧和打网球的技巧的差别。现在再想一想转圈圈游戏那类的游戏。这里有娱乐性这一要素,但是有多少别的特征却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考察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游戏;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出现而又消失了的情况。
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10]P47-48
维特根斯坦此番尝试的结果是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并非专属于对游戏的反思,有着更深层的哲学含义。也正因如此,它恰恰更好地解释了游戏概念的模糊与多义。正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体型、相貌、眼睛颜色、步姿、性情等等相似之处。不同的游戏似乎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游戏的家族: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并无法用一组共同的语义特征全部包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无法被清晰地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林林总总的游戏共享着一系列“家族相似性”。这系列家族相似性贯穿在游戏的动态性、超越性与文化性之中。游戏是动态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leika” 意义甚广,包括“自由移动”、“把握”、“使之产生”、“摆弄”、“从事于”、“打发时光”、“练习”等等含义。[11]P39而汉语中“玩”与游戏的“玩”,也体现着游戏以动态方式所涉及的诸多活动,既可以“玩足球”、“玩捉迷藏”,也可以是“玩音乐”。游戏是具有超越性的,是对世俗和日常生活规则的超脱。孩童可以在一本正经的课堂之余,大汗淋漓地奔跑、追逐,暂时甩掉学业的压力;康德经常使用“思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deas),“幻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magination),“宇宙观念的全部辩证的游戏”(the whole dialectical play of cosmological ideas)[12]P40,则是思维层面超越于世俗功利计较的思想活动。游戏是文化性的。它深深植根于各具特异的地方文化系统中。游戏的文化属性体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贯穿于人们对规则甚至道德标准的共识中,外化于游戏的器物与具体形态中。这一切,为人们从文化意义上解读游戏提供了必要的场景。
二、游戏的文化蕴含
千百年来,游戏构建出了一个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专注性聚焦场域。人们在游戏中体会到的更是一番心境。 正如赫伊津哈所说:“即使在最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游戏,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个事实隐含着游戏本身的非物质属性。”[13]P3当我们审视游戏包含的意义,它仿佛在向四处放射的同时又在不同的地方交汇成结点形成网状。在游戏的意义之网中,我们得以窥见它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一)游戏:作为文化传承的手段与路径
秉持着功能主义的逻辑,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游戏自然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好帮手。在以性欲为主题之一的《野蛮人的性生活》中,特罗布里恩德儿童们玩的盖房子、过家家等游戏都直接地加入了性的成分,为儿童未成熟的性欲和性放荡提供了发泄途径。未婚的青年人玩儿的游戏也直接带有调情的色彩。这些游戏满足了青少年对体育的热爱、审美和娱乐感的需求以及性欲的释放,成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一道独特的风景[14]。
于是在功能主义者眼里,游戏便作为常见的人类活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游戏总是先与儿童联系在一起,社会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游戏实现的。在游戏中,少年儿童的智能和体能都能够得到锻炼,说在游戏中儿童实现社会化或者濡化的过程一点也不为过。有民俗学者总结了游戏对于教育儿童的功能:智能方面,游戏可以训练语言的表达能力、增强计算能力、丰富想象并提高人的反应能力;体能方面,游戏则可以增强体力强健体魄,发展各种技巧;此外游戏对于塑造儿童健全的人格也是影响深远的,在游戏中可以培养勇敢坚强的心理素质,树立诚实公正的处世态度以及加强群体互助的合作意识。[15]
对于成年人来说,游戏同样是富于魅力的。作为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游戏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常常能为生活增添乐趣,同时越是竞赛性质越明显的游戏在增强集体意识、加强群体凝聚力方面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拔河,这个富有对抗性的游戏,在隋唐得到广泛推广。在隋代,人们以为拔河可以镇邪,通过拔河时鼎沸的人声和鼓乐喧天的欢庆,可以将危害农耕的鬼魅吓跑或愉悦主管农耕的神灵,是对农业生产丰收的祈福。[16]P20,133-134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专辟章节讨论“文化与娱乐及游戏的需要”。他说:“另一种完全非生产和非建设性质的游戏,如公开游艺,体育比赛,凡俗舞蹈等……它们在社会团结上却有它的很重要贡献。松弛和自由的空气,及此种公共游艺需要众多的参加者各点,都可促成新的社会结合。”[17]P82-83
(二)游戏:作为文化的象征与隐喻
“游戏是对重要生活事情滑稽性的模仿”,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得出游戏是“文化玩具性质的残余”的结论。[18]在他看来,因纽特儿童用雪盖房子、澳大利亚孩童玩标枪、苏格兰男孩大声对伙伴说道“你是我的人!”都与这些族群特有的古老文化相联系,是文化的涓涓细流流过人们身上的痕迹。泰勒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中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为纯粹的遗留,而游戏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跟古代文化的最富有教益的阶段之一有关”。很多游戏的源头已无可考,但从泰勒的观点看来,游戏与文化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局部与整体、功能发挥的关系,它本身就在展现着文化。
从解释主义路径出发,掩埋在游戏背后的社会文化机理能够更清晰地展现。解释主义人类学大师格尔茨和他那著名的斗鸡游戏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在格尔茨看来,游戏同音乐、仪式、文学等其他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供人类学家解读文化的一种文本。在巴厘岛上,雄鸡是男人的象征,人们热衷于尚属非法的斗鸡,它“展示出一个巴厘人实际是怎样的,如同在棒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道上或围绕一个牌桌所表现出的美国外观一样,巴厘岛的外观就在斗鸡场中。因为表面上在那里搏斗的只是公鸡,而实际上却是男人”。[19]P477斗鸡之于巴厘人不是理性驱使的逐利行为,而是边沁意义上的“深层游戏”(deep play)——让人陷入无理性状态的游戏。雄鸡的拥有者将鸡视为自我人格的代理者,一旁的赌博者则将斗鸡视为地位的争斗,而女人、青年人等社区边缘人群则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斗鸡根本上是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过程,通过将巴厘社会地位关系戏剧性地(拍打的翅膀和震颤的腿、羽毛、血、人群和金钱都是这场戏剧的重要内容)展现出来,社会现实(或者被想象的现实)及其意义“更加强烈地表达和更加准确地被感知”。[20]P502如此一来,抽象的社会等级秩序在能够被经验、被感知的维度上得以展现,也使得巴厘人看到自身主体性的一个维度,形成和发现自己的特征。而这种展现在格尔茨看来并非如功能主义者们声称的那样,旨在强化已有的社会秩序,而在于斗鸡本身的解释作用,是巴厘人“讲给他们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21]P506
同样是斗鸡,在中国是和走狗、六博、踏鞠等出现于先秦时期的古老游戏。[22]P5而在庄子那里,对制胜秘诀的解读透出了一派东方神韵。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庄子·外篇·达生》。
为周宣王驯养斗鸡的纪渻子,看到鸡“方虚憍而恃气”、“犹应向景”、“犹疾视而盛气”,判断斗鸡的胆识还没有练就出来,相反,只有“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即到了那看似呆滞的境地,反而修行齐备,具有了吓退对手的气势。流传至今的庄子解读,将动与静、强与弱的辩证关系演绎得生动直白。如此看来,游戏总可以担当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为人们理解特定的地方文化与思维范式提供重要的脚本。
(三)游戏:作为人类精神诉求的寄托
以上的分析在宣称“游戏就是文化、就是文明”的赫伊津哈看来定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游戏中诞生的:“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就像真正的酵母一样。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因此,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就是游戏的文明。文明绝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文明在游戏中诞生,文明就是游戏。”[23]P203赫伊津哈在此谈论的游戏,与其说是具体的游戏行为或游戏活动,毋宁说指的一种抽象的“游戏精神”或者“游戏性”。这种游戏精神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平等的竞争,对规则的遵守,自由与束缚之间适当的张力等都是游戏精神所包含的。赫伊津哈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欲望没有节制,苦苦追寻着确定的结果,昔日的神圣如今降为世俗,导致严肃性逐渐取代游戏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文明事实上不进反退。他的结论是“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24]P243
这里赫伊津哈对游戏的高度赞誉,已经超出具体的游戏活动与形式。当从人类精神需求层面理解游戏时,从有限的游戏进入无限的游戏成为另辟蹊径的思考通道。当代哲学家卡斯在其著作《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中指出:“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如果有限游戏有获胜者,那么这个游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终结。”[25]P3那些有限的游戏包含在无限游戏里,具有明确的时空边界。事实上,人生与世界是一场无限的游戏。无限游戏的形貌更受制于内在视阈而非外在规制。它的意义正是在于阻止游戏结束,而不在于像有限的游戏那样追求终结与结局[26]P7-8。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揭示到,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既不象植物那样,自己从无机的物质里加工制作其有机的建筑材料 ,又不象动物那样,通过各种本能与环境结构的联系先验地掌握自然韵律。[27]于是,人发现世界的偶然性,便有着双重行为:一方面感到诧异,因此,去探索、膜拜无限延展世界的可能性;一方面,不可遏制地寻求拯救,追求渺小的自我在大千世界生存的规律。人们在有限游戏的活动中,感受到无限的游戏的精神。哪怕是嬉戏的竞争中,人们体会到自身的力量、规则的阈限以及超越于世俗的无极心境,恰恰吻合了人们追求生存的力量、感慨世界无边的精神需求。由此,游戏具有了一份隽永的魅力。它从历史中走来,源远流长,诉说着时代风貌。
三、中国古代游戏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游戏,若从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算起,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而从地下考古资料的发掘来看,更是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出土于山西省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7000年)一个三四岁小孩墓葬中的石球已经可以被看作是当时儿童的游戏器具。[28]P3有学者总结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戏产生的四个主要历史渊源。一为生产劳动,如中国传统的投射游戏射箭、投壶、石球等投射游戏的起源大多都与原始狩猎劳动有关。甚至如今广受欢迎的荡秋千也起源于春秋时北方一个名叫山戎的部族的生产劳动。居住在山间的山戎人或为采集食物或为躲避野兽或为迁徙有时便会抓住藤条,荡过山涧。事后人们为了回味飘荡在空中的快感,便自娱自乐创造了最原始的秋千。第二种来源为军事活动,像我们今天熟悉的足球运动的祖先蹴鞠,据考证最初很有可能便是一种军事体育活动。风筝的发明也与战争有关,最早的风筝木鸢便是用来刺探军事情报的。第三种游戏的渊源则属社会风俗。比如起初用来赶走恶鬼的炮仗爆竹到今天已经成了喜庆之日必不可少的物品。 人们对神话传说的祭拜与敬畏,也成为衍生游戏的源泉。如乞巧游戏(每年七月初七少女们向织女乞求贤惠)便与牛郎织女的传说紧密相关。这一风俗自南朝开始流行,原本具有妇女祈求自己的针线活能像织女一样精巧的功利意义,慢慢这样功利色彩逐渐淡化,演变出很强的娱乐性和嬉戏性。第四种来源便为文化交流。如盛行于我国唐代的马球便来自于西域的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会带来游戏形式和内容的更新。[29]P77-93
从以上对我国古代游戏源头的分析来看,游戏大都产生于具有实用、功利性质的生产生活行为。人们同时挥洒着聪明才智将日常生活中那些充满刺激、自由、愉悦的环节进行着提取与再创造。游戏便在源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又在其所营造的规则体系与竞争模式中给人们带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超现实色彩的释放与欢乐。
从类型学上划分,我国古代游戏类型大致分为五种类型:角力型、竞技型、斗智型、猜射型与博戏型。角力型是力量的直接碰撞,通过游戏者力量上的竞争和较量来分出胜负。在古代,如相扑、拔河、包括蒙古族的摔跤都是典型的角力型游戏。相扑在宋代极为流行,凡朝中有盛大宴会都会请相扑手来助兴。《清明上河图》的一处便展示了民间相扑比赛的场景。小桥旁的大树下围着一群观众,中间两位相扑手赤裸着上身,正扬起手来互相进攻。这足见相扑在宋代的受欢迎。竞技型游戏比的不是游戏者的力量,而是一些特定的技巧和方法。射箭、蹴鞠、马球、甚至荡秋千、踢毽子都可以被视为要求游戏者具备一定身体技巧与技能的竞技型游戏。斗智型游戏顾名思义,主要是脑力活动的切磋。在中国古代游戏史上,围棋、象棋应当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斗智型游戏的代表。围棋在先秦时期便已流行,至明清时一直盛行不衰,如此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在中外游戏史上都是罕见的。它的规则十分复杂,对于思维能力的要求很高,必须高度发挥人的智慧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够玩转。直到今天围棋都被视为人类智慧与思维的结晶。猜射型游戏主要是通过游戏者对某些事物的形状、大小、颜色、数量等方面的猜测、揣度来决出胜负。它的运作与围棋、象棋等一般智力游戏要求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游戏者也须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各种社会知识。最典型的猜射型游戏当属猜谜语、猜灯谜了。古代的谜语或运用大量诗词典故,或结合生活经验,既能够考验人们的文学造诣、生活经验,也能够调节节日聚会气氛,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博戏型游戏与赌博类活动类似,胜负的结果需要以钱财来兑现。但与赌博不同的是,博戏更注重娱乐性,赌博更大程度上纯粹是为了获得钱财。偶然性恐怕是博戏型游戏最大的特点了,即使再高超的技术也不能保证始终不输。正是在这胜负难料的刺激间,人们寻找到博戏型游戏的乐趣。在今天广受欢迎的麻将便属这一类。麻将起源于清朝中叶,相传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流传到全国的。麻将娱乐性强,又有较强的刺激性,广受人们的喜爱。[30]P37-67
作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游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样貌形态、流行趋势,对游戏活动的定位也与所处时代的价值观、社会思潮等息息相关。蔡丰明认为我国先秦时代的游戏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样式并不丰富,风格也较粗犷原始,但那时留下的一些古老的游戏规则和技艺对后世的游戏影响非常之大,可谓我国游戏的滥觞期。汉魏时期社会高层权力的人物对于游戏的普遍热衷与爱好,使游戏活动带着浓厚的官家色彩,为我国游戏的发展时期。唐宋时期是我们游戏发展的鼎盛阶段,各种各样的游戏形式层出不穷。这段时期由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有力地冲击了旧有的贵族势力和门阀制度,使得游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普及化、通俗化特色。到了明清时期,游戏总体上来说种类齐全,但创新不多。放在古代流行过的诸多游戏活动,如蹴鞠、打球、相扑、斗禽、秋千、风筝等等,到了明清时代都十分盛行。虽然总体上创新不多,但明清时期棋牌类游戏,围棋、象棋等形式都达到了巅峰阶段。[31]P5-31李屏则认为儒家思想在历代的沉浮也投射在游戏道德性的消长面相中。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是我国游戏道德性确立的时期。“孟母三迁”的故事传达出儿童的游戏环境与游戏内容应当与读书求学这种“正事”相一致,游戏的道德性得以体现。魏晋南北朝至唐游戏十分繁荣,也是我国游戏道德性的淡化时期,自由开放、反对道德束缚的思想背景使得游戏中的道德性大为淡化。此一时期十分注重游戏的娱乐性,斗鸡等娱乐性强的游戏很盛行。同时受胡风影响,唐代女子也积极参加各种游戏活动,如围棋、骑射、蹴鞠、马球、秋千、捉迷藏等。宋元时期我国游戏的道德性得以恢复,在儒学复兴、重整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游戏的道德性得到强调。原本在以往自由奔放的游戏在宋代日益规范化、道德化。此时期多数女子也失去了外出游玩的自由。明清时期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而游戏娱乐的形式及内容也世俗化了。其实质是对于游戏道德性的强调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游戏与教化结合得比宋元更加紧密。一方面,达官贵人们的游戏走进寻常百姓家,世俗的游戏之乐也为士大夫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人们更加注重通过游戏来实现教化。如蹴鞠在这一时期被认为不仅具娱乐健身功效,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仁义礼智信物种德性。游戏能够修身养性被人们普遍接受。[32]
游戏,作为一个窗口,悄然承载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轨迹。从远古时代走来的游戏,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有的或许早已如烟飘散,有的或许穿上了新衣,至今还在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
四、作为文化遗产的游戏
游戏的种类、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它们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作为人类文化生活重要形式的游戏也被深刻地改变了。 如今的青年一代谈论游戏时, 电脑桌前手指与键盘鼠标的亲密互动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毫无疑问社会和时代技术的发展为游戏的形式和内容都注入了全新的血液,极大地形塑着当代游戏的形貌与功能。当携带着文化遗产的视角来审视游戏的前世今生时,游戏作为文化遗产的存在与涵养也展现出独特景象。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和历史一样,被赋予了纵深的时间维度,但是遗产更承担者连接古今的作用。人们谈到“文化遗产”时,常常用“保护”这一具有扶植、呵护含义的动词来统摄宾语。相反,如果“文化遗产”被砸烂、抛弃或销毁,则往往受到指责。可见人们对“文化遗产”所持有的意向性态度。遗产的生命形式是一项复杂工程。继承和保护文化遗产则可以被理解为延长文化遗产寿命的过程。[33]P116-124游戏,以其器物、规则、形态、甚至是道德与礼仪色彩的深浅映射着时代风貌,承担教化与传承之文化功能,吐露着解读地方性文化模式的密码,更承载着人类之于大千世界从渺小中寻求永恒的眷恋。由此,游戏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遗产。同时,人们探索如何延长游戏作为文化遗产的寿命时,又会遇到诸多困境。这些困境在一定意义上来源于游戏自身的多义与动态。人类会最终抛弃游戏吗?恐怕不会,因为剔除了游戏的世界,无异于精神的沙漠。既然游戏活动会一直进行下去,又何谈“延长寿命”?这里,便需要在“游戏”概念下进行更细致地划分。在游戏的嬗变中,可以从游戏的正式化程度分为:高度组织化、中度组织化及自发状态的游戏。高度组织化的游戏通常指被官方认可,并给以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组织化支持的游戏、竞技活动,比如古代的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中度组织化的游戏指具有民间组织依托或市场导向的游戏活动,这些游戏通常依托于宗教、节庆等民俗活动、商业活动等,鲜明地体现着地方文化和时代步伐。比如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中的搏克、赛马、射箭,再如网络化时代出现的网络游戏大赛,体现了互联网时代新一代游戏者跨越时空展开游戏与竞争的能力。自发状态下的游戏,是缺乏正式组织、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娱乐活动,最常见的是孩童的游戏,比如孩童们喜爱跳皮筋儿、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打麻将、划拳等活动。正如彭兆荣、格拉本等学者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环境和问题,每个国家都应当寻找更适合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途径。这些探索也具有全球的普遍意义。[34]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游戏保护,更应关注的是在专业化竞技比拼与展现的同时,需要以制度化方式保护游戏精神必备的公平与公正。比如,面对日益发展的人体替代器械研发,人们批判残奥会如今不再是残疾运动员意志力与体能的竞争,而逐渐演变成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人体机械化水平的竞争。如今AlphaGo与围棋选手李世石的人机大战也在游戏的场景下提醒人们关注人类与科技的边界机器关系。同时,通常专业化组织化的游戏竞争结果,往往附带着明确的奖励机制。这更容易导致人们背离游戏原本的超越性,而陷入世俗与功利。它也是人类社会在延展高度组织化游戏活动中应当警醒的悖论。
对于中度组织化的游戏,在追求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生命力过程中,由于其与地方文化的密切关联,更应关注游戏与其原生文化系统之间的自然承接。比如很多学者认为那达慕最早记录于1227年《成吉思汗碑铭》。这一传统保留至今,每年在牛羊肥硕的夏季,以蓝天白云大草原为背景,人们以搏克、赛马、射箭评价蒙古男性的阳刚之气,成为展现游牧民族精神和意志的重要手段。[35]试想,如果草原因为开采矿产而退化、小伙们因为外出打工而不能归家,这样的游戏盛会又怎能在21世纪依然保持曾经的赤诚与热烈?对于曾经有浓郁的民俗支撑、并有民间组织支持开展的游戏项目,其涵养与保护并不仅仅在于对游戏本身的保持,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变迁浪潮中,尽可能动用制度和文化的手段,保护社区人们的原生文化生态系统,以实现对游戏的呵护。另外,这些携带着浓郁地方文化的游戏,在网络技术迅猛更新的时代,不妨以网络游戏方式给以开发、推广。比如于潇翔试图设计“傣寨接宝”等便携式游戏,将傣族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电子游戏[36]。新媒体介入地方游戏,既可以推广文化多样性,又可以为这些获得地方组织支持的游戏,提供超越地域限制的形象显示度,从而间接为更多的人更好地认识这些中度组织化的游戏提供更多可能性。
自发状态中的游戏,与游戏者的日常生活更加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状态,而且这样的融合是散漫的、却又是惊人的。看似简单活泼的跳皮筋游戏,也可以直接反映时代主题。五十年代有一首歌中唱到“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37]楚雄紫溪上镇板凳山彝山小学生有一种名为“梭木头”的游戏:一二十个小孩子面对正为排成两队,对面的人用双手互相扣住握紧,形成一个长长人造链条。然后,一个小孩趴在这个链条的一端。这时候,大家就依次抖动手臂,将这个小孩从一端梭动着向另一端运行,直到末端。这一游戏实则和当地的生产生活交相呼应。楚雄市紫溪山镇当地多山,当时是原木生产的地方。伐木工人伐倒树后,需要把木头从山上“梭”到山下装车运输。一般是在圆木下垫上能滚动的小木棍,再用撬棍,梭动圆木并调整方向。有时也可以顺着山势直接用撬棍梭动。这些生产场面被孩子看到,自然就会产生模仿,化成游戏的方式取乐。[38]这些自发状态中的游戏,缺乏明确的组织者,因而显得散漫、随意,然而它是儿童教育中寓教于乐的自然通道,也是社会生活的微观缩影。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自发状态下的民间游戏,和许多草根艺术一样,既有其活态传承性,又有其流变性。[39]面对自发状态下游戏,在欣赏它的自然纯朴时,更需要俯身将这宝贵的生活细节给以记录,既可以以此理解人类心智发展过程,又可以体会社会发展的脉动。
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游戏,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活,与当地的生态和文化土壤直接相连,凝结着丰富的智慧和精神财富,在时间长河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的功能。游戏精神则直接体现着人们对于自然界、宇宙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保护和传承传统是每个民族的共识。正如刘魁立指出的,“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光荣任务,是繁荣和发展世界多元文化的必经之路,而且是每个民族对世界和时代应承担的责任。”[40]
[1][5]辞源.建国60周年纪念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Z].见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陈秉才译注. 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汉]司马迁.史记[M]第七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3.
[8][9][11][12][13][23][24][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10][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4][英]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M]. 刘文远等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15]萧放.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游戏娱乐[J].民俗研究,1993,(1).
[16][32]李屏.中国传统游戏研究——游戏与教育关系的历史解读[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
[17][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18][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20][2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2][28][29][30][31]蔡丰明.游戏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25][26][美]卡斯(CarseJ.P.).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M].马小悟,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27][28][德]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伯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33]彭兆荣,张颖. 文化遗产的生命样态[J]. 厦门大学学报,2015,(5).
[34]彭兆荣,Nelson Graburn, 李春霞.艺术、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中操行的体系[J]. 贵州社会科学,2012,(9).
[35]白红梅. 文化传承与教育视野中的蒙古族那达慕[D]. 中央民族大学,2008.
[36]于潇翔.严肃游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研究与应用[D].北京林业大学,2015.
[37]李翠含.民间儿童游戏跳皮筋的游戏仪式与文化表达[D]. 北京体育大学,2013.
[38]张新立.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儿童民间游戏研究[D]. 西南大学,2006.
[39]孙婕.贵州布依族小打音乐组成及文化探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6).
[40]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