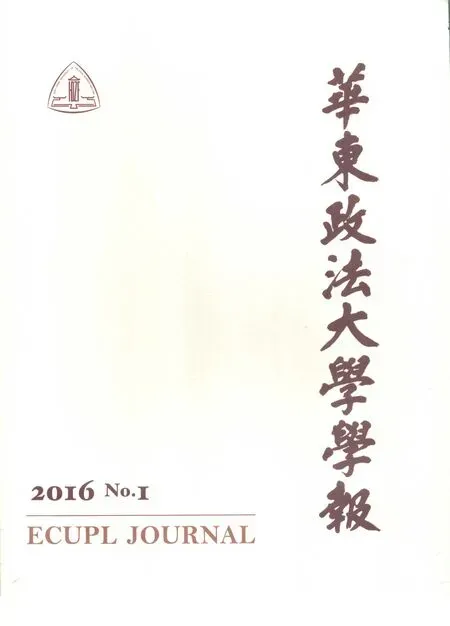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法学学术之开端
刘 猛
论中国现代法学学术之开端
刘 猛*
目 次
一、法学的基础:法律教育
二、现代法学的要件:研究机关与研究学人
三、结论
现代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是建立在清末民初四五十年的法科教育基础上的。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学研究,清末一系列的学堂和民初的法政专门学校,都是以实务为倾向,着力于培养政治人才和司法官吏,无法也不可能担负起寄养现代法学学术的重任。处身20世纪的世界学术格局中,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须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是要有现代的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关,一是要有中国的受过西方法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以法学为业研治学术。1917年的北大改革,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环境;20世纪20年代一批留学生的回国任教,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智识基础。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现代法学在中国才落地生根。
中国现代法学 法律教育 法政专门学校 北大改革 朝阳大学
在晚清七十年的变局中,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军事、技术的西艺到制度方面的西政,次第变更开来。经过国际公法的引入及清末新政修订法律继受西法,法律知识也开始了从传统律学到现代的法学的转换。
一、法学的基础:法律教育
传统中国的学问,是以经、史、子、集为标准分类,并以登科取仕的制度方式加以巩固和传承的。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天文、数学等西式学问,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最初,治国者虽然认为它们好玩儿,但并不把这些技巧与国家治理联系到一块。等到列强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国人开始正视西方,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科学”者,分科治学;相应的按照西式的分类,法政为其中一科。学习“科学”学问的一个载体便是学堂。
(一)晚清的同文馆及法律类学堂
关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论著,已有很多,论者大多都不约而同地把其源头追溯至京师同文馆。〔1〕关于法律教育的著述颇丰,主要有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上)、(下),载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亦载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贵连:《中国近现代法学的百年历程(1840~1949年)》,载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1867年12月,设立初衷为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创立后的第五个年头,聘请英文教习丁韪良开设国际法方面的课程。这跟丁氏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有关,也与一起外交事件有关。1864年普丹战争期间,普鲁士军舰在渤海湾拿捕一艘丹麦船,清廷按照惠顿著作中领海规则,提出抗议,船只得以获得释放。这让秉持实用主义的清政府意识到西方游戏规则的用处,为国际法的本土学习敞开了大门。〔2〕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页。丁韪良在回美国进修一年之后回到中国正式上任,教授万国公法。其后同文馆开设国际公法的课程,并组织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的最新国际公法方面的著作。然而,范围仅限于国际公法方面,未曾突破到民法、刑法等领域。〔3〕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页。个中原因,无非同文馆隶属于政府,朝中人士的着眼点还是在于能立竿见影的救亡图存工具,并没有学问的概念和长远的规划。其实严格说来,教授“万国公法”是为了培养外交人才,“万国公法”只是外交人才必须掌握的一门科目,不能算作法律教育,就像当下财经院系开设“经济法”,但不能把它们算作法律教育是一个道理;且按照那时的学科体系,“国际公法”能否算作法学尚属未定之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划入政治学的范畴。所以,以“万国公法”的教授作为近代法律教育的开端也不是没有质疑的余地。1897年开设的湖南时务学堂,还有其他各地的学堂,也有开设万国公法课程者。其主事者为梁启超,他的出身和活动重点决定了此学堂不可能侧重法律,其目的在于培养政治人才而非法律人才,法律学课程不过是这个培养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罢了。〔4〕关于湖南时务学堂,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下)》,载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0页;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70页。
甲午一役,中国战败,清廷不得不变法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1902年5月12日),谕曰:“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随后设立了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905年4月24日)两人奏请设置法律学堂,以培养专门的法律人才。法律学堂于1906年开学,除了有两门中国法(指大清律例等传统律学)的课程为中国教员讲授外,其他大部分的课程都由来馆修律的日本法律顾问担任。〔5〕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除此之外,学部在1907年2月2日设立了京师法政学堂,初“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继改为“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对应用的重视程度加强。京师法律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的培养目标不同,“再京师及各省法政学堂所设别科,其学科程度毕业年限,均与京师法律学堂大略相同。惟法律学堂专攻法律,毕业者宜专任之于司法官。法政别科兼习法律政治,毕业者可用之于行政司法两途,其性质微有不同”。〔6〕《学部奏法政学堂别科酌奖出身片》,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宣统新法令》(第二十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印行,第18页。关于京师法律学堂与京师法政学堂一个较详细的比对,参见孙慧敏:《从东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学教育与中国律师的养成(1902-1914)》,载《法制史研究》(台北)2002年第3期,第180-181页。所以严格算来,中国现代正规且系统的法律教育应自京师法律学堂开始算起。在地方上,开办较早的有1905年开设的直隶法政学堂,以培养佐理地方政治人才为目标,强调“以期适于实用”,其各科讲授者也是聘请日本人担任。〔7〕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9-204页。其后1910年,为了满足司法人才的需求,清廷要求各省法政学堂次第扩充,“特别要尽快培养审判和检察人员,以应付各地审判厅的急需”,并准予设立私立法政学堂。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各省的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是聘请日本人或者留日学生讲授课程。这些留日学生还编定了大量的法科讲义,实际上都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讲义的编译性作品”,先在日本编译印刷,然后运回国内发售。〔8〕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6-207页。关于法政学堂的名单,参见该书第211-216页。
清末之际,政治的氛围是救亡图存,所以这些法政学堂都是为了应人才需要而创设,并无长远的规划,带有极大的功利色彩。“除了京师法律学堂以外,中国政府之所以开办法学教育,并不是因为对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有所认识,而只是因为分设法律科与政治科,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教育体制,所以清末中国的法政学堂,大都是以培养行政官与外交官为主要目标。而那些在‘法政学’观念笼罩下的法校学生,虽然接受的是法学教育,但还是将找寻救亡之道、累积入仕资格当做主要的求学目标”。〔9〕孙慧敏:《从东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学教育与中国律师的养成(1902-1914)》,载《法制史研究》(台北)2002年第3期,第195、196页。主事京师法律学堂的沈家本、伍廷芳,中西合璧,深具世界眼光和长久打算,其计划创设的学堂自然别开一面,非其他学堂所能望其项背,但这毕竟是特例。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原来的入仕做官一途彻底断绝,官方和民间都在寻找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人才的接续和社会矛盾的消解,留学一项被纳入其中。留学生考试授官逐渐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10〕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9页。也可参见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56页。在留学所学学科中,无论是从难易程度考量还是与政途所需的应用性考量,法政科都是首选。特别是留日学生的示范效应,使得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影响了清末民初几十年的法科学习氛围。另一个替代方案便是大兴学堂。〔11〕关于兴办学堂填补科举制的功用和科举废除后造成的士与大夫的分离,参见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科举终止后,“各省次第将旧有书院改设存古学堂,以解决士子读书和出路问题”。〔12〕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其他学堂亦大兴,其中尤以法政学堂最为兴旺。而民间“乃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13〕《竞明〈法政学校今昔观〉》,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8页。因为在新近传入的西式学科中,法政科和仕途最为接近,实际上在清末民初背景下法政人才俨然成了传统“士大夫”的现代翻版。但是统而论之,这些学堂,无一不是以造就实用政治人才为目的,以弥补科举制废除带来的人才断缺为目的,不存在学问研究的概念;也就是说,那时虽然学制框架转换了,但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依旧,传统的登科入仕理念还是深植在每个学堂习法政科的人心中。
(二)大学里的法科
民初培养法政人才的机关,概分两类:一类是综合大学里的法科,一是专门法政学校。清末民初出现了大学,这些大学很多设有法科,但是面临的困难似乎大多一致,那就是教员的缺乏、授课内容完全照搬西方某一国家的法律或法条。这一方面与聘请的教员所属国家有关,也缘于中国尚未有自身的现代法典和单行法律这些载体。另外,其时大学中法科的诱惑力好似远小于法政专门学校,相比较来说,法政专门学校更易接触到法界名流并听其讲课,又因集众效应更容易进入法界工作,所以大学中的法科不占主导地位。其时设有法科的大学,概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堂(北京大学将在下文论述)。北洋大学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其“法律科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14〕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其从1895年开办之初就在章程中列有法律学门,“并在其下设若干法律课目”,在1899年产生第一批毕业生二十几人。〔15〕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第154-155页。虽然其中有王宠惠这样之后名扬国际法学界的学者,但是中西冲突下发蒙阶段的法律教育,在当时尚没有办法脱离单纯的翻译、介绍水平。1907年的时候,法律科仅有两名教师,美国人林文德教外国法,中国人刘国珍教中国法律。〔16〕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第155页。随后也多聘外籍教员,均以外语讲授,带有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大约在1914年,北洋“有外籍教员五十三人,除物理、土木工程系各有一英籍教员,法律系有一奥籍教员外,其余均为美国人。……法科的美国教员没有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他们除给学生讲些固定的课本外,就把学生硬塞到许多美国案例里;法科学生肚子里装满了美国案例,但要当律师、做法官,还得自修中国法律,因此不少北洋法科的毕业生都转入了外交界”。〔17〕北洋大学史料小组:《北洋大学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据《国立北洋大学三十七年班毕业纪念刊》记载,从1905年到1911年,法科法律学门毕业生仅9名。〔18〕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下)》,载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后来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建议,北洋法科并入北大,1918年停办,结束了其短暂的法科办学历程。
山西大学堂在最初筹办时,与英国驻沪总教士李提摩太达成协议,将山西赔偿教案的五十万两白银用于筹办中西学堂,后改为西斋并入山西大学堂,创办之初便筹划有法律学门,为西斋五门中的一门,内分政治、财政、交涉、公法等学。〔19〕《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将中西大学堂归并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折(附合同缮具清单)》,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到了解荣辂任监督时,在西斋添设一门法律学门,偏重欧美法律。〔20〕《〈山西大学纪略〉记教学上的重要设施》,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8页。在1906年的职教员表中,西斋教员英国人毕善功教授法律,并拿中西两斋教员中最高的薪水。〔21〕《1906年职教员表》,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0-1002页。外国人讲授,中国人翻译,学生笔记,下课后互相对证。由于师资落后、教学方法落后以及课程贫乏,学生所得知识十分有限。〔22〕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下)》,载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无论是北洋大学还是山西大学堂的法科教育,都少有可圈可点之处,皆需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进行讲授;虽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只因是其时少有的大学,其对法律教育的贡献实则乏善可陈。
(三)法科专门学校:以“北朝阳南东吴”为例
民初之际,清末的法律学堂纷纷改名法政学校,如前述的京师法律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便与财政学堂三所一起,合并为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也有很多是新设立的。而公立的法政专门学校,“乃据历来视学报告,其中办事尚称合法者,固亦有之。而如吉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风不良,教员学生诸多旷课;福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滥收学生,程度诸未适合,管理教授,亦多懈弛;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所招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中有英文算学尚抄写不清者;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既多缺席,管理尤欠精神;其余类此者,亦复不少”。〔23〕《1914年9月18日教育部咨行各省声明本部对于法政教育方针》,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页。私立法政学校更是有名无实,“无论合格学生不易招集,即相当教员亦所难求。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24〕《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为讲习科》,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5页。特别是南京的法政学校,管理宽纵,教授松懈,“此类私立法政,能少收一学生,则少误一青年,而国家社会将来可少受一分祸害也”。〔25〕《〈教育周报〉记南京法政学校》,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1页。政府因此饬令浙江私立赤城法政专门学校因招生人数突增、无端添列科目、倒填入学日期而停办。政府还停办了江苏省私立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26〕《1913年教育部派员察视私立法政之结果》,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7、648页。其中比较好的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是少有的几所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之一,约1916年之际,“最近邵校长任内,专任教员多至六人。周校长接办已减为四人。至饶前校长时,专任职或聘二、三人不等,余皆以兼任职充之。校长接事时,专任教授者仍有两员。至本年暑假后,魏易、陈介两员辞职,则仅添聘一人,而兼任教员,乃至有五十一员之多。据此实况,颇与初愿相违,惟事实所呈,亦竟不得不尔。本校为专门学校,以养成专门适用之才为务,以故如司法、如财政、如银行、关税等科学,历年以来,皆聘选法院、财部、银行等机关学有专长、经验宏富之员分别讲授。此项教员虽系兼任,亦既多历年所,于所任之讲科,类能以实务上之体验,为专精之启发。较之专任教员但能讲授学理者,于学生方面之利益,所获转多”。〔27〕《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五~六年度状况报告》,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627页。学校方面,更倾向于任用兼职的、从事实务工作的人为教员,历年皆是如此,国立学校尚且如此,其他各地的法政专门学校的实用倾向,管窥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如上海民国法律学校,其目标不在培养司法官或行政官,而是要使国民具有“完全法治之常识”。〔28〕孙慧敏:《从东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学教育与中国律师的养成(1902-1914)》,载《法制史研究》(台北)2002年第三期,第186页。
这些法政专门学校,以朝阳大学和东吴法学院在后世历史上名气最大,当然这基于多方面原因。朝阳大学是1912年由汪有龄等人创办的私立法科大学,次年8月开始招生,不长的时间内便获得教育部和法部的表彰。〔29〕参见王郁骢:《校史志略(一)》,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8页。其以注重司法实践著称,其毕业生多去做司法官,〔30〕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55页。这样一所法科学校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材为目标,而非培养法律研究人员。相对于其他私立法政学校,其课堂纪律较好,学校亦利用各种关系帮助学生谋取职位,以维护学校的声誉并继续招生于长远。经过多年的沉潜,朝阳大学的毕业生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至1930年代中叶,开始在法政等机关占据中层地位。〔31〕参见杨昂:《学风、世变与民国法学:朝阳大学研究(1912~1946)》,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1-62页。在这种集众效应之下,“无朝不成院”的格局逐步形成。正如陶希圣在《朝阳大学二三事》中回忆的:
中国法学与司法界,朝阳大学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说是主流。法律教育史上,朝阳大学应居第一位。希圣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出身的一个人,何以这样推重朝阳大学及其校友。我推重朝阳大学,并不是贬低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法科与法律学系出身的人士不一定进司法界,朝阳大学的校友却大抵受任法官。中国司法史上,法官之第一流,不止于朝阳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专门学校、还有东吴法学院,皆出了第一流法官。但若说朝阳大学出身的人士为司法界的主流,我想朝阳大学的校友是当仁不让的。〔32〕黄怀周:《〈法律评论〉纪念朝阳大学创立70周年和〈法律评论〉创刊60周年专刊简介》,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60页。
朝阳大学还有值得称赞的,那便是《法律评论》周刊和讲义。《法律评论》(The Law Weekly Review)创刊于1923年7月,主要有论说、判例商榷、法界消息、外国法制新闻、裁判小说、参考资料、大理院解释、大理院判决及裁决全文、重要法令及公文等栏目,每期30页左右。《法律评论》“意在商榷法制,批评判例,凡足资司法改良者,靡不具载。”其旨趣“要在保司法之尊严,图法制之改善,而溺职违法者,且将予以针砭,期于法治能举其实,司法独立,而后国家乃有法治之可言”。〔33〕张耀曾:《题辞》、林长民:《题辞》,载《法律评论》周刊创刊号,1923年7月1日,第1、4页。其目标在于“1、研究法律问题以推进司法改革。2、评论法院裁判以探究法律真谛。3、公布各省法院新闻,使民众知晓各地司法是如何运作的。4、刊发介绍各国的法律和司法。5、当司法受干预时,帮助法院维护真理和正义。6、当司法人员有公职不法或违反法律时,帮助民众申冤。7、评论关涉上海及他处会审公廨和领事裁判权的事务,以引起外国人的注意”。〔34〕Kiang Young,“The Law Weekly Review Foreword”,载《法律评论》周刊创刊号,1923年7月1日,背面第1页。可见,《法律评论》创办的意图,并非在打造一份学术期刊,而是意在研究、改进司法实践。从创刊号中张耀曾、梁启超、章宗祥、林长民的“题辞”和江庸的“发刊词”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几位论述时代背景及创刊心愿,所谈的都是法官和司法问题,没有法学研究的内容。即使它间或刊载一些较有学术性的文章,可是在正本期刊中所占分量极小,不能算它的主要部分,它与《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那种动辄一篇文章十几二十页的学术期刊,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学报》,在学术性上也要比它强出很多。
朝阳讲义的名气很大,据学子回忆:“学校自办有印刷部,教师讲义在授课一日前交稿,至授课之日一定发出讲义,授课时口授者及黑板补充者,学生随堂笔录,由各班优秀学生随着整理出朝阳大学一套法学讲义,于法学各科称得起是完美无缺,一时各大学多取为研究法学或应考法官与一般文官重要参考资料。”〔35〕黄怀周:《〈法律评论〉纪念朝阳大学创立70周年和〈法律评论〉创刊60周年专刊简介》,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55页。陶希圣在《朝阳大学二三事》中说:“民国19年(1930年)之前,朝阳大学出版的法学讲义,包括民刑实体法与诉讼法,一部丛书,事实上全国各省区法政学校大抵采用为法学教本……北京大学法科或法学院一直未将法学讲义出版问世。朝阳大学出版可以发行全国的一套讲义便遍行全国各省区法政学校,为课程和参考的典籍。北大法科既不争先,朝大也就当仁不让了。”〔36〕黄怀周:《〈法律评论〉纪念朝阳大学创立70周年和〈法律评论〉创刊60周年专刊简介》,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60页。北大何以不印制讲义呢?因为在蔡元培改革前的北大,“以教员印发讲义,而在讲堂上照讲义演述一遍,便算尽责,并且这种讲义,年年如此,永不修增。学生领了讲义,就算得了学问,不要笔述,也不要看参考书,不要做实验的工夫。”参见蔡元培:《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这导致了学生的不用功,“只是用现成的讲义,按部就班地去教学生。学生得了讲义,心满意足,安有进步?”参见蔡元培:《〈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以至于“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参见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0页。因此,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就说要“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静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参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关于此措施的具体实施情况,可参见杨瑞:《通往学术之路:蔡元培与北大法科的学术化进程(1916-1927)》,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46页。它风行一时的直接原因却是:
何以民国17至19年(1928至1930年)以前,法学讲义总是北大与朝大领先?这问题的答案是当年北京是国之首都,而民刑事法令与法院审判依据的法理,皆是清末改制的法律案传承下来的。清朝设立修订法律馆,修订民刑律及民刑诉讼法,大抵聘日本法学家协助起草。如刑律即是冈田朝太郎,民律即是松冈义正,商法即是志田钾太郎等主编。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暂行新刑律是以冈田博士主编的刑律草案为底本。民律草案未得公布实施,民事审判以修订法律馆订定的《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为依据而参考松冈博士的民律草案,名之曰《法理》。”“于是北大及朝大的法学课程,刑法及民法为其主课,刑法教授张孝移先生原是协助冈田朝太郎起草刑律的刑法学者。民法教授余棨昌先生就是大理院的民事庭长,后来升任大理院长。各级法院民事审判固然依据《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实际上仍以大理院民事判例为准则。棨昌先生讲授民法,自当居于权威地位。张孝移先生讲授刑法,不发讲义。学生们记下笔记。在北大法律学系里,林佛性同学的刑法笔记后来编辑成书。林先生亦以助教讲授刑法,并升为教授。由此可见,朝阳大学的法学讲义,自有其权威。其通行全国各省区法政学校,为课本或主要参考,甚至辗转传抄,是事理所当然与必至的了。〔37〕黄怀周:《〈法律评论〉纪念朝阳大学创立70周年和〈法律评论〉创刊60周年专刊简介》,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60、61页。
可以看出,朝阳大学讲义风闻一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撰写讲义的教授是实务部门的领军人物。揆诸历史,以今之视昔,这种讲义教科书中有多少学术含量,值得思量!
应该说,有两个因素限制了朝阳大学的法学研究,一是其任教者多以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留日学生带有很大的速成成分。朝阳大学从成立时主导其事的汪有龄到后来的董事长居正,还有很多任教的老师,都是留日学生,带有浓厚的“东洋化”色彩。〔38〕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1页。留日学生无论是留学的心态意向还是所选学校,都有很大的实务倾向。“在学术上,留学欧美的学者大量学成归国,在政府与欧美关系日渐加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政学两界逐步取代了留日学者的地位,这一潮流的更迭体现在法学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朝阳大学在法学界的地位开始走向衰弱”。〔39〕杨昂:《学风、世变与民国法学:朝阳大学研究(1912~1946)》,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2页。二是师资方面虽然其时在朝阳任教的教授大多为名流,但“朝阳大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四川还是在北京,都是巧妙地利用北平(京)高校集中的优势,聘请兼职教授,或婉商的办法,聘请著名教授讲课,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科教授和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均是朝阳大学的教授。即使设有专职,也是极少数”。〔40〕韩培基:《回忆朝阳大学的办学精神和教学特色》,载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69页。其教员多为兼职教授,这些人往往以授课为主,对于学校的义务也仅止于此。
通观朝阳大学的教师、期刊和讲义,以及主政者的办刊办学理念,可以看出朝阳是一所以实务为导向的法科学校,而“无朝不成院”的氛围形成之后,已成的优势只会渐次的加重这种倾向。正如有人回忆的:“我校与法理一项,固属研究无疑,而法典条文之娴熟,阐明之准确,尤为他校望尘莫及。使执同学于途,诘以某事实,及其应适用何种法文,率皆前后贯通,应对如流,故我校以法律之实用见称,良有以也。”〔41〕赵金亭:《离别感言》,载《朝大校刊》(校庆特刊)1935年6月10日;转引自杨昂:《学风、世变与民国法学:朝阳大学研究(1912~1946)》,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寥寥几句,道出了朝阳的实用风格。在这种实务导向的教学风格之下,朝阳大学很难谈得上有法学研究。
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东吴大学的政治学教师、也是一位律师兰金(Charles Rankin)1915年“心血来潮”在上海创办的,他认为这是“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出色贡献的绝好时机”。〔42〕[美]康雅信:《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王健译、贺卫方校,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兰金的计划得到了曾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罗炳吉(Charles S. Lobingier)的热情响应。罗氏是比较法和罗马法专家,到中国后,他就“关注建立法学院的可能性”,并认为“应当首先将外国法律制度教授给中国年轻人,让他们将来从中选取素材建立他们新的法律体系”,他为其新探索设计了一种内容广泛的比较法课程,并提议将“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作为法学院的名称。在1919年的一份课程表上看,“法学院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充分掌握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以培养可以为中国法学的创新和进步做出贡献的学生为宗旨”。〔43〕[美]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贺卫方校,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这一时代中国没有自己的法典,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摆在面前,学习西方相关国家的法律也就成了应急之策,于是,东吴法学院提出的对策就是讲授比较法。但是,无论法学院如何宣称,事实上它早期的课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比较法学习。正如一位20年代的毕业生所说,“很明显学院被认为是一所比较法学学院并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它同时教授中国法和英美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学习不同的法律本身,而从未更进一步(指进行认真的比较法学习)”。〔44〕[美]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贺卫方校,第587、589、591页。
由此可以看出,甫经成立的东吴法学院主要是进行英美法的学习,在交通中西方面尚未成长成熟。据康雅信教授的研究,1927年至1939年这段时间,东吴法学院“才建立了它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法教学”,“在所有方面实现了真正的比较法教学,包括开设的课程、教学方法,以及通过其研究生课程和刊物进行的学术研究”。〔45〕[美]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贺卫方校,第593-594、616页。
20世纪最初十年期间,由于清政府的推动和现实利益考量,法政学校遍地开花。到1916年时,法政学校与学生的数目都远高于同期其他科类的学生数目。据民国初年的调查,许多私立法政学校“完全是营业性质,教员资格不够,常时缺席,敷衍教学,学生程度很差,来去无常,学额任意填报。”无论是清廷直接开办的还是地方开办的,无论是综合大学里的法科还是法政专门学校,在1920年之前,要么因须聘外国人讲授而缺少中国的研究者,要么因为实务导向法政学科始终不脱工具窠臼,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充斥现代理念的学术研究机关,其根本不具有现代法学生长所需的土壤,都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它们不过是在强国御侮的形式下奉行实用主义的工具性托付,这种工具性托付一是由于外敌侵犯,期望反抗列强;二是由于内部的帝制,期望改变无能的政治,在最短期内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如此,哪里会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在内,哪里会有法学可言!〔46〕关于清末到北洋时期一个法学发展的概括,参见王泰升:《四个世代形塑而成的战后台湾法学》,载台湾法学会台湾法学史编辑委员会编:《战后台湾法学史》(上册),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贰部分。
二、现代法学的要件:研究机关与研究学人
以上梳理了近代中国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法律教育状况。当下研治中国法学史的学者,往往会不经意地把法律的讲授算作法学发展的一个步骤,并把中国现代法学的开端追溯至同文馆“万国公法”的讲授,实则并非如此。虽然法律教育对于现代法学的诞生居功不小,是中国近代法学萌芽和诞生的基础之一,〔47〕何勤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载《法学》2003年第12期。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学研究。法律教育可以是一种职业教育,现代法律是舶来品,只要有能讲授法律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留学归来知晓大概却并无精深研究之人,大体都能开班授徒;但是这些教员并无研究法学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过是在传授一种技能罢了。现代法学作为一种学问,必然不会产生于培养外交、行政人才的清末法律学堂中,也不会产生于职业性的法律学校中,它只能诞生在一个现代的大学或研究机关里;〔48〕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曾说,“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关于大学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性,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230页。且“中国现代法学”的出现,不可能依靠外籍教员的力量,只能倚靠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所以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学术,必须奠基于两个条件之上:(1)现代学术研究机关的存在;(2)中国致力于学术并以此为志业的研究学人的存在。法学亦是如此。
(一)研究机关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这已属定论。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其预备科和附设的带有官员速成培训性质的仕学馆、进士馆中,便有大量的法律课程;由京师大学堂监督的译学馆,也开设有法律类课程。〔49〕参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3页。1909年3月,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在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开学,法律学门第一届12名学生。〔50〕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北京大学校史》中说“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参见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北大档案馆工作人员李向群在“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历史”中所述,“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于1910年3月31日在马神庙公主府旧址举行”,文载《北京大学校报》第1116期,2007年3月20日第4版。似“1910年3月31日”最为可信。课程中有《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律考》《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等,并具体规定了各科目的讲习办法及教材的编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传授。〔51〕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页。后法政科改为法科,下设法律学门、政治学门和经济学门。不论哪个阶段的法律教育,仍然以培养行政人才和外交人才为目标,其实务倾向加上这种发蒙阶段的初练,仍然谈不上学术研究层次的法学。民国六年(1917)之前,要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么是贩卖西学西风压倒东风,但是都没有注意到研究。〔52〕参见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3、834页。
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及法科:“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要求学生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在掌校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广纳人才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提倡研究设立研究所增加参考书,设立各种学会砥砺学生的品性和人格,一匡时弊,风气为之一变,才使得北大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学术研究机关。〔54〕关于蔡元培的改革综述,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第275页以下。
之前的法政教育,“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55〕蔡元培:《〈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那时候的北大也是如此,“各科以法科为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56〕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但是风气最差,大多数人“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57〕蔡元培:《传略(上)》,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实际上这是清末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传统的延续,这种科举时代的门生观念和升官发财的陋习,并未因共和制的政治改变而洗尽,还传染文科理科甚重。〔58〕参见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蔡元培的初衷,是保留“学”的科目,把北大办成文、理科的大学,其他的“术”科如法科、商科调出北大,成立专门学校,但是因遭反对未能成立。其后,在他的办学理念统筹下,北大评议会通过《研究所通则》《研究所办法草案》,规定设立了法科须设研究所,包括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研究所,其中法律学门的研究方法是各国法律比较学说异同评、名著研究、译名审定等。〔59〕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5页。1917年12月,王建祖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法科各研究所“可告成立”,开设的科目中有“比较法律”,担任之教员是王宠惠。后来“王君宠惠担任之比较法律,前月即已开始研究,每星期由研究员分班前往就学”。〔6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王宠惠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后又游历欧洲诸国,是真正具有比较法视野的大家。后来蔡元培回忆:
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国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习,引起求学的兴会。〔61〕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蔡先生的这段回忆,常常被人引用,但是没有人把它当做一段很重要的学术史资料。实际上正是这段话,框定了现代法学在中国诞生的大体时间。正是蔡元培一系列的改革,才使北大成为一个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学术研究机关。受西方特别是德国教育理念熏染的蔡元培,把北大提高到一种学术研究的高度,开始脱离传统上登科取仕工具的趣味,对于研究者、学习者来说大学不再单单是一种工具,而更高一层的,还是一种目的,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载体。〔62〕关于蔡元培所受德国大学观影响的研究,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32页;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载氏著:《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增订版。那么其时的北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呢?概而言之,可以说是以研究为主导的学术独立自由氛围、学人间交流的环境。前者是蔡元培通过大力改革、聘请新人专任学者、设立研究所实现的;后者则立基于废止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和学长,改设为五组十七学系和系主任,法律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史学为第五组。这样是为了能够科际沟通,以打破各自的界限。〔63〕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第294、295页。也可参见杨瑞:《通往学术之路:蔡元培与北大法科的学术化进程(1916-1927)》,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近世早已不是上古时代那种学科贫乏的年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得学者们逐渐无力靠个体的力量来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20世纪这种风气越来越盛,这种集合成一个研究社群的好处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得到证明,研究机构成员运用的是一套话语系统,他们之间定期、不定期的交流会激荡思想的火花,“思想与思想的接触往往明显地刺激了观察与创造性。没有相互接触,观念和经验将仍然保留为严格地属于个人;可是,通过互动的媒介,观念和经验就可以变成创新和发现的要素”。〔64〕[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1页。
作为当时改革最成熟成果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显示出了这一学者、学科间沟通的成功,“这一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机构,通过所内各式各样的集会以及期刊的发行,为学者提供了会面及纸上交流的机会,显然是促进学术成长的一个关键的、极为重要的因素”。〔6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4页。关于学术期刊在近代学术建制中的作用,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效果很快明晰的显现出来,其影响是全国性的,吕思勉在谈出版问题时曾说:“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不是肤浅的政论,就是学校教本,或者很浅边的参考用书。当这时代,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为不合时宜……还记得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也。”〔66〕吕思勉:《蔡孑民论》,载《宇宙风》1940年第24期;转引自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页。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和涵养之下,法律学系延揽了一大批有学识的专任师资,包括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等,他们不是官吏,不是律师,而是受过正经西方学术训练的职业学人。他们以教书研究为职业,也以教书研究为志业。
这批人开展学术研究,之间的讨论交流和合作十分频繁;还在北大指导学生进行翻译,间接地进行学理研究。他们创办了《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北大同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有其他社会科学的教授如黄右昌、顾孟馀、陶孟和、高一涵、皮宗石等形成了一个“研究问题、输入学理”的学术社群或共同体。这一切,都是这个地理上与北大文、理科并行的第三院,给现代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二)研究学人
现代学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不能靠聘请的洋教习,也不能靠出国买一张文凭回国混迹政学两界的半通不通者,更不能靠以教学为中转站却怀揣升官发财之梦时刻准备进入政界的人;它必须靠的是本国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鉴于现代法学是一种西方的舶来品,所以这种法学学者是由留学产生的,他们在国外扎扎实实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回国后把教书研究作为职业、志业,期望媒介中西调和法理,形成中国文明的法学。〔67〕留学生在中国现代法学发展中的作用,参见何勤华:《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6期;对于留学生在“学院化法学”建置过程中的作用,参见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参见袁哲:《法学留学生与近代上海(清末—1937)》,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清末的强国御侮之道,分为两途,一是国内的自强,以洋务运动为样本的购买新式武器和聘请洋人帮忙的方式,另一方面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期待他们学成回国对国家有所助益。老大中国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有赖留学生这一群体的爱国激情和智识努力。〔68〕关于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140页。留学运动始于向西方学习的20世纪下半叶,有论者把清末这场浩浩荡荡的法科留学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即1874年到1895年的初始无意识的零敲碎打阶段,1895年到1911年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蓬勃发展阶段。前一阶段是无计划的派遣,后面一阶段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滚滚成洪流之势。〔69〕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就现存资料来看,首先出洋留学修习法科的人是伍廷芳,时为1874年。其后有自费的个人或小规模的政府派遣,目标国家主要集中于欧洲的英法。〔70〕参见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页。甲午之后,国内留学之风从之前的趋向英美转向趋向东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距国较近、路近省费、语言近于中文这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跻身强国之列,这一系列为国人刮目的举动所产生的范例效应,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东渡日本习法政的人数增长并未换来成正比例的后果,归国之后,这些留日学生绝大多投身政治,并未带动中国法学的发展。〔71〕其实,那时日本也是一个刚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其学术原创性少。胡适当时说:“中国人在日本留过学的,先后何止十万人,但大多数是为得文凭去的,就是那最好的少数人,至多也不过想借径日本去求到西洋的文化。”(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虽然胡适说这话带着欧美留学生轻视留日学生的心理,但也是有很大的道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关,法政学仅为一“术”,不足以言学问,且传统上读书便是为了取仕做官。没有一个理念上的转变和制度上的支撑,单凭个人之力无法移山。所以回国后他们要么把大学当做晋升的中转站,要么当做赚外快的兼职。时掌北大的胡仁源校长总结教员如流水来去不已的原因,其中一条便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72〕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习法政学科之人大多是抱着回国实用的目的,上者怀报效祖国拯救政治之愿,下者无非看作升官发财之阶梯。这种整体心态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去日本留学者入大学者颇少,入速成科者尤多。入大学本身较难,另外他们对于自身所要学习的也颇有一些清醒,知晓无须进入研究的地步。加上时局混乱,结果是种种乱象横生,社会评价度也很低,蔡元培回忆说:“那时候到日本学法政的很多,有大部分是入私立学校或入速成科,并不认真求学,甚有绝不到学校,也不读书,在日本过了多少时候,就买一张文凭回国了。”〔73〕蔡元培:《〈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大半因为日本国立名校能够接纳留学生人数较少,大多数留学者入私立学校或速成科,总体质量当然差劲。〔74〕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8年1月3日)《学部奏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及各省按年分认经费章程折》中说:“然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7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曾尔恕等点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七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6页,当然,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许多人对国家贡献多有,并非个个不成气候。〔76〕参见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留日学生对于中国的近代政治、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77〕关于留日学生在政治及教育中的贡献,可参见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留学生在法制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参见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但是对于中国法学贡献甚微。
随后,清政府对留日习速成科采取了限制政策,之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渐次增多起来。民国初年,去向欧美留学的人员增多起来,庚款、稽勋局等委派输出大量人才。归国后的留欧美学生和留日学生也俨然两个集团,前者大多看不起后者,认为他们是从“二道贩子”那里学到的知识。蔡枢衡感觉到留日习法者作风的共同特色是“注释或解释条文中心主义”,“德、法的法学著作常比日本的法学著作质高品优”;〔78〕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无论是以其时经历此过程者的描述,还是百年之后再回顾,持之平允地说,欧美留学生确实整体上比留日学生水准要高。〔79〕与留日学生相比,“欧美的法科生明显学养深厚,他们大多进入正规的法律学院肄习,学有所成。”一个证明性的例子是,1906年,学部举行第一届回国游学毕业生考试,考取最优等的四名法科生都是欧美生。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即使在社会层面,按工资的标准,留日学生也是沦为二等,参见袁哲:《法学留学生与近代上海(清末—1937)》,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这恐怕还是与留学意向有关,留日者大多数为了学习法政常识取得功名以回国投身政治;而留学欧美者则是处身于西方的现代大学中,受西式大学理念的熏陶渐染,回国前概已形成“以学术为业”的理念,回国后自然倾向于进入大学做研究一途。蔡元培改革北大,并裁减官员型教员和兼任教员,增加专任教员的数量,〔80〕杨瑞:《通往学术之路:蔡元培与北大法科的学术化进程(1916-1927)》,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亦为这些想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留学生提供了职位。但是,我们不能说留日归来的法科教授没有为中国法学的诞生做出过贡献,只是他们的贡献要等到蔡元培的北大改革、等到留学欧美的人回来导致风气为之一变之后,他们才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法学诞生与发展的合流中,积小流以成江海,共同作用渐次成型。
清末民初是中西冲突下建构民族国家的时代、文化交融的时代,也是西化很风行的时代,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有大批留学德、法、美、英、日的青年人回国,带回西式的理念和信仰,带回现代学术的种子,他们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法学的中流砥柱。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意义重大。“他们在中国各法律院校任教,传播法律知识,翻译法学著作、教材、论文,创办法学刊物等方面均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81〕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页。到了20世纪40年代,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大学教授与副教授,法科有339人,其中留学海外的300人,占88.5%;参见该书121页。由于在西方时受到熏染,认识到大学教授承载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传承之重任,虽是一种职业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翰林,不以做官为目标。加之国内新式学校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既能糊口又能张扬梦想的场所。改制后的北大作为拥有法学研究机关的最高学府,为这些法科留学生提供了研究的环境,提供了一展身手的空间,在吸纳了一批留学生为教授后,开启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征程。〔82〕许章润教授把近世中国的法学家分为五代,其中清末民初的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王宠惠等诸公为第一代,王世杰、钱端升、吴经熊、程树德等人为第二代;第一代法学家亦中亦西,且多涉身政治;1920年代初期第二代“接受了现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律从业者逐渐上场,面对新问题,秉持新理念,尝试新范式,整个法学面貌为之一变,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滥觞于此,为第二代。”许章润:《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至20世纪20年代左右,经历清末民初近四五十年的史前准备,实现由“法学在中国”到“中国的法学”之转换,既因征程劳力,也是水到渠成。如果按照费正清剑桥学派“挑战—回应”模式分析中国近代史的话,那么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不得不反抗,不得不下水,去参与国家间竞技的世界游戏。这毁了中国,使得传统凋零不已;也成就了中国,使其在涅盘中获得重生。暂且不置价值性评估,我们可以看到,法学作为一门舶来的科学,不同于“博稽中外”、“参酌各国法律”的立法活动,也不同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文馆、法政学堂讲授,还不同于民国时期以习“术”为目的的专门法律学院的照本宣科。它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律学或律学解释学,而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法律产生运行的一门学问,它至少、应该要达到一种研究的水平。改革后北京大学为现代法学提供了一个机构的预备,留学归来、具有扎实学问的学者为现代法学提供了智识基础。如果说法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话,至少是这两者齐备之后的事。确切地说,是王宠惠在北大法律研究所指导研究、甚至“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之后的事,那时才可作为现代法学的开端之时。研究者多把中国现代法学溯至同文馆或京师大学堂甫成立之际,“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83〕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氏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实在是对学术史“考镜源流”无甚裨益。因此,按照上述两项必要条件,即研究学者和学术机关,1917年改革后的北大,其法科研究才算中国现代法学的开端,1920年代左右现代法学在中国方始诞生,这之前的法律学研究都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学术。〔84〕王泰升教授在《四个世代形塑而成的战后台湾法学》中说:“许多在欧美或在中国接受西式法政教育者,例如,张君劢、王世杰、钱端升、吴经熊、杨鸿烈等,于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已渐次在当时中国的法政论坛上崭露头角,并使得中国法学面貌为之一变,故具有纯粹学术意义的中国的新式/西式法学,可谓系滥觞于此。”(载台湾法学会台湾法学史编辑委员会编:《战后台湾法学史》(上册),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页。)此论断与本文在结论上是一致的,但缺乏详明的论证。
三、结论
研治中国法学史,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须给予一个大体明晰的时间界定。对于法学乃至任何学术而言,法律教育自有其重要性但也并非必不可少,它只是积几十年之功给法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氛围和推动力。现代法学的诞生,不得不注意的两点,应该是研究学人和研究机关。恰如日本法史学家滋贺秀三氏认为:“某种科学要在学术界确立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必须在大学里正规地系统地讲课。”〔85〕[日]滋贺秀三:《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吕文忠译,载《法律史论丛》(第3辑),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转引自陈新宇:《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可见大学在现代学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学科必须以大学为依托。中国现代法学,需要以学术为业的中国学人,筚路蓝缕孜孜不倦,白手起家而渐有所成;中国现代法学,需要有一个提供给学人的研究环境,这个环境在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只能是以研究而非技能传授为格调的现代大学或研究机关,〔86〕中国现代的学术研究机关,除却理学、工学的,文科类的大多存在于综合研究机关内,主要的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平研院没有法学的研究,中研院的法学研究开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参见刘猛:《法律科学的中国命运,1912~1949——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的考察》,载许章润、翟志勇主编:《历史法学》(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这个自主的机关通过学术氛围给个体的学人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机会。纵然,法学并非简单的由这两个因素构成,还有作为载体的著述、杂志、教育等进行宣传和代际传授,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为研究机关和研究学人,其他因素不过为法学的发展锦上添花而已。以此标准,中国现代法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在1920年代左右的北京大学诞生,并延续下来。〔87〕刘梦溪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时间,应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刘梦溪:《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收见氏著:《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很明显,法学要晚于现代文史之学学术的产生时间。此与时人论述,大体契合。1919年陈启修评论说:清末维新,泰西法律思想,始渐输入,迄今二三十年,法校林立,法案山集,号称明律之士,遍地皆是。然入其肆,则除翻译书外,国人自著之名作无有也。叩其人,则法学专家无有也。欲从各种法律草案,窥中国法学之程度,则草案皆属翻译,不足为凭。欲从实际法律家考之,则法官及律师,大抵为新官僚及高等流氓,不足与谈。故居今日,欲审中国法学之程度,几有末由之忧。〔88〕陈启修:《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载《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第22、23页。
纵观近代法学发展史,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在近代史上早就有几十年的法科教育,法学却产生如此之晚?其实,法科学校集众效应,在短期内就能取得成功,非无由也。就拿朝阳学院来说,往往借助有实力的官员的力量,比如让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来做董事长就是极显明的例子。民国时期,现代中国初开,专业分工不甚明朗,学人游荡于政学之间的情况极为普遍,官员退职后挤入大学也在在多有,这种情形在法律、政治学系则尤为普遍,因为法律、政治者,和实践密切相关。对此,曾有人讽刺说:“这几个私立大学,除教会办的以外,没有像样的。也有名教授,也有好学生,几个学校又都自吹是辛亥革命后老革命党人办起来的,叫做什么‘中国’、‘民国’、‘朝阳’、‘平民’、‘华北’、‘郁文’等等,名字好听得很,可是事实究竟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东城的朝阳大学法律系出了几个法官、律师,就有点名气。其实谁都知道,那不是靠上课,是靠关系,是靠名流校长不单挂名。”〔89〕金克木:《难忘的影子》,载《金克木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6页。他在文末“评曰”:《难忘的影子》写的是大学生,都是过去的人和事。现在人,尤其是青年,恐怕有点不大相信是真的了,所以叫做小说很合适。这几十年的一统天下,容易使人忘了过去,中国的过去和世界的过去。参见《金克木集》(第一卷),第854页。但是在那时,这种官吏兼任教员的行为颇获学生的赞许,于是学校也便为了后续招生迎合学生,使这种状况成为常态。“惟官僚、政客未必有学问,则以自身从政经验而充任法政科大学教职,往往成为在野官员的首选。而法政大学,为藉官员名声以扬本校盛誉,凭政客关系,为本校学生拓宽求职面,也不免假借官僚声名与关系网络”。〔90〕杨昂:《学风、世变与民国法学:朝阳大学研究(1912~1946)》,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6页。法学在传入中国之初,不过扮演了传统律学的功能性角色而已,这种长久形成的氛围没有新风气的冲击是不会改变的。其实,聘请有能力的实务官员进行讲授,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本无可厚非。法学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并非基础科学,英美法系所说的法学是一项技能,并把其放在职业性的律师学院中教授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般学生来说,修习法律的目的在于学会一项技能,他们对于理论的研究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关注。只有到这种研究具有实地用途时,他们才产生兴趣,而这种高深的研究往往只有遇到“疑难案件”时才可能派上用场,但是实务中能有多少疑难案件呢。因此,法学终究是少数人的事儿。寓身于20世纪上半叶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法律学,现实需要远大于学术研究需要,而法学之不彰、法律(立法)超越法学研究,可能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责任编辑:肖崇俊)
* 刘猛,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初稿承陈新宇老师阅后给予建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