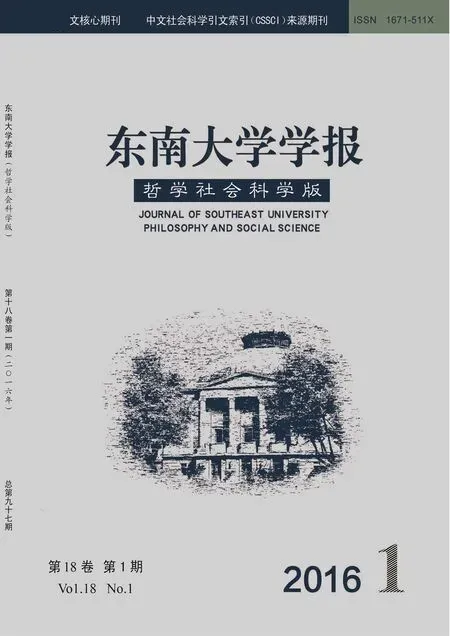本雅明论作为生命及其形式的艺术
支运波(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上海200040;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本雅明论作为生命及其形式的艺术
支运波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上海200040;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本雅明最著名的艺术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宣告了技术引发艺术生命政治的革命性转向。本雅明认为技术渗透艺术身体之后,制造了艺术的三重生命形式。以灵韵隐喻生命属性的艺术的生物生命转变为以复制品为象征的艺术的形式生命。在这种时代转向和生命隐喻的背后,本雅明乐观地预见一种具有救赎美学价值的未来生命的共同体愿景。
[关键词]本雅明;福柯;艺术;生物生命;形式生命;未来生命
本雅明的经典文献《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被认为是他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文章。对该文献的阐释与解读,可谓蔚为壮观。然而,在有关此文的阐释史中,太多的研究者对其进行艺术社会学解读,却极少在艺术形式的自足框架内投以注视的目光,更没有在生命政治理论视域中审视本雅明的研究成果出现。因此,从本雅明视艺术为生命及其形式的观点出发理解本雅明生命政治理论思想中的艺术问题,在全球资本治理新范式已然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因为,这将为我们打开一个艺术在生命政治时代的可能缺口,去发现人类未来的生命潜能,从而坚持一种有意义的积极艺术人生观。
一、艺术的生命及形式
生命政治的诞生是与福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并非是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在早些时候的德国,一些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们已经在国家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使用了生命政治概念。也就是说,生命政治理论有德法两种传统。在德国,本雅明从施密特那里汲取思想养料,从其所处的现代性视域出发,着眼于生命政治的暴力面向却意在其积极属性;在法国,福柯从尼采那里获得思想启发,沿着其有关权力积极性的发现进行开掘,矢力于生命政治生产特性却不忘“死亡政治”[1]维度。他们在生命政治的同一主题下,各自奔向了差异性的两极。
本雅明有关生命及其类型的论述是他对生命政治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他的这一观念有巴霍芬的思想印记[2]和对波德莱尔的主动吸收,也有犹太隐秘主义影响,同时与他个人忧郁的个性亦不无关系。在生命及其类型的认识和探讨中,本雅明较为详细地区分并论述了诸如“永恒生命”、“无辜生命”、“有罪生命”、“纯粹生命”和“赤裸生命”等一系列重要概念,这对后来阿甘本、德里达等著名生命政治理论家们对于生命形式的认识奠基了理论基础。[3]本雅明重视生命的观点同样也渗透在他有关文学艺术的卓越看法中。例如,本雅明视“形式”为艺术作品的首要因素,并赋予作品及其形式“一种自然生命”[4]的理解。当然,创作、阅读和翻译活动也不例外,本雅明同样认为它们无不是一次生命过程。同样,传统的文学形式——讲故事,是一种“生命铸造”;新近的艺术形式——电影,则是一种复制、记录生命的机械装置。更为甚者,像书籍和页码、摄影的曝光过程,乃至于流行时尚,在本雅明眼中也都被看做为“与有生命的躯体相关联”的。[5]
本雅明曾坚持认为,“艺术阐释的任务是将艺术的生物生命聚焦于艺术思想。”[6]这一文学阐释的思想强烈地贯穿于他意欲做德国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的理想之中。所以,“在他的所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本雅明其实只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政治生命,在其中生物生命与未来生命两者如何共存的问题”。[7]基于此,本雅明认为杰出作品与二三流的作品的根本区别是开创还是保留作品的生命形式。毫无疑问,他最为著名的艺术理论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自然也贯彻了“生命”——这个他特有的“核心性的有机比喻”。[8]其实,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构成姊妹系列的《讲故事的人》和《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也毫不隐晦地宣扬他的生命隐喻。《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诉说了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此消彼长的经验的贬值和在生死转换中权力的变迁,从而得出了故事时刻就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状态的观点;《拱廊街计划》中,他迫不及待地直接声明“他将用幻景这样的最直接的形式来阐明19世纪‘诸多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创造物’”。[9]
本雅明的生命比喻是个涵盖多重意味的概念。有时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有时指形式上的文本生命,有时也指时间序列上的历史生命。在《翻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认为:“只有当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非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代。”[10]另据他本人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作出的思考,正是处于现代的“时钟脚步中”给“艺术理论提出的问题赋予某种真正的现代形式”,[11]以捕捉“19世纪作为‘命运’的艺术作品”[12]在终结时刻的讯息。本雅明认为历史决定了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而理论家的任务则在于“透过包罗更广的生命历史去理解自然生命的一切。”[8]
置于历史场景中去理解《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表述的“灵韵(aura)衰退”宣言,其根本性的变革意义在于解开了艺术不是由上帝而是由政治和“综合科技”缔造[13]的生命密码。简言之,艺术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由政治与技术书写的历史。这样,艺术就自然地生命政治化了。此外,被技术控制的艺术的接受者也必然“受制于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以及一整套的程序,也可以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来表述。”[14]福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如此众多的生命政治理论家无不都沿着这条思路论述生命政治如何成为塑造当今事物呈现状态的政治意志和技术力量的。艺术被赋予生命政治属性,这意味着:其一,作品获得生命的形式,艺术逃离作品之外成为在场与不在场的矛盾体;其二,艺术进入(人的)生命之中并成为感知的对象;其三,艺术以生命的形式运作,拒绝在作品内部终结自身,又渴望在作品之外获得生命。
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关联到伦理与政治,是只限于人类的一种朝向城邦生活的生命形式。”[15]《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将艺术与生命并置透过其中复杂的生命政治装置技术,本雅明在以灵韵为代表的神圣生命,经由机械复制为特征的世俗生命向以拯救为价值的未来生命过渡的必然趋势中,流露出了惋惜、雀跃与忧郁的情感关怀。
二、艺术的三重生命
该书开篇,本雅明提醒在艺术的物质部分之外,不可忽视“现代权力和知识运作的影响”。但技术对艺术全方位的改变则是前所未有的。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而言,一方面技术使作品失去了时空个性,本雅明称之为形成作品真实性的生命存在的“此时此地”性;另一方面使作品“具备了更多的文献真实性”。[16]美国左派艺术理论家格罗伊斯(Boris Groys)首次指出这种艺术成为文献所指涉和记录生命的属性是当今艺术独特的生命政治学。[17]就艺术作品的物理表象而言,技术就如同一把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或科学机械的设备装置可以直接修复与制造出新的事物;就大众的接受与感知方式而言,技术在解魅神圣与复魅俗物的过程中解放了人们的知觉系统。简言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表述了本雅明有关艺术及其形式的生命隐喻观念下技术改写了艺术的“生物生命”(Crea⁃turely Life)(以神圣为特征)进而转化到“世俗生命”[18]和未来生命的生命政治学转向。
技术对艺术“生物生命”的改变是以艺术“灵韵”的消失为标准的。其实,灵韵并非艺术所独有。本雅明明确地说“真正的灵韵出现在所有事物中”。[19]他集中于灵韵,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灵韵来自于一种宗教活动的崇拜仪式以此强调自然事物的“膜拜价值”以及人们对它所产生的感受性。传统社会的人们是穿透艺术作品靠把握灵韵去找寻、亲近宗教仪式的。就是说艺术品是铭刻仪式,是宗教仪式的寓所。人们膜拜的不是艺术品的物质本身,而是物质之外的仪式。艺术品以物质的在场显示艺术的不在场。在《论波德莱尔作品中的一些主题》中,本雅明将对灵韵的体验基础在人与生命的反映和人与物的反映进行迁移(或等同),认为发现艺术中的灵韵就意味着赋予它像人反观我们那样“反过来看我们的能力”。灵韵作为艺术的灵魂复活了艺术,即将艺术人化了,这样艺术也就具备了与人进行沟通的能力了。另一方面,灵韵衰落也解放了灵韵中的秘密体验——一种上帝在场的宗教时刻。作为客体对象的复制品成为人的伙伴连同一览无余的平等距离成了“相互幸福的标记”[20]。艺术品以主体间性的面貌出现,便也就宣告了公共的、非艺术化的大众艺术时代的来临。
在现代技术社会,艺术一方面以技术确定其真伪,另一方面又被技术推向了两极生存空间。这表现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迅速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退缩到由少数人占有的私人空间或者博物馆、展览厅等这种独特场合;缺乏独特性而千篇一律的艺术复制品大举进攻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不断获得文化产品的身份,被人们想象为艺术品而发挥着实用/非实用的并杂功能。独特场合的艺术品常常以艺术的神圣价值来显明它“活着”这一事实,以凭借独特的占有关系而可随时行使终结手段以强化其存在的危险。就算将其放置到有安全措施保护的博物馆,也不能消除表情陌生的闲逛者的冷漠。[21]也就是说,这种场合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例外与正常模糊难辨的,类似于生命政治学中的“活死人”状态。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大量复制品,虽然并不是真实的艺术品,也缺乏独一性。可在大众世界,却是享受中艺术的目光和文化的礼遇。它们摆放的空间就是艺术品曾经受供奉的位置。也就是说,大众把对艺术的情感投射和心理地位都给予了徒留下的艺术表象形式。概括地说,技术将艺术品和复制品都推向了“形式生命”(form of life)的共同道路上了。形式生命具有分离,片段和任意处置的特点。与舞台演员相比,电影演员需要依靠机械这个中介完成自身活动与艺术产品的分离,他们实施着生命活动,却不再有灵魂;对着机械中介(镜头)作出的姿态经过专门技术人员利用一系列装置和技术制作的影像是由“孤立的单格影像”这么一个个单子组成的如有机物切片一样的片段;这些复制品处于的空间——无论是私人藏所、博物馆、展览厅,还是都市景观物——都是艺术品的生命存在展示的“集中营”(camp)。
本雅明是赞成艺术品两种生命(灵韵的与展览的)的分离的。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技术使艺术品失去了灵韵,但在世俗中艺术品的灵韵还能受到唯美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维护。相反,维护灵韵只会让艺术高高在上,献祭给那些崇拜者。比较艺术新形式在大众那里获得的亲近不仅复活了艺术,还使技术直接捕获了艺术形式制造出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本雅明真正雀跃的是技术带来的新的共同体以及所引发的新的生产美学。
三、救赎的未来生命
由于,不满为何人不能“活的像件艺术”的生存美学难题,福柯提出了“身体解剖学”的“修身技艺”的解答策略。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在“生命政治学”的框架下如何具有美或活出美来,就福柯生前所做的上帝—子民的牧领政治探讨来看,基本堵住了美学的出口。反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通过技术这一现代性手段直接消除了筑基于宗教仪式的崇拜美学,从具有亵渎姿态的大众美学中看到了政治美学在未来社会的奠基可能。而且,本雅明通过艺术的新形式——摄影机和剪切技术“显示出艺术已经脱离了‘美的表象’,而以往人们以为艺术一旦少了这美的表象就注定会衰亡”。[13]他明白地指出了美的可能和技术让艺术活的生命政治。尽管,人们不能排除技术制造的新的所有者会出现许多不正常行为。例如,像收藏家可能依据对艺术品的占有关系对艺术品实施非理性行为,公共空间中闲逛者也难以避免做出亵渎姿态,集体大众的暴力倾向等。但,最根本的是私有专属制彻底内公共财产关系取代了。可以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福柯生命政治美学理论的遗憾,给出了集体主义的生存美学的救赎希望。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纲领性意义在于绘制了艺术的生命政治转向后,“观众作集体而同时性”审美活动的蓝图。在本雅明看来,“电影一方面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支配我们生活的一切日常必需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活动空间。”[13]另外,观众可评价乃至于批判与分析,或者做些与观看无关的事情。人们可以有目的也可无目的地发生与艺术的中介关系,观众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系统、生产技能成为话语掌管者或生产者。这彻底变革了福柯牧羊统治中,处于受身体惩戒、行为监控以及哑言状态的以照管为名实为囚禁且随时可能面临丢弃与处置的生命临界时刻。时刻保持警惕性的顺从行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漫不经心的姿势和纷呈不断的无意识之花。原作“邀人静观冥想”希望观众“专心”;电影诱人穿越历险,希望观众“散心”。一个是将肉体的感受封闭在精神的岩石之下,一个是刺激它以使其苏醒去打碎束缚的生产关系枷锁。读者成为生产者,可以倾诉情感或发表心得,也可能同艺术这个公共财产实现权力的占有。本雅明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集体生命政治的转变,在福柯的牧羊人—羊群的不可逾越的种的差异关系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的根本意图是希望将原作中富有神圣性的东西拓展到个体大众生命之中,从而与人类生命的单一性联系在一起。文化遗产“不只属于那些天才的创作者,也属于那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苦工”,[22]这样,艺术在贵族阶级的占有关系的极权主义生存就转换到了具有大众普遍性和人类单一性的生命政治学。本雅明的根本发现就是为这种过渡寻找合法性。这样的话,既避免了艺术品随时沦为赤裸存在的机会,也回避了少数特权者任意处置的发生。技术复制使原作不再成为孤本,并通过商品价值特征阻止附加于它的暴力行为,并且给它存在的空间,比如博物馆或展览厅、私人收藏所,附加了一系列的安全装置。另一方面,解放艺术的所有权,将其系于普遍性、民主性的大众,这种解放性质内在地联系于人类生命的单纯相关性,这样也就给了艺术一个法的规定性。实现了艺术所有权的变更和艺术生命的保障机制。复制技术悬置了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本雅明欢呼技术,似乎技术带着“弥撒亚”讯息,在艺术的灵魂为艺术身体“设宴”的时刻,消灭“历史的封闭密室”再次重新开启朝向未来的“历史密室”,艺术的律法与权力被打破并重新分配了。
技术时代大众艺术的松散关系破碎了物(财产)的主导者的所有关系。演员既不能掌控表演过程,也不能对影像结果产生亲近感。他们焦虑于自己在镜头前的卖力、挖空心思却不能想象最终的作品。同样的生产关系,站在读者角度进行审视反而是另一番景象。传统上的作家的权力地位不见了,数万的读者群体都可以轻松地实现生产者的地位转换。他们拥有了话语权。甚至,凭借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获得权力地位。以往只属于少数人的文化艺术,现在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平等、民主的公共财产。早期,奠基于崇拜仪式的艺术作品阶段,大众对艺术怀着神圣而恐惧的心理是完全臣服的地位;可在人人都可享受的复制品时期,反而在观众那里出现了批判精神。
福柯牧羊政治的单边关系奠基于神/人或人类/动物的种的先天性差别的假设前提下。而本雅明不仅取消了种类的差别,还进一步解除了所有者关系和特权的存在以专注于同类内部考察其美学问题。本雅明与福柯的另一个不同是他不是首先聚焦于主体,而是将视点挪移到物(艺术)上去探索物给主体创造的美学空间。高高在上的艺术品——不管是实体距离还是心理距离——与大众的隔膜正是复制品以“接近”姿态所主要消灭的对象。救赎是本雅明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涵盖本雅明所有艺术理论之核心概念的主要问题。[23]《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所主张的救赎美学是艺术的“崇拜仪式价值”,经由“展览价值”过渡到政治价值得以奠基的。在政治美学化之外倡导艺术的政治化,其“最大作用就是重新审查艺术本身所依赖的特有技术,并使这种技术能够发挥它的潜能,甚至是发挥乌托邦的作用。这是艺术政治化的最深刻意义。本雅明指出,真正要问的问题是艺术品在生产关系里的位置,而这个问题也就是艺术品运用的技术问题”。[24]
四、结语
从艺术的形式因素出发,立足技术的关键切口,本雅明创造性地以生命譬喻了艺术存在及运作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处于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同一视域中的相异面向。技术一旦进入艺术,便使艺术获得了生命政治技艺的辖域化,并开启了被书写、调节以及被制作的历史。从此,技术接管了艺术制造过程中的全部事项:制造、修复、贮藏、购置、流通、生活以及剪辑出美来。它实现了政治权力的架构所能承担的使国家更自由、平等、长治久安,让人民幸福、快乐和长命百岁的国家职责。如果说福柯是在国家与人口的层面讨论生命政治议题的话,那么,相应地,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便是以技术与艺术的角度阐释了同样的理论话题。技术复活了艺术,并且将艺术从以前“期待让一两名或极少数观众欣赏”转变为“期待数量更多的观众欣赏”;从同时欣赏变成间接欣赏;从以前的保守变成激进态度(批判—接受)。这种祭祀价值到展览价值的成功实现,把隐匿处境中的艺术首次搬到大众生活的公共空间。艺术随之发生了功能让位于形式的变迁,这是技术带给作为生命及其形式隐喻的艺术在现代性社会的政治景观。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Vol. 1.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Vintage.1990.
[2]Nitzan Lebovic.Ecstasy and Antihistoricism:Klages,Benjamin,Baeumler,1914–1926[M]//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Palgrave Macmillan,P.91,101.
[3]Vernon Cisney.Categories of Life:The Status of the Camp in Derrida and Agamben[J].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8 Vol. XLVI,p.161-179.
[4]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6]Walter Benjamin.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0[M].Trans. By Evelyn M. Jacobs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224-225.
[7]Miguel Vatter.Married Life,Gay Life as a Work of Art,and Eternal Life:Toward a Biopolitical Reading of Benjamin[J].Philoso⁃phy and Rhetoric,Vol.44,No.4,2011,p.309-335.
[8]朱大成.文化的宗教性:本雅明、伽达默尔、勒维纳斯的文化理论[M].台北:道风书社,2010.
[9]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M].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1]Walter Benjamin.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0[M].Trans. By Evelyn M. Jacobs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509.
[12]Parallel Lines.Printmakers,Painters and Photograph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7-43.
[13]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M].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Thomas Zummer.Attachments of voice[M].Artnodes,no. 12(2012),p.111-118.
[15]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 3-5.
[16]尤金·哈贝马斯.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郭军译[M]//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7]Boris Groys.Art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from Art Work to Art Documentation[M].Documenta 11–Platform5,Exhibition Cata⁃logue,Germany,Hatje Cantz,2002,p.115.
[18]Leland de la Durantaye.Homo profanus:Giorgio Agamben’s Profane Philosophy[J].boundary 2 35:3(2008),p.27-63.
[19]Walter Benjamin.Protocols of Drug Experiments,On Hashish[M].trans. Howard Eiland et al. Cambridge,Mass.,2006,p. 58.
[20]戴维·罗伯特.光晕以及自然的生态美学,郭军译[M]//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1]支运波.生命政治:技术时代艺术的新机制[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2).
[22]弗莱切.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M].田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Miguel Vatter.Married Life,Gay Life as a Work of Art,and Eternal Life:Toward a Biopolitical Reading of Benjamin[J].Philoso⁃phy and Rhetoric,Volume 44,Number 4,2011,pp. 309-335.
[24]马国明.班雅明[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
[作者简介]支运波(1980—),男,安徽怀远人,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西方美学、生命政治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趣味变迁与文化权力演变关联性研究”(14CZX062);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项目“海德格尔后期诗学研究:以Ereignis为进路”(JUSRP11472);上海市教委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Ⅱ高原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理论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5-21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1-0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