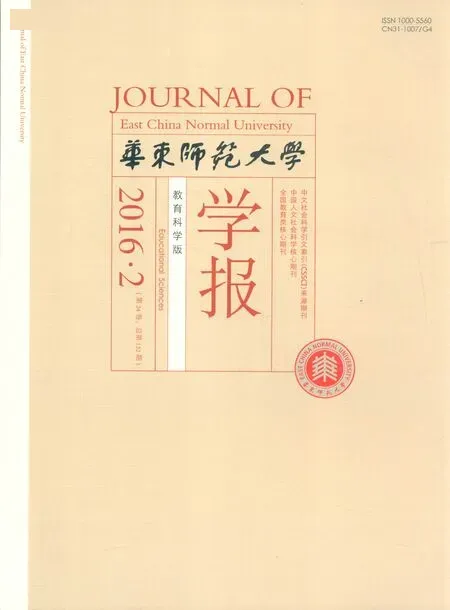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机制研究*
张 旸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西安 710062)
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机制研究*
张 旸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西安 710062)
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是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个体教育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过程。研究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不仅能够为反思实践中的教育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一个视角,而且也为研究教育价值观念的个体发生奠定基础。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先天基础,自我意识的发展及其调节作用和个体存在环境中的“核心他人”的教育需要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主客观条件。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过程包括具有先天性的个体认知需要的初步展现及其不断增强、发展性障碍的出现及其看护者作为“核心他人”的教育需要的逐渐出现等五个阶段。
教育需要;个体发生机制;认知需要;发展性障碍;需要冲突
任何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种不争的事实不仅渗透在人类与教育同起源共发展的历史之中,而且在现代社会知识经济的发生中不断彰显。所以,教育在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重视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个人的青睐。此消彼长的个体对他们所接受教育的否认、厌恶和拒斥并没有消解个人对教育的需要,而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人们需要的是对他们有价值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需要也应该具有合理的边界。但无论如何,个体的教育需要不会因为厌恶去学校读书、否定某种教育教学活动等一系列现象的存在而得以消失。个人对教育的种种依赖和要求,既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价值。“教育问题的产生不仅起于教育和其所处的社会,而且源于社会人的‘教育需要’。‘教育需要’并不是‘教育’的同义反复……对人的教育需要的研究表征着教育自身的又一次觉醒。人应该从意识、反思和完善自身的教育需要出发,改进、提升和发展教育活动。”(张旸,2012)因此,研究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机制,不仅能够为反思实践中的教育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一个视角,而且也为研究教育价值观念的个体发生奠定基础。个体教育需要是指个人对教育活动不断表现出的缺乏和要求、依赖和倾向。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是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个体教育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过程。
一、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先天基础
个体的教育需要虽然受到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他者性,但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绝对不是完全由他者给予和决定的。个体的认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先天基础。美国人格学家默里(H.A.Murray)提出了人的28种需要,其中认知的需求表现为:凡事喜欢追问、对新奇事物非常有兴趣、喜欢探讨和钻研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在其人类动机理论的需要层次的研究中,虽然直接论述认知需要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对认知需要的探讨却体现出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马斯洛认为,虽然对认知需要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已有心理学研究的重视,但是,具有客观性、先天性和独立性的认知需要对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马斯洛,2007)认知需要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以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马斯洛,2007)。人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未得到解释的事物,而对共知的事情则往往感到索然无味,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对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自我厌恶和身体压抑的人进行适当的诸如恢复业余学习、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等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其次,马斯洛认为认知需要包括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的欲望、寻找意义的欲望、创立价值系统的欲望,这些内容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而且,认知需要是没有止境的,“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马斯洛,2007)还有,认知需要展开的过程具有双重的情感体验:一方面,认知的过程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但另一方面,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情感体验,例如焦虑、恐惧等。最后,马斯洛论述了认知需要在需要层次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意动需要的关系。马斯洛认为,必须提防那种极易将认知需要同他前面所论及的基本需要分离的倾向,因为认知需要具有基本需要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认知需要“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striving)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personality needs)”(马斯洛,2007)。但是,马斯洛却并没有将认知需要简单地归入需要的层次系列之中,而是认为它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来,它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人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是智者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
关于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的研究也最具权威性。虽然马斯洛自己也承认,“自我实现”这一术语并不是他所首创。但从需要的角度系统全面地思考自我实现,马斯洛无疑具有重大的贡献。而且,马斯洛对自我实现需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随着他对此问题思考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拓展的( Leontiev,Dmitry A,2008)。
首先,关于自我实现需要的内涵问题。马斯洛(2007)认为,“一个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self-fulfill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有的人可能想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想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中成就自己。而且,“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一般来说,做饭、做父母以及主持家务,可能具有创造性,而诗却不一定具有创造性,有时可能不具有创造性”。(马斯洛,1987)自我实现需要是人人都具有的需要,不能将“自我实现的需要”同“自我实现者”混为一谈。其次,自我实现需要具有基础性、成长性和超越性多重特质。在马斯洛看来,自我实现需要首先是根本的需要,即那些不能再追溯下去的、全人类所共有的欲望和冲动。在《缺失性动机和成长性动机》一文中,马斯洛又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同其他的基本需要相比,具有成长性需要的性质,即被自我实现的取向激发,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等的需要,而且,此种需要对其他基本需要具有超越性。后来,特别是在1967年发表的《自我实现及其超越》等论文中,马斯洛在保留自我实现需要对其他基本需要具有超越性的同时,又将自我实现的超越性质理解为对个体自我性的超越,是从小写的人到大写的人的超越。最后,自我实现需要及其满足的过程具有丰富的内在价值。越是在较高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个体,其更具有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和丰富感。所以,较多地在自我实现需要的层次上生活的人,大都能超越活动或工作所具有的工具倾向和功利价值,和其所从事的活动或工作打成一片,并使活动或工作成为他们自身内在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人会在不断地感受到“高峰体验”的降临,从而在其过程中形成自我实现需要从小我到大我的满足和超越。事实上,“高峰体验”就是一种目的体验、终极体验或存在体验,在这一体验中,个人“挣脱了功利取向的羁绊,超越了缺失性认识的偏狭,进入到存在认知的境界,领悟到了‘存在价值’”。(彭运石,1999)
从马斯洛对于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研究出发,我们认为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先天基础。个人对具有外在性和他者性的教育活动是否需要和需要什么,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和成人的教育需要完全决定,而是必须以与人人先天就具有的教育活动具有密切联系的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为基础,才能在基础与条件、先天与后天、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之中保持应有的张力。
二、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条件
看似个体随时做出的教育选择和展开的教育活动,都必然受到个人教育需要的驱使,而具有隐匿性和习得性的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不是无缘无故没有条件的。分析和研究驱使个人教育活动的教育需要发生过程中的条件,对研究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过程、分析教育活动的偏差、反思教育结果的限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客观条件
个体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此环境中的“他人”的教育需要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客观条件。虽然个人的认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具有的先天性在为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提供一定的可能性的同时,制约着个体教育需要展开和满足的过程和结构。但是,它们仅仅是个体教育需要的先天基础,并不能单一决定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
恩格斯(1995)指出,“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斯洛对似本能概念的开创和阐述,正是在尊重人与动物具有相同之处的同时,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从而力求从价值论的角度提升和规范人性。而且,基本需要似本能的性质非常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发展的影响,看到了有意改变和创设环境对人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他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文化背景(有时甚至也包括政治制度在内),但是,他回避了经济制度这个根本问题,看不到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看不到生产关系对人们活动的根本制约作用。”(许金声,1985)有限的个体如何把握无限的存在,也许有限的精力及其关注视角的差异可以成为人们要求完美但却无法完美的合理理由。但不管怎样,“似本能”的概念不仅强调基础需要的先天性,但更强调它的潜在性、可能性及其在后天环境和条件中的实现。
对于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来说,个体生长的环境及其环境中的“核心他人”是其教育需要发生的客观条件。环境作为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综合体,是个体生活的背景和条件。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不仅受到个体所在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制约,而且受到个体所在社会中的教育实然存在的制约,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影响个体成长的“核心他人”的教育需要也成为其教育需要发生的客观条件。当然,作为客观条件的后者与社会文化环境相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超越性,这是因为教育需要作为一种人的本质活动和特性,必然包含着主观的观念、目的、愿望等。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能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能将自己的需要同目的、动机联系起来,实现客观向主观的转化。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认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指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这里的“核心他人”指在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过程中对其具有直接影响的他人,其中也包含那些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的“重要他人”。在影响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他人”中,看护人和监护人、教师、国家权力人士及其社会大众分别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他人”,正是他们在他们的文化中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及其教育需要一起影响着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他们在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过程中,以“成人的身份”具有矛盾地联合在一起,影响、指导或制造着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而且,这些“他人”之间关系的民主性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教育需要发生和展开的民主性,而且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在非民主或不民主的社会中,父母及其家人、教师和同学的教育需要在受到国家权力人士控制的同时可能同其一起成为控制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外在力量。于是,学生先天具有的认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并非总是受到外在环境中“他人”的重视和尊重,它们之间有可能对立起来,使得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缺失内在的基础和条件。
(二)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主观条件
教育需要的个体发生必然以具有主观性的自我为内在条件。没有个体自身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就无法真正展开和实现。在个体有限、偶然的身体生命历程中,却存在着意识和精神的必然和无限,具有着个体自身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这不仅产生了人对动物的超越,也具有了人自身的丰富和升华。于是,在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过程中,除了先天的可能性、环境的客观性之外,还必然存在着个体主观意识和精神的参与。
但是,个体意识和精神不是以均衡的方式参与到自身教育需要发生的始终,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及其所展现出的特点,蕴含着个体意识和精神的逐渐成熟性,而对这种逐渐成熟的个体意识的把握是探讨个体教育需要发生过程中的主观条件的基础和前提。个人意识的成熟不仅与其身心的发展相伴随,而且以个体自我意识的产生和成熟作为其发展的最高阶段。而自我意识的发展及其调节作用是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主观条件的核心。自我调节发生的底线是个体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具有了进行自我调节的心理能力。刚出生的婴儿在人类环境中生活了一二个月后,就开始产生了朦胧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但那时却没有对教育需要的自我调节。随着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开始和发展、孩子大脑的发育和成熟、以及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认识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思维和实践的能力也获得了相应的提高。于是,孩子对教育需要的自我调节就具有了初步的可能。随着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他对教育需要的自我调节就具有了较大的可能和现实基础,但依然受到他所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
三、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过程
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过程应该是在尊重个体认知与自我实现需要的基础上,经由客观环境中“核心他人”的合理教育需要的影响,依靠自我的成熟和调节而逐渐展现、丰富和实现教育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在做出合理教育选择和展现恰当教育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过程具有以下几个阶段:
具有先天性的个体认知需要的初步展现及其不断增强是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第一阶段。“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1972)具有“似本能”特质的认知需要早在婴儿时期就可以初步表现出来,而且随着婴儿大脑的成熟和活动能力的提升而不增强。婴儿在还不能翻身之前,就可以对自己视域范围之内的颜色鲜艳的红色进行短期的注视,而且眼珠可以随着鲜艳物体的运动而移动。而且,婴儿对颜色鲜艳的有声音的可以运动的玩具(例如转转熊)也逐渐会发生浓厚的兴趣,并会不断产生探索和认知的需要。即使只能躺着的婴儿只要一听到玩具的音乐响起,就会开始寻找声音源,并伴随着胳膊和腿脚的运动。随着婴儿大脑的发育和翻身、坐、爬、走、握、捏等运动能力的提升以及运动空间的扩大,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随之增强。他会用手去够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爬向自己想探索的某些东西,对着镜子并用手去抓,拉开抽屉将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用手去戳墙上的小洞、喊着要拿大人手上拿着的东西……这些都说明了小孩认知需要的增强。他试图探索对他来讲的周围一切未知的世界,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都为教育需要的发生提供了先天性的基础和可能,而且,这些基础和可能必须依靠人类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才能得以展现和实现。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浸染在一定文化中的个人,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发展性障碍的出现及其看护者作为“核心他人”的教育需要的逐渐出现,就成为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第二阶段。作为看护者的“核心他人”在满足孩子在第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求知需要的同时,也是在用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文化来教育和建构孩子的社会性世界。所谓发展性障碍,就是孩子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当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事实性知识之后、在探索相对自身的未知世界时所出现的困惑和疑问,是孩子求知需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根据内容的不同,将发展性障碍分为知识性障碍、能力性障碍和德性障碍。知识性障碍一般表现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它是什么颜色”、“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男人会长胡子”等“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障碍。能力性障碍一般表现为“怎样打开这个”、“如何放好这个”、“怎样弄好它”等“怎样做”的障碍。德性障碍一般表现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给他”、“他为什么不和我玩”、“他为什么要撒谎”等人性和人际的障碍。这些障碍的出现为教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绝佳的时机,此时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是否能在作为看护者的“核心他人”这里被有张力地打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健康和谐的发展,也考验着看护者的智慧和胆识。看护者对孩子的”发展性障碍”的态度和解答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儿童观和教育观,而这些观念的背后隐匿者他们复杂的教育需要。看护者外显的实践方式和缄默的教育需要一方面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孩子的教育观念和教育需要。如果父母在孩子具有发展性障碍时进行引导,并有意在提升自身知识、能力和德性的同时与孩子一起发展和进步,反思自身对孩子的引导方式和教养方式,那么父母的教育需要就在尊重孩子的认知需要的基础上初步显露出来,并随着孩子知识性、能力性和德性障碍的不断解决而发展。而且,父母也可以从自己的教育需要出发,引导孩子思考一些“为什么需要教育”等问题,这为孩子教育需要的发生奠定了直接的意识条件。所以,父母的教育需要的产生不一定以孩子的先天性的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为前提,但肯定与父母自身的境界紧密相关,也与父母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相联系。在此阶段中,个体的教育需要有可能会以自发或无意的状态表现出来。
学校教育需要的发生及其教师作为另一“核心他人”的显现,这是教育需要个体发生的第三个阶段。接受学校教育使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具有了确定性和统一性的特质,也丰富了个体教育需要发生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求知需要的不断扩大,作为家庭环境中“核心他人”的监护人需要将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以满足人类、社会、国家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需要,虽然这些需要与孩子的学校教育需要之间以及这些需要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教师作为另一“核心他人”出现在孩子的生命历程之中,同孩子的父母一起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孩子教育需要的主体。不过,虽然孩子的学校教育需要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因为需要也可以通过学习或强加来获得,但相对于社会、国家和父母的学校教育需要来讲,孩子的学校教育需要一开始往往以自发或无意的状态与他们的认知需要、发展需要和尊重需要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个体性。于是,在社会和国家的法律要求下,大多数父母基于自身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考量,成为个体从孩子角色到学生角色的直接决定者,也可能成为从自身对学校教育的需要出发来制造孩子的学校教育需要的直接推动者。虽然此时的一些孩子可能有着朦胧和初步的对学校教育的需要,但也可能会存在只参与学校教育活动而无学校教育需要的情况,因为孩子还没有意识和能力来决定自身对学校教育的需要。所以,在学校教育需要驱使下的个体学校教育活动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孩子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必将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体现和承担着人类和社会的传承和责任。但是,这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发生可能导致一些损害学校教育需要所具有的个体基础的结果,即对学生自身认知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忽视、漠视甚至扼杀。虽然认知需要的满足和实现、学习过程的展开中具有的与激情和兴奋同在的痛苦和煎熬可能成为孩子产生自觉学校教育需要的阻碍,但是,以父母和教师为直接“核心他人”围绕学校教育所开展的活动对于孩子和学生的引导或控制,也会成为学生产生自身学校教育需要的影响因素。
需要冲突出现、发展性障碍增强及其自我实现需要的不断展现是个体教育需要发生的第四个阶段。随着孩子的学校教育需要的原初展现,具有孩子和学生双重角色的个体与父母、教师等成人之间的教育需要可能发生一定的冲突,这些冲突也可能成为孩子厌学的理由之一。学生自身的学校教育需要内部也会发生诸如目的性教育需要和手段性教育需要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现有教育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个体社会化和个性化的不断拓展,其始终存在的发展性障碍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自觉和自我实现需要的逐渐增强也愈加丰富。知识性障碍、能力性障碍和德性障碍逐渐与需要冲突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个体自我教育需要不断展现的一些内外部的原因及其内容。于是,在本阶段,虽然还存在着家长和教师的教育需要对学生教育需要的僭越和强加,但是也存在着个体自我教育需要的不断凸显,虽然这其中内含着“核心他人”对其教育需要的制造,但也存在着个体对教育需要的选择和要求。因此,对于个体来讲,愈加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的什么、需要怎样的教育,虽然他所需要的教育在事实中不一定存在,抑或他所需要的教育充满着功利的性质,抑或他的教育需要充满着个人的色彩。但不管怎样,这些都是个体自我教育需要的不断出现。于是,在有些个体身上,就会出现其教育需要发生的下一个阶段。
自我调节能力的逐渐增强及其教育需要自主性和自觉性的提升是个体教育需要的发生可能出现的最后阶段。之所以认为是可能出现,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个体的教育需要的发生都能够走到这个阶段。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仅仅以从众的心理来展现着自身对教育的需要,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教育需要的存在及教育需要是什么。自我调节能力随着个体自我意识、心理素养和物质需要的提升和满足而不断增强,从而为自身教育需要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展现提供前提和基础。在此阶段,个体不仅愈加了解自身的教育需要,而且能够在主动调整个体教育需要与社会教育需要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教育需要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的统一,强调教育需要与人的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的相互促进,也会作为拥有合理教育需要的“核心他人”影响着自己周围的人。
Leontiev,Dmitry A.(2008).Maslow 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JournalofHumanisticPsychology,48(4),451.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4.
彭运石.(1999).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67.
许金声.(1985).马斯洛需要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心理学报,(1),31-37.
亚伯拉罕·马斯洛.(2007).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1,32,33,33,29.
亚伯拉罕·马斯洛.(1987).存在心理学探索(李文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22.
张旸.(2012).人的教育需要:困境及超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4),9-18.
(责任编辑 陈振华)
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15SZZD01)。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