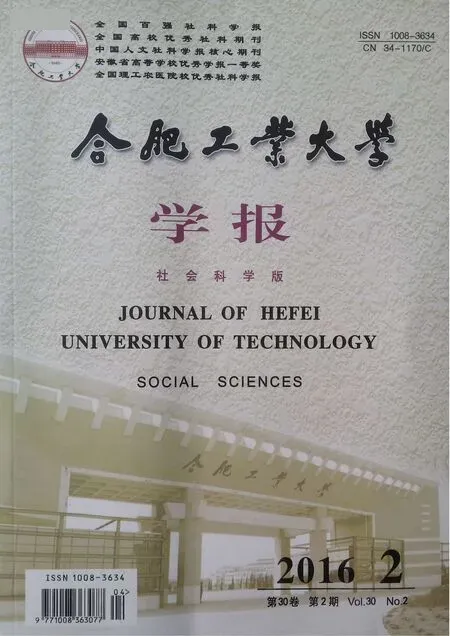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唯美诗学
——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碧奴》
钱 钰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唯美诗学
——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碧奴》
钱钰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230039)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苏童创作了《我的帝王生涯》和《碧奴》以及其他历史小说。文章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两部小说对历史的碎片化处理和对个体命运的发掘及重构,并阐释了小说的由唯美语言所构筑的诗学意境。
新历史主义;苏童;唯美;文化诗学;个体命运
一、历史的碎片化和文本性
苏童在自己的创作自述中曾说过:“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1]这种创作理念与新历史主义的领袖格林布拉特的主张不谋而合。众所周知,“历史”是文学不可或缺的根本的参照轴线,由于作家身处于特定的历史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其历史观也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迹。因而传统的历史小说总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为基础,描写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其基本特征,极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达到所谓“以史为鉴”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的界线日益模糊,由此创作出的小说被纳入了政治学话语和社会学话语的轨道,丧失了文学话语本身的特质。另一方面,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客观主义的历史观是不存在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单一线性并且内在和谐的历史视野了,小说因此并不“反映”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成为作家文本中的存在,宏大历史被颠覆,在虚构中进入一种鲜活而空灵的境界,逼近了从“审美”而非“阐释”角度解读历史的诗性存在。历史经由文学作品和不同领域的文本相勾连而具有了文本性的内涵。苏童的两部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和《碧奴》作为新历史主义的厚描,其“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制衡与倾斜;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2]也成为了作品的主要特征。
《我的帝王生涯》看似具有一个传统历史小说的架构:王国和帝王、权利的争夺、后宫干政、荒淫的君王、得宠的宦官、被放逐的忠臣等等元素在小说中依次登场,十几万字里浓缩了若干王朝的兴衰史。但是燮国是虚构的,帝王端白也是虚构的。在所谓“大历史”的仿古气息中,是一个全然自我的世界,营造的是作者想象飞扬的虚化历史,历史的碎片化则带来错乱的荒诞感和宿命的荒凉。皇子端白突然被祖母皇甫夫人推上王位,经历了荒淫暴虐的帝王生涯,而后竟流落为民间的走索人,最后隐居在山间,宠妃惠妃则沦落到在集市上贩卖帝王的信笺。尽管第一人称的叙述带来“亲临”的即视感,但如此大起大落的情节却加深了文本的虚幻色彩,历史成为作者主观讲述的戏剧化人生,尤其在一些细节上反复提示了文本的虚幻与荒诞。如端白的祖母用寿杖捅孟夫人的嘴:“我会把你撵回娘家的豆腐铺去,你只配做豆腐,不配做燮王的母后。”[3]14深宫的妃嫔竟如市井小人一般争吵,身后则是对边疆急报漠不关心的帝王,还有炼丹炉的老疯子孙信反复低吟的“燮国的灾难要降临了”。这些奇异的片段混杂在一起,构成一个绵长诡谲的世界,即作者凭借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建构的“推理破案”般戏剧化的世界。朝代的更迭和个人的命运在文中并非线性发展,在回溯中出现盲点和空白,作者极力描绘的并非战火的洗礼和家国的变迁,却是帝王在民间作为卖艺人名声大噪的经历。这种可谓“游戏历史”的写法正是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终极意义和多重可能性的拷问。
如果说《我的帝王生涯》还沿用了“大历史”的架子,那么《碧奴》这个重述的神话则是彻底从其原型中脱离,创造了一个简约灵动的新世界。原型“孟姜女哭长城”中对修筑长城和秦王暴政的描写被完全剔除,男主角在文本中完全失语,仅以女主角碧奴送冬衣的旅程勾连起一个个人物和线索。碧奴用头发哭泣、魂魄变成青蛙的母亲、莫名出现的白蝴蝶,都给文本增加了魔幻色彩,凸显出“神话”的存在;而碧奴路途上遇到的或粗鄙或蛮横或猥琐的鹿少年、太守、狱卒等,又把故事拉回了尘世,在“神”与“人”的角力中拷问与挣扎。所谓的重大历史事件被弱化和搁置:王的去世没有留下任何波澜,大燕岭的工程是否完工不得而知,甚至也没有描绘碧奴辨认丈夫尸骨的情节。小说反复出现的是碧奴对自己是否能变成葫芦的惶惑,对无法隐藏眼泪的恐慌,以及拿回冬衣的执拗。在这些细节和心理描写中,没有任何历史的重压、伦理的束缚抑或两性的窘境。作者剥离了原有的矫饰和冷峻之后,作品呈现出抒情唯美的意境,“已消去了历史传说所应有的纵深度和苍凉颜色,更在意童话般的境界和简约、质朴的传承”[4]。
二、对个体命运的发掘与重构
新历史主义注重对“逸闻轶事”的发掘,认为这种处江湖之远的历史偶然和文化碎片才能触摸到更为真实的历史和更加鲜活的生命。其兴趣点不在于具有规范化和普遍性的抽象历史,而在于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在特定偶发情境下的即兴式历史。作者的创作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在文学作品的文化文本中也同样蕴含着权力颠覆与形式遏制的二元消解机制,将颠覆性的不稳定因素不断融合到艺术形式的文本结构中。”[5]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完成自我塑型的过程。读者在面对作品中超越传统的历史形式时,往往会从阅读“诧异”到接受“惊叹”直至审美“共鸣”,尽管宏大叙事被解构,但对个体命运的发掘与重构却走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的帝王生涯》与其说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兴衰史,毋宁说是主角端白的心灵史,仿若有一个忧郁孤独的游魂飘荡在小说中,整个故事空间呈现出一种诗性的空灵。故事从主角端白的追忆开始,在父王驾崩的那天,他记住的是“犹如破碎的蛋黄”的太阳,留下“哀婉啼啭和几片羽毛”的白色鹭鸟,至于对父亲的记忆和权力的交接则被一笔带过。端白浑浑噩噩地成了燮国的王。令人惊异的是,这位国王似乎对一切都抱持着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得到王位、邻国入侵、蕙妃的得宠和被放逐、失去王位流落民间,直至最后燮国灭亡隐居山间。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场又谢幕,只为衬托端白的内心世界,其中的人物关系“全部转换成了深埋人物内心的‘自我对立’,人物生成自身,同时也毁灭自身”[6]。 被错位地安放在帝位的主角,内心真正渴望着如飞鸟般自由翱翔。剥离了权势和爱情的外壳,留下的是对人类追求精神自由可能性的拷问。飞鸟的意象在文中反复出现,父王驾崩时从乌桕林中低低掠过的鹭鸟,惠妃用双手模仿飞鸟展翅的动作,故事到端白踏在绳索上飞翔达到高潮。隐藏在平静和漠然的表象下是对命运无法自我掌控的惶惑,是挣脱金笼奔向自由的喜悦。因此端白在面对从帝王到走索艺人的巨大落差反倒认为“看到我的两只翅膀迎着雨线訇然展开,现在我终于飞起来了”[3]165。行文至此,主角看似从“笼中鸟”转换为“飞鸟”,终于求得了精神的救赎,然而故事最后燮国灭亡,端白变得孑然一身,梦见所有鸟都飞上了天空,自己却选择在苦竹寺度过余生。文本在这里戛然而止,或许这也是作者给自己及读者的疑问: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牢笼,转换了身份和时空后就能挣脱吗?小说由此从历史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已不仅仅是一个帝王的故事,或者说,主角的身份和故事的背景已不再重要。故事本身击中了每个读者对自我精神困境的共鸣和挣扎,促使读者和作家一起思考,如何能求得真正的自由而非逃避的敷衍。
在全球化语境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碧奴》,更是一个自我求索的文本。在《我的帝王生涯》中除了主角端白外,还勾画了蕙妃、燕郎等重要配角。而《碧奴》中除了主角碧奴外,配角都成为了符号化的存在。作者甚至将“孟姜女”这个名字都抛弃,从而彻底放下了历史和语言的沉重包袱,使叙述离开世情转向想象的天空。原作中孟姜女和万岂梁的爱情在小说中被设定为“愚笨”的碧奴不得不嫁给穷困的岂梁。小说的开端时岂梁已经客死他乡,在之后的叙述中也不再有关于岂梁的回忆和追溯。这样,神话原型中孟姜女的爱情元素就全然被打破,剩下的只有一个女子近乎执拗的坚守和追寻。这种不知缘由,令人惊异的执着使碧奴踏上了送冬衣的旅程,从桃村到市井再到王朝,一个故事勾连出另一个故事,由此带出了纷繁杂乱的众生相:对碧奴冷嘲热讽的桃村女人、魂魄变成的通灵青蛙、百春台君王豢养的鹿人少年、以生命换来一个“媳妇”的小偷门客芹素,詹刺史府用各种味道的眼泪熬成的“泪汤”……这些故事或诡谲或迷离,女主角碧奴在其中则一次次遭遇着难以逾越的困境:冬衣被抢走、险些被活埋、被逼嫁给一个死人,在混乱的人群中抢夺衣服,成为作“泪汤”的工人,最后一无所有却还是背着石块上了大燕岭。我们无从分辨碧奴的执着是出于爱情还是伦理良心,简洁的故事线索只是证实了碧奴执着自己的信念和目标,用强大的心灵对抗一切困苦。在简洁的线性时空秩序下,呈现出的是久违的一个人坚守自我的巨大能量,不是执着于繁杂具体的某个事物,而是执着于执着本身带来的感动。“历史不过是一种叙述和修辞,历史作为故事的背景凸显的是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心灵困境”[7]。因而在文本中,碧奴从原本那个只会用头发哭泣的女子,变成了一个泪飞顿作倾盆雨倾倒长城的“神”的行为。这是近乎西西弗斯抑或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无畏于孤独的生存困境,始终坚持真的自我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碧奴》这个简单的自我追寻的故事比原型神话更为超脱和灵动,对主人公形象的展示也更为鲜活和立体。
三、唯美语言架构的诗学意境
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下,作品中蕴含着对“权力关系”的颠覆——遏制模式,通过文本结构和艺术化的处理,达到对权力颠覆的艺术消解过程。作者则在创作中利用语言叙事和文学经验达到对自我的塑型。“我们可以把新历史主义的实践当成本文与语境之间关系的延续”[8]。 在颠覆/遏制的二元机制中,颠覆性的不稳定因素被不断包容,并融合到以艺术形式存在的文本结构中。能指的诗学功能因此漂浮出来,凸显于文本之上。读者内心复杂的动态文化力量被唤醒,浮现出某种隐喻,从而使作品超越了自身形式边界达到一个更为广博深渊的世界。奇幻的想象和灵动摇曳的文字构筑了一种澄澈空灵的意境,迷离闪烁中跨越了时空,总能在小说行进到最逼仄的阶段化腐朽为神奇。
苏童的叙事语言精致中包含水汽,充满抒情意味,将可悲可怖的故事娓娓道来,阴气弥漫中偏又露出几许魅惑妩媚之姿。《我的帝王生涯》的辞藻可谓是华美的。无论是形容太阳如同“破碎的蛋黄悬浮”还是灵魂如同美丽的白鸟“自由而傲慢地掠过苍茫的天空”,奇特的比喻带来一种细腻微妙的氛围,抽离了历史架构的厚重,纯粹的诗性直觉诉说着人生的孤寂无力。绮丽的文字带来主角絮絮的个人独语,在其中能捕捉到思绪和情感的流动。“故事借助诗化的语言轻灵地绵延伸展出细腻之至微妙之至的触丝,营造出一种怀古感伤的氛围,构筑了一种飘忽的摇曳生姿的意绪结构。”[9]行文中反复出现的“燮国的灾难就要降临了”与秋深、火熄、暗箭已发连缀在一起,给文本笼罩上一层神秘不可知的宿命气息。这个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故事,由于作者行云流水的优雅语言表达,产生了一种江南雾气般迷蒙的虚幻感,从而减轻了悲剧性的压力,给读者带来诗意的阅读体验。在文本中对色彩美学的运用也使叙述幽怨婉转而气韵跌宕,充满了唯美的画面感。白色的鹭鸟、金黄色的雏菊、红馆、蓝紫色的天空等大团的色块使色彩的叙事功能被发挥到极致。明朗温暖的颜色书写的却是灾难与死亡,强烈反差带来的巨大张力给阅读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温暖中的寒意。此外,作者在小说中还调动了多种感官,营造了一个立体可感的世界。飒飒秋风落叶和间或响起的夜漏梆声,混合着冷宫的夜半歌声,是无从排解的死寂与凄凉;薄荷、芝兰和墨砚混合的香味,则是对故国最后的一缕回忆。这样立体的幻境书写了真实的灵魂状态,“将不堪一顾的生命抽样,幻化成阴森幽丽的传奇——就像那闪烁暧昧光芒的夜繁华一样”[10]。 历史的尘嚣散去,留下的是空灵悠远的意境和旷远传来的诗意表达。
如果说《我的帝王生涯》的基调是阴郁腐败,到了《碧奴》中则彻底变为了温暖丰沛。作者牢牢抓住了“眼泪”这个线索,以主角碧奴的哭泣连缀成整部小说。碧奴起初被设定为只会用头发哭泣的女子:“她的头发整天湿漉漉的,双凤发髻也梳得七扭八歪,走过别人面前时,人们觉得是一朵雨云从身前过去了”,到最后在五谷城的牢笼里全身都在哭泣:“它细小清澈,却流得那么湍急,闪着寒光,像一支支水箭一样射向人群”[11]181。眼泪的隐喻传递的是以自身坚定温暖的圣洁力量对抗暴力和嘲讽,其渗透到读者内心,传递着久违的真情。原型中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幻化一个个奇幻的意象。尤其是在碧奴即将到达大燕岭的时候,官道上如银箭般的水流,青蛙排成的灰绿色队伍,还有如白色镶金的花带般的白蝴蝶群,奇幻的景观和色彩的渲染构成了唯美诗意的视觉盛宴。作者还将碧奴的心理与环境融为一体,营造出细腻入心的情境。如碧奴在树下绝望地等候死神时:“黎明时分,暗蓝色的天光已经勾勒出树林苍老的线条,空气里弥漫着苔藓杂疼淡淡的腥味,树枝分割的天空很零乱,有的地方亮了,有的地方还沉在一片幽寂之中。”[11]65叙述方式的迷离传奇,语言的灵动唯美,结构的简洁自然,使“一个人的故事”成了诗篇,展现出了这个民族的风格与文化,谱写了一曲“人”的赞歌,织就了与天地对话的经纬。
要而言之,苏童在新历史主义视野的关照下,坚持自己的写作特质,从历史的碎片和缝隙进入,使作品呈现出唯美的诗学特质,达到了诗化和历史的圆融结合。但是他在进入时代性较强的写作时往往写得较为匠气和僵硬,显得灵气不足。此外,在小说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效应方面,需要警惕沉沦历史、陷入小历史相对主义、走向历史不可知论及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的趋势。
[1]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苏童.我的帝王生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4]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6]吴晓,吴智斌.从先锋作家历史叙事看新历史小说接近文学本体的方式——以苏童创作为例[C].中国历史文学的世纪之旅——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242.
[7]吴雪丽.苏童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王卫红.面对历史的凭吊与对话——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75-77,81.
[10]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苏童.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蒋涛涌)
Aesthetic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On Su Tong'sMyLifeasEmperorandBiNu
QIAN Y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From the 1990s, Su Tong creat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novels such asMyLifeasEmperorandBiN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destiny in these two novels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New Historicism. It also explains the poetic artistic conception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his beautiful language.
New Historicism; Su Tong; aestheticism; cultural poetics; individual destiny
2015-04-09
钱钰(1991-),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生。
I247.7
A
1008-3634(2016)02-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