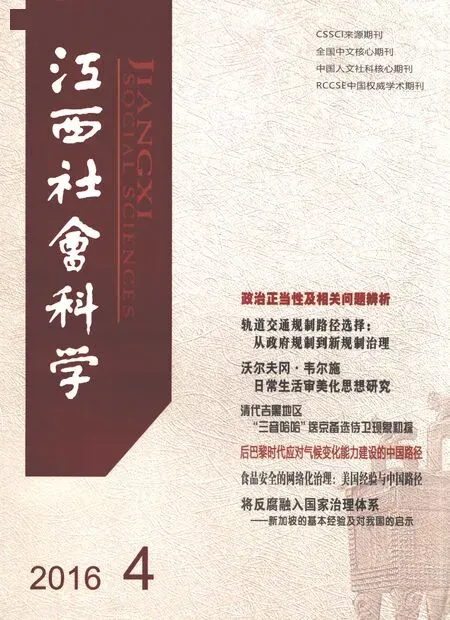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路径
■曾文革 冯 帅
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路径
■曾文革 冯 帅
《巴黎协定》的达成昭示着后巴黎时代的到来。从《巴黎协定》的内容可知,其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发达国家利益诉求色彩,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下的CBDR原则也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导致中国在能力建设上面临形式、角色和立法的诸多挑战。尽管中国已加强能力建设政策和立法制定,并大力实施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其在立法规划、立法科学基础和立法内容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有鉴于此,中国应在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立法方向、立法基础、制度完善和《巴黎协定》的落实等方面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完善INDC内容、加强组织机构能力建设、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并强化国际气候立法的国内实施。
《巴黎协定》;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
曾文革,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 帅,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重庆 400044)
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①是减弱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影响的重要保障,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履约能力的首要条件,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气候谈判地位的必然选择。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hange,以下简称《公约》)、《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和“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等均对其进行了规定。②这些文件将中国纳入发展中国家阵营,认为其应当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然而,由于这些大会成果或过于原则化,或时限仅至2012年,或仅具有“决议”(decision)性质而无实际法律约束效力,因此,作为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协定,《巴黎协定》的通过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 “后巴黎时代”的到来,并对后巴黎时代的能力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至中国而言,《巴黎协定》将中国置于“三元划分”模式的第二梯次,构成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CBDR)原则的弱化,③进而影响中国能力建设的未来走向。[1]在《公约》中,能力建设规则设置的初衷即促进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这一目标之前,需要为中国预留一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然而,《巴黎协定》大大简化了这一程序。能力建设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是缔约方参与减排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在《巴黎协定》下,中国的能力建设将面临艰难的路径选择问题。
由于《巴黎协定》于近日才得以达成,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完全跟进,且基本未涉及后巴黎时代的中国能力建设问题,但在《巴黎协定》的体制安排面前,中国的能力建设将面临重大挑战,其国内能力建设体系也逐渐暴露出潜在缺陷,并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及其国家形象,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刻不容缓。鉴于此种考量,本文拟提出一种分析思路,以期抛砖引玉。
一、《巴黎协定》给中国能力建设带来的挑战
诚然,《巴黎协定》的达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进程可知,各国在相关条文上虽已形成一些共识,但分歧依然明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阵营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内外压力,这些压力对中国的能力建设构成了较大挑战。
(一)形式上从“他助”转向“自助”
从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可知,能力建设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而言,主要形式有二,一是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援助而进行能力建设,二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通过本国政策和立法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前者谓之“他助”,后者称为“自助”。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相关资金和技术规则均指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侧重于“他助”层面。尽管在后续《公约》缔约方会议上达成的一些“决议”中,“他助”有弱化之趋势,但其时因“决议”的软法性质而未能发挥较大效用。然而,《巴黎协定》正逐渐打破这一平衡。
作为能力建设的主要方式之一,《巴黎协定》的资金规则第9条第4款和第9款强调应优先确保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效获取气候资金资源;在能力建设规则第11条第1款中,《巴黎协定》认为尤其需要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帮助;在透明度规则第13条第3款中,《巴黎协定》明确不应当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当负担。这些条文将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两方”中单独抽出,④意味着国际气候谈判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之前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两方”逐渐走向“发达国家缔约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三方”。再观《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对“两方”的划分,其主要依据是各国的“能力”,也即能力建设的“他助”是指“能力强”的国家对“能力弱”的国家的援助。在“三方”格局下,很显然,“能力弱”的国家指的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因CBDR原则而不至于立即切断了“他助”的可能性,但中国能力建设从“他助”转向“自助”的趋势却十分明显。此外,在《巴黎协定》文本之前的 “主席提案”(Proposal by the President)中,“能力建设”部分第74条第f款认为,应探索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逐步自主建设和保持的能力。尽管“主席提案”并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但其至少代表着一种发展趋势,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将逐渐实现从“他助”到“自助”的转变。
(二)角色上从“接受方”转向“接受方”与“施予方”并立
受“他助”形式影响,于《公约》生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能力建设上处于 “接受方”地位,具言之,至少在国际法依据上,中国的能力建设应当主要是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这种模式是由国际气候谈判的利益集团划分所决定的,其时中国正处于“77国集团+中国”阵营,《公约》通过缔约方历史排放理论确立了欧盟和“伞形集团”的减排要求,同时基于公平原则将“77国集团+中国”置于能力建设的被动接受方,目的是待这些国家能力建设完成至一定阶段时,再适当参与减排,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进程和能力建设状况来看,距实现这一目标尚需一段时间。然而,《巴黎协定》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公约》缔约方在“三集团”的基础上组建了 “雄心壮志”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且有意无意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鉴于近年来“77国集团+中国”的部分成员在对待中国减排义务问题上更趋向于欧盟与“伞形集团”的立场,因此,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该联盟是否主要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此情形下,中国不仅需要面对欧盟和“伞形集团”的“外部”压力,更要面对来自“77国集团+中国”的“内部”压力。这一点在《巴黎协定》的减排条款中得到了印证,其在第4条第4款和第6款中指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并提高其减排目标,并逐步实现绝对减排或限制减排,而最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编制、通报其国内温室气体低排放的计划与行动。可见,中国正处于从无强制减排阶段向绝对减排或限制减排阶段的过渡时期。如前所述,能力建设指向的是减排责任,在中国减排责任被加大的同时,按照《公约》的逻辑,中国的能力建设定是已发展至一定程度,而根据《巴黎协定》的能力建设条款可知,“能力强”的国家需要向“能力弱”的国家进行支助,由此,中国不仅从发达国家缔约方处得到的援助会减少,而且还需对其他“能力更弱”的国家进行支助,其能力建设的“接受方”的国际法地位也将逐步转向“接受方”和“施予方”并立的局面。
(三)立法上从“被动调整”转向“主动促进”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均将中国置于“接受方”地位,并要求发达国家对其进行援助,因此,在能力建设上,中国侧重于“调整”型立法,也即中国仅需在能力范围内与其他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其时能力建设立法并无强制性保障机制和措施,如《节约能源法》第8条指出国家应促进节能技术创新与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采取此种立法模式彰显着中国在能力建设立法上的宽松环境。尽管《公约》体系下的部分决议要求中国参与减排,但由于决议的软法性效力,这一诉求并未对中国能力建设立法造成过多冲击。然而,《巴黎协定》正在改变这一状况。
《巴黎协定》的重大意义之一即在于其具有法律约束力,与之前达成的“决议”具有本质区别。就国际气候立法而言,《巴黎协定》属于框架性协定,相关减排议定书和技术规则将随之重新制定,然而,就《巴黎协定》第2条而言,其要求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之内,这与之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所指向的2.7℃目标相比严格了很多,据此多出的150亿吨的减排任务分担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9%,若后续谈判围绕这一数据而进行立法,中国的减排任务之大将会空前。[2]诚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所言,为了应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法律开始逐渐演化。[3](P122-137)接着,在“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理论基础上,卢曼指出,如果没有与社会其他功能系统结构进行耦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将会崩溃。[4](P385)按照该理论,在《巴黎协定》对中国的减排责任和资金、技术的受援助程度构成较大挑战的情况下,为了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5](P2)相关国内立法必然面临着重构的命运,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面前,中国在能力建设上将逐步转向主动性的“促进”型立法,并对国内能力建设立法提出更高期待和要求。
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进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社会视野时起,中国一直积极探索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加强能力建设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并大力推行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然而,客观而言,中国现有能力建设的进程仍存在立法规划难以有效实现、立法科学基础薄弱和立法内容尚存缺陷等问题。
(一)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进程
尽管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立法和政策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段差距,但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却是有目共睹。
1.制定能力建设政策方案
作为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发展型”需求和应对新增气候变化风险的“增量型”需求。[6]在这两种需求交织下,中国能力建设政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无疑是平衡二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中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均开展了能力建设政策方案的制定工作,并已基本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能力建设政策体系,为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保障。
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自此,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受重视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并已作为国家政策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至2012年期间,国家和部门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便已达到117项,省级行动方案和规划为52项。[7]其中,在国家层面上,专门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有8项,包括《“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等,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和措施等进行了统筹协调;在地方层面上,因地理位置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往往具有其特殊性,以满足各地区的不同需求,如天津和江苏等省市将海岸带作为能力建设的重点领域,而安徽和重庆等易传播疾病风险的省市将公共卫生作为能力建设的主要方面之一。[8]
2.完善能力建设立法体系
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政策与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法”与“非法”的界限,政策是尚未被整合进法律中的政府惯例,[9](P464-466)政策只有被融入立法中,才有可能实现法治建设。[10]因此,相较于政策而言,立法的价值在于为整个社会设置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表现为一种常态管理,是长时效的。[11]
基于这一原理,在国家政策基础上,中国的能力建设立法也在不断完善中,在国家层面先后制定、修订了《草原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专门性法律法规,涵盖农林业、大气污染等领域,对农林业生态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规定。相对而言,地方层面的能力建设立法发展较为缓慢,但也对其地区特殊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如2010年《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作为全国第一部地方政府部门规章对青海省气象灾害预防、建筑采暖能耗等问题进行了规定。考虑到现有能力建设立法内容涵盖有余但体系性不足等特点,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探索制定一部较系统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并已经过讨论、论证形成了较全面的文本草案。此外,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环保法”[12]的2015年《环境保护法》强调了对大气、水和土壤等的保护,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由上可知,相关能力建设立法已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对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3.推行能源节约制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将降低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作为国内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并先后制定、修订了《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坚持节能优先,以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技术进步为根本,以法治为保障,加快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电力、太阳能等产业,为能源节约与利用、新能源开发使用等指明了方向,通过逐步转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形成能源节约机制,逐渐走向能源节约型社会。
1991年至2005年,通过制定能源效率标识、引进先进能源技术、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措施,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其中,煤炭使用年均降低4.1%。据计算,在上述15年间,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根据另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2005年至2013年间,中国单位GDP能耗降低了26.4%,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8%,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3.5亿吨以上。[13]在节约能源的同时,中国还注重对能源结构的改善,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达到1.66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14](P321)可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中国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做出了显著贡献。
4.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21世纪初,为了进一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中国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开始施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现今,中国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已有42家,另外,北京、上海和深圳等7个省市还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已全部上线交易。2014年,中国又开启了低碳工业园区和社区试点工作。根据中国十三五规划进程,中国碳消费量有望在2030年见顶,煤炭消费则有望在2025年见顶。[15]
除此之外,中国还发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等文件,通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⑤将经核证的碳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CERs)转让给发达国家,以获取额外资金和先进友好环境技术。总体而言,CDM项目合作可以降低温室气体的减排经济成本,再加上中国一贯坚持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驱动,中国对CDM项目合作尤为重视,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和CDM基金。据统计,2009年,仅中国参与的CDM项目所产生CERs成交量就占了全球的84%,[16]注册项目数占全球注册项目总数的58%,其项目注册数和年减排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截至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CDM项目共计5073项,其中已经获得CERs签发的中国CDM项目达到1468个。[17]与国内层面的节约能源不同,CDM项目是在国际层面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CDM项目合作形式,中国将获取的资金和技术用于支持能力建设,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举一动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面临如此压力,中国仍努力探索能力建设的可行性途径,制定、颁布了能力建设政策和立法,并大力实施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宗旨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对实现“控制全球平均升温较工业化水平前2℃以内”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促进《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内容的有效落实做出了贡献。然而,受制于中国发展中国家性质和立法水平较低等因素,中国在能力建设上仍有待于完善。
1.立法规划难以有效落实
作为融国际技术转让、国际投资于一体的国际商事交易,碳排放权交易需要稳定、明确、长期有效的法制环境。[18]然而,无论是从传统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来看,还是从新近的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来看,现有能力建设立法内容均存在落实难的困境。其一,关于传统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传统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体系主要包括能源立法、农林业立法等,但从现有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鼓励”、“支持”或“引导”等词出现的频率非常之多。一般而言,这种表述往往出现在行政指导性文件之中,发挥引导作用。由于缺乏国家强制性,现有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实效性将大打折扣,难以实现立法初衷。新《环境保护法》虽淡化了各单行法的“引导性”规定,大多数条文具有强制约束效力,但由于其是统领能源、资源、环境等的一般法,所以相关条文还是较为原则,缺乏专业性和具体性。其二,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如前所述,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起步较晚,其主要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再辅以两个部门规章——《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在这三部法律文件基础上,北京、上海等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均制订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碳排放管理施行办法》等地方政府规章。从这些试点方案和管理办法的内容来看,其对超碳排放配额的处罚措施主要限于罚款、企业信用不良记录、不得享受优惠政策等,而后两种约束方式并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难以有效落实立法规划,另外,就超额碳排放行为的罚款责任方式而言,其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利于实现“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的目标。[19]
2.立法科学基础较为薄弱
作为司法与执法的前提和依据,立法须具备充分的科学性和可靠的现实基础,其中,立法的科学性要求其具有规律性、有序性与和谐性。[20]然而,就中国现有能力建设立法体系的制定来看,其仍落后于能力建设政策体系的出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在有序性方面,中国能力建设立法呈现出较为混乱的态势。立法有序性要求法律具有确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等特点,然而,中国现有能力建设的文件仍主要表现为国家和地方政策,立法数量较少,尽管有学者将散见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划分为减缓型气候变化立法和适应型气候变化立法,[21]但这种划分方式仅作为学理上的研究和分析,并不十分稳定,虽然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中均有能力建设的影子,但客观而言,这种立法模式过于分散和混乱。另外,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方面,目前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事项较为原则化,缺乏具体的、专业性的实施细则来规定该交易的具体运行过程,导致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仍不完善。其二,在和谐性方面,中国能力建设立法出现了立法断层。立法和谐性要求立法者审时度势,实现气候正义,以确保法律和社会之间的适应关系。现今,在中国,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主体,企业在减排方面缺乏应有激励,更毋言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可见,在和谐性上,中国现有能力建设立法也存在较大缺失。长此以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将走向迟缓,难以实现市场交易的可持续发展。
3.节能立法内容仍有待于加强
我国的能源法制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侧重开发利用转向利用与保护并重的过程,但能源节约制度仍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厘清和检视。首先,未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节约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更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节约能源应处于优先地位,[22]但现有能源节约立法基本未将其与应对气候变化及能力建设挂钩。其次,未充分体现农村节能内容。《节约能源法》对农村节能的规定仅体现在第59条,过于简单,不似工业节能、建筑节能等用专门章节加以强调。鉴于农村能源利用技术欠发达,能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将其进行专门规制应是《节约能源法》需重点考虑的方向之一。再次,未充分调动公众参与。若公众无法充分参与,则节能目标将成为空中楼阁。由于立法缺失,公众仍存在重开发、轻节约的倾向,仅将能源节约作为缓解能源供需矛盾的权宜之计。而且,作为比事后监督更为重要的事前参与和预防,现有节能法基本未加以涉及。最后,未清晰界定政府的监管职能。中国节能法将监管职能赋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未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调,也未明晰各部门的权利义务,造成监管体制混乱和执法障碍。
4.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内容尚存缺陷
现今,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在为全球减排行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现有机制的不足。其一,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尚未实现互连,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企业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主体,但试点地区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还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行政干预力度过大,缺乏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易衍生“权力寻租”⑥现象。因此,现阶段,中国通过市场化配置环境资源的进程较为缓慢,难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3](P102-113)其二,作为全球CDM项目的最大供应方,中国在国际CDM项目合作上缺乏定价权。中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主要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自愿减排的项目为主,采取协议定价模式,而不是由市场供应链所决定。换言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是由双方商讨后议价而成,且往往以低于国际水平出售给发达国家,可见,在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方面,中国的市场权力极为匮乏。[24]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机制还远没有形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量也十分有限。其三,由于缺乏完善的立法体系,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举步维艰。企业是否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应当有可靠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加以核实,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中介机构服务体系还很缺乏,使得很多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而且,鉴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经济属性,其应与财政、金融等活动挂钩,但目前中国对此考虑得并不充分,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造成极大限制。另外,从各试点省市公布方案来看,其均将碳排放强度指标 (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总体目标,而不是以碳排放总量指标(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量)作为基础,因此,这对企业未来绝对减排量的界定极为困难。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攻坚期,面临着资源“瓶颈”性约束和大气环境污染两大难题,[25](P378)却仍然以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身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鉴于其发展中国家性质,中国能力建设的立法规划仍有待落实,立法科学基础尚待加强,极具发展潜力的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也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后巴黎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
在后巴黎时代,中国能力建设的形式、地位和立法方式均受到较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力建设进程所存在的问题也更为集中地凸显出来。对此,中国需要统筹能力建设政策和立法,确立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和方向,夯实能力建设的立法基础,充实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并强化国际气候立法的国内实施。
(一)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晰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生态文明建设被首次列入中国的五年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科学有效防御气象灾害,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大力改善大气污染状况,而这也正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26]
因此,现阶段,为了进一步明晰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中国需要逐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并努力做到以下三点:一是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重视气候安全就需要充分认识气候规律,并增强气候灾害风险的应对能力。由此,中国需要将气候安全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构建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的科学研究,并注意提升全民气象防灾意识。二是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气候资源包括光资源、水资源、太阳能资源等,能力建设要求充分利用这些气候资源发展现代农业,将气候资源纳入生态管控制度,建立气候承载评估制度和基于气候承载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等,并逐步实现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气候安全型”城市和国家的宏伟目标。[27]三是加快生态保护红线立法制定工作。
为维护国家和区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目标。目前,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正征求意见,而区域层面的立法工作虽已开展,但进展缓慢。因此,中国需要细致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内容,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以高标准、严要求对红线区域进行保护,并设置生态补偿机制和红线区域产业退出制度等,同时将红线区域的监督管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和自然资源资产的离任审计。
(二)完善INDC减排目标,确立能力建设的立法方向
“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是于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各方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减排承诺机制,根据该机制,各方应自主提交一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方案,这与《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承诺模式具有本质区别。就国内层面而言,INDC的法律属性虽暂难以确定,但其将是各国减排行动和气候立法的主要依据仍不容置疑。在 《巴黎协定》下,中国无法独善其身,需要不断加大减排力度。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了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自主减排目标。⑦
然而,就INDC内容来看,其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一方面,中国INDC应扩充减排温室气体的类型。中国INDC确立的减排承诺对象为二氧化碳,也即其60%~65%的减排目标仅指二氧化碳的减排量,而不包括二氧化硫和甲烷等温室气体。反观其他国家的INDC,大部分《公约》缔约方均将温室气体类型扩展至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甚至包括《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六类温室气体。据悉,全球仅中国单就二氧化碳进行了减排承诺,而对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关注程度还不够。[28]另一方面,中国INDC应充分阐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的难度。中国的INDC就行动目标、政策措施和谈判意见等进行了阐释,基本未涉及中国减排目标实现的难度。中国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其国内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短期内无法完全脱钩。INDC文件缺乏减排难度的阐述将把中国推向减排制高点,中国可能因此而面临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中国应在充分性、实现目标能力等方面借鉴和总结国外相关经验,不断完善INDC内容,进而确立能力建设的程度、阶段和方向,确保能力建设立法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三)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夯实能力建设的立法基础
政府机构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由此,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增加了部分职能部门。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管理、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和机制。[29]然而,领导机构虽已完善,但办事机构及其管理体制仍然缺乏,且在运行过程中的法律依据和支撑较为薄弱。
对此,中国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制定一部法规或规章。⑧明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法律地位,规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应采取措施的责任,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的衔接,明确农村节能的重要性,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政策及相应激励与惩罚措施,建立气候治理的执政问责机制,规范办事流程,使气候变化问题真正进入国内法调控领域。二是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体系。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专门条文规范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程序和评价机制,建立低碳行业标准标识制度,完善部门分工合作机制,并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强化能力建设的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四位一体的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机制,在明确政府监管职能的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能力建设的行动,具体方式包括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两种,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明晰自身权利和义务,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充实能力建设的法律支撑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育迟缓,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体制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缺乏减排意愿。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升级、充实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立法进行补充和完善。
首先,确立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原则。这些立法原则应当包括逐步推进原则、奖惩相结合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等。其中,逐步推进原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起步较晚,短期内难以一步到位;奖惩相结合原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积极性和法律约束效力,企业减排积极性可以通过经济激励、通报表扬等形式进行,法律约束效力可以通过经济制裁、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等予以维护;公开透明原则主要考虑到市场信息的推广和市场监督的确立,以杜绝违反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不法行为,提高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体系的公众认可度。
其次,明晰碳排放权交易立法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所涉及的法律行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客体、碳排放权交易方式、碳排放权交易总量控制、碳排放权交易初始分配、碳排放权交易定价和评价等法律制度,[30]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所涉及的法律行为包括国家行政许可和指导、第三方核证主体的审评和确认、市场中介机构的信息提供及碳排放权交易 (包括CDM项目交易)四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包括一级市场主体和二级市场主体等;碳排放权交易的客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经 《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六种温室气体;碳排放权交易方式包括碳期权、期货交易和投资等;碳排放权交易总量控制要求采取适中原则,在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同时考虑企业的减排成本;碳排放权交易初始分配可以采取先免费分配再有偿分配的途径;碳排放权交易定价主要包括一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初始定价和二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按需求及碳金融衍生品的定价;[31]而碳排放权交易评价主要是交由公正的第三方核证机构予以执行。
(五)强化国际气候立法的国内实施,推进《巴黎协定》的全面落实
对于参与国而言,国际制度并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深入到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和程序中,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32](P32-40)这一理论置于气候变化领域同样适用。在后巴黎时代,面对《巴黎协定》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国需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气候立法的有效衔接,以全面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具言之,中国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加强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资金、技术的“受援助”地位,但作为大国,中国可以适当对其他更不发达国家施以 “援助”,以实现资金和技术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时鉴于国际组织的相对中立性和客观性,中国可以与其合作以传递中国立场和观点,进而应对气候变化。
二是跟进传统资源与环境立法。对传统资源与环境立法予以跟进,需要贯彻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的各项规定,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维护投资各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和区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33]以环保手段“绿化”《对外贸易法》,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安全供给,建立能源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同时完善林业碳汇、陆地碳贮存和吸收汇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体制等。
三是推进CDM项目的立法工作。对CDM项目进行立法主要是指在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高位阶的行政法规,将涉及CDM的外资和技术引进、项目审批与监管、违规处罚等问题纳入其中,[34]使其更具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
四是推动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⑨的国内立法研究工作。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CCS的域外立法已臻完善,[35]但中国的CCS立法尚未启动,未来的CCS立法需要在低碳经济、风险为本、利益衡平等立法理念和环境安全、公众参与、国际合作等立法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二氧化碳的法律定性,确立CCS申请核准管理制度,制定CCS风险评估、管理、应急和转移机制,尤其侧重对CCS泄漏与突发事件的风险预防和应对措施,并对CCS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刑事责任追究,[36]同时建立CCS多元化融资机制,加强CCS与排污权交易等法律制度的衔接。[37]
作为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承担方面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并提交了INDC文件,明确了自身在减排方面的宏伟目标。然而,《巴黎协定》的通过,大大加快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承担的进度,中国能力建设的形式、角色和立法也随之发生动摇。对此,中国应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完善INDC内容、加强组织机构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应对,以确立能力建设的行动方向并促进其角色转型。
四、结论
2015年12月12日达成的《巴黎协定》带有浓重的发达国家利益诉求色彩,与《公约》不同,协定加大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对中国能力建设的形式、地位和立法等带来了诸多挑战。尽管自《公约》达成开始,中国便积极制定能力建设政策、完善能力建设立法并加大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受发展中国家性质和立法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在能力建设制度上的不足也逐渐凸显:一是能力建设立法多采用指导性用语,淡化责任追究力度,导致立法规划难以有效落实;二是能力建设立法在有序性与和谐性方面存在不足,表明立法科学基础较为薄弱;三是农村节能、公众参与和政府监管等方面存在缺漏,映射出节能立法内容仍需加以完善;四是中国CDM项目缺乏定价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较为混乱,暴露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尚存缺陷。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回归到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立法方向、立法基础、制度完善和《巴黎协定》的实施等方面,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推动和影响下,逐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路径和制度完善建议,全面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不断促进国际气候立法的国内实施,进一步加强中国能力建设的发展,逐步强化中国在国际气候立法中的作用,为以后的国际气候谈判做准备,也为能力建设的国际气候合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及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合理、有效、有序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根据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术语表,能力建设是指“在气候变化中,开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技术技能和机构运转能力,使这些国家参与从各个层面的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研究并执行京都机制等工作”。如无特别注明,本文所指“能力建设”均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能力建设。
②《公约》第9条明确指出,应当设立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需要;《京都议定书》在第10条第2款e项中亦强调,应加强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人才和机构能力方面的建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培训此方面的专家;“巴厘路线图”试图通过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等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能力建设进行重申或推进,并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能力建设进行扶持。
③自2012年“德班决议”采用了“适用于所有缔约方”(apply to all parties)的表述开始,针对CBDR原则的未来走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讨论,多数学者预测在《巴黎协定》中CBDR原则很有可能会被重释——仅强调共同责任而忽视有区别的责任,抑或被“优惠待遇”或“差别待遇”原则所取代。然而,从《巴黎协定》内容来看,其依然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了,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了CBDR原则,并未走向另一极端。但是,《巴黎协定》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剥离开,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置于三元划分模式的第二“梯次”,导致发达国家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承担,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相应责任,构成对CBDR原则的弱化。
④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的阵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方三集团”,其中,“两方”指的是南北两方,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三集团”指的是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和“77国集团+中国”等三个利益集团。“三集团”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解决各国的减排义务分配问题。一般而言,三集团因立场差异代表着国际社会的三种不同观点,其中,欧盟认为,所有的经济体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均应承担减排义务,并主张为“基础四国”设定一个减排峰值;“伞形集团”的成员多为排放大国,其认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强制性的量化减排义务,并主张应建立“自主承诺+公开评议”的国际框架;“77国集团+中国”一直是CBDR原则的坚定守护者,认为发达国家应履行《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减排责任。参见姚莹著:《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我国面临的减排挑战》(《法学》2014年第9期)。
⑤CDM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三机制之一,另外两种机制分别为联合履约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贸易机制(Emissions Trading,ET)。一般来说,CDM主要包括如下潜在项目:改善终端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替代燃料;碳汇项目等。
⑥所谓的“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
⑦《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在第一部分“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指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⑧如日本的《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该法由日本国会于1998年10月通过。参见孙磊著:《日本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对策》(《科协论坛》2008年第3期)。
⑨CCS是指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源分离出来,输送到一个封存地点,并保持长期与大气隔离的过程,是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 《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曾文革,冯帅.巴黎协定能力建设条款:成就、不足与展望[J].环境保护,2015,(24).
[2]李建广.解读“双12”巴黎协议[EB/OL].http://carbonmkt.cn/plus/view.php?aid=7995.2015-12-26.
[3]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4]Niklas 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Cambri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5](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Pan J H,Zheng Y,Markandya A.Adaptation Approaches to Climate Change in China:An Operational Framework.Economia Agrariay Recursos Naturales,volume 11,2011.
[7]彭斯震.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现状、问题和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9).
[8]许吟隆.边缘性适应:一个适应气候变化新概念的提出[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3,(5).
[9](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0]鲁鹏宇.法政策性初探——以行政法为参照系[J].法商研究,2012,(4).
[11]郑敬高,田野.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12]金煜,王硕.解读“史上最严格环保法”[EB/OL].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szgc/2014430/100433.html.2015-12-01.
[13]李俊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回顾与展望[J].中国能源,2014,(2).
[14]丁一汇.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影响、适应及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15]何建坤,斯特恩.中国的气候承诺[EB/OL].http:// 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728/3634815.shtml.2014-07 -28.
[16]李志学.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状况、问题和对策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4,(11).
[1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已获得CERs签发的中国CDM项目(1468个)[EB/OL].http://cdm.ccchina.gov.cn/NewItemAll2.aspx.2015-12-16.
[18]何鹰.我国碳交易法律规制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2,(1).
[19]王彬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其立法跟进[J].时代法学,2015,(2).
[20]冯玉军,王柏荣.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标准初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21]张梓太.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框架体系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5).
[22]庄贵阳.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经济的低碳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07,(5).
[23]彭江波.排放权交易作用机制与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24]卫志民.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25]《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6]白屯.生态文明建设:在适应气候变化中前行[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6).
[27]杜受祜.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J].社会科学研究,2014,(6).
[28]冯相昭,等.从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变化[J].世界环境,2015,(6).
[2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EB/OL].http://www.ccchina.gov.cn/archiver/ccchinacn/UpFile/Files/Default/20131108091206779023.pdf.2013-11-23.
[30]何晶晶.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初探[J].中国软科学,2013,(9).
[31]董岩.美国碳交易价格规制的进展及其启示[J].价格月刊,2011,(7).
[32]唐永胜,徐弃郁.寻求复杂的平衡: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33]万钢.科学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J].中国科技投资,2008,(7).
[34]李静云,别涛.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保障[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35]Simon J.Bennett,Michael Kelleher,etc.The European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 Network-A forum for first movers.Energy Procedia 4,2011.
[36]彭峰.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利用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1,(11).
[37]Tim Dixona,Sean T.McCoyb,etc.Legal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on C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40,2015.
【责任编辑:宋 晴】
D922.683
A
1004-518X(2016)04-0146-12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研究”(15JZD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业贸易生态化转型的法律保障研究”(12BFX14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庆大学重大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贸易法律问题研究”(0226005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