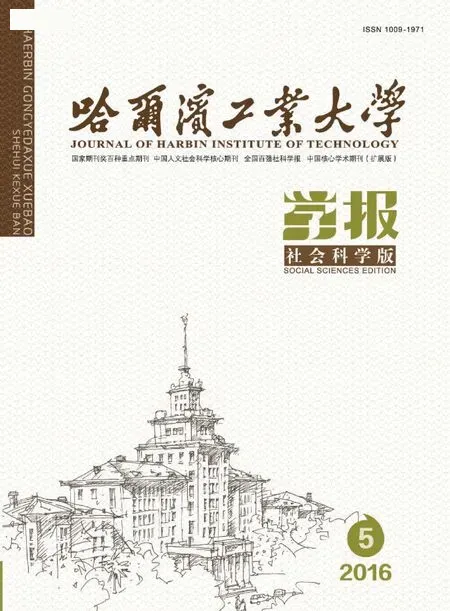八十年代想象“乡村”的方法及其文学史解释结构
——以“寻根文学”和对沈从文的文学评价为中心
练暑生
(闽江学院中文系,福州350108)
八十年代想象“乡村”的方法及其文学史解释结构
——以“寻根文学”和对沈从文的文学评价为中心
练暑生
(闽江学院中文系,福州350108)
乡村是“传统的”、“落后的”,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学形象相互对照。这种观念预设构成了20世纪八十年代想象“乡村”的基本方法和文学史解释的基本结构。在如何评价“寻根文学”和沈从文等“乡村”题材的小说问题上,这种想象“乡村”的方法遭遇了解释学困难。新启蒙政治性解释惯例无法接受“乡村”的“世界性”、“现代性”。革命文学的政治与审美的二分模式,弥合了作为“落后传统”主要载体的“乡村”与启蒙政治解释惯例之间的观念裂缝,“乡村”在审美层面获得了属于“现代的”、“世界的”文学史形象。因此,当年真正属于“审美”的文学史主要存在于对“寻根文学”和沈从文小说的“乡村”形象的文学史评述上面。
农村想象;审美化;文学史解释;寻根文学;沈从文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在中国“追求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文学形态,无论是在启蒙还是在革命视野下,“乡村”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被人们反复演绎和表述,并因此形成了种种具有强大延续性的想象和解释“乡村”的惯例。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惯例逐渐出现了解释学的困难。这个困难的出现与“寻根文学”的出场有直接的关系。除了《棋王》等少数作品外,当年“寻根文学”普遍取材于广袤的乡村生活。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了与“现代”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简单质朴、崇尚野性和情义,充满着原始野性的力量。从中呈现的“乡村”并不是启蒙视角下落后国民性的主要聚集地,也不是革命视角下充满着革命原动力的区域。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同时也就关系到如何用启蒙与革命视野之外的另一种眼光叙述“农村”。立足于今天全球化和现代化相互交织的历史语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农村”想象的当代意义——人们从中挖掘出了“抵抗现代性压抑的丰富矿藏”[1]。而在20世纪八十年代“走向世界”——追求现代的文学史愿景中,“寻根文学”寻求“民族之根”的想象“乡村”的方法,无疑触动了当年新启蒙文化汇聚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种种文学惯例,并因此制造了诸多文学史解释学困惑。考察八十年代的人们如何评价“寻根文学”和沈从文“湘西世界”问题,可以让我们很具体地观察当年体现在“走向世界”视野中的新启蒙文学史观念结构如何动摇、民族性与地方性、政治与审美如何又冲突又相互调谐。而其中各类文学史观念要素的分分合合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八十年代关于“乡村”的种种文学史论述如何“逃逸”出新启蒙追求现代的政治性要求,最终走向审美化的观念学原因。
一、“中国”与“世界”:想象乡村的两种视阈
“寻根文学”与新启蒙的差异是很鲜明的,其提倡者是在重申“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部分作家还因此公开批评了“五四”割断了传统文化的“根”。当然,这不是表明“寻根”的主旨明确是回到“古老的过去”或反对启蒙,多数“寻根文学”的提倡者和辩护者都不忘提到“寻根”的“更新民族文化”的意义。作家郑万隆指出:“寻根”是“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2]。李杭育则通过区分“传统的、规范之内的中原文化”和“非传统的、规范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维系“寻根文学”与新启蒙的联系,“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国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3]。一些当代文学史家,也是力图在“重铸民族灵魂”的意义上给“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做出定位,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在“审视”、“重铸”“民族灵魂”的意义上评述了“文化寻根”的意义,认为“‘文化寻根’派的作品主要是重新审视联络过去的道路;‘反传统’派作品则是以借鉴和引进为特色,焦灼地寻觅未来的路;传统写实主义的作品则是牢牢把握现实的路,他们殊途而同归于对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其精神是可以打通的”[4]15-27。
虽然强调“民族”、“民族特色”,但我们从“寻根文学”的创作及其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民族”与启蒙视角所讨论的“民族”的内涵有着很大的不同。韩少功《文学的“根”》开头首先提到的是“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5],而李陀所怀恋的是少数民族“达斡尔文化”[6]。“寻根”文学作品中那些广袤无垠的草原、偏远的山村、奇异的原始风光、少数民族风情,所呈现的“民族”形貌更多是多样化的地方特色,而不是启蒙视角下具有着某种统一属性的“民族传统”或“民族文化”。如果使用汪晖的概念,人们这里经常提到的“民族”无疑应属于是与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叙事相对立的广大“地方性”[7]。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说呈现的“乡村”既是新启蒙意义上的“世界”之外的区域,也是近代以来启蒙和革命过程所构建出来的“民族国家”叙事之外的边缘领域。因此,李杭育区分所谓“规范传统”和“非规范传统”不只是体现为如何沟通“寻根”与文化启蒙关系,事实上,这里面隐含着“民族”内涵的重大置换,新启蒙视角下的“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相对立中的“民族文化”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文化”与不具有“民族国家”属性的广大“地方性”之间的对立。
“寻根文学”出现后,曾经受到不少批评,这些批评有来自新启蒙主义者,也有来自代表着国家意志的声音。因为促进“中国”现代包括构造“新中国”是现代以来中国各种文化启蒙运动的基本目标所在,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最大的“现实”性,因此两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虽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批评“寻根文学”脱离了“当代现实”是他们的共同关切点。李泽厚明确指出:一些作家“逃避现实”“去寻求那似乎是超时代、超现实的永恒的人生之谜……就我个人来说,却总感到不满足”,“希望能多看到时代主流或关系到亿万普通人(中国有十亿人,不是小国)的生活、命运的东西”[8]。同年发表张炯在《文学自由谈》上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固然不应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但如果在社会主义时代,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却要到民族的原始神话、古代的老庄哲学、神道佛教、以至陋风呱俗中去寻‘根’,这种背向现实而面向古代的做法,能说是正确的吗?”[9]针对这些批评,有不少论者从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意义上,论证“寻根”的当代意义。正如有论者所言,“我在其中看到了作家们对于现代化的热切关切和对于后现代化的严肃思虑——这是注意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精神困扰的结果。”[10]无疑,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位论者所指出的“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所着重体现的并不是“中国”当代意义,而是“世界性”的当代意义。其中隐含的差别,事实上是立足于“中国”还是立足于“世界”思考问题。两种不同的思考立足点有着不尽相同的问题性,因而对“寻根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乡村”表现出不同的兴趣面。
二、乡村:徘徊在民族性与地方性之间
两种问题性和兴趣面相互交叉落实在八十年代文学知识分子身上的时候,通常被表述为“双重文明的压力”,“一方面,传统意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封建性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民族生命力的病弱;另一方面,正在膨胀的工业文明也带来了它的痼疾和局限,并形成对人性全面发展的新的压抑。于是,寻根者产生了反压抑的冲动,企图超越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的冲突和缺陷,去寻找第三种更为完善的文明”[11]。在启蒙语境下,无论“现代文明”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这种“第三种文明”如何具有“世界性”意义,面对新启蒙视角的鲜明的“中国”性质以及从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现代化冲动,两种问题性和兴趣面所构成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如何应对其中的矛盾,作家李杭育也只能寄希望于,“希望将来我能获得一个更开放的民族意识,好让我心安理得地加以捍卫”[12]。
相比之下,另一些“寻根文学”的辩护声音则更多地包含着“中国”立场。陈骏涛认为“寻根”不是“猎奇”,而意在改造民族精神,寻找“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的“同构关系”,“以便扬弃其非人性的部分,放大其合乎人性的部分,最终达到彻底改造民族精神,建立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的目的”[13]。从广大“地方性”因素中寻找“民族精神”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无疑是当年具有新启蒙意识的文学知识分子接受“寻根文学”的一个主要立足点。但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性”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陈述,包含着对“中国”的一种整体性的思考。因此,从广大乡村“地方性”因素中寻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的思路,和李欧梵等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力图从自发的城市经验中考察“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一样,无疑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中国“民族性”叙事普遍性和城市与乡村广大“地方性”因素独特性的关系。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农村”包括中国的“民族性”作为追求现代化的结果,它们的落后与先进,反动与进步,需要一种关于“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叙述的支持。因此,无论“寻根文学”在广大乡村地方性因素中发现了多少具有“生命力”的资源,“地方性”并不能离开“民族国家”范畴,独立呈现出自身的意义,其结果都还必须接受启蒙视角下关于“中国民族”整体性评判的检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达在认可“寻根文学”具有“改造民族灵魂”的意义的同时,在结尾明确指出,“文化寻根派”作品“侧重超稳定性而缺乏应有的运动感,这就使得大量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无法为其容纳,远不及‘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提法有更宏大的宽容度”[4]15-28。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诞生于中国追求现代性过程的文学,其主流形态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后来的革命文学,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主要体现在如何再造“中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方面。由于承担着构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职责,启蒙和革命意识形态对乡村的兴趣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陈述,而不是对个别“地方性”因素的关切。和现代主流文学一样,“寻根文学”也对存在于广大乡村因素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是,由于“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二元关系被隐性地置换为“世界性”与广大非现代的“地方性”之间的二元关系,“寻根文学”所呈现的“乡村”事实上是未经普遍性的“民族国家”叙事征用或者说中介的“乡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年围绕“寻根文学”的“当代意识”的论争,所谓“思古幽情”和“直面现实”的关系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隐含了如何处理“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的关系问题。对此,唐弢表达的相当明确,“‘根’是民族、国土的本身,而不是降低为仅仅是依附于民族、国土上面的一些派生出来的东西”[14]。
由于是在构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大叙事中想象“乡村”,因此,无论是作为落后传统主要载体的“农村”还是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农村”,事实上都是表现为政治化的“乡村”。而“寻根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乡村”——作为未经“民族国家”叙事普遍性征用或中介的广大“地方性”因素,其现实性或者说政治性无疑被大打折扣。对此,当年的不少辩护者也有着充分的意识。有研究者曾经明确认为,“寻根文学”只具有“审美意义”,“如果当今的‘文化寻根’,不把它局限在文学艺术的范畴中,那么,它将失去其积极意义,而与整个时代的开放潮流相左[15]。这个看法在当年也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事实上,在新启蒙视角下,包括雷达在内的当代文学史家,在评述“寻根文学”的当代文学史意义的时候,更多地表现出对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美学特征”的兴趣。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样评述了“寻根文学”,“他们在敏感地注意到向传统本位文化进行纵向寻求的思路。这种在新的审美方向的执意追求,是文学创作生机勃勃的表现。而且他们在实际也写出一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但由于‘寻根’只是回视、寻找我国本位文化的形象表述,而不是改造历史心理结构的自觉理论观念,因此,他们直接表述的文化见解常常不够正确”[16]。这一段评述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寻根文学”的政治价值和审美价值进行分别评价的文学史立场。
因为启蒙和革命视野下的“农村”是包含着丰富政治性的普遍性表述,因此,走出国家意志“一体化”的文学语境中,政治与审美的二分结构事实上使“乡村”的广大“地方性”在文学领域获得了浮现机会。在这种浮现背后,隐含了审美与政治,世界、民族与地方等文学史观念要素之间的复杂的结构互动。也正是在这种文学史观念的结构性互动中,现代文学史中那些非启蒙或非革命视野下的“乡村”逐渐找到了自我定位的空间。沈从文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可以这么说,在“重写文学史”过程中,人们对沈从文解释与评价的变迁过程几乎可以看作人们如何理解和阐述“寻根文学”过程在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领域的投射。沈从文最令人称道的地方是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这个“世界”被认为表现了一个人性的美好“殿堂”。在左翼阶级论视野下,必然带来阶级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八十年代的种种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建立在“新民主主义”论述基础上的文学史著着重在非阶级化的层面上批判了沈从文。与此相应的是,那些力图摆脱国家意志的政治化束缚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了重新评述沈从文的文学史价值。从1980年《丛刊》发表《答凌宇问——沈从文先生谈自己的创作》开始,人们都普遍突出了沈从文如何表达了“人性美”的一面,“湘西牧歌”是“希望之歌”[17]。
三、审美化的“乡村”及其不可能性
普遍人性、“人性美”是当年新启蒙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沈从文由此能够获得人们的重视,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在于沈从文所构筑的“人性的美好殿堂”被建筑在“乡村”,无疑,如何解释同属于“乡村”的“湘西世界”和作为落后传统载体的“农村”的关系,是当年的研究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的解决思路与对“寻根文学”的思考几乎如出一辙。或者是在“世界”视角下,强调沈从文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力中寻求医治现代“文明病”的途径[18]。或者是在类似区分“规范传统”与“非规范传统”的思路中,区分沈从文的“乡村”与落后传统中的“农村”的不同,并且进一步论证沈从文的创作如何探索“改造民族性”的新途径[19]。不过,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由于“新启蒙”无法免除的“中国”性质,因此,在以重归“五四”为自我期许的八十年代文学史语境中,沈从文的“乡村”最终还是要接受启蒙视角下的“农村”的检验和评判。赵园的长篇论文《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涉及了前述的种种有关思考,文章对沈从文创作的“世界”意义、审美意义包括“改造民族性”意义进行长篇论证之后,没有忘记提及沈从文“哲学的贫困、文化的贫困”,以此说明沈从文对城市、现代与乡村世界之间的“片面化了的比较”[20]。
或许是出于对沈从文的艺术才能的爱护,或许是突出非政治化的审美追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将近两页的篇幅中,突出强调的是沈从文的“抒情笔调”、“文体能力”和所描写的美好人性。至于“湘西世界”与作为落后国民性主要载体的“农村”之间的冲突,《三十年》只是在文章中间,用一句话一笔带过,“那种正义的、人道的爱国思想,使得沈从文面对旧社会的污浊,一相情愿地设想用农村原始的人情美来改造社会,来恢复民族性格,所谓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个“一相情愿”是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意义上提出的,而且在这一段话的最后面,还特别指出:“返归过去,肤浅,脱离现实,但又多么真诚,正是京派与左翼作家思想分野的所在。”[21]可以看出,写作者在努力抹平“改造民族灵魂”的政治化的“农村”与“湘西世界”审美化的“乡村”之间的差异,但闪烁其辞的落笔过程,充分体现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政治性与追求独立的审美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与“寻根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广大“乡村”“地方性”一样,在启蒙视角下,“湘西世界”也只能在审美层面上获得自我证明的可能,如果说它有什么文化政治意义,这种文化政治意义也只是体现在非政治化的独立的审美追求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指出沈从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作家,这个“世界”和“寻根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中的“世界”一样,或者只能是属于文学想象领域的“世界”,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种种弊端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而不是在新启蒙视角下,与落后“民族”或者说落后“中国”相对照的“世界”[22]。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和沈从文在八十年代的出现不只是让人们重新发现了“民族传统”的现代价值,它更是暴露出“新启蒙”和“走向世界”文学史解释框架的内在困难,从而让八十年代的“民族”和“世界”想象均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文学史形态,动摇了把“乡村”等于“落后传统”的意识形态想象。此外,八十年代开启了追求“纯文学”或独立地属于“文学”的文学史写作活动,而在新启蒙政治化“农村”和“湘西世界”等审美化的“乡村”之间的对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真正属于“审美”的文学史解释形态不存在于依据“个人写作”或“纯文学”概念展开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当中,而主要存在于对这些“乡村”想象的文学史评述上面。
[1]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4.
[2]郑万隆.不断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J].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85,(9):191-192.
[3]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J].作家,1985,(9):75.
[4]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J].文学评论,1987,(1):15-27.
[5]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2-5.
[6]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J].人民文学,1984,(3):121-127.
[7]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30.
[8]李泽厚.两点祝愿[N].文艺报,1985-07-27.
[9]张炯.文学寻“根”之我见[J].文学自由谈,1986,(1):65-70.
[10]韩抗.文学寻“根”之我见[J].芙蓉,1986,(1):134-136.
[11]方克强.寻根者:原始倾向与半原始主义[J].上海文学,1989,(3):66-71.
[12]李杭育.“文化”的尴尬[J].文学评论,1986,(2):50-54.
[13]陈骏涛.寻“根”,一股新的文学潮头[J].青春,1985,(11):56-58.
[14]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J].新华文摘,1986,(7):139.
[15]宋耀良.文学、文化、心态——文学中文化寻根问题探讨[J].福建文学,1986,(3):64.
[16]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J].新华文摘,1986,(11):141-148.
[17]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J].读书,1984,(8):60-70.
[18]凌宇.沈从文:探索“生命”的底蕴[G]//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9]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J].文艺研究,1986,(2):64-73.
[20]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50-67.
[2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21—322.
[22]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J].湘江文学,1983,(1):70-72.
The Rural Imagination in 1980s and Its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Focus o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Interpretation of“Root-seeking Literature”and SHEN Cong-wen's Novels
LIAN Shu-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closely the value and place of“Root-seeking Literature”and SHEN Cong-wen's novels in literature history,in order to examine what is the source ideology leading to be aesthetic countryside.This paper stated that the binary structure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provided possibility for“countryside”to escape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nlightenment.
rural imagination;aestheticization;literary history interpretation;root-seeking literature;Shen cong-wen's novels
I206
A
1009-1971(2016)05-0097-05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6-06-20
练暑生(1972—),男,福建武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