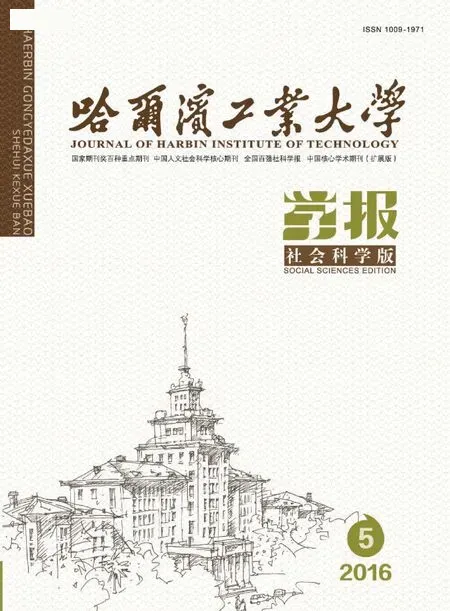胡适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本土文化情结
刘辉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88)
胡适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本土文化情结
刘辉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88)
胡适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之功引人瞩目、备受赞誉,同时也因为其在研究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西学化学术风格引起世人的争议和质疑。深入考察胡适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文化情结,其西学化的表达形式无非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和权变的学术研究方法而已,这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他为了展示中国哲学核心内涵和发扬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真实意图。造成胡适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本土文化情结的根源在于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而且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甚至影响其一生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胡适;中国哲学;本土文化情结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普遍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造成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呈现出西学化倾向,其中,胡适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和重新构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西学化特征,故有人称胡适为“西方文化派”。然而,这种称呼或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时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冲击,在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时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就胡适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来看,更多地呈现出语言、思维层面上的极端“西化派”和本质上的中国本土文化情结的双重特征。
一、西学化的形式表达
胡适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是在吸收中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整体框架,并且以著作、论文、日记等不同书写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由于胡适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他在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西方哲学、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一定说胡适完全认同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用西方的哲学与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哲学与文化。
胡适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时,习惯用西方文化中流行的观念和术语来表达中国哲学思想,例如在他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常常会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用主义”等等术语,通过使用西学术语将中国传统哲学以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导致胡适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形式上呈现出“西化派”的特征。
“进化论”一词本是英国科学家、进化论思想家达尔文提出的解释社会问题的科学术语,但是,胡适将这一科学术语运用于分析和阐述中国哲学。他在《先秦诸子进化论》中,用“进化论”一词来表达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他说:“一部《易经》便是孔子的进化论。”[1]12他把《易经》视为孔子的进化论,进而他还认为,“孔子既知进化之迹由简易变为繁赜,所以他把全部历史当作一条古今不断的进化,由草昧野时代进而成高等繁赜的文化。”[1]14胡适从社会进化论的视角来解释孔子的思想,使孔子思想具有明显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特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西方科学家赫胥黎使用的科学术语,胡适同样将其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例如,他评价《列子》中“齐田氏祖于庭”一段小故事时说:“今《列子》这一段话,方可算是真正物竞天择的学说呢!”[1]18他用“物竞天择”一词来概括《列子》中这一故事的内容,具有明显向西方文化靠近的倾向。他在评价《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时说:“庄子的进化论有时很像近人的‘适者生存’之说。”[1]21他不仅指出庄子具有进化论思想,而且还具有“适者生存”的基本理念,这完全是用西方文化的术语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诸如此类运用西方社会、文化术语来解释中国哲学的现象比比皆是,反映出胡适非常熟悉西方文化、推崇西方文化,也希望利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在西方文化中,胡适最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并在许多研究领域中用它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现象。在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中,胡适会自觉地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来使用。他说:“‘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2]278实验主义亦即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仅强调它的实用性,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2]283。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培养人们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在学术研究中,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能够以一种客观的、中立的价值观去研究被严重扭曲的学术价值判断,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和“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中,非常重视实用主义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使用。他说:“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3]673从科学研究求真、求信的角度来看,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传统训诂、考据的求真方法相契合,而这种方法具有新颖性和可行性,更容易让人们接受。
胡适运用西方文化的术语和思维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不免在形式上会造成“西化”的印象,例如,他在评价北宋思想家李觏时说:“李觏是一个实用主义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乐利主义。”[4]直接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用西方的学说流派来作界定,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说法,姑且不论其结论是否准确,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当时的金岳霖对胡适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看法即是如此。金岳霖曾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5]1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该书的写作中,他是依据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写作范式完成,以致于使中国读者感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而且,会造成其西方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直观印象,未免有些“奇怪”。因此,我们再对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来看,金岳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持一种批评意见也就不难理解,他说:“哲学既离不开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5]18“实用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种“成见”,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判断,用西方的价值判断来解释中国哲学与文化,就不免给人以“西方化”的印象,就连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大家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成见”来看,那么,一般人就更容易将“实用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看待,自然会给胡适的学术研究贴上西方文化的标签。如果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无疑是一种“以西解中”的学术研究路径,会淡化中国本土哲学和文化的特质。但从事实上来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胡适中国哲学文化研究的本质。
二、中国文化情结的深层展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发表了激烈的“反传统”言论,因而被称为“反传统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从中西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上来看,胡适并非完全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并非以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为目的,而是从根本上具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高度的认同感,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是为复活、复建和复兴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而作的努力,只不过他在方法上不同于传统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胡适结合时代使用了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更加普及化、大众化的方法,这是他在特定时期、特殊条件下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本位情结的一种深层次展示。
与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钟情于儒家思想不同,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儒家独尊的地位,“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6]。他全面观照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家各派,而且,他还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放在了与其他子学代表人同等的地位,不仅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全面关注的学术视野。这一点,胡适很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7]胡适对自己中国哲学史研究意义的说法看似有些狂狷,但是,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胡适的这一部并不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有它的独特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胡适秉承“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注重使用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等方法来重新检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各种经典。他对儒学的异端《荀子》、《老子》、《墨子》、《管子》等子学典籍进行考证,其目的是用西方科学的精神结合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来发现诸子学的思想和价值。如同余英时所言:“这样对一部一部的子书深入地整理下去,最后必然导向诸子思想的再发现。这是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引申到子学研究上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发展,但却绝不是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回向原典’时所能预见的。”[8]由于时代变化,尽管胡适也使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目的不是要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发掘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新内容。更重要的是,胡适在“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指导下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势必导致他的研究结论会对前人有所突破,把墨子和孔子一视同仁,而不是独尊孔子、儒家,从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去展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丰富内容,这样一种研究成果的确引起当时学术界的“一项小小的革命”[9]378。因此,也开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在西方“实用主义”科学精神的指导下,胡适特别详细地检讨了被人们忽略的先秦名学,并将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深入挖掘。除了研究人们熟知的儒释道思想与文化之外,胡适也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其他内容,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普遍重视以及具有全面考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学术视野,这是他所具有的中国哲学与文化本位情结的具体表现,他希望通过全面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使中国哲学与文化能够重新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他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学派同时盛行。”[10]12在胡适看来,研究儒家之外其他各派的思想具有与研究儒家思想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些“伟大的哲学学派”在历史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而实际上他们与儒学同样有价值,尤其是涉及中国哲学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时,他“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0]12。注重挖掘像名家等非主流思想中与西方文化相契合的地方,以此赋予中国哲学与文化活力,从而可以全面提高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除了对先秦名学给予足够的关注外,胡适对“中绝”千年之久的墨学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强调墨学中逻辑理论的重要意义。针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的衰落,胡适指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10]10在胡适看来,方法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正是因为没有找出合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梳理和发展中国哲学和科学,造成近代中国哲学文化、科学的普遍衰落。落后的根源既然是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方法上存在问题,所以,胡适积极提出西方的实用主义方法来弥补我国研究方法的不足,并希望通过实用主义方法在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具体应用,提高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水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这就有可能将西方文化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运用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学术研究中。他说:“现在,中国已与世界的其他思想体系有了接触,那么,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乎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10]10
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固然对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全盘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会导致中国哲学与文化失去自主性,从而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属品,对于这种现象胡适表现出了忧虑。从借鉴西方文化和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担忧上,也能看出胡适并非完全赞同西方化,更不是要变中国哲学与文化为西方文化,而是希望在保持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其中充满了胡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浓郁情感。因此,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重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挖掘自身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比附。
三、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
胡适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源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及少年时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青年时期赴美留学的经历又使胡适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熟悉,他能够熟练使用中英文语言表达中西方哲学与文化,这就使他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西哲学与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加深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交流。
胡适自启蒙开始,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他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情结的根基所在。胡适三岁时进入私塾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学习和诵读《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等等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重要典籍,深受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影响。除了读经典之外,还有专门的教师给他讲解“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从义理方面系统掌握中国经典,这就更加深了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内涵的理解,而且通过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知识、文化理解一直影响他以后的治学态度和走向。他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11]30讲字即从文字入手,讲解字词、句读等基本文字学方面的内容;讲书即是对书本的思想、义理等内容进行阐发。二者包含了对文本资料从文字训诂到思想义理的全面讲解,是中国最传统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成为影响胡适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启蒙教育阶段,对胡适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父亲的教育。胡适的父亲自编教材对胡适进行知识传递、人格培养方面的教育。少年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胡适学术兴趣的培养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深厚感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5年,胡适阅读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后,他认为,梁启超的文章阐述中国学术思想的脉络清晰,内容丰富,不失为研究中国哲学文化的经典之作,但是,他也发现,梁启超的文章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11]62。缺失了的三个紧要部分就引起了胡适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兴趣,因此,他也希望能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具体内容做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索。“替梁任公先生补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11]62就成为胡适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直接动因。正是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启发,他才真正投身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才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11]62
正是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确立了胡适以后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治学路径。因此,在胡适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方法中,除了使用他所推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外,他更加注重使用中国传统“汉学”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而这两个方法是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方法,亦即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所以,从方法上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依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他以后的学术研究能够体现中国本土文化情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已经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内涵和研究方法有了非常纯熟的了解,因此,他赴美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在康奈尔大学从农学改为其他学科专业,尽管期间也使用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胡适认为,“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9]274在一定程度上说,早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胡适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厚情感也蕴含其中。
四、简短的结语
虽然胡适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西学化倾向非常明显,他也曾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667这里的“不如人”的“人”是指西方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西方文化。从这些言论来看,胡适似乎在强调和认同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但事实上,他是希望通过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才能够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不断地进取、创新,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文化、思想。在哲学与文化方面,胡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希望能够发现和提升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价值,力图使中国哲学与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胡适运用了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通过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重新梳理和建构中国哲学与文化,使中国哲学与文化焕发新机,获得新的生命力,促进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推陈出新,进而在世界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胡适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和推崇,但是,他在潜意识中具有浓厚的“中国本土文化情结”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表现便是明证。
[1]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M]//胡适全集:第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胡适.实验主义[M]//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胡适.记李觏的学说[M]//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0
[5]金岳霖.金岳霖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M]//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4.
[7]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M]//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47.
[8]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2004:243.
[9]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胡适.先秦名学史[M]//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胡适.四十自述[M]//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Native Culture Complex of Hu Shi in Hi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LIU Hui-ping
(School of Ma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Hu Shi's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was impressive and award-winning.But because of his obvious western academic style in the course of research,Hu Shi aroused worldwide controversy and doubt.From in-depth review of Hu Shi'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we will find that hi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was rooted deepl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plex.The western expression forms of Hu Shi was no more than an external,representative and contingency methods for his academic research,which couldn't thoroughly deny his real intention on how to show the co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The root that caused Hu Shi's Chinese philosophy complex li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his childhood.The influence of the education was deeply ingrained and even effected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 lifetime academic research.
Hu Shi;Chinese philosophy;native culture complex
B12
A
1009-1971(2016)05-0074-05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6-03-23
刘辉萍(1974—),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研究。